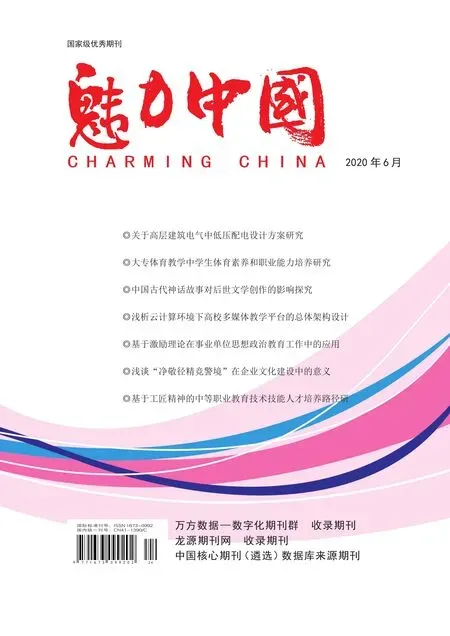從功能對等理論分析兒童小說《愿望》的漢譯
——以第十一章的漢譯為例
吳佳美 吳丹
(貴州大學外國語學院,貴州 貴陽 550025)
在兒童時期,如果孩子們能夠讀到一部好的作品,對他們的一生來說都將是寶貴的財富。在當今社會,由于社會觀念和生活方式的轉變,很多父母不會再因為孩子而繼續維持他們已經沒有感情的婚姻,這就導致單親家庭越來越多,而單親家庭孩子的身心健康應該引起社會的重視。而《愿望》(Wish)就是一本關于11 歲的單親家庭孩子查莉(Charlie)的成長故事,其語言動靜結合,意義深刻,是一本出色的兒童文學作品。但遺憾的是,目前國內還沒有這本英文作品的漢譯本,導致大部分國內兒童無法閱讀這一優秀作品。鑒于此,本文作者兼《愿望》一書的第十一章漢譯者,從功能對等理論出發,期望探討其漢譯策略與技巧,也想借此機會把這部作品介紹給國內兒童讀者。
一、《愿望》概述
《愿望》是一部由作家芭芭拉·奧康納(Barbara O'Connor)于2016 年完成的兒童文學作品,適合9 到12 歲的孩子閱讀。該作品主要講述了11 歲的查莉在父母離婚后,被送到鄉下姨媽家生活的故事。查莉從四年級開始,每天都會許同一個秘密愿望。她甚至列出了所有可以許愿的時刻,例如在吃下一片餡餅的最后一口時許愿。但是,當她被送到鄉下與姨媽一家人一起生活時,她的愿望似乎就不太可能實現了。直到她遇到了一只瘦小的流浪狗許愿骨(Wishbone)并深深喜歡上許愿骨,并和一個住在附近并在很多方面都令人驚訝的男孩霍華德(Howard)成為好朋友,同時在寬容慈愛的姨媽姨父的影響下,查莉才逐漸認識了家庭的真正意義。
二、功能對等理論概述
翻譯理論家尤金·奈達(Eugene A.Nida)的功能對等理論是翻譯史上等效效應理論的變體。在歷史上,英國翻譯家泰勒是第一個提出“同等效果”的人(楊司桂,2007 年)。泰勒在1790 年出版的《翻譯原則》一書中提出了著名的三個翻譯原則,即翻譯應完全反映原作的思想;翻譯的風格和方式應與原文在本質上相同;翻譯應與原文一樣流暢。1896 年,德國翻譯理論家考爾在《翻譯藝術》一書中將泰勒的翻譯原則命名為“相似效果”。1953 年,里德正式提出了基于等效效應理論的概念(楊錫貴,2007)。1960 年初,奈達提出了“形式對等”理論。1964 年,奈達在《翻譯的科學探索》一書中首次提出了“動態對等”的概念(韓麗,2015)。在“動態對等”概念中,奈達認為,所謂的翻譯活動,從本質上來說,就是在譯本中用最貼切又最自然的對等語再現原語的信息,首先是再現意義,其次才是再現文體。1965 年,著名英國翻譯家和語言學家卡特福德發表了《翻譯的語言學理論》一書。在該書中,他提出翻譯對等的條件是原文本和目標文本同時具有有形特征(至少在部分上具有),即至少有些指稱實體的特征是一致的(黃遠鵬,2010)。1982 年,為了防止公眾對“動態對等”產生誤解,奈達在其著作《從一種語言到另一種語言:圣經翻譯中的功能對等》中將“動態對等”改為“功能對等”(盧揚,2015)。在對“功能對等”的闡述中,奈達對“文本信息”做了進一步闡釋。奈達認為,因為文本形式也有意義,所以文本信息不僅包括思想,還包括語言形式,所以“功能對等”不但要求內容對等,還應該盡可能地做到形式對等。隨著奈達的理論進一步發展成熟,功能對等理論至少包括四個方面的對等,分別是:詞匯對等、句法對等、篇章對等和文體對等。
三、翻譯難點及解決辦法
(一)詞匯對等
英漢兩種語言的差異在詞匯上體現得相當明顯。例如,英文喜歡用名詞,而中文喜歡用動詞;英文喜歡用代詞,而中文喜歡重復同一名詞;英文無量詞,而中文有量詞;英文有冠詞,而中文無冠詞等。中英文詞匯的差異,導致有些時候無法直譯原文詞匯。此外,由于中英文化的差異,有些原文詞匯代表的意義和意象,在目的語環境中卻很少用甚至沒有,這時候如果譯者僅從字面意思理解奈達的詞匯對等原則,則很可能造成目的語讀者對原文信息的缺失。事實上,譯者對奈達的功能對等的正確理解,應該是在進行翻譯活動時,不追求文字表面的死板對應,而是要在兩種語言間達成功能上的對等。
例1.原文:By the time Howard finally got there,my temper had settled down from a boil to a simmer.
譯文:等到霍華德終于上車的時候,我的憤怒程度已經由極為憤怒轉為微微憤怒了。
分析:原文的“boil”和“simmer”用得十分形象傳神。其運用了比喻的修辭手法,使得查莉的情緒變化生動地呈現在讀者面前。但是,由于目的語無這類比喻和說法,如果直譯,會引起目的語讀者的疑惑。基于此,譯者在詞匯對等原則下,采用意譯方法處理,譯為“我的憤怒程度已經由極為憤怒轉為微微憤怒了”,這樣的處理,雖然沒有譯出原文的比喻辭格,卻最大化地呈現了原文的意義,而這一點在此處顯得更加重要。
(二)句式對等
英漢兩種語言分屬不同語系,因而存在諸多差異。例如,英文喜歡用長句,而中文喜歡用短句;英文句子之間的邏輯關系用各種顯性的詞匯表達出來,而中文的則暗含在句子之間;英文句子比較聚集,而中文句子比較流散等。(連淑能,2010)因此,在英漢差異比較大時,一方面,譯者應該仔細理解英文句子含義,用漢語的思維習慣來重現原文信息。另一方面,要注意句子的修辭運用,盡可能保留原文的藝術特色。
例2.原文:The next day at school,it seemed like the clock had stopped and the day was stuck in a never-ending torture of math and social studies and gym.
譯文:第二天我坐在教室里,時間仿佛停住了腳步,只剩數學、社會研究、體育三門課程輪番上陣折磨人。
分析:原文描寫的是查莉剛到鄉下學校上課時,由于不喜歡鄉下的環境而覺得時間過得異常慢的心理描寫。在句法對等原則下,原文是陳述句,且兩次運用比喻的修辭手法,因此,在譯文中,譯者同樣采用陳述句,將“it seemed like the clock had stopped”譯為“時間仿佛停住了腳步”,將“the day was stuck in a neverending torture of math and social studies and gym”譯為“只剩數學、社會研究、體育三門課程輪番上陣折磨人”。在譯文中運用同樣的修辭格,再現了原文的句式特點,做到了句式對等。
例3.原文:“You can’t sit here,” I said.She made an ugly face at me and said,“Yes,I can.”“No,you can’t!” I sort of hollered.
She flinched a little and gaped at me.“You can’t save seats,”she said.“That’s the rule.”
譯文:“你不能坐在這里,”我說。奧黛麗·米歇爾朝我做了一個難看的鬼臉說,“我可以。”“你不能坐在這里!”我大喊道。我的聲音把她嚇住了,她呆呆地望著我說,“你不能占座位,這是學校校規。”
分析:原文是小說作品中不可缺少的人物對話描寫。人物對話描寫能更直接的刻畫人物形象和性格特點。根據原文信息,譯者可以知道查莉由于對新環境的防備和新同學的不友好,在處理事情的過程中會有點急躁。此外,這里的對話描寫還為后文講述查莉由于父親因打架入獄而非常自卑,但卻不知如何變大自己的情緒埋下伏筆。這樣精彩的人物對話,譯者應該盡最大可能再現給目的語讀者。在句式對等原則下,譯者采取直譯策略,將原文的意義和形式再現給目的語讀者。
(三)篇章對等
中英文在篇章的布局方面也存在很大差異,例如,英文之間的段落銜接很多時候依靠故事情節推進,而中文喜歡用復現部分詞語的方式推進;英文喜歡用演繹式結構,而中文喜歡用歸納式結構等。在翻譯時,譯者應考慮其差異,選擇合適的翻譯策略與技巧。
例4.原文:Then Howard whipped some papers out of his backpack and thrust them at her,grinning.“Ta-da!” he said.
譯文:奧多姆夫人問完問題之后,霍華德從背包里抽出幾張試卷給奧多姆夫人,笑著說,“當當當”。
分析:原文是獨立的一個段落,其前一段落講述的是奧多姆在問霍華德和查莉一些問題。所以在翻譯這一段落時,在篇章對等原則下,譯者把原文的“Then”做了增譯處理,譯為“奧多姆夫人問完問題之后”,這樣的處理符合漢語篇章的布局方式,做到原文譯文的篇章對等。
(四)文體對等
原文《愿望》是一部適合9 到12 歲的兒童閱讀的小說。這一年齡階段的兒童,首先是心智開始慢慢成熟,但也還不能較好地認識和處理一些負面情感。其次,他們有了一定的知識積累,有能力閱讀一些語言難度大一點的文學作品了。所以,一方面,《愿望》原文語言風格偏向平緩樸實,沒有出現表達強烈消極情感的詞匯。例如,查莉在父親因為打架進入監獄后,被母親送到鄉下姨媽家寄養,但是全文從開頭到結尾沒有出現過類似“abandon”這一類會極度傷害兒童心理健康的詞匯。另一方面,原文中有大量的心理描寫和對話描寫,語言不僅符合兒童話語特征,在有一點點難度的基礎上,語言精彩豐富。基于此,譯者翻譯《愿望》時,應充分考慮原文和譯文的文體特點,爭取獲得質量較好的譯文。
例5.原文:Finally the dismissal bell rang and I hightailed it to the bus.I plopped down in my usual spot and waited for Howard.He must’ve been taking his own sweet time because the seats were starting to fill up.
譯文:終于,下課鈴響了,我沖出學校,奔向校車,一屁股坐在我經常坐的座位上等霍華德。他一定走得慢悠悠的,因為車上座位已經快被坐滿了。
分析:原文共三個復合句,第一、二句是用“and” 連接的并列復合句,第三句是用“because”連接的因果復合句。但是,由于原文屬于小說的動作描寫,且描寫的是查莉放學后迫不及待奔向校車的場景。讀者可以想象得出,那時候查理的動作應該很急。在漢語中,短句更能傳達動作的急匆。所以,在文體對等原則下,譯者采用拆分的翻譯技巧,將原文的三個復合句譯為中文的7 個小短句。采用這樣的處理辦法,使得譯文更加符合漢語兒童小說的文體特點。
四、結語
在功能對等理論的指導下,譯者有根據地解決了翻譯《愿望》第十一章中遇見的部分翻譯難題,說明功能對等理論對兒童小說的翻譯具有較明顯的指導意義。因此,今后譯者在進行此類文本的翻譯時,可以考慮以功能對等理論為指導,綜合恰當運用翻譯策略與技巧,力爭得到更高質量的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