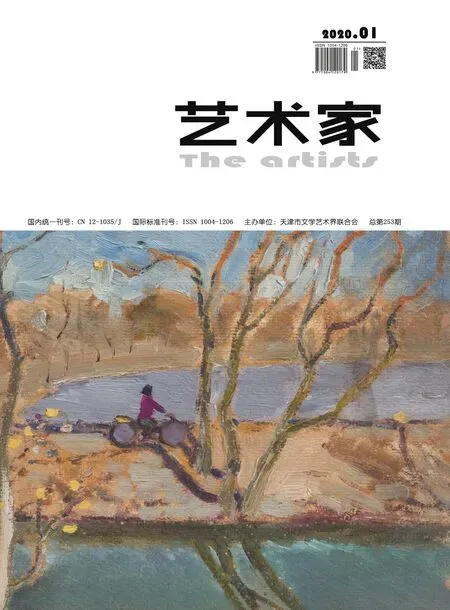日本“文化戀母原型”溯源
——論《古事記》中的女性崇拜
□吳佳偉 福建師范大學文學院
在比較文學的視野中,大多數國家“太陽崇拜”的對象都是男性,而日本的最高神“天照大神”卻是女性。日本文化的這一特異之處對民族的深層心理及其文學表現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借用精神分析學的術語,可以稱之為“文化戀母原型”。不過需要強調的是,這里的“母”是文化母親,內在含義是指母系文化所形成的女性崇拜。在受到父權文化壓制的情況下,文化戀母情結就轉化為民族無意識中的原型,暗中支配或制約著后人的思想行為,尤其是藝術創作[1]。
一、與肖書文教授商榷《古事記》中的女性地位
“女性崇拜”形成的前提是兩性關系的建立,而兩性關系始于男女的性欲,是一種延續種屬的本能。在《古事記》中,性欲最初是作為一種“生產國土”的本能將男女的肉體聯系在一起的。原始先民面對性欲沒有像現代人一樣刻意地隱晦,而是采取一種坦率的態度。從這里也可以看出,兩性關系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而逐漸被遮蔽的。所以要想更好地理解日本文學史中的“母親原型”,我們就有必要對文化戀母原型的源頭——神話中的女性崇拜進行進一步的探究。
華中師范大學教授肖書文在《從〈古事記〉看日本婦女性格的形成》一文中認為速須佐之男殺害大氣津比賣而沒有受到懲罰,“表明婦女的地位已開始下降,成為完全被動的、為男人服務和任男人宰割的一方。[2]”如果我們認同肖教授的觀點,那么神話作為“文化戀母原型”的源頭,其重要性將會大打折扣。肖教授理論的依據是“肇事”后速須佐之男并沒有受到任何處罰,那么確定《古事記》中是否存在審判者便至關重要。在基督教文化中,通常是以至高神的教訓為倫理核心的,上帝是最高的制裁、懲罰之神。然而,日本傳統的宗教信仰中并不存在制裁、懲罰之神[3]。況且,《古事記》中的謀殺行為也不止這一處,因此肖教授關于《古事記》中女性地位的論斷有待商榷。那么《古事記》中女性的地位究竟如何呢?下面我們將從從社會、婚姻和愛情三個方面對女性的地位進行論述。
二、社會生活中的女性地位
在神代,女性的社會地位普遍高于男性,這樣的思想觀念在《古事記·三貴子分治》中就有明確的體現。伊邪那岐在舉行完祓禊儀式之后,心情大好,于是令三貴子分治,而其中天照大御神統治高天原,具有最高的統治權威,作為男性的建速須佐之男則被“冷落”。另外天照大御神善良寬容,對弟弟的無理行為并沒有加以譴責,反而替他進行申辯。天照大御神作為高天原的最高統治者,并沒有威嚴而不可親近,反而具有女性善良、體貼的特點,這與母系氏族社會時期,“女性崇拜”有著莫大的關系。
二、婚姻中的女性地位
當然,在之后的故事中,男性最終戰勝女性,卻又說“因為我的心地潔白,所以我生的孩子是柔和的女子。”同時,在《古事記·黃泉國》中,伊邪那歧到黃泉國尋找自己的妻子,因沒有遵守妻子的囑托,看見女神猙獰的面目后害怕逃跑。遭受羞辱的妻子先后調動了黃泉丑女、八雷神和黃泉軍來進行追殺,女神伊邪那美在黃泉國權力可想而知。由此可見,男性在當時部落中的地位尚且不如女性。正因如此,婚姻關系并沒有對女性形成嚴重的束縛。
在《古事記·訪問根國》中,大穴牟遲神通過須勢理毗賣的暗中幫助解決了速須佐之男故意提出的幾道難題之后,速須佐之男作為父親最后也默許了他們的婚事,大穴牟遲神帶著須勢理毗賣從陰間回到陽世。遵照約定特意前來與大穴牟遲神完婚的八上姬因害怕正妻須勢理毗賣而返回家鄉。很顯然,她的這一決定并未與任何人商量,包括她的父親。正是這種“自作主張”體現出女性在婚姻關系中的自主權。
三、愛情中的女性地位
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結合造國土時,伊邪那岐雖然認為女人先說不吉利,但也沒有權力完全地拒絕,只能勉強完成交合,只是在生完孩子后才商議解決的辦法。二神商議后說:“我們這次生的孩子不好,應該察報天神。”于是便一同去向天神請教。結合上文第一次交合后伊邪那岐的評價,我們似乎可以看出伊邪那岐雖然沒有預料到結果,卻深諳解決的方式,二神商議請教天神更像是伊邪那岐通過天神的權威來確定自己的判斷。從這個角度來說,男性在當時的兩性關系中并沒有絕對的權威,甚至還要借助于天神的力量來確定自己的判斷。天神的指示在這里更像是一種宣判,代表著母系氏族社會時期“女性崇拜”已經開始衰落。但父權制的早期并沒有對女性造成嚴重的壓迫,而還是還保留了原始時代男女之間互相傾慕的愛情關系,雙方結合的主要原因還是情感的力量。
在《古事記·天照大御神與速須佐之男命》中,兩人為了證明誰更純潔而發誓要生孩子,速須佐之男命對天照大御神說:“因為我的心地潔白,所以我生的孩子是柔和的女子。”關于“柔和女子”的論述更像是原始母系氏族社會關于“女性崇拜”的遺留。我們還應該注意到繁殖方式是無性繁殖和有性繁殖并存。男神和女神除了可以通過男女結合進行有性繁殖外,還都保留了無性繁殖能力,能從自己的身體里產生下一代。因此,在遠古時期,女性并不是單純的生育工具,男女之間的結合也不單純是為了傳宗接代,可以說在兩性關系中相互欣賞的成分占據了很大一部分,與階級社會的觀點大相徑庭。
日本神話中描寫的男女關系非常豐富,不僅包括親情關系,還有婚姻關系、愛情關系等,都很好地保留了原始初民的思想觀念。當然也可以對這些神話做另外解讀,如原始初民的信仰、生活方式等,但其隱含的大背景都是以女性為中心的母系氏族社會。總體而言,在社會中“女性崇拜”普遍存在,如伊邪那美、天照大御神都是各自屬國的統治者。另外,兩性之間的關系也比較單純,婚姻和愛情都建立在相互欣賞的基礎上,女性尚未淪為單純的生育工具,且具有獨立的人格,如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大穴牟遲和須勢理毗賣之間的兩性關系。正因如此,女性在社會生活中隱私也具有不可侵犯的特點,即便是自己的丈夫也要遵守,否則就會遭到懲罰。當然,神代也是“女性崇拜”表現最充分的時期,這是其他時代都無法比擬的。
結 語
這種以女性為中心的世界的遺存還延續著,但我們此時不得不正視父權的天皇制對母權制的強烈沖擊。尤其是天皇編年時代,男尊女卑的觀念進一步發展,女性地位下降,逐漸淪為男性的附庸,再也沒有了神代時的自由與單純,以女性為中心的世界也就此宣告結束。今天,透過神話,還原當時女性的中心地位,并以此為起點去審視日本文化中的“文化戀母原型”,為理解《竹取物語》《源氏物語》《棉被》等作品提供文化上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