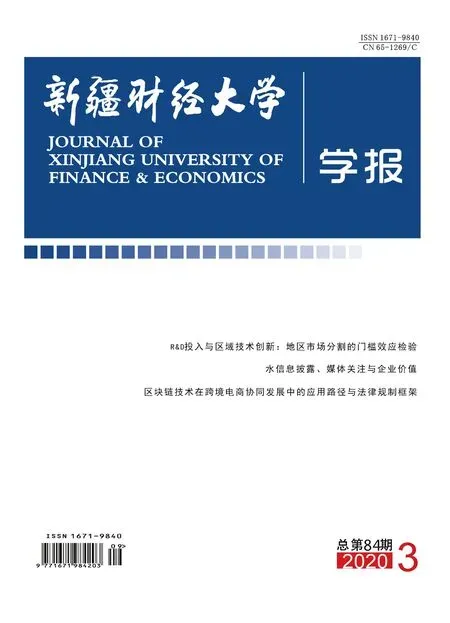論超比例違規增持行為人的民事責任承擔
胡 萍
(中央財經大學,北京 100089)
一、問題的提出
近年來,我國證券市場超比例違規增持現象頻繁出現,由此引發的股價波動、公司控制權爭奪以及訴訟對抗等情況時常出現①詳見姚蔚薇著《違反證券交易大額持股披露及慢走規則的民事責任探析》,原載于《證券法苑》2017年第2期,第61~77頁。。現實中,超比例違規增持主要表現為投資者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以下簡稱《證券法》)第八十六條②《證券法》(2014修正)第八十六條規定,“通過證券交易所的證券交易,投資者持有或者通過協議、其他安排與他人共同持有一個上市公司已發行的股份達到百分之五時,應當在該事實發生之日起三日內,向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證券交易所作出書面報告,通知該上市公司,并予公告;在上述期限內,不得再行買賣該上市公司的股票。投資者持有或者通過協議、其他安排與他人共同持有一個上市公司已發行的股份達到百分之五后,其所持該上市公司已發行的股份比例每增加或者減少百分之五,應當依照前款規定進行報告和公告。在報告期限內和作出報告、公告后二日內,不得再行買賣該上市公司的股票。”的規定增持上市公司股票,不履行大額持股信息披露義務,不遵循慢走規則③學界對違反《證券法》(2014修正)第八十六條的行為有“超比例違規增持”“違規增持”“大比例違規增持”等表述,本文借鑒張戈羲在《超比例增持股票行為的定性探析》一文中的觀點,采用“超比例違規增持”這一表述方式。。對于超比例違規增持,監管機關雖有權追究行為人的行政責任,但事實證明僅追究行政責任對市場主體的約束作用并不明顯,部分涉案股權變動股東在明知違反規定的情況下故意不披露增持股票的信息,趁目標公司毫無防備而獲得控制權,事后再依據證監會的行政處罰對此前未披露的信息予以披露并交納罰款,由此便能通過低成本的補充披露和交納罰款的方式獲得目標公司的控制權。因此,越來越多的糾紛逐漸傾向于通過訴訟途徑進行解決,但目前的理論探索仍集中于監管機關應對超比例違規增持行為人追究何種行政責任,而對其民事責任承擔問題的研究較少。
此外,通過比較有關超比例違規增持的典型司法案例如*ST新梅案④案號為(2015)滬一中民六(商)初字第66號。、成都路橋案⑤案號為(2017)川0107民初858號民事判決書、(2017)川01民終14529號。、康達爾公司案⑥案號為(2016)粵0304民初7145號、(2016)粵03民終13834號。、西藏旅游案⑦詳見《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關于訴訟結果的公告》(公告編號:2016-044號)。可以發現,實踐中關于超比例違規增持民事訴訟案件的審判存在一些爭議,如超比例違規增持交易行為是否有效,其行為是否侵犯了控制權和反收購權,目標公司股東大會或董事會是否能決議限制行為人的股東權利,以及如何認定證監會的行政處罰決定等。在成都路橋案和康達爾公司案中,雖然法院在調查詢問、走訪證券監管部門、參考類似案例及學者觀點后作出了具有一定示范意義的判決,但對超比例違規增持行為所侵犯的民事權利并未進行深入論證①詳見《2017年十大典型案例(七):李某訴某路橋公司確認公司股東大會決議無效案》,https://www.sohu.com/a/227713254_99998872。。在西藏旅游案和*ST新梅案中,案件最終以雙方當事人達成調解告終,法院并未作出宣示性的司法裁判,未能對今后此類案件的裁定提供更多的借鑒。
《證券法》(2019修訂)第一百九十六條新增了關于收購應負賠償責任的規定,即“收購人及其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利用上市公司收購,給被收購公司及其股東造成損失的,應當依法承擔賠償責任”。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將結合《證券法》重新認識超比例違規增持行為人民事責任的承擔問題,以期對司法實踐提供參考。
二、對超比例違規增持行為人民事責任承擔的再認識
目前,我國行政監管機關在追究超比例違規增持行為人的行政責任時,主要是依據《證券法》(2014修正)第一百九十三條、第二百零四條、第二百一十三條對相關行政責任承擔的認定,但民事責任與行政責任的認定依據不同,不能以行政責任直接追究行為人的民事責任。對于超比例違規增持行為人的民事責任,有學者主張通過內幕交易路徑予以追究,也有學者主張通過虛假陳述路徑予以追究,但本文認為這兩種路徑均存在認定和適用上的困難,而應通過一般侵權責任路徑予以追究。
(一)以內幕交易責任路徑追究超比例違規增持行為人的民事責任
有學者認為可依據內幕交易的民事責任承擔追究超比例違規增持行為人的民事責任。根據《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證券市場內幕交易行為認定指引(試行)》第二條的規定,“本指引所稱內幕交易行為,是指證券交易內幕信息知情人或非法獲取內幕信息的人,在內幕信息公開前買賣相關證券,或者泄露該信息,或者建議他人買賣相關證券的行為。”由此可知內幕交易違法行為的構成要件包括:其一,行為主體為內幕信息知情人或者非法獲取內幕信息的人;其二,行為客體是內幕信息;其三,主要行為是買賣證券、建議他人買賣證券或者泄露信息;其四,行為發生在內幕信息的價格敏感期內。若將此對應于超比例違規增持行為則可形成以下認定:首先,根據《證券法》(2019修訂)第五十一條第二項,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東屬于證券交易內幕信息知情人,而超比例違規增持行為的最低節點是5%,故無疑滿足內幕信息知情人的主體條件。其次,根據《證券法》(2019修訂)第八十條第二項,公司股權結構的重大變化屬于重大事件,而超比例違規增持至少為5%,足以導致目標公司股權結構發生重大變化,可以歸于內幕信息,因此超比例違規增持滿足內幕交易的客體條件。最后,內幕信息敏感期指內幕信息自形成至公開的期間,超比例違規增持便是在這一期間繼續買入目標公司股票,因而滿足內幕交易的時間和行為條件。因而超比例違規增持的主體、客體、時間和行為條件與內幕交易行為一一對應,行為人作為內幕信息知情人在超比例違規增持這一內幕信息形成但未公開之前繼續買入目標公司的股票,屬于“內幕信息知情人利用內幕信息進行證券買賣”,故主張以內幕交易責任路徑追究超比例違規增持行為人的民事責任。
但本文認為通過內幕交易責任路徑追究超比例違規增持行為人的民事責任還需商榷。首先,從理論角度來說,目前學界對內幕交易行為的責任追究是否應包含對受害人進行私力救濟的爭議很大②詳見馮果著《內幕交易與私權救濟》,原載于《法學研究》2000年第2期,第91~101頁。,投資者事實上并不比監管機關了解或掌握更多有關內幕交易的信息,如果鼓勵私人訴訟則可能導致濫訴①詳見耿利航著《證券內幕交易民事責任功能質疑》,原載于《法學研究》2010年第6期,第77~93頁。。其次,從實際操作角度來說,目前對內幕交易行為法律責任的承擔只在規范層面作了原則性規定,尚未對原告資格、損失范圍和計算方法等進行詳細規定,因而認定難度較大②詳見耿利航著《證券內幕交易民事責任功能質疑》,原載于《法學研究》2010年第6期,第77~93頁。。
(二)以虛假陳述責任路徑追究超比例違規增持行為人的民事責任
一些學者認為可依據虛假陳述的民事責任承擔追究超比例違規增持行為人的民事責任。理由是《證券法》(2014修正)第八十六條規定行為人有披露大額持股信息的義務,并可依據第一百九十三條的規定將超比例違規增持行為人劃至“其他信息披露義務人”③《證券法》(2014修正)第一百九十三條規定,“發行人、上市公司或者其他信息披露義務人未按照規定披露信息,或者所披露的信息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的,責令改正,給予警告,并處以三十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的罰款。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給予警告,并處以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的罰款。發行人、上市公司或者其他信息披露義務人未按照規定報送有關報告,或者報送的報告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的,責令改正,給予警告,并處以三十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的罰款。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給予警告,并處以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的罰款。”,若其不披露超比例違規增持信息即為“其他信息披露義務人未按照規定披露信息”,由此認為可根據虛假陳述的責任路徑追究超比例違規增持行為人的民事責任。《證券法》(2019修訂)似乎為此種觀點提供了支持,如第七十八條擴大了信息披露義務人的范圍,將“其他信息披露義務人”明確歸在信息披露義務人的范圍內④《證券法》(2019修訂)第七十八條規定,“發行人及法律、行政法規和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規定的其他信息披露義務人,應當及時依法履行信息披露義務。”,并在第八十五條規定了信息披露義務人因未承擔義務而使投資者遭受損失的應承擔民事賠償責任⑤《證券法》(2019修訂)第八十五條規定,“信息披露義務人未按照規定披露信息,或者公告的證券發行文件、定期報告、臨時報告及其他信息披露資料存在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致使投資者在證券交易中遭受損失的,信息披露義務人應當承擔賠償責任”。。
但本文認為在既有的規范體系內,很難通過虛假陳述責任路徑追究超比例違規增持行為人的民事責任。原因在于:第一,《證券法》(2019修訂)第六十三條的權益變動規則由權益披露規則和慢走規則構成,超比例違規增持行為往往體現為對這兩種規則的共同違反,但《證券法》(2019修訂)第八十五條只規定了違反權益披露規則的行為,并未明確在交易窗內繼續交易的行為。第二,追究虛假陳述行為人的民事責任需滿足4個構成要件⑥詳見邢會強主編的《證券法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135頁。并需證明因果關系的存在,而在超比例違規增持民事案件中,根據供求關系原理及對目標公司的看好心態,披露大比例增持股票信息多會引起股價上漲,市場其他投資者買入股票并未產生損害結果,此時不會構成虛假陳述,無需承擔民事責任。此外,受侵害的權利主體往往是賣出股票的當事人,根據《關于審理證券市場因虛假陳述引發的民事賠償案件的若干規定》第十八條、第十九條規定,損害與結果之間并不構成虛假陳述認定中的因果關系⑦《關于審理證券市場因虛假陳述引發的民事賠償案件的若干規定》第十八條明確規定,“投資人在虛假陳述實施日及以后,至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買入該證券”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虛假陳述與損害結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同時第十九條也明確規定當被告舉證證明原告“在虛假陳述揭露日或者更正日之前已經賣出證券”,人民法院應當認定虛假陳述與損害結果之間不存在因果關系。。第三,支持虛假陳述違法行為路徑的人多認為構成了“誘空型虛假陳述”⑧“誘空型虛假陳述”指虛假陳述者發布虛假的利空消息,或者隱瞞實質性的利好消息不予公布或不及時公布,使得投資者在股價向下運行或者相對低位時賣出股票,在虛假陳述被揭露或者被更正后因股價上漲而導致投資者遭受損失的行為。,原因在于行為人隱瞞大額持股這一信息不公布,使得投資者在低價位時賣出股票,進而導致其在行為人披露大額持股信息后因股價上漲而遭受損失。然而,目前我國在規范層面并未對誘空型虛假陳述進行規定,在司法裁判中法院很難認定其他投資者賣出股票所遭受的損失與被告違反權益披露規則和慢走規則的行為之間是否具有因果關系,其他投資者的主張很難得到支持。第四,即便假定“誘空型虛假陳述”成立,其侵犯的是因虛假陳述行為而造成損失的其他投資者的權利,但就實踐中的超比例違規增持案件來看,提起訴訟的往往是目標公司及其大股東,而他們并非虛假陳述的適格原告。綜上,本文認為依據虛假陳述責任路徑追究超比例違規增持行為人的民事責任并不能很好地解決司法實務中的現實問題。
(三)以一般侵權責任路徑追究超比例違規增持行為人的民事責任
有學者根據《證券法》(2014修正)第一百二十條①《證券法》(2014修正)第一百二十條規定,“按照依法制定的交易規則進行的交易,不得改變其交易結果。對交易中違規交易者應負的民事責任不得免除;在違規交易中所獲利益,依照有關規定處理。”的規定,認為超比例違規增持行為侵犯了股東的知情權和交易機會權等民事權利②詳見矯月著《上海新梅股權之爭風波再起第一大股東之位歸屬待解》,原載于《證券日報》2015年1月13日版。,從而以侵權責任的構成要件為論證起點,認為可以一般侵權責任路徑追究超比例違規增持行為人的民事責任。本文認為目前此種路徑較為合理,原因如下:
第一,在規范層面具有追究超比例違規增持行為人一般侵權責任的法律依據。《證券法》(2019修訂)第一百九十六條第二款規定“收購人及其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利用上市公司收購,給被收購公司及其股東造成損失的,應當依法承擔賠償責任”,該款表明《證券法》單獨規定了超比例違規增持行為的一般侵權責任。雖然從字面意思來看規定的是收購人的收購行為,但超比例違規增持行為人的增持目的具有主觀性,在未真正公開之前,監管機關和其他市場主體均無法判斷其真實目的,而且行為人的目的并非一直不變,可在持股達到一定比例后由前期以投資為目的轉為以收購為目的。同時,在超比例違規增持案件中不論是否以收購為目的,行為人往往都具有較大的主觀惡意性,其行為具有違法性;且《證券法》(2019修訂)將權益變動制度的適用股份限定于有表決權的股份,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權益變動制度主要用以規制上市公司收購行為的立法意旨。此外,從體系解釋角度來說,《證券法》(2019修訂)第六十三條將大額權益變動規則設置在“上市公司的收購”一章。綜上,超比例違規增持行為可適用《證券法》(2019修訂)第一百九十六條關于民事賠償責任的規定,可將其視為單獨的一般侵權責任。
第二,在適用層面追究超比例違規增持行為人的一般侵權責任更有利于裁判說理。就適用性而言,以一般侵權責任路徑追究超比例違規增持行為人的民事責任其包容性更強。實踐中通常是由目標公司及股東提起超比例違規增持訴訟,原告往往主張侵權行為限制了股東權利、侵犯了目標公司及管理層的控制權和反收購權。在當事人不能達成調解協議時,法院必須對焦點問題予以回應,并在判決書中進行詳細說理。但在超比例違規增持訴訟中,目標公司及管理層實際上并不一定進行了股票交易,主張內幕交易責任追究路徑和虛假陳述責任追究路徑會面臨僅憑原告不適格就被駁回訴訟請求的窘境,而一般侵權責任路徑能使法院對于是否支持原告的訴訟請求進行充分說理,對原告主張的法益是否屬于侵權責任法所保護的法益進行合理解釋,因而這一路徑更具包容性和靈活性。
三、超比例違規增持侵犯的民事權利
一般侵權責任以侵權行為、過錯、損害結果以及因果關系為構成要件。侵權行為的違法性和行為人的主觀過錯性在超比例違規增持案件中較為明顯,因此,證明超比例違規增持行為造成的損害事實及其與侵權行為之間的因果關系是認定一般侵權責任的關鍵。通常來講,大額權益變動對證券價格有較大影響,超比例違規增持往往會擾亂正常的證券交易秩序③詳見吳英霞著《投資者違反慢走規則法律責任體系的構建》,原載于《南方金融》2018年第2期,第96頁。,但這只會引發監管問題,行政監管涉及的是公法上的行政機關和行政相對人,并不存在私法上的權利主體,無法引發民事訴訟。故要追究相關主體的侵權責任,就必須有對某類權利主體的損害事實,而損害事實可通過是否構成對相關主體權利的侵害進行論證。此外,在探討超比例違規增持對相關主體權利的侵害時,雖然投資者和股東身份多有重合,但股東更多是相對于公司而言,主要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進行規制,而投資者更多是相對于市場而言,主要適用《證券法》進行規制,二者的側重點不同④詳見徐聰著《違反慢走規則買賣股票若干爭議法律問題研究》,原載于《法律適用》2015年第12期,第101~106頁。,下文在結合*ST新梅案的論述中也將投資者和股東視為不同的受侵害權利主體。
(一)超比例違規增持侵犯了目標公司的反收購權
在*ST新梅案中,法院僅論證了目標公司大股東并非反收購權的權利主體,而未涉及若將目標公司作為原告并主張行為人侵犯了其反收購權時應如何認定的問題。對此需要明確的是,反收購權的權利主體是目標公司而非目標公司的控股股東①詳見姚瑤著《公司收購中違反大額持股申報義務的法律責任——基于“上海新梅案”的分析例證》,原載于《河北法學》2017年第2期,第183頁。。在股份有限公司中,公司法人人格獨立,股東承擔的是有限責任②《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三條規定,“公司是企業法人,有獨立的法人財產,享有法人財產權。公司以其全部財產對公司的債務承擔責任。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以其認繳的出資額為限對公司承擔責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東以其認購的股份為限對公司承擔責任。”。股東的利益并不能完全代表公司的利益,這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對關聯交易進行嚴格限制的一個原因③《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二十一條規定,“公司的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不得利用其關聯關系損害公司利益。違反前款規定,給公司造成損失的,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可見,反收購權的保護對象是目標公司而非目標公司控股股東。既然目標公司有反收購權,那么反收購權是否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中應當保護的法益呢?本文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的保護客體不僅包括法律明文規定的權利,還包括法益④詳見姚瑤著《公司收購中違反大額持股申報義務的法律責任——基于“上海新梅案”的分析例證》,原載于《河北法學》2017年第2期,第181頁。。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雖未明確規定采光權、日照權等物權,但這無疑應當為法律所保護,任何人侵犯他人的此項權利都應承擔侵權責任。所以,盡管《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并未對公司反收購權進行明確規定,但其本身仍是法律應當保護的法益。法院在審理超比例違規增持民事糾紛案件時,應更多考察違法增持行為是否造成侵權法上的損害,以及損害結果與侵權行為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而不能簡單根據反收購權不是法定權利而否認其仍然是被法律所保護的法益⑤詳見翟宣任、肖寧卉、鄭艷著《“違規舉牌”的法律后果研究——基于*ST新梅案的思考》,原載于《金融理論探索》2017年第2期,第60頁。。
(二)超比例違規增持侵犯了公司股東對公司的控制權
在*ST新梅案中,法院認為目標公司控股股東的控制權并非股東權利,此種控制權僅表現為對公司管理事務的表決權。對此,本文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作為組織法,在客觀上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法權關系:一種是股東之間、股東與公司之間、公司與債權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另一種是公司治理結構中產生的公司組織機構之間、控股股東與公司之間的管理與服從關系,即權力與服從的關系⑥詳見郭富青著《論控制股東控制權的性質及其合理配置》,原載于《南京大學學報》2011年第2期,第60~71頁。。股東持有的股份與其享有的表決權往往成正比,由于控股股東持有絕對或者相對多數的股份,其可通過表決權控制公司,此時控股股東的股東權利就異化為控股股東對公司的支配權力⑦詳見郭富青著《論法權形態異化的本質及其法律矯治》,原載于《河北法學》2007年第11期,第54~59頁。。因而控制權雖源自于股東股權,但它一旦脫胎于股權,就具有了與股權判然不同的特性,成為了“一種新的利益存在方式”⑧詳見甘培忠著《公司控制權的正當行使》,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頁。。以收購為目的的行為人故意違反權益披露規則和慢走規則,導致目標公司股東因缺少對該信息的反應時間而在未采取應對措施的情況下便發生了控制權轉移,從而可視為對原公司控股股東控制權的侵犯。控制權雖未被視為一種獨立的權利,但其也是一種法益,“受侵權法保護的法益須有社會一般意義上的可識別性,而非為潛在侵權人所不可感知”⑨詳見于飛著《侵權法中權利與利益的區分方法》,原載于《法學研究》2011年第4期,第104~119頁。。從一般社會認知來看,因行為人的不披露行為造成控股股東喪失對公司的控制權,則其利益無疑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損害。
(三)超比例違規增持侵犯了投資者的知情權
在*ST新梅案中,法院認為被告王某的超比例違規增持行為的確侵害了包括原告在內的廣大投資者的知情權,應對遭受損害的投資者承擔賠償責任,但在該案中,原告并未主張財產性權益損失,根據處分原則,法院只能在當事人請求的范圍內進行審理和裁判,所以法院沒有判定行為人賠償原告財產性權益損失。關于超比例違規增持是否侵犯了投資者的知情權,本文認為,由于證券市場存在一定程度的信息不對稱,為保護投資者權益,需賦予投資者以知情權①詳見陳甦主編的《證券法專題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93頁。。信息公開透明是對證券市場的基本要求,投資者從事證券交易,應是在了解市場和目標公司情況的基礎上作出投資決策。按照正常的交易規則,在股票交易中,交易的達成是基于雙方的自由意志,買賣雙方均不會構成對對方的權利侵害。但在超比例違規增持交易中,投資者賣出股票是因行為人未遵守權益披露規則和慢走規則,正常情況下,行為人若遵守大額持股變動規則并及時披露信息,出于對目標公司的看好預期,投資者一般不會或至少不會提前賣出股票,正是因行為人的過錯和違法行為,才使投資者產生預期利益損失。
需要說明的是,大額權益變動中的慢走規則雖然禁止增持者在特定時間內進行股票交易,但目標公司股票仍可進行其他正常交易,證券市場上的其他主體也可進行股票交易。此外,大額權益變動規則是由權益披露規則和慢走規則構成,在股份增持比例達5%時,增持行為人需履行信息披露義務以保障投資者的知情權。同時,慢走規則限制的也是增持行為人的交易權,投資者的交易權并不受限制,只是其所作出的股票交易決策因行為人未履行信息披露義務而受到影響②詳見徐聰著《違反慢走規則買賣股票若干爭議法律問題研究》,原載于《法律適用》2015年第12期,第101~106頁。。因此,超比例違規增持行為并未侵害交易對方的公平交易權。
對于侵權行為與損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目前學界對因果關系的認定主要是依據必然因果關系理論③必然因果關系實質上意味著僅在虛假陳述行為和損害后果之間存在絕對的、客觀的、本質的聯系時,才能認定加害行為和損害后果之間具有因果關系,才能構成侵權。和相當因果關系理論④詳見李伏夏著《誘空型虛假陳述的因果關系認定研究》,原載于《金融服務法評論》第十卷,第364~390頁。。根據相當因果關系理論,因果關系的成立需滿足侵權行為對損害后果的發生產生實質性影響以及該侵權行為造成損害結果的發生是大概率事件這兩個條件。也就是說,行為人的違規行為對權利人的權利造成了實質性損害,而且這種損害結果的產生是行為人能夠合理預見的。據此,本文認為對超比例違規增持行為人的民事責任可采取相當因果關系理論進行認定。
四、超比例違規增持行為人民事責任的承擔
超比例違規增持行為侵害了目標公司的反收購權、目標公司控股股東的控制權以及投資者的知情權,導致相關主體經濟利益受損,本文認為在對超比例違規增持行為人的責任追究中,不能以行政責任取代民事責任,行為人應當承擔表決權受限以及賠償損失等民事責任。
(一)行政責任不能取代民事責任
《證券法》(2014修正)第八十六條的大額持股披露規則和慢走規則規定在“上市公司的收購”一章中,從契合性和對應性的角度來看,違反該條義務應適用第二百一十三條⑤《證券法》(2014修正)第二百一十三條規定,“收購人未按照本法規定履行上市公司收購的公告、發出收購要約等義務的,責令改正,給予警告,并處以十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的罰款;在改正前,收購人對其收購或者通過協議、其他安排與他人共同收購的股份不得行使表決權。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給予警告,并處以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的罰款。”的規定進行處罰,但實踐中的行政處罰案例卻統一適用第一百九十三條關于虛假陳述的責任條款⑥詳見姚蔚薇著《違反證券交易大額持股披露及慢走規則的民事責任探析》,原載于《證券法苑》2017年第2期,第61~77頁。。《證券法》(2014修正)第一百九十三條和二百一十三條都規定了“責令改正”的責任承擔方式,其中第一百九十三條指向“信息披露”,第二百一十三條指向“公司收購”。但就違反《證券法》第八十六條規定的行為而言,如何責令改正尚不清晰。根據第一百九十三條,“責令改正”的內容應為“對信息披露違規情形”的改正,而不包括對在禁止交易期買賣股票的改正;根據第二百一十三條可推定若收購人改正了違規行為則能行使表決權,表決權的行使以收購人在改正違規行為后仍持有權益股份為前提,并且未涉及違規持有的權益股份如何處理等問題①詳見李振濤著《我國上市公司大額持股變動的法律責任探析》,原載于《法律適用》2016年第1期,第106~113頁。。以上關于“責令改正”內容的模糊使得“責令改正”這一救濟措施無法真正起到約束行為人超比例違規增持行為的目的。此外,《證券法》(2014修正)第一百九十三條和第二百一十三條無論是“責令改正”還是“警告”“罰款”都是由行政機關適用的行政責任條款,并未單獨規定超比例違規增持行為人的民事責任。
對此,《證券法》(2019修訂)徹底摒棄了將限制表決權規定在行政責任條款中的做法,其在第六十三條新增了第四款規定,即“違反第一款、第二款規定買入上市公司有表決權的股份的,在買入后的三十六個月內,對該超過規定比例部分的股份不得行使表決權”。這表明《證券法》對超比例違規增持股份表決權限制問題的規制已擺脫了行政權力前置的困局,為司法機關和上市公司等民事權利主體限制表決權提供了法律依據,這是對大股東權益變動制度的最大突破。與此同時,《證券法》(2019修訂)第一百九十六條第二款新增了關于收購應負賠償責任的規定,即“收購人及其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利用上市公司收購,給被收購公司及其股東造成損失的,應當依法承擔賠償責任”,該款明確規定了超比例違規增持給被收購公司及其股東造成損失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因而,在對超比例違規增持行為人的責任追究中,不能以行政責任取代民事責任,行為人應當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
(二)民事責任的承擔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十五條,侵權責任的承擔主要有停止侵害、排除妨礙、消除危險、返還財產、恢復原狀、賠償損失、賠禮道歉以及消除影響、恢復名譽等8種②《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第十五條規定,“承擔侵權責任的方式主要有:(一)停止侵害;(二)排除妨礙;(三)消除危險;(四)返還財產;(五)恢復原狀;(六)賠償損失;(七)賠禮道歉;(八)消除影響、恢復名譽。以上承擔侵權責任的方式,可以單獨適用,也可以合并適用。”。對于停止侵害而言,《證券法》本就規定了慢走規則,因此行為人在法定期限內不得再買賣股票。對于賠禮道歉和消除影響、恢復名譽而言,其主要適用于名譽權、榮譽權、著作權、商標權、專利權等人身權和知識產權糾紛案件,而不適用于超比例違規增持案件。對于其余5種責任承擔方式在超比例違規增持案件中的適用主要涉及3個問題:一是返還財產、恢復原狀類主要涉及交易行為的效力問題;二是排除妨礙、消除危險類主要涉及股東權利限制問題;三是賠償損失類主要涉及財產性權益損失賠償問題。由此,超比例違規增持行為人的民事責任承擔也可分為3種情形。
1.不予適用返還財產、恢復原狀。目前,理論界和實務界對超比例違規增持交易行為的效力問題已達成基本共識,即認為行為的違法性不影響行為的效力③詳見陳潔著《違規大規模增減持股票行為的定性及懲處機制的完善》,原載于《法學》2016年第9期,第105~112頁。。理由如下:第一,違反大額權益變動規則的交易行為僅僅是對目標公司及股東、其他投資者產生影響而并不損害社會公共利益。《證券法》(2019修訂)第一百一十七條④《證券法》(2019修訂)第一百一十七條規定,“按照依法制定的交易規則進行的交易,不得改變其交易結果,但本法第一百一十一條第二款規定的除外。對交易中違規交易者應負的民事責任不得免除;在違規交易中所獲利益,依照有關規定處理。”規定了證券交易結果恒定原則,否認交易行為的效力就意味著破壞交易結果恒定原則,將會對證券市場的發展產生較大的負面影響⑤詳見丁冬和陳沖著《證券市場違規增持的司法規制:角色、策略與難題》,原載于《證券法苑》2017年第1期,第83~96頁。。此外,交易所內的證券交易屬于商事活動范疇,效率和安全是商事法律規范的主要追求,對于上市交易行為,不應輕易否認其效力⑥詳見徐聰著《違反慢走規則買賣股票若干爭議法律問題研究》,原載于《法律適用》2015年第12期,第101~106頁;吳飛飛著《違規舉牌相關爭點回應與規制路徑探尋》,原載于《證券市場導報》2017年第9期,第61~68頁。。第二,違反大額權益變動規則的交易行為并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當規定的設定目的是為否認所規定行為的效力時,違反該規定就會造成行為無效的后果;而當規定的設定目的僅是要求行為主體履行某種義務時,則違反該規定并不會導致交易行為無效①詳見王保樹著《商事審判的理念與思維》,原載于《山東審判》2010年第2期,第8~10頁。。設定大額權益變動規則的目的是要求增持者按要求披露信息,在規定時間內不得進行證券買賣,并不是否認大額權益變動行為的效力。因此,違反該規則雖有一定的違法性但行為本身仍有效②詳見姚蔚薇著《違反證券交易大額持股披露及慢走規則的民事責任探析》,原載于《證券法苑》2017年第2期,第61~77頁;劉沛佩、趙航著《慢走規則下大額持股變動的法律性質與規則適用》,原載于《證券法苑》2017年第2期,第78~94頁。。第三,從《證券法》規定的違反慢走規則的法律后果來看,違反慢走規則的交易行為仍然有效。《證券法》(2019修訂)第六十三條第四款規定了違反大額持股披露規則購入的股票,對超出比例部分在36個月內不得行使表決權,因此可推斷在此期間增持者仍可繼續持有股票,且36個月之后就可獲得表決權。而如果合同無效,其自始就不產生法律效力,所引發的法律后果就是恢復原狀。那么,行為人如何才能恢復原狀呢?只有行為人將因超比例違規增持所持有的股份處置出去才能使公司控制權恢復到原有狀態。在此種處置思路下,行為人既然已經處置了因超比例違規增持所持有的股份,就意味著其不再享有股份更談不上表決權問題③詳見虞琦楠著《違規舉牌收購上市公司股份:行為效力與法律責任完善》,原載于《金融市場研究》2017年第6期,第105~116頁。,那么此時《證券法》(2019修訂)第六十三條第四款關于限制表決權的規定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可見,只有承認交易行為的有效性,《證券法》(2019修訂)第六十三條第四款才有實際意義。因此,既然承認了超比例違規增持交易行為的有效性,那么行為人便不必承擔返還財產、恢復原狀的法律責任。
2.適用排除妨礙、消除危險——限制表決權。在*ST新梅案、西藏旅游案、成都路橋案和康達爾案件中,違規增持股票的表決權問題均是案件的爭議焦點。《證券法》(2014修正)將限制表決權規定在第二百一十三條中,并以行政責任條款的形式存在。這在司法實踐中便會產生如何認定行政監管機關“責令改正”的問題。在成都路橋案、*ST新梅案、康達爾案件中,法院均承認和認可監管機關的決定,這也是很多司法機關在處理與證券市場有關的糾紛時所普遍采取的做法。若按此邏輯,行為人在違反權益披露規則和慢走規則后,只要根據監管機關的要求補充信息披露,即可認定行為人“改正”了違法行為。而目前我國對違反權益披露規則和慢走規則的行政處罰力度不夠,這可能使大額權益披露規則成為投資者通過補充披露和罰款而對違法行為進行“漂白”的路徑,不利于規范大額權益變動行為④詳見吳英霞著《投資者違反慢走規則法律責任體系的構建》,原載于《南方金融》2018年第2期,第91~98頁。。
如前文所述,對超過規定比例部分的股份的表決權問題,《證券法》(2019修訂)在第六十三條第四款⑤《證券法》(2019修訂)第六十三條第四款規定,“違反第一款、第二款規定買入上市公司有表決權的股份的,在買入后的三十六個月內,對該超過規定比例部分的股份不得行使表決權。”中進行了重新修訂,摒棄了將限制表決權規定在行政責任條款中的做法,直接規定“違反第一款、第二款規定買入上市公司有表決權的股份的,在買入后的三十六個月內,對該超過規定比例部分的股份不得行使表決權”,因而今后法院在認定行為人表決權問題時,可直接據此對股東表決權進行限制。
此外,關于超比例違規增持行為人的股東權利還有一個問題值得關注,即公司章程或者董事會決議是否能夠對行為人的股東權利進行限制。為阻止惡意收購,很多上市公司將反收購作為一項重要內容規定在公司章程中;抑或是在出現超比例違規增持情況后,通過股東大會或董事會決議限制行為人的股東權利。對此,證監會曾明確表示上市公司章程中涉及公司控制權條款的約定需遵循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不得利用反收購條款限制股東權利⑥在2016年8月26日中國證監會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針對部分上市公司選擇修改公司章程來避免惡意并購一事,新聞發言人張曉軍表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證券法》《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的規定,上市公司章程中涉及公司控制權條款的約定需遵循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不得利用反收購條款限制股東的合法權利,證監會依法監管上市公司收購及相關股份權益變動活動,發現違法違規的,將依法采取監管措施。詳見http://www.gov.cn/xinwen/2016-08/27/content_5102788.htm。。在成都路橋案以及康達爾案件中法院也認為公司章程對股東權利限制無效。本文贊同監管機關和法院的做法。首先,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四條的規定,股東的表決權等權利是股東法定的、固有的權利,公司章程應當符合法律規定,股東大會以及董事會應當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決議,不得對股東固有權利予以限制和剝奪。其次,公司和股東的私法自治應有邊界,《證券法》(2019修訂)第六十三條性質上屬于涉眾性條款,股東表決權等權利不在公司和股東私法自治的邊界范圍內①詳見吳飛飛著《違規舉牌相關爭點回應與規制路徑探尋》,原載于《證券市場導報》2017年第9期,第61~98頁。。因此,公司章程并不能對《證券法》規定的36個月作出改變。最后,《證券法》(2019修訂)已對表決權限制作出了規定,公司章程再規定表決權限制條款并無實際價值,反而易產生其與《證券法》之間適用不明的問題。
3.適用賠償財產性權益損失。如前所述,超比例違規增持行為侵犯了目標公司的反收購權、目標公司股東的控制權以及投資者的知情權。就投資者的知情權而言,超比例違規增持行為人因侵犯了投資者的此種權利而造成投資者預期利益的損失,因而投資者可向行為人主張財產損害賠償,至于損失金額的計算,則需結合具體情況予以認定。此外,對于超比例違規增持行為對目標公司的反收購權及目標公司股東的控制權等造成的損害,則應由目標公司及目標公司股東承擔證明責任。
五、結語
長期以來,我國證券市場的監管主要以行政監管為主,對一些違法違規行為民事責任的規制明顯不足,而更為有效的監管模式應是由行政監管和司法規制共同規范市場行為,由行政部門和司法部門共同發力,實現功能互補,形成監管合力②詳見丁冬和陳沖著《證券市場違規增持的司法規制:角色、策略與難題》,原載于《證券法苑》2017年第1期,第83~96頁。。在對超比例違規增持行為進行責任追究時,若僅對其進行行政責任追究則無法形成有效約束,行為人在承擔行政責任之外還應承擔一定的民事責任,對民事責任的追究也不宜通過內幕交易或虛假陳述的責任路徑進行認定,而應以一般侵權責任路徑進行追究,同時適用限制表決權、賠償財產性權益損失等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