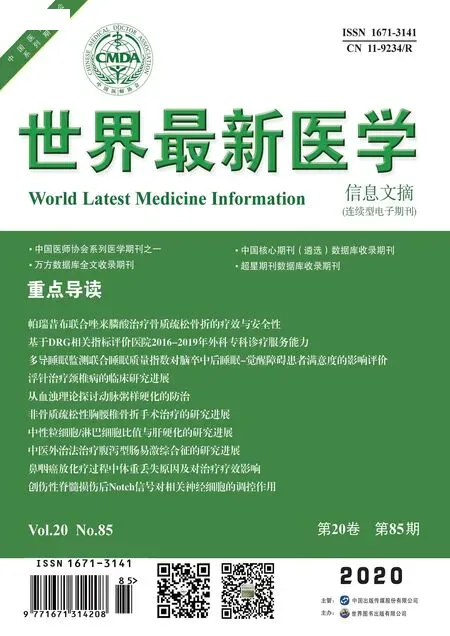參苓白術散治療脾虛夾濕型大腸癌術后腸道功能紊亂的臨床研究
陳明歌,劉松江
(1.黑龍江中醫藥大學,黑龍江 哈爾濱;2.黑龍江中醫藥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黑龍江 哈爾濱)
0 引言
結腸癌和直腸癌是我國常見的消化系統惡性腫瘤,總稱為大腸癌,近年來其發病率和死亡率均明顯升高[1]。目前認為結直腸癌的發生與飲食結構異常、遺傳基因等因素相關,常見治療手段包括外科手術、放化療、靶向治療等。結直腸癌患者在接受手術切除及局部放療后常出現腸道功能紊亂的癥狀,如腹痛、腹瀉、里急后重、腹瀉與便秘更替等。現代醫學認為其發生與大腸癌根治術中肌肉與周邊神經損傷、腸道內菌群紊亂等因素相關,治療上以抑制腸蠕動、調節腸道菌群為主,但治療效果不盡如人意,上述癥狀難以根治,嚴重影響了患者的生活質量。近十年來臨床研究證明中醫藥治療有助于腸道功能恢復,且在提高患者生活質量方面具有突出優勢[2]。筆者在跟師臨證過程中發現結直腸癌術后患者多見腹瀉、黏液便、排便不盡感等癥狀,屬于中醫“泄瀉”的范疇,辨證屬脾虛夾濕證,劉師采用參苓白術散加減治療該證型,取得較好療效。故本研究采用參苓白術散加減治療大腸癌術后脾虛夾濕型腸道功能紊亂的患者60 例,探討中醫藥治療手段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現報告如下。
1 資料和方法
1.1 臨床資料
1.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9 年1 月至2019 年10 月就診于本院門診的脾虛夾濕型大腸癌術后腸道功能紊亂患者60 例,依據隨機數字表法分為研究組和對照組,每組各30 例。研究組男17 例,女13 例;年齡51~68 周歲,平均(61.2±8.5)周歲;病程1~25個月,平均(6.5±3.1) 個月。對照組男18 例,女12 例,年齡49~70 歲,平均(59.3±9.1)歲;病程1~25 個月,平均(7.1±3.8)個月。2 組一般資料比較差異較小(P>0.05),具有可比性。
1.1.2 診斷標準
參考《功能性胃腸病的羅馬Ⅲ診斷標準》[3]制定的胃腸道功能紊亂的診斷標準。
1.1.3 辨證標準
參照《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泄瀉篇”[4](2002 年版)及林洪生主編的《惡性腫瘤中醫診療指南》[5]相關內容擬定,具備主癥及次癥一項以上,結合舌象、脈象。擬“脾虛夾濕證”標準如下,主癥:大便時溏時瀉,水谷不化,稍進油膩之物,則大便數增多,頭身困重,食少納呆,脘痞脹悶。次癥:神疲乏力,少氣懶言,四肢倦怠,口中黏膩或有甜味,小便頻;舌脈:舌質淡胖或有齒痕,苔白或白膩,脈濡緩或緩弱。
1.1.4 納入標準
1)年齡18~70 周歲;2)所有患者均進行過大腸癌根治術;3)經病理檢查確定為結、直腸癌并且排除腸炎等疾病的可能性;4)預計生存預期≥3 個月;5)入組期間無其他治療;6)愿意加入本研究,并簽署知情同意書。
1.1.5 排除標準
1)不符合納入病例標準者;2)對試驗藥物過敏者;3)合并嚴重心、腦、肝、腎等重要臟器疾病者;4)依從性差不能配合治療者;5)入組期間并發或繼發惡性腫瘤需其他治療者。
1.2 治療方法
1.2.1 研究組
予參苓白術散加減治療。處方:人參15g,白術15g,茯苓15g,桔梗10g,白扁豆15g,砂仁10g,薏苡仁10g,蓮子10g,山藥10g,甘草5g。久瀉脫肛者加五味子25g、訶子10g;腰膝酸軟者加龍眼肉20g、補骨脂15g;氣虛乏力者加黃芪30g;心悸者加炙甘草15g、煅龍骨20g、煅牡蠣20g。日1 劑水煎服,300mL 日2 次早晚分服。
1.2.2 對照組
患者口服鹽酸洛哌丁胺膠囊(西安楊森制藥有限公司,規格:每盒2mg×7 粒)治療,第1 次服用藥劑量為4mg/次,出現異常排便后再進行服用,每排便一次服2mg/次,服藥劑量≤20mg/d。
2 組均以連續服藥1 個月。
1.3 觀察指標與統計學方法
1.3.1 觀察指標
記錄2 組治療前后的中醫證候積分,進行比較。中醫證候積分記錄參考《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泄瀉篇”[4],主要選取大便泄瀉(大便性狀、排便次數、是否影響生活、是否需要藥物干預)、腹脹腹痛、腸鳴、食欲不振、倦怠乏力等癥狀,按照無、輕、中、重分別計為0、1、2、3 分,癥狀越重,分數越高。
1.3.2 統計學方法
使用SPSS 22.0 統計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s)表示,組間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組內采用配對樣本t檢驗;計數資料采χ2檢驗,等級資料采用有序變量的兩獨立樣本比較的秩和檢驗,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療效標準與治療結果
2.1 療效標準
參見《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泄瀉篇”[4]擬定。療效指數=(治療前中醫癥狀積分-治療后中醫癥狀積分)/治療前中醫癥狀積分×100%。臨床治愈:大便泄瀉、腹脹、腹痛、腸鳴、食欲不振、倦怠乏力等癥狀完全消失或基本消失,療效指數≥90%;顯效:大便泄瀉、腹脹腹痛、腸鳴、食欲不振、倦怠乏力等癥狀明顯改善,90%>療效指數≥70%;有效:大便泄瀉、腹脹腹痛、腸鳴、食欲不振、倦怠乏力等癥狀均有好轉,70%>療效指數≥30%;無效:癥狀均無改善,甚或加重,療效指數<30%。
2.2 兩組療效比較
表 1 顯示,研究組總有效率93.67%,對照組79.61%,2 組相比,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

表1 兩組療效比較例(%)
2.3 兩組癥狀積分比較
表 2 顯示,兩組治療后癥狀積分較治療前均有改善(P<0.05),且研究組與對照組相比,研究組癥狀積分改善情況更佳(P<0.05)。
表2 兩組治療前后癥狀積分比較(±s)分

表2 兩組治療前后癥狀積分比較(±s)分
注:與治療前相比,①P<0.01;與對照組治療后相比,②P<0.05。
組別 例數 治療前 治療后研究組 30 17.84±7.31 2.90±2.58①②對照組 30 20.32±9.01 4.39±3.29①
2.4 2 組不良反應發生情況比較
治療期間,研究組出現多食易饑1 例,不良反應發生率為3.33%(1/30)。對照組出現口干1 例,皮疹1 例,不良反應發生率為 6.67%(2/30)。2 組不良反應發生率相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3 討論
大腸癌術后腸道功能紊亂可歸屬于中醫學“泄瀉”的范疇,《臨證醫案指南·泄瀉》[6]:“泄瀉,注下癥也。經云:……濡泄之身重軟弱,濕自盛也;滑泄之久下不能禁固,濕勝氣脫也。”大腸癌患者經手術創傷后氣血不足,正氣虛弱,體內“濕”、“痰”、“毒”、“瘀”留存,脾胃受損,腸道傳導失司,水濕潴留,停于下焦,發生泄瀉,正所謂“濕勝則濡泄”。脾虛失運可致水濕停聚,濕邪侵襲可影響脾的運化升清,脾虛與濕邪相互影響,互為因果。病機總屬濕邪侵襲,脾胃功能障礙,基本病位在脾胃,與大小腸密切相關。辨證屬脾虛夾濕證,治療以扶正健脾益氣為主,兼以緩去濕邪,脾氣健運,傳導水濕,升降有常,則濕邪無以為聚;濕邪難生,則脾胃運化無有干擾,水谷精微運化有司,得以滋養臟腑經絡,疾病漸去矣。劉師結合多年臨證經驗及現代藥理研究成果,在參苓白術散的基礎上進行靈活化裁施治。參苓白術散出自《太平惠民和劑局方》,主治脾虛濕盛諸證。全方以四君子湯之人參、白術、茯苓、甘草為基礎,養胃益氣、健脾燥濕。人參健旺脾胃之氣,資生氣血;白術、茯苓共用健脾除濕之力更強,運化停聚之水濕;甘草甘溫調中,固護脾胃之氣。蓮子、山藥入脾、腎經,補脾益腎,固精止瀉,避免泄瀉不止耗傷真陰;薏苡仁健脾利濕,《本草新編》云“薏仁最善利水,不至耗損真陰之氣,凡濕盛在下身者,最宜用之”;白扁豆補脾不膩,除濕不燥,促進中州運化,為健脾化濕之良藥;砂仁行氣化濕溫中,貫通上下氣機,為醒脾和胃之要藥。桔梗為手太陰肺引經藥,肺與大腸相表里,如舟楫載藥上行,達于上焦以益肺,通調水道,運化水濕,以上諸藥,共奏補氣健脾滲濕之功。
近年來現代醫學將大腸癌根治術后出現的排便頻率增加、肛門重墜、排便失禁、等癥狀歸為前切除綜合征(anterior resection syndrome,ARS)的范疇[7]。腸道括約肌功能損傷和肛管直腸抑制反射等神經通路異常是目前較為廣泛承認的ARS 發生機制。吳承堂等[8]對腸道屏障功能的研究表明大腸癌手術可造成腸黏膜屏障損害,致使腸道內原住寄生菌群易位而出現腸道內微生態失衡,這提示ARS 的發生可能與腸道內微生態紊亂相關。辜沅[9]等基于腸道微生態的參苓白術散藥理研究進展表明參苓白術散能增促進益生菌生長,抑制病原菌或條件致病菌繁殖,通過維持腸道內菌群的動態平衡,促進腸黏膜屏障功能的恢復,維持腸道正常排泄的功能。董開忠[10]等研究表明參苓白術散對胃腸運動具有雙向調節功能,方內主要藥物可上調節機體免疫功能,抑制致病菌繁殖,減輕胃腸黏膜水腫,有助于組織修復。
本研究顯示,參苓白術散能明顯改善脾虛夾濕型大腸癌術后腸道功能紊亂患者的臨床癥狀,且具有一定的安全性,與鹽酸洛哌丁胺相比具有較強優勢,能進一步提高臨床療效。受制于客觀因素,研究過程存在小樣本、單中心、觀察周期短等問題,其結果有待深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