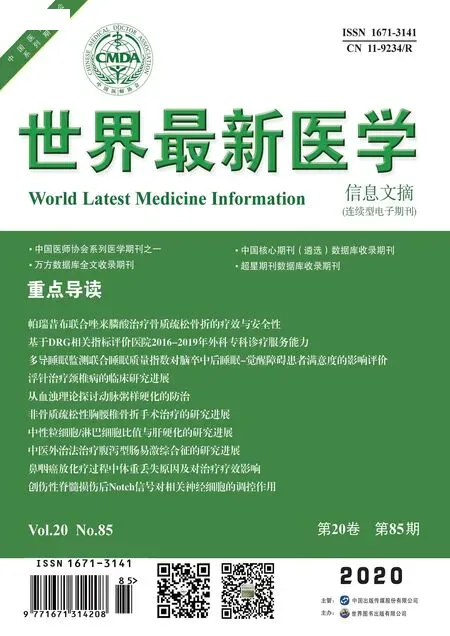境外輸入型COVID-19 患者不確定感及身心體驗的質性研究
張瑩,魏花萍*,吳雨晨,馬芳麗,寇彩艷,靳修,張志剛,蔡小林
(1.蘭州大學第一醫院,甘肅 蘭州;2.蘭州市肺科醫院,甘肅 蘭州)
0 引言
2019 冠狀病毒病(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在中國武漢首先發現。于2020 年2 月11 日被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命名,被國家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納入乙類傳染病,采用甲類傳染病防控措施[1-3]。且于2020 年1 月31 日WHO 宣布COVID-19 為“全球突發公共衛生事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PHEIC) ”[4]。目前,COVID-19 事件已在全球范圍內流行,甘肅省蘭州市接國家衛健委的委派對伊朗回國人員進行集中隔離觀察,并對確診患者進行積極救治。截止,3 月19 日,除37名確診患者外的274 名密切接觸者全部解除留觀[5]。
隨著全球一體化進程和人口流動的加快,近日來,境外輸入病例逐漸增多,截至3 月27 日24 時,甘肅省蘭州市累積收住確診輸入型COVID-19 患者36 例[6],其中信仰伊斯蘭教的回族患者多達88%。調查發現93.8%%的穆斯林患者認為醫務人員缺乏宗教文化知識,無法提供令人滿意的醫療護理服務[7]。研究發現醫護人員在了患者的文化信仰和價值觀的情況下,實施準確照護,不僅可減少因為文化差異而導致的沖突,而且還可以提高患者對于醫護人員的滿意度和信任度[8-11]。COVID-19 具有爆發性、不可預測性、甚至危及生命,在心理學上被認為是創傷應激性事件,隨著疫情的不斷升級,影響人們生活的不僅有病毒,還有心身感受。面對來自具有多元化文化背景的境外輸入型COVID-19 患者,只有了解其文化背景和身心體驗才能對患者進行科學、全面地評估,實施準確的照護[11]。因此,本研究以質性研究的方法對境外輸入型COVID-19 患者的疾病感受和身心狀態進行分析,為臨床照護提供理論基礎。
1 研究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本研究采用目的抽樣方法,選取在甘肅省某醫院定點救治的COVID-19 患者9 名進行訪談。納入標準:①年齡≥18 歲;②無意識障礙;③2020 年3 月3 日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發布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七版)》診斷標準為依據確診的COVID-19 患者;④境外回國的患者;⑤自愿參與本研究。排除標準:①訪談中途退出者。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半結構訪談進行資料收集。訪談者根據研究目的,參照Kallio[12]的半結構訪談提綱形成步驟。首先,確定使用半結構化訪談的先決條件:本研究是對輸入型COVID-19 患者疾病相關不確定感及身心體驗的探索研究,半結構化訪談有利于COVID-19 患者表達自我感受;其次,通過查閱文獻并與2 名境外輸入型患者前期的護理專家討論后形成初步的訪談大綱;最后,與2 名COVID-19 患者進行預訪談后對訪談大綱進行調整,形成最終版的半結構訪談提綱。①您被確診時的反應是怎樣的?②當您被確診后轉至我院治療后,您有哪些顧慮、擔心?③您覺得隔離治療期間您自身發生了哪些變化?④您是怎樣解決您目前遇到的這些問題的?⑤您在隔離治療期間最期望醫護人員為您提供哪些幫助?⑥您還有哪些困惑或者需要?
1.3 資料收集
研究者與受訪者提前約定訪談時間,以受訪者的身心狀態及意愿為準,通過面對面交談的形式進行訪談,訪談時間為25-30min。訪談前向患者解釋研究的目的、意義和方法,并向患者保證與其交談的所有信息僅用于醫學研究,發表內容不涉及任何個人隱私,征得患者同意后進行訪談并記錄。訪談中結合患者感受對部分問題進行追問和深入探究,也可以采用自我暴露的方式,與患者分享類似感受,盡可能的鼓勵患者達內心真實想法,增加訪談的深度。訪談完畢向患者致謝并再次承諾保密。
1.4 訪談資料分析
每份訪談資料在訪談結束24h 內由兩名研究者將訪談記錄補充整理完。采用現象學資料Colaizzi 七步分析法對收集資料進行分析[13-14]。逐字閱讀文字材料,按照編碼系統將相同或相近的資料合并,找出資料之間的聯系。通過推理分析,提煉出主題。
2 結果
2.1 基線資料
本研究對9 名輸入型COVID-19 患者進行了語音訪談,以輸入型的第一個單詞“Inpute”的首字母“I”作為編號碼。患者的年齡在19-62 歲(30.56±17.37),回族8(88.89%) 例,漢族1(11.11%)例;有宗教信仰者8(88.89%)名,均信奉伊斯蘭教,入境至確診時間間隔天數1-10 天(4.11±3.14)。其余信息見表1。

表1 訪談對象的基本信息
2.2 訪談結果
本次訪談結果發現青年患者與中老年患者的遷移應激及心身體驗有許多相似點和異同點,通過總結分析并進行主題提取,共提取出3 大類8 個主題:分別是民族信仰是與身心體驗;強烈的疾病不確定感和對未來生活的擔憂。
2.2.1 I類民族信仰與身心體驗
2.2.1.1 淡定超然大部分境外輸入型患者在確診后表現淡定平和,能很快就接受自己現在的狀態。I4:我都已經在蘭州新區醫院觀察了10 天了,他們讓我收拾東西,我以為我沒問題他們要送我去酒店了,結果下車后我發現我到了這里,我很不確信的問了一句:“我是被確診了嗎?”,他們工作人員說:“很可能是的”,我有點兒意外,但沒什么大不了的,聽從上天的安排吧。I2、I3、I4:“我是第二次做完核酸檢測,他們就把我接到這里了,在這里又做了一次咽拭子檢查、CT檢查后告訴我,省級專家會診結果我被確診了,我當時也沒覺得很意外,第一次核酸檢測結果是陰性,我被隔離在新區醫院,沒有接觸其他人,也戴好口罩了,第二次核酸檢驗就陽性了,這是注定好的”。I8:“我記的很清楚是3 月18日開始覺得嗓子不舒服,干咳,之前有慢阻肺,但我心里隱隱的擔心,21 日回國后,他們給我做了核酸檢驗,就把我送到你們這里了,說是我被確診了,也在意料之中沒什么不能接受的。I7: “我覺得是老天安排好的,沒什么意外的”。
2.2.1.2 民族信仰與角色轉換障礙
因為境外輸入型患者均有自己的民族信仰,他們認為自己被感染是因為上天的安排,自己接受這個事實,但是出現不同程度的患者角色轉換障礙,主要表現為角色缺如和角色行為強化。I1、I2、I3、I5:我剛開始還是不能接受我被感染這個件事,我被隔離在這里了,我爸爸媽媽和其他的家人就跟我說,這是老天的安排,讓我自己在反省、凈化。他們每天都會跟我視頻、通電話,告訴我聽主的安排,照顧好自己,現在我聽從主的安排,好好自我反省。I7、I8:這個新冠病毒我們都是看不見的、摸不著也聞不到,為什么就我被感染了呢?你能看的見、摸得著嗎?(反問訪談者),你也不能吧,所以這都是主的安排,其實我可能沒有感染的,我是被關禁閉讓我自省的。I6:剛開始把我送到這里復查后醫生告訴我被確診了,我真的不能相信,但是現在我都已經接受治療20 天了,每天吃飯、喝藥、霧化、曬太陽、打游戲,我覺得我是真的被感染了,所以我每天按時吃藥、霧化、吸氧,我還老覺得我的胸口疼。經常胸悶上不來氣。I9:除了剛開始到這里你們醫生告訴我說我確診了,我覺得不可思議,畢竟我都已經在新區那邊隔離10 天了,還是覺得很意外,現在我已經接受治療6 天了,除了不能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停頓了一下),其他都還行,既然被感染了就接受治療吧,雖然我也出現了一些副反應,但我也只能接受了,不然可能會更嚴重。
2.2.2 主題2 疾病相關不確定感
在臨床治療和護理的過程中,我們也遇到了很多的問題,比如有的患者說這個藥的副反應太大了,我不想吃;也有的說這是治療HIV 的藥物,我又沒有得艾滋,為什么要給我吃這個藥?這個病究竟能不能好啊?會不會有什么后遺癥?我會不會像武漢的那些人一樣上ECOM 什么的?國家到底什么時候才有疫苗?
2.2.2.1 擔心藥物治療的不良反應
本次訪談的9 名患者在接受治療初期都訴說克力芝、ɑ干擾素還有中藥湯劑有不良反應,不愿意服藥。其中I9:“我其實很不想吃克力芝這個藥,也不想做那個霧化(ɑ 干擾素),我之前就查過這個藥是治療HIV 的藥,有很多副反應,拉肚子都是小事兒,對肝臟功能、腎臟功能,甚至還有什么骨壞死的反應,我很害怕,”I4:現在是我在這里治療的第12 天了,我發現每天梳頭都會掉很多頭發,我不確定這與我們吃的藥有關系嗎? I7、I8:我還是有些擔心治療的副反應,但是我都活了幾十年了,我相信很多事情都是上天的安排,他讓我們在這里反省隔離15 天,我會謹遵主的安排,但是克力芝是治療HIV 的藥物,我又沒有得艾滋,為什么要給我吃這個藥?這個要的副反應很大,我有那么一刻懷疑主的安排。I1、I2、I3、I5:我其實還是挺擔心治療的副反應的,不論是吃的克力芝還是霧化吸入的α 干擾素,我覺得對我影響挺大的,用了這些藥后我比較愛睡覺、也惡心、嘔吐還拉肚子了,不過醫生都開了藥,現在基本沒感覺到了,但我不知道對我的身體長期會不會有不好的影響,尤其是克力芝。I6:已經連續吃了9 天克力芝了,現在已經不吃了,但我常常在想不會留下什么并發癥吧?現在我一擦身體就會感冒,會不會跟吃藥、霧化的藥有關系啊?
2.2.2.2 擔心預后
因為科技網絡的迅速發展,所有的患者都有知情權,也會自己搜索COVID-19 相關的治療及研究進展,針對COVID-19 治療、預防及預后等疾病相關知識的不確定性導致患者對其預后產生懷疑和不確定感。I1、I6:我不了解胸悶、胸痛與我病情變化有什么關系,有時候莫名其妙的就疼,疼的時候感覺上不來氣,過了這個點兒就沒什么感覺了,感覺又好好地,我有時候在想等我出院還會不會有這樣的情況,會不會一直伴隨我?I2、I3、I4、I5:說不擔心那是假的,但是你們又有什么其他好的治療方法嗎?在死亡和未知的生存狀況之間來說,主可能更希望我們在經歷磨難之后活著。I3:我自己一個人的時候會想不管以后會經受什么,至少現在我被安排治療可能是最好的安排。I7、I8:我相信我現在所遭遇的一切都是主的安排,以后可能出現的所有并發癥也都是主的安排,我擔心但是我要接受,因為我是逃不掉的。I9:我肯定還是會擔心的啊,剛開始服藥的時候我就有反應,惡心嘔吐,畢竟到現在還沒有有效的治療方案,我看網上SARS 時期生存者現在生活的很痛苦,有骨壞死,說是與激素治療有關,我們現在吃的藥不是激素嗎?洛匹那韋/利托那韋(LPV/r)不是也有骨壞死的反應嗎?
2.2.2.3 對檢驗結果及臨床診斷結果的不確定
由于目前對COVID-19 的認識處于起步階段,且國家衛健委根據前期治療效果對診療方案做了6 次修改,每一版本都發生了一定的變化。在大數據時代只要會上網都可以看到COVID-19 相關的信息,這對患者也產生了一些不良影響。I7:“自從我們回國我就一直關注這個病毒的治療,我看了國家衛健委對診療方案修改了一次又一次,到現在我看都已經第六版了(訪談者打斷了一次說:現在實施的是第七版診療方案),哦,對,都第七版了,每一版本都在改變,我看網上你們很崇拜的哪些專家還有說這個病毒的潛伏期是21 天的,所以我真的有點兒擔心(重復擔心)我會在出院14 天后再發燒”I6、“我現在真的不確定我接受的治療或所服的藥物是否有效,我已經治療了20 天了,剛開始吃的藥基本都停了,所以我不知道我到底是被感染了還是就是(停頓了5 秒)誤診了?”。I6:“我覺得醫生說話模棱兩可,充滿了很多的不確定性,我都做了6 次核酸檢查、4 次CT 檢查了,每次結果都是陽性,我都不知道我的治療到底有沒有效果”。I3、I4:“其實我不確定我是不是被感染了,因為在我之前周圍好幾個都被拉走了(住院治療),但是我后來問他們都是疑似,后來就排除了,我怎么就確診了呢?”。I2、I5:我覺得我的癥狀仍持續不穩定地變化無法預測結果的好壞,我也不確定檢查結果的準確性,因為還會偶爾有嗓子不舒服,突然間干咳,呼吸不順暢。
2.2.3 對未來生活的擔憂和社會期望度
2.2.3.1 對未來生活擔憂
I3、I4、I9:因為治療的緣故,使得我可以做和不可以做的事情總在改變,而且變故很大,因為藥物的副作用使得我變得很虛弱,很困,每天我不能按時學習、鍛煉身體,我不知道以后會不會出現這樣得狀況。I4:我現在脫發很嚴重,我最近老在想頭發這樣掉下去,以后會不會變化才能禿頂或者光頭啊?I9:我不知道這次的治療對我將要參加比賽有什么影響嗎?我會不會被決絕參賽?如果被拒的話我以后要干什么?我還能做自己喜歡干的事情嗎?I7、I8:雖然我在這里隔離是主的安排,但是我還是想我什么時候才可以開始工作,因為我還有孩子在上學,家里還得靠我每個月的收入生活,我擔心主會讓他們和我一起反省。
2.2.3.2 社會支持的期望度和治療費用訴求
國家衛健委剛開始的政策對春節期間COVID-19 患者免診療費用,這一政策影響到輸入型COVID-19 患者對自己住院費用、住院伙食費用提出了疑議,對隔離治療期間的食宿不滿意程度高。I1、I2、I3、I4、I5:我們看到國家對這個病是免費治療的?為什么我還要交差不多1 萬塊錢的住院費用呢?治療期間的伙食費是誰定的?一日三餐達不到每日80 元的標準啊?這住院費用我要去哪里報銷,能報銷嗎?I2、I3、I5:我還是學生有免費治療的政策嗎?I5、我是建檔立卡戶,我是不用交住院費的吧?I1、I2、I3、I4、I5:我希望國家能免費治療,幫我把住院費用和伙食費能免了,畢竟我還沒有工作,只是個學生。I2、I3、I5:我還是希望社會能多多的幫助我們,為我們提供綠色通道,就像學校里的那樣。
3 討論
3.1 重視少數民族患者的文化照護
宗教是人類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伊斯蘭教是世界第二大教信徒多,世界范圍內分布廣泛[15-16]。穆斯林患者有自己特殊的生活方式、行為習慣,并且他們有自己對健康疾病的態度和應對方式。本次訪談結果顯示境外輸入型COVID-19 患者在被確診后表現的淡定超然,這與此次疫情中臨床護士被感染后的震驚心理反應大相徑庭[17]。這是因為伊斯蘭教對信徒的生死世界觀產生了深刻地影響,對生死、苦難等世人無法理解、不能預測因素的恐懼和無奈,是穆斯林信仰伊斯蘭教的主要心理根源[18]。因此,他們認為所有好的、不好的事情都有它存在的原因,他們心底堅信這一切都是主(上天)安排好的,安排他們到這里關禁閉15 天。因為民族信仰的問題讓他們表現出一定程度的角色轉換障礙,表現為患者角色缺如,不愿承認自己是被感染的COVID-19 患者,也不愿意相信核酸和CT 檢查等的診斷結果。醫護人員在治療護理過程中,只有了解其文化背景、尊重患者宗教信仰才能對患者進行科學、全面地評估,實施文化照護[9-10,19]。
3.2 疾病相關不確定感
李歡[20]等人對不明原因發熱患者的疾病不確定感的研究中發現患者在住院期間普遍存在疾病不確定感,且處于較高水平。對疾病的了解程度、患者自覺嚴重程度是影響患者對疾病不確定感的主要影響因素。而COVID-19 作為新型一級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截至目前,由于其流行病學及發病原因不明、咽拭子核酸檢驗仍存在假陰性病例、潛伏期患者具有傳染性、傳播途徑多樣化、治療方法不明確等一系列與其相關的不確定因素造成公眾群體恐慌,對公眾的心理會產生一定影響[21]。而此次公共衛生事件患者面對遠不止病情的變化、隔離觀察、復雜的治療,還有后期不明朗的藥物的不良反應、疾病的轉歸以及中長期結局等等。這系列的不明朗使境外輸入型患者產生疾病相關不確定感[22-23],青年患者表現出的疾病不確定感更強烈。但是因為伊斯蘭教信徒的根深蒂固的生死觀,他們對生死、苦難和將來要經歷的都能欣然接受。
3.3 對未來生活的擔憂和社會支持的期望度低
穆斯林患者有很強的社會支持系統,穆斯林家族中男性長者是家中權威,有很高的地位,受到家人的尊敬,并有重要事情的決定權[18,24]。本研究中兩名年長患者是家庭主要經濟來源的主力,他們對這會支持的要求較低,因為伊斯蘭教有自己的教會和組織,有自己獨立的小團體,他相信他不在的時候,他家族中的其他人會安排好一切,因為主自有他的安排。而其他5 名出院伊斯蘭教青年患者對治療費用的訴求比較高。青年境外輸入型COVID-19 患者對未來生活擔憂程度比老年患者明顯,這可能是因為青年患者接受教育程度及文化學習的影響,使得他們的精神追求更豐富有關。
4 研究的局限性
由于輸入型患者的特殊性和突然性,參與研究人員的培訓時間有限,設置的訪談提綱有一定的局限性。其次,由于COVID-19 疾病的特殊性,本研究采取語音訪談法無法觀察患者的面部表情變化,訪談對象中8 名患者為信奉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僅1 名患者為漢族,不能比較宗教信仰對COVID-19 患者的身心體驗的影響。
5 總結
本研究通過對9 名境外輸入型COVID-19 患者進行深入訪談,揭示了信仰伊斯蘭教患者在感染新冠病毒(SARSCoV-2)的不確定感和身心體驗,主要包括3 大類:民族信仰與心身體驗,疾病相關不確定感,對未來生活的擔憂和社會期望度。包括淡定超然、民族信仰與角色轉換障礙、相信偉大的中國共產黨、擔心藥物治療的不良反應、擔心預后、對檢驗結果及臨床診斷結果的不確定、對未來生活的擔憂、社會期望度低而經濟訴求高8 個主題。結果表明伊斯蘭教信徒的生活、對生死和悲傷的態度及臨床常見問題與漢族或者是無宗教信仰的患者存在很大差別,在以患者為中心的醫學模式的倡導下,醫護人員應關注穆斯林患者的文化背景,實施文化照護,為信仰伊斯蘭教患者提供精確的照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