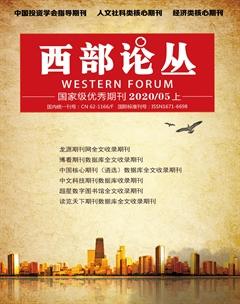《平原上的夏洛克》
摘 要:不同于《鄉村愛情》里雞飛狗跳的鄉村生活,不同于快手里土味十足的鄉村大爺,在這部電影中,講述了農村大爺超英和占義為了探明朋友樹理車禍的真相,一路探案求索而引發觀眾笑與淚的故事,在這部電影中有城鄉二元對立視域下農民的遭遇和心境,有粗糲生活下生機勃勃的可愛,有以超英為代表的農民達觀知命的處世哲學。在這部電影里,麻木不是一個貶義詞,縱使與世界格格不入,也會堅持心中所想,構建出精神世界的烏托邦王國。
關鍵詞:《平原上的夏洛克》;城鄉二元對立;技術景觀;城鄉壁壘
一、城鄉 二元對立下的類型敘事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將城鄉關系變遷概括為“城鄉分離”、“工業化和城市化”、“城鄉融合”三個階段,在電影的故事中,城市和鄉村處于相對分離的階段,電影聚焦于不再年輕的老人,年逾花甲的老人來給超英蓋房子,他們都有一門能養活自己的手藝,而村里的年輕人難得可見。
由于鄉村的年輕人進城務工,造成鄉村的勞動力缺失,進一步造成鄉村的經濟凋敝進而形成惡性循環,再加上年輕人的缺失帶走了鄉村的活力,在這個電影中,城市和農村的差距顯而易見,不僅僅是景觀環境還包括獨特的人文生態和文化特征。
(一)中國鄉土的“人情社會”。在中國逐漸向城市化邁進的道路上,鄉村常常作為城市的對立面出現,在城市處處標語:講文明、講規則、講禮貌,一切都是以規則建立起來的理性社會,但在鄉村,生硬的規則必須給“熟人社會”的自然法則讓路。
為了找到肇事車主的方位,超英和占義選擇了向神婆求助:“香自心誠起,煙從信里來,一誠通天界,諸君下瑤臺。”這樣神神叨叨的神婆借著“真言不傳六耳”的名義“泄露天機”和鄉村小店真實客觀的監控記錄形成鮮明的地位反差,感性玄學和理想科技的強烈對比讓觀眾感受到一種荒誕魔幻的意味;但在城市里,因為制定的規則,他們連一個小區的大門都進不去。這就說明了在鄉村人們有著自己約定俗成的行事方法,可能粗鄙簡陋,但確實是行之有效的中國鄉土獨有的“人情社會”。
(二)技術景觀的階級展現。交通工具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彰顯了個人身份和階級層次,在《平原上的夏洛克》中,作為現代交通工具的汽車成為了技術景觀之一,整個故事因為一起車禍而起,通過監控記錄發現三輛疑似肇事車輛分別是中國車、日本車和德國車,國產車對應的是五金店店主,這象征著消費社會中落伍的商品經營者,一邊感嘆著鄉村購買力的慘不忍睹,一邊面臨著小店不得不即將關門的未來,日本車的主人是一位在高中教書的老師,代表著當今社會被束縛的孺子精神,德國車的主人是有錢有勢的企業家范總,代表著階級社會中亦黑亦白的上層名流。
汽車的品牌以及價位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這三位“嫌疑人”的身份階級,作為農民身份的他們,交通工具是一輛牛車、一輛電動三輪車以及一匹馬。當超英和占義馳騁著電動三輪車開向城里時,他們迷離迷惘的眼神,在周圍的滾滾車流顯得格外突兀,所以電影中的交通工具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樹立人物形象和展現階級地位的重要作用,以技術景觀來展現階級沖突與對立。
(三)城鄉壁壘的黑色幽默。城鄉二元對立之中,城市和鄉村有著天然的鴻溝和壁壘,在鄉村里,人們習慣以結團的形式共同對抗,集體面對天災人禍,而初到城里的超英和占義就自然而然的失去了主場優勢,成為了兩個格格不入的外鄉人。
他們在尋找肇事司機的過程中翻墻進到了學校,大汗淋漓的老師正帶領著距離高考還剩30天的一群學生振臂高呼著一些成年人從出生到死亡依舊不懂的大道理,所有人都被這樣渲染焦慮的氣氛所同化了,墻外刷著“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墻內粉刷著“核心意識、看齊意識”,這代表了一種被壓抑被束縛的集體觀念,這種強勢的精神植入是超英和占義之前從未接觸過的,當特寫鏡頭搖過去時,暮氣的農民被象征著騰騰希望的校服包裝著,和這些孩子們一起站在諾大的孔子雕像下喊著一樣的口號,如此帶來的身份錯位和身份對比帶來了喜劇真相,讓觀眾感受到了辛辣的黑色幽默。
二、理想化的騎士,景觀化的農村
在中國的文藝作品中,鄉村似乎是割裂而矛盾的結合體,一種是離開鄉村去往城市是成功的象征,城市是成功人士的理想天堂,而鄉村則是窮山惡水出刁民的低級平臺,另一種鄉村是美好悠閑的代表,是從冰冷的城市摩天大樓間脫身而歸的精神家園,而城市成為了罪惡之源。更多的時候,鄉村是一種雜糅的存在,同理可得,鄉村中的人有著似多面體的狡黠,農民可以是理想化的騎士,鄉村也可以是景觀化的鄉村。
(一)浪漫英雄主義的求索。樹理因為給超英幫忙而車禍受傷,超英有兩個選擇,一是放棄報警讓合作醫療報銷70%的醫療費用了事,二是由超英自己負責找到肇事司機,但要承擔找不到肇事司機自己全部負責的風險,超英陷入了“to be or not to be,this is a question”的莎士比亞的困境中,這種道德拷問考驗著超英的良心,正是這種未知性和不確定性,給超英帶來了一種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悲劇英雄式的崇高和壯美,也開啟了為正義為理想而奮斗的破案求索之路。
當超英騎著一匹馬“達達”的去追逐占義——因為心疼超英為給樹理治病和討回公道掏空了家底,又不肯拿不義之財,所以才試圖一個人去拿錢,他就像一位俠客一樣策馬奔騰卻又不緊不慢,在那一刻觀眾們能看到令人崇敬的自我道德約束,他是一介農夫,但不妨礙他也是一個崇高壯美的英雄。
(二)鄉村詩情和老年浪漫。在年輕人的世界里,鄉村似乎和落后畫上了等號,老人似乎和落伍畫上了等號,但其實不然,在我們目光不能及的地方,麥子老了還有玉米和西瓜在生長,農夫老了還有朋友在身邊,“夏日天長,輕煙彌漫,田野芳香,細雨落下,葉子油亮”,一種朦朧的詩情在田地里彌漫,都讓觀眾感受到鄉村的愜意美好,也感受到了人們之間和諧融洽的情感互動。
在電影中,寧靜鄉村不是喧鬧城市的對立面,而是一個補充面,補充著城市沒有的人情味和煙火氣,情感的互動不是靠錢來維系的,而是憑著好兄弟就是一輩子的承諾,雋永無聲、質樸無言,反映出獨特的老年浪漫。
(三)直面殘酷并繼續生活。放棄了范總的不義之財,意味著老伴的遺愿可能永遠實現不了,超英的夢想是很多人的夢想,房子寬敞明亮,兒孫繞膝歡笑,幸福的晚年建立在一套新房上,可賣牛換得的蓋新房的錢,為了幫好兄弟治病全部給了醫院,直到結尾,理想中的“幸福家園”也沒有建立起來,但超英可以“直面生活的平淡和殘酷,又能給人以繼續生活下去的力量”,真實的傷痛被阿Q式的精神勝利法掩蓋著,底層人民把苦難以一種更藝術化的形式轉化成達觀知命的生活哲學,因為生活還要繼續向前,正如影片最后響起的音樂——在希望田,人生總得繼續向前。
三、結語
“稻草人肩膀,蒲公英遠方”,電影用這句話作為最終結尾,鄉村獨特的意象構成一種雋永含蓄又飽含希望的意境。加繆說過:“如果說生活注定是荒謬的,無意義的,那么就應該更好的去經歷它。”
超英用直面荒誕的遲鈍感和麻木感做磚石,用經久不變的初心和質樸情感做粘合劑,筑造出獨屬于他自己的烏托邦王國。
參考文獻
[1] 白永秀.城鄉二元結構的中國視角:形成、拓展、路徑[J].學術月刊,2012,44(05):67-76.
[2] 戚靖.荒誕與反抗——論加繆筆下的局外人形象[J].哈爾濱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20,11(01):144-146.
作者簡介:蔡金娥,(2000—),女,漢,湖北省宜昌市枝江市,本科,重慶郵電大學,傳媒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