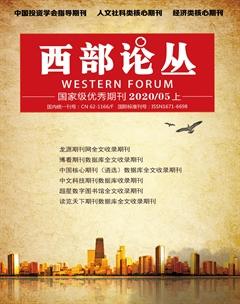中國古代司法文化的特點
摘 要:司法文化是法制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古代的司法文化結合了儒家、法家、道家等各派的法律思想,特別是儒家法律思想,適應了中國古代文明的形態。司法文化作為中華法系的基本內容,在歷史的傳承中形成了自身的特點,是中國傳統法制文明的重要成果。
關鍵詞:文化;司法文化;行政兼理司法
中華民族具有五千多年絢麗燦爛的文明史,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古代司法文化汲取了中國本土的儒、法、墨、道等各種哲學思想,特別是儒家法律思想,適應了中國古代農業文明的形態,與自然經濟、宗法社會和君主政治互為表里。古代司法文化作為中華法系的基本內容,是中國傳統法制文明的重要成果,對當代司法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一、有關文化的概念
當代我們所用“文化”一詞,其實是外來語的意譯,對應于英語和德語。在中國古代,“文化”一詞原與“武功”相對應,有文治教化之意《易·責卦》中說:“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艾,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這是中國古代對“文化”最早的理解一《周易正義》中解釋道:“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圣人觀察人文,則濤書禮樂之謂,當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這已有從觀念形態談文化的含義,強凋文化對人類認識、改造世界和進行道德教化所起的蓖要作用和功能一西漢劉向在《說苑,指武》篇中說:“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 凡武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誅。夫下愚不移,純德之所不能化,而后武力加焉。”晉束皙在《補忘詩·由儀》中更明確地說:" 文化內輯,武功外悠”梁昭明太子蕭統注日:言以文化輯和于內,用武德加于外遠也。”從這些論述中不難看出,中國古人雖沒有形成類似于近代西方對“文化”的概念,但“文治教化”的意蘊與“文化”的特點功能有相通之處,與當代我們所稱“文化”的規范、教化、凝聚等軟約束功能是相通的。
上述各類關于文化的定義,從不同的側面和視角展示了文化的共有內涵,所謂文化“就是這樣一個層層疊加而又互相包容的復雜相龐大的系統,其真實意義只能在不斷地從整體到部分,再從部分到整體的循環往復中得到說明”。研究司法文化亦不例外,只有在把握了文化的共性認識的基礎上,對司法文化的個性認識才會更加科學和準確,在此基礎上的司法文化建設才能夠有明確的目標、管用的措施和切實的效果。
二、傳統法律文化的內涵
傳統法律文化屬法律文化的一個分類,要考察我國的傳統法律文化,必須首先了解法律文化的一般理論。
單從法律文化的概念來說,在我國學術界也眾說紛紜。有些學者認為,法律文化主要是指法律文化史的積累,有些學者則指法律傳統及其對當代人心理與行為的影響,還有些學者將其界定為法律及其相關問題,而不問是否傳統的或當代的;另有學者則強調以文化分析的方法研究法學和探討法律的作用等。實際上,法律文化是以社會生產力發展為前提,以社會經濟為基礎的,體現著一定社會歷史時期的政治要求的所有法律現象的總和。包括法律心理、法律行為、法律制度以及組織機構。
首先,法律文化是人類文化的一種,法律文化簡單地說就是與法有關的諸種文化因素的總和,是特定的國家或民族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步創造并積累下來的與法有關的各種物質因素和精神因素的總和。具體包括一定的法律制度、法律習慣、法律意識(或叫法律思想或法律觀念)三個基本要素。其中,法律思想又是法律文化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因素,它決定著一定的法律制度(法律規范、法律原則、法律體系)的建立,也決定著一定的法律習慣(法律運作、行為模式、習性)的形成。法律思想又包括對法律的認識、對法律的情感取向和法律價值觀,其中尤以法律價值觀對法律文化產生的影響最大。它不僅影響并決定著特定法律制度的確立和法律習慣的形成,而且還影響著其它法律思想,如法律認識、法律情感的形成。法律價值觀主要是指人們對法律價值的基本看法,它屬于社會意識形態范疇,具體說,法律價值觀是法律與主體需要之間的關系在人們意識中的反映,是人們對法律價值的主觀判斷、情感體驗和意志保證的綜合。它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法律價值追求(或法律價值目標)與法律價值尺度(或法律價值標準),其中法律價值追求(或法律價值目標)是更為根本的,它決定了主體的法律價值標準,二者之間是目的與手段的關系。當然我們也不能完全忽視法律價值標準的作用,它有時也會對法律價值目標(或追求)產生一定影響。法律價值追求作為法律價值觀中帶有根本性的問題,同時也是法律文化中起主導作用的基本因素,其涵義實質就是人們期望通過法律要達到何種目標。不同的國家制度,不同的歷史階段,不同的文化底蘊,以及不同的民族習慣,其法律價值的追求目標是不同的,但一般說來,秩序、安全、自由、公平、正義都是法律價值追求的重要方面,同時也是法律文化的主要內容。
法律文化作為社會上層建筑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和其它社會意識形態范疇一樣,具有鮮明的特征。首先,法律文化具有鮮明的時代性。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就有不同的法律制度和不同的法律價值觀。其次,法律文化具有強烈的民族性。人類是社群交往行動的動物,但任何特定社群既有無限開放性的一面,還有自我封閉性的一面,尤其以民族為范圍定界的社群往往形成該社群的獨特文化,即使人類不同國家間的政治對話、經濟交易和文化交流發展到如此程度,被人們以‘一體化或‘全球化來形容,它并未消滅也消滅不了特定的社群文化封閉性的一面。最后,法律文化具有多元性。多元性是指法律文化在保持本民族、本國家、本時代特征的前提下,也即在保持不同的文化個性的前提下,古與今、東方與西方、落后與發達之間在法律制度、法律觀念上的對話、交流、繼承、移植,并由此形成多元化的法律文化現象
三、中國古代司法文化的特點
中國古代司法文化由于受當時經濟、社會形勢、文化發展的影響,呈現出不同的特色,但也存在一定的共性。
1.司法理念
西周時期以德為立國之道,以“明德慎刑”為訴訟的指導意義,以息訟的最終目標。秦國在商鞅變法后,法家的思想理論一直占據國家的統治地;秦朝統一中國后,崇尚韓非等法家代表的學說,排除儒家“禮治”、“德治”以及“息訟”學說的影響,貫徹“事斷于法”的精神,厲行封建法治,形成了有別以往的司法關念。在司法權的分配上實行高度集權,“事無大小皆決于上”,使君主集各項大權于一身,并推行“重刑推斷”的原則,從重懲輕罪人手,嚴厲處斷各類犯罪案件,特別是對侵犯封建國家與地主財產的犯罪行為實行嚴厲鎮壓的方針,造成刑罰使用酷濫,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矛盾,加速了秦王朝的敗亡。漢朝建立后,吸取秦朝敗亡的教訓,在西漢武帝時期確立了儒家化的司法理念,開始實施“春秋決獄”,其方法是依據《春秋》等儒家經典大義審判刑民,而不僅是依據漢朝法律審理,從而使漢朝的審判進入二元化審判的時期。
2.司法思維
西周的審判非常謹慎、科學,要求訴訟時原被告雙方都要到齊,且司法官從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五個方面去考察案情;同時,在決定刑罰時要根據犯人的具體情況包括主觀狀態、社會的具體情況和法律條款來共同處理。
3.司法機構設置合中有分,形成“行政兼理司法”的模式
一方面,司法與行政合一。中國古代社會行政與司法權不加區分,司法組織、司法權的運行都從屬于行政權,因而司法權不具有獨立的地位。可以說,古代中國的司法一直處于或依附或受制于行政的從屬性地位,形成“行政兼理司法”的模式。“行政兼理司法”模式,是指行政首長兼任司法長官直接處理或最終決斷司法事務,司法受到行政直接干預與影響的權力結構模式。從中央層面觀察,盡管各朝均存在司法審判的專門化機構,但司法并不由獨立的司法機關行使,而往往由行政機關分割,并且最終歸屬于皇帝直接控制。而在地方各級,司法行政合一表現更為充分,地方長官就是同級司法審判官,審判斷案也就是地方長官的主要職責之一。另一方面,司法權分割行使而相互制衡。如果說司法與行政合一更多體現在皇帝一身以及各封建地方政權上的話,司法權權分割相互制衡則可以體現在各封建王朝中央司法機關的設置上。歷數秦朝以來的中央司法機關,秦漢時期中央最高的司法部門為廷尉,屬中央九卿之一;唐代,中央的司法部門為大理寺、刑部、御史臺和三司,其中刑部是最高司法機關;宋代的中央司法機關有大理寺、審刑院和刑部;明代則由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組成中央司法機關,清代沿襲明制。在歷朝歷代中司法機關都只是古代朝廷的一個職能部門,是政府的組成部分。 在中央層面上,雖然古代中國建立了專門的司法機關,但是司法機關要絕對服從于皇權,皇帝掌握最高的審判權;同時,中央司法機關及其權力的行使受制于中央行政機關,比如皇帝可以直接派非司法機關的官員參與審判,大案要案設立會審,如清朝的“九卿會審”制度,這些體現古代中國法律文化的特色制度是行政權對司法權的直接干預。 在地方,司法事務長期由地方行政長官兼理,沒有形成獨立的司法組織體系。秦漢時期,地方實行郡縣制度,郡設“太守”,既是地方行政首長,也是最高司法長官,下設“決曹掾”處理司法事務;縣的行政首長是“令 ”,是縣級的最高司法長官 ,下設 “縣丞 ”,是縣令的副手,負責處理司法事務。郡縣行政長官都不必親自審判。漢代以后地方行政首長名稱與秦漢相同,唐代實行州縣制,縣負責初審,州只有權判決徒刑以下案件,其他案件的審判權收歸中央。宋代地方行政建制為路州縣三級,且規定州縣長官必須親自聽獄審問。明代地方行政分為省府(州)縣三級,其中縣府的案件一律由首長兼理。清代地方行政增設一級,為省道州縣四級制,也是由行政長官兼理司法。在地方,司法機關隸屬行政機關的特征更為明顯。古代中國地方司法權并未成為一種與行政權相當的權力。直至清末變法,西學東漸,司法隸屬行政即“行政兼理司法”模式才有所松動 。古代中國司法或直接沒有審判權或“審”“判”分離的權力配置結構以及隸屬性的組織架構,導致司法權只能依附于行政權,某種程度上也并未形成西方意義上的“司法權力”。 古代司法實質上只是皇權的附屬品,也只是行政的一個環節,是對政治意志和皇權利益的執行。
4.司法價值觀注重禮法融合
禮法融合,突出體現了中華法系極為濃厚的倫里色彩,也是中國傳統司法文化中最為獨特的風景。禮,最早由部落氏族的風俗習慣轉化而來,隨著社會發展,禮制內容逐漸膨脹,幾乎涉及一切社會領域。但至春秋戰國時代,“禮崩樂壞”,禮逐漸退化為以人倫道德為主要內容的教化手段。秦朝時期,由于長期處于戰爭的歷史環境下,開始推行法家路線,注重用法律統一人民思想。漢武帝時,開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學說從此成為中國歷代封建王朝一以貫之的正統思想。伴隨著儒家思想對法律的滲透,出現了以儒家經義為指導的審判方式——春秋決獄,奠定了禮法融合的基礎。
5.司法思維模式重刑輕民。我國傳統司法制度下,律以刑為重,所謂的司法審判多與量刑適用緊密關聯,民事糾紛的訴訟通常適用刑事訴訟程序,在追究當事人經濟責任的同時,也往往以刑罰為處分,因而具有“重刑輕民”的特征。在對刑事案件的審判中,審判人員往往注重案件的實體公正而非程序公正,“辨曲直、平冤獄”一直是刑事審判追求的目標,也是官方和民間對公正的正統理解。在民事審判方面,“無訟”作為儒家主張的法律思想,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基層司法官員對于民事案件往往首先適用強有力的息訴模式——調解,不過這種調解往往并不完全以當事人的同意為基礎,而具有相當的強制性。
參考文獻
[1] 邱玉強.中國傳統司法文化中“盡情察獄”研究[D].遼寧大學.2017.
[2] 任家寬、王翠紅、孟慶方. 論中國古代司法文化特征——以“行政兼理司法模式”為例[J].甘肅高師學報. 2016(8).
[3] 張晉藩.論中國古代司法文化中的人文精神[J].法商研究.2013(2).
[4] 張晉藩.中國古代司法文明與當代意義[J]. 法制與社會發展. 2014(2).
[5] 張本順,陳景良.試論中國古代司法傳統中的善治藝術[J].蘭州學刊. 2017(3).
[6] 徐清. “大刑伺候”的禁而不止:清末民初刑訊廢除運動的思考[N].人民法院報. 2018-11-30 (005).
[7] 邢朝國、郭星華.從摒棄到尊重:現代法治建設與傳統文化[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 2012(4) .
[8] 孔祥軍.論古代燕趙司法“青天”的群體特征與現代啟示[J].法制與社會 2018(20).
[9] 王斌通.中華傳統法律文化的全景再現——張晉藩先生《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十二講》推介[J]. 人民法治. 2019(1).
[10] 陳沖.試論中國傳統法律文化[C]. 2020全國教育教學創新與發展高端論壇會議論文集(卷二)2020-3.
基金項目:本文系2017年度黑龍江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規劃項目“現代法治視角下的中國傳統司法文化研究”的階段性成果,課題編號:17FXE283。
作者簡介:鄧立強(1965-),男,山東日照人,教授,碩士,從事法學及遠程開放教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