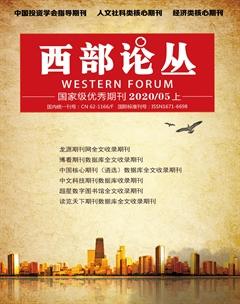漢末時局與荊州方土勢力的離合
摘 要:東漢末年,荊州的命運很大程度上掌控在本土大族的手中,而荊州大族的態(tài)度往往伴隨著時局以及利益的變化而變化。無論是接納劉表還是投向曹操,究其原因都與時局和利益變化有莫大聯(lián)系。把握好時局與利益的變化,能夠讓我們更好地理解漢末荊州大族復雜的政治態(tài)度和行為。
關鍵詞:劉表;荊州大族;時局
初平元年(190),劉表接任荊州刺史,得到荊州大族蒯良、蔡瑁等人的支持,最終得以平定荊州亂局。而數(shù)年后,荊州大族卻逐漸呈現(xiàn)出一種與劉表割裂,逐漸向曹操靠攏的趨勢,這個趨勢經(jīng)歷了由個人到集體,由荊南向荊襄全境蔓延的過程。究其根本,時局和利益變化是荊州大族態(tài)度轉變的主要原因。
東漢靈帝以降,天下紛亂,先有太平道信徒發(fā)動黃巾起義,后有董卓專權,豪強以討董為契機而起兵,此后群雄割據(jù)便一發(fā)不可收拾。在這種大局勢下的荊州也難免于難,靈帝中平年間,荊州先后經(jīng)歷了張曼成、趙慈、孫堅以及袁術等人的劫掠,為因應這種局面,一部分荊州大族阻兵作亂,割據(jù)地方,成為了“宗賊”,一時間荊州“宗賊”大盛。在這種背景下,荊州大族迫切希望能夠結束亂局,使荊州恢復安定。此時,劉表奉命出刺荊州,他雖在荊州毫無根基,卻因為荊州刺史的身份而成為荊州大族眼中平定亂局的最佳人選。雙方在共同的利益下一拍即合,以平定荊州為共同目標的利益集團形成。在蒯越的謀劃下,劉表得以迅速平定“宗賊”,并逐漸將孫堅、袁術的勢力趕出荊州。此時天下局勢紛亂,蒯越替劉表謀劃“南據(jù)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可見荊州大族在乎的只是本州的安定,并無意于天下紛爭。
天子都許后,劉表采取“內不失貢職,外不背盟主”的策略,意圖在曹操、袁紹之間首鼠兩端,繼續(xù)延續(xù)坐保江漢,以觀時變的政策。但是此時的時局已然發(fā)生變化,曹操與荊州關系亟待解決。曹操平定荊州的謀劃由來已久,曹操在與荀彧書信中追思郭嘉時提到:“追惜奉孝,不能去心……又人多畏病,南方有疫,常言‘吾往南方,則不生還。然與共論計,云當先定荊……”[1]郭嘉給曹操的這個建議雖沒有具體時間,但是曹操在建安二年和三年的上半年對張繡、劉表頻繁用兵,疑是依循此計劃進行。
荊州從事南陽人鄧羲是第一個反對劉表“內不失貢職,外不背盟主”策略的荊州大族,鄧羲的言辭已失傳但尚有另外一人的言論可供參考。《三國志·魏書·武帝紀》注引皇甫謐《逸士傳》載汝南王儁見劉表連結袁紹而言于劉表:“曹公,天下之雄也,必能興霸道,繼桓、文之功者也。今乃釋近而就遠,如有一朝之急,遙望漠北之救,不亦難乎!”[2]鄧羲的言語當與此當為類似。在劉表不采納鄧羲的建議的情況下,他便托病不出。這是劉表與荊州大族分裂的一個開端,但是此時劉表與曹操尚未兵戎相見,荊州大族的利益尚未直接受到威脅或損害,故而大多數(shù)荊州大族并沒有反對劉表首鼠兩端的政策,劉表與荊州大族的聯(lián)盟并沒有因為鄧羲一個人而受太大影響。
到了建安二年以及三年間,時局再次發(fā)生巨大變化,一方面,曹操開始對荊州用兵,劉表、張繡屢次戰(zhàn)敗。另一方面,荊南的長沙太守張羨在長沙大族桓階的慫恿下于建安三年反叛劉表,投向曹操。從蒯越獻給劉表平定荊州的策略“南據(jù)江陵,北守襄陽,荊州八郡可傳檄而定”可知,劉表一開始統(tǒng)治荊州主要依靠的是南郡的大族,主要力量也集中在南郡,對荊南的控制很薄弱,荊南大族與劉表關系并不密切。因此,在時局變動中,荊南大族最先與劉表決裂。
建安四年以后的數(shù)年里,曹操忙于應對北方的袁紹而無法繼續(xù)南征,對于荊州的施壓,更多的是通過政治手段來實現(xiàn)。曹操一手對荊州大族示好,另一手則是巧妙地利用其他軍閥勢力對荊州施壓。對于奉命詣許的荊州人士,曹操總是予以高官,厚結荊州大族。《三國志·魏書·劉表傳》注引《零陵先賢傳》載劉先出使許昌,數(shù)以言語沖撞曹操,曹操最后還拜他為武陵太守。后來出使的韓嵩也被拜為侍中、零陵太守。而這兩人最后都成為官渡之戰(zhàn)前夕荊州降曹的主要倡導者,與此恐怕不無關系。王夫之把韓嵩受曹操所代表的的朝廷的封賞與陳珪受賞并談,認為“(陳)珪與(韓)嵩之計得,而呂布、劉表之危亡系之矣”[3],看到了二者的共同之處。除此之外,曹操還利用劉表與劉璋、孫策的矛盾,以天子的名義讓孫策、劉璋共同征討劉表。《三國志·魏書·衛(wèi)覬傳》載:“太祖征袁紹,而劉表為紹援,關中諸將又中立。益州牧劉璋與表有隙,覬以治書侍御史使益州,令璋下兵以綴表軍。”[4]《劉璋傳》里“以(趙)韙為征東中郎將,率眾擊(劉)表”[5]當是在此時。《三國志·吳書·孫策傳》注引《江表傳》:“策被詔敕,與司空曹公、衛(wèi)將軍董承、益州牧劉璋等并力討袁術、劉表……(劉勛)告急于劉表,求救于黃祖。祖遣大子射船軍五千人助勛……策與戰(zhàn),大破之。”[6]此時的荊州雖然沒有曹操的直接威脅,但是其局勢卻也十分緊張。西面有劉璋的軍隊駐在益州與荊州的邊境上,東面有孫策向荊州步步逼近,南面還有張羨、桓階的叛亂尚未完全平定。荊州大族急迫的需要一個能夠解決眼下困局的人來統(tǒng)領荊州,而劉表的能力無法改變荊州的這種不利的形勢,保證大族的利益,由此,荊襄掌權的大族與劉表的分歧越來越大。此時的局面迫切需要荊襄掌權大族做出選擇,在權衡利弊之后,他們逐漸投向了有能力改變荊州窘迫時局,保證他們利益的曹操。一方面,投向曹操,劉璋、孫策便沒有正當?shù)睦碛晒ゴ蚯G州,荊州窘迫的局面能迅速得以緩和。另一方面,在曹操危急關頭雪中送炭比起為袁紹錦上添花所能謀得的利益更多,曹操善待陳登、臧霸以及張繡的前例,自然也讓荊襄掌權大族對投向曹操后的前途有信心。在這種背景下,官渡之戰(zhàn)爆發(fā)前夕荊襄的掌權大族集體站在曹操一邊的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也就成為了情理之中的事了。
而關于荊州掌權大族在建安四五年左右就有投向曹操的意向,而最終實現(xiàn)卻拖延到了建安十三年,其原因亦可尋。一方面,曹操在建安四年以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都在與袁紹及其子嗣爭奪河北,無暇顧及到南方荊州的情況。荀彧在建安九年為曹操謀劃,“愿公急引兵先定河北,然后修復舊京,南臨荊州,責貢之不入,則天下咸知公意,人人自安。”[7]可見建安九年曹操所急尚仍在北,南面平定荊州之事被規(guī)劃在河北事以后。另一方面,則是時局的變化緩解了荊州的局勢。建安五年,劉璋部下趙韙反叛劉璋,引兵數(shù)萬攻打劉璋,與東邊的荊州劉表則采取“厚賂荊州,與之連和”的做法。同一年,孫策為許貢賓客所殺,江東也陷入危機,荊州東邊的局勢也暫時緩和下來。荊南張羨也在此時病死,劉表乘機急攻荊南,一舉平定了這次叛亂,荊州的局勢再次暫時穩(wěn)定下來。在這種背景下,劉表和荊襄掌權大族的態(tài)度都有所保留,雙方矛盾心照不宣。劉表把被曹操打敗來投荊州的劉備安置在離襄陽不遠的新野,名為防備曹操,實際上也起到了威懾荊襄掌權大族的作用。直到建安十三年,曹操再次南征,緊接著劉表病亡,荊州的平衡局勢再次被打破,荊襄掌權的大族抓住機會,在劉琦、劉備尚未作出反應之前,脅迫繼任荊州牧的劉琮投降曹操。至此,荊襄掌權大族以荊州投降曹操的行動才勉強得以完成。
注 釋
[1] 《三國志》卷十四《郭嘉傳》注引《傅子》。
[2] 《三國志》卷一《武帝紀》注引皇甫謐《逸士傳》。
[3] 【清】王夫之:《讀通鑒論》卷九獻帝第十九條,中華書局,2002年6月,第248頁。
[4] 《三國志》卷二十一《衛(wèi)覬傳》。
[5] 《三國志》卷三十一《劉焉傳》,《后漢書·劉焉傳》改“擊”字作“備”,《華陽國志》作“征”,有差別。
[6] 《三國志》卷四十六《孫策傳》注引《江表傳》。
[7] 《三國志》卷十《荀彧傳》。
作者簡介:周衛(wèi)平(1992—),男,漢族,四川宜賓人,編輯,歷史學碩士。研究方向:中國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