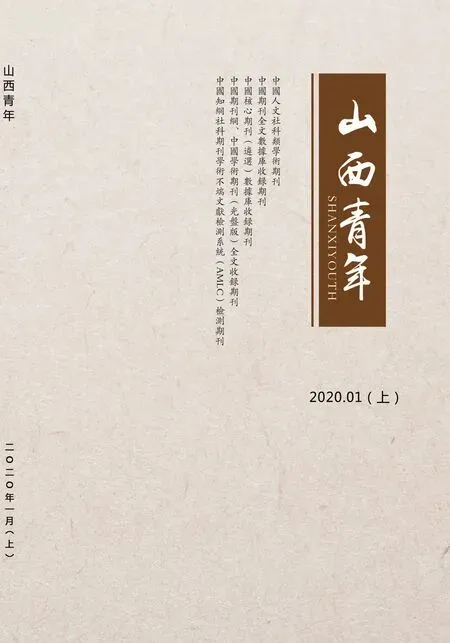試論六國舊貴族在秦末農民戰爭中的作用
張鮑龍
包頭服務管理職業學校,內蒙古 包頭 014000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被派往漁陽(現北京地區)戍守的農民,遇雨受阻。依《秦律》規定,戍守誤期當斬首,眾人遂在陳勝吳廣率領下,在大澤鄉揭竿而起。陳勝提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號召人民“誅暴秦”。①起義軍迅速壯大并建立了張楚政權。起義軍雖在秦軍殘酷鎮壓下遭遇挫折,兩路義軍相繼被擊潰、陳勝吳廣被殺,但起義的烽火最終將我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封建王朝秦朝化為歷史的灰燼。對于起義的性質我國學術界有不同的認識,每種認識都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華東師大房蕓芳認為當時“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的矛盾根深蒂固”,“秦統一后,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把所有國的農民階級一起推到了自己的對立面。”盡管有其他階層的人加入起義,但農民無疑是主要階層。綏化師范專科學校歷史系副教授江連山認為,“不僅有沉重的賦稅、繁重的徭役和嚴酷的刑法,更有宗教、風俗、人口、地理環境及起義領導者職業、經歷、性情、個人奮斗目標的影響。是這些原因交互作用,引發了農民大起義。”朱紹侯、張海鵬、齊濤主編的《中國古代史(新版)》(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七月第一版)認為秦末大起義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從陳勝吳廣揭竿而起到陳勝被殺——這一階段起義的性質為農民起義;第二階段為陳勝死后的起義運動,直到劉邦入咸陽為止——這一階段的運動性質書中并沒有給出明確的答案。趙錫元認為,秦末農民起義的性質是以農民為主體的人民反秦大起義,作用是堵塞了奴隸制的發展道路;由于勝利果實被地主階級篡奪,因而在中國確立了新的封建制度。這種看法能夠相對客觀的反映起義軍的組織構成,能夠較好的解釋這場運動所導致的諸如六國貴族的復辟及項羽和漢初的大分封等歷史事件,但是這些觀點有一些瑕疵:
1.起義的確是由農民起義開始,但是隨著大量反對秦朝的六國舊貴族、士人階層這些具有深厚社會背景的貴族加入,農民是否仍然是起義軍的主要力量,這一點值得商榷。
2.起義軍的領導權是在農民階級手中或在農民階級的代表陳勝手中后被篡奪了,還是農民階級從一開始就沒有掌握領導權?
3.起義的過程與結果為什么只反映了貴族階級的意志而絲毫沒有反映農民階級的意志?
我們需要解決這些問題。
一、裝備精良的“農民軍”
陳勝吳廣自大澤鄉起事、攻蘄至陳,反秦者踴躍響應,在極短的時間內隊伍由九百人擴張成為“車六七百乘,騎千馀,卒數萬人”②的強大部隊。騎兵是當時那個時代最強的作戰兵種。騎兵的戰斗力、經費遠遠高于普通步兵。戰馬在戰爭當中極易傷亡,很難被大量俘虜。因此,農民起義軍的騎兵來源有些蹊蹺。而戰車就更不可能是農民軍所應該擁有的了。只有像諸侯國那樣的政治、軍事組織才有能力進行生產。無論是駕駛戰車還是利用戰車作戰,都需要經過一定訓練,農民不可能在這么短的時間利用其戰斗。那么大量騎兵和戰車的出現只能說明一個問題,那就是有大量地位較為特殊的人加入起義軍,這些人擁有充足的財力,受過專門的軍事訓練,有一定的作戰經驗和技巧,這些人有很深的政治背景,但有著質量上的和素質上的優勢。這些人是六國的舊貴族及其追隨者。
秦滅六國后東方各地仍有頑強的地方勢力,秦政府為了徹底鏟除六國舊勢力,采取高壓統治,秦滅六國后,六國王室不是被殺,被軟禁,就是被遷徙流放。如魏王假投降,立即被處死;燕王喜被俘,不久被殺;趙國滅亡后,趙王被留放到房陵(湖北房縣),囚禁期間,思念故國,感慨萬千;因此他們對秦朝懷著刻骨的仇恨。
這些舊貴族不但有著極大的號召力而且也具有極強的凝聚力。秦雖滅六國,六國貴族殘余的影響力仍然存在,并有相當的市場。
從春秋開始,士人階層開始在中國的歷史舞臺嶄露頭角。這個階層由知識分子、游俠組成。他們沒有官職和權力也沒有封地,他們唯一的生存手段就是給士大夫們做客卿。當秦統一六國奪走了士大夫的權力和封地,士人階層就喪失了賴以生存的靠山,當時一些儒者和游士仍有復辟封建貴族的割據思想,他們常認為“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并引證《詩》、《書》、百家語,“以古非今”。丞相李斯認為,再不禁止,“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于是建議秦始皇推行焚書坑儒政策。士人階層遂成為秦朝誓不兩立的仇敵。九百名戍卒“斬木為兵,揭竿為旗”,攻取大澤鄉后,士人階層第一時間跳出來響應。當六國舊貴族加入起義之后,士人階層終于恢復了往日的活躍。他們紛紛投靠這些舊貴族,士人階層的投靠給了義軍貴族階層強大的人才保障。
一支軍隊的作戰能力不是只以兵員數量作為衡量的,六國的舊貴族及其舊部在作戰能力上有著質量上的和素質上的優勢,士人階層又給他們增加了智慧的力量。雖然“車六七百乘,騎千余”比起“卒數萬人”是少數,但是騎兵和戰車的強大戰斗力再加上智慧的力上加力,以六國的舊貴族為首的貴族階層必然成為起義軍的主要力量。
二、“農民軍”的將領
起義軍在陳建立政權后,陳勝以陳為中心,向秦王朝發動總攻。陳勝派武臣、張耳、陳余北徇趙地,魏人周市略魏地,鄧宗徇九江;主力則兵分三路,目標直指秦王朝的巢穴——咸陽:一路由吳廣帶領進攻滎陽;二路由宋留率領迂回南陽扣武關;三路由周文率領,進攻漢中。這些人是起義軍的重要將領,他們的出身必定影響他們的政治立場及政治利益,從而決定起義軍的性質,因此我們有必要分析這些起義軍將領的出身:
武臣,陳人,陳勝“故所善”③之人,應該九百名戍卒之一,出身于農民。
張耳,大梁人,年輕時“及魏公子毋忌為客”,后來亡命至外黃,并且娶了當地一個富家守寡的女兒,“女家厚奉給張耳”,還作過官。由此可以判斷出張耳以前比較富裕,有一定的學識和能力。做過客卿和官說明他屬于士人階層。
陳余,大梁人,“好儒術”,因為有一定的才能,“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
周市,魏人,陳勝曾欲立他為魏王,他婉言謝絕,并前后五次迎接寧陵君到魏做魏王。周市說:“天下昏亂,忠臣乃見,天下共畔秦,其義必里立魏王后乃可。”堅決不做魏王并且能夠說出一番大義,周市也應該出身于士人階層。
周文,“陳之賢人也”。曾經在項燕的軍隊里當占卜的文職官員,并“事春申君”④出身于士人階層。各地響應起義的主要將領:
項梁、項羽,項家“世楚將,封于項,故姓項氏”。劉邦,“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吏,為泗上亭長。”由此可以判斷出其出身決不是農民,也應屬于士人階層。
張良,其祖父與父親都是韓國的大臣,是韓國的貴族。
可以看出起義軍將領當中至少一半是屬于士人階層的;而士人階層是站在貴族的政治立場上,他們與農民階級有著完全不同的目的和方向;武臣在張耳、陳余的勸說下自立為趙王,周市立魏咎為魏王,田自立為齊王證明了這一點。而其他響應者當中勢力較大的基本上都是貴族武裝。例如:代表楚地勢力的項梁、項羽。在這種情況之下,農民階級勢必被貴族階層所排擠,逐漸失去其影響力。因此起義軍的性質不可能是農民為主體的起義軍,最高領導權也一定不在農民階級的代表陳勝手中。
三、舊貴族的“棋子”——陳涉
陳涉、吳廣揭竿而起的時候,大小舊貴族、士人、官吏等名義上是響應陳勝吳廣起義,實際卻是利用這一大好時機為恢復并擴大自己曾經的利益而戰。在起義的初始階段,舊貴族的目標還能與農民階級的目標相一致——為了“伐無道、誅暴秦”。但隨著反秦運動的不斷發展,舊貴族的目標與農民階級的目標開始相左。起義軍打到陳的時候,陳勝要稱王,而張耳、陳余明確提出反對并且提出應首先恢復六國舊貴族的利益。在講了一番道理后又說了一句有警告意味的話,“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從這些話中可見包括士人在內的貴族階層對陳涉稱王的不滿。武臣占據邯鄲以后,張耳、陳余挑撥他與陳涉的關系并慫恿其自立為趙王;韓廣掠取燕地在燕地貴族慫恿下自立為燕王,他們不再聽從陳涉的號令,任其自生自滅。
陳涉很清楚自己的處境。葛嬰因為錯立了襄疆為王而被陳涉所殺。目的只有一個——維護他的王權的完整性,不允許出現別的干擾。任命朱房、胡武這些人監察眾將,目的很明確——是讓朱房、胡武等人幫他辨別眾將是否對他忠心,這也是為了維護他的王權。他要牢牢地控制他得來的權力。
大澤鄉的起義給了舊貴族復辟的希望。利用其革命首倡者的威望打擊秦朝,借此來達到恢復自己權力的目的。從上面的論述中我們可以分析出起義的領導權與控制權一直牢牢掌握在舊貴族的手中。六國的舊貴族從沒有把農民階級的代表陳涉奉為最高統帥。他們只是在利用陳涉,利用這次起義。向西攻秦的軍隊被章邯各個擊破,吳廣被自己的部將田臧殺死,陳涉甚至連斥責的勇氣都沒有,隨后自己也死在車夫莊賈的手里。
四、結論
秦政府在統一六國后,為了徹底鏟除六國舊勢力,采取高壓統治。秦統一六國時不具備當年秦國那樣的變法環境。自然引起天下各階層的強烈反感;公元前209年,陳勝、吳廣帶領900名戍卒在大澤鄉揭竿而起,開始了反秦大起義的序幕。六國舊貴族、士人階層、官吏、農民,各階層反秦人士紛紛“贏糧而景從”;六國舊貴族依靠其較強的作戰力、號召力和與士人階層的特殊關系,成為起義軍的主導力量,并實際掌握了起義的領導權。貴族階層利用民眾普遍對秦統一六國前政治秩序的懷戀,成功的進行了復辟。綜上所述,筆者認為這場對后世有著深遠意義的大起義是由農民起義引發的,以貴族為主導的,各階層人民復辟戰國分封制的大起義。在這次以貴族為主導的各階層人民大起義中,陳涉、吳廣所領導的農民起義是這個大起義的序幕。它就像一枚引爆了重鎊炸彈的雷管,而真正產生巨大沖擊波的是那根雷管后面的東西。
注釋:
①司馬遷.《史記·陳涉世家》.中華書局,1982年11月第二版(以下為相同版本),1952頁.
②司馬遷.《史記·陳涉世家》.1952頁.
③司馬遷.《史記·張耳陳余列傳》.2573頁.
④司馬遷.《史記·陳涉世家》.195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