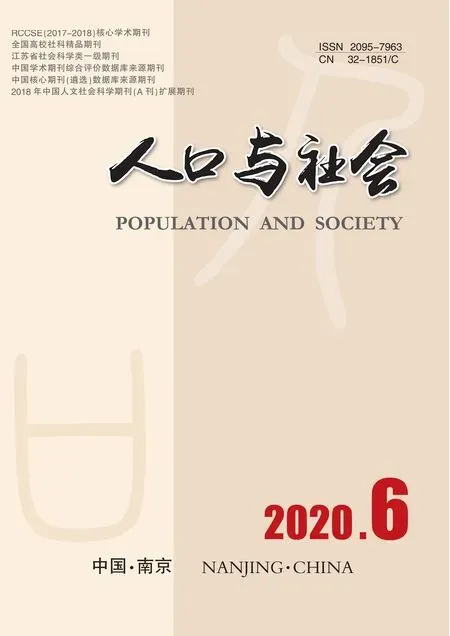自有住房流動人口的健康狀況及其影響因素分析
——基于2017年湖北省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數據
尚 越,石智雷
(1.江漢大學 商學院,武漢 430056;2.江漢大學 武漢城市圈制造業發展研究中心, 武漢 430056;3.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武漢 430073)
一、問題的提出
改革開放四十余年,我國經歷了快速的社會轉型,2019年末城市化率上升到60.60%,比2018年末提高1.02個百分點[1]。農村勞動力的鄉城流動是城市化的重要推力,也是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而能夠維持較好的健康狀況是農村勞動力鄉城流動的基本條件[2]。然而,社會轉型期人們生活行為方式的變化給人口健康帶來了嚴峻挑戰。目前我國有2.36億流動人口,他們的健康關系到其能否持續在城市務工,也關系到城市化能否順利推進。俗話說“安居才能樂業”,擁有穩定舒適的住房是生活美滿的必要條件,良好的住房環境是流動人口融入城市生活的重要途徑,也是有序推進農民工市民化的前提之一。因此,討論自有住房流動人口健康狀況及其影響因素是促進流動人口發展、助力健康中國行動中需要研究的重要問題。
居住狀況是影響流動人口健康的重要因素,但關于影響效應的已有研究結論并不統一。有研究利用上海市抽樣調查數據發現,自有住房流動人口自評健康狀況較差、慢性病患病率較高[3]。更多研究得出了與此相反的結論:基于區域流動人口數據的多項研究發現,“群居”是流動人口的居住常態[4],這對其健康狀況存在不利影響[5],而住房條件改善能夠顯著促進健康狀況[6];梁櫻等基于全國勞動力數據的研究也得到類似結論,并強調不良居住環境強化了生活壓力對流動人口心理健康的負面影響[7]。國外研究也基本一致認為居住狀況會影響勞動力健康。不良居住狀況與呼吸類傳染病的傳播蔓延相關[8],改善住房環境能夠顯著降低上述傳染病的發病率[9]。在心理健康方面,不良居住狀況會引發焦慮、煩躁和抑郁,甚至導致越軌性行為或社會隔離[10]。
流動人口健康影響因素的研究大多基于健康經濟學理論框架展開,建立在健康需求理論之上,認為健康人力資本既是消費品也是投資品:作為消費品直接進入消費者效用函數,提高消費者效用;作為投資品增加投資者工作和閑暇的總時間,通過影響收入間接提高投資者效用。在影響健康的諸多因素中,社會因素對于健康的影響遠超過醫學技術[11],其中社會經濟地位更是學者們的關注焦點。住房是個人社會關系和經濟地位的空間呈現,同時社會經濟地位能夠通過一系列中間變量的交互機制影響健康狀況[12]。遺憾的是,現有研究僅籠統地討論了流動人口健康影響因素,鮮有關于不同住房類型流動人口健康影響因素的研究。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已有研究已經證實居住狀況對人口健康的影響,但缺乏針對流動人口的大規模調查數據,多為利用區域抽樣調查數據進行的研究。更重要是的,已有研究沒有關注自有住房流動人口這一具有鮮明特征的群體,也沒有對相關因素對其健康狀況的影響及其內在機制給出理論和經驗解釋。和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文在充分考慮自有住房流動人口特殊性的基礎上,利用2017年湖北省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數據,對自有住房流動人口特征和健康狀況進行描述,并利用Logit回歸分析相關因素的影響效應及其內在機制。
二、研究設計與實證策略
(一)研究設計
本文試圖考察自有住房流動人口的健康狀況,解釋相關因素的影響效應及其作用機制。為此,首先根據流動人口居住房屋的性質判斷其是否為自有住房流動人口。要考察自有住房流動人口健康的影響因素,必須進行流動人口健康指標的選擇,結合問卷信息,最終選取了自評健康、慢性病患病和急性傷病患病三個維度進行評價。
自有住房流動人口居住隔離較弱,社會融合更深,社會經濟地位更高,從而對自身健康狀況的主觀評價和期望更高。另一方面,自有住房流動人口收入相對較高,生活行為方式可能更為不健康,如生活不規律、缺乏運動、肉食性膳食、吸煙或過度飲酒,最終會增加慢性病患病風險。與此同時,自有住房流動人口不必面臨“群居”的窘境,避免了人員擁擠、通風采光差、潮濕陰暗和噪聲污染,居住環境相對安全、寬敞,公共設施更加齊全,這將減少其急性傷病的患病風險。
(二)數據說明
本文所使用的數據來源于原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開展的2017年全國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選取了其中流入地為湖北省的流動人口數據。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采用分層、多階段與規模成比例抽樣方法,抽樣范圍覆蓋湖北省內的14個省轄市和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湖北省調查的總樣本量為5 000,調查對象為截至2017年4月年齡為15周歲及以上、在本地居住一個月及以上、非本區(縣、市)戶口的流動人口。調查內容主要包括流動人口的家庭成員情況與家庭收支情況、就業情況、流動及居留意愿、健康與公共服務等方面。
在詢問被訪者住房性質時,備選項包括“單位/雇主房”“租住私房(整租)”“租住私房(合租)”“政府提供公租房”“自購商品房”“自購保障性住房”“自購小產權住房”“借住房”“就業場所”“自建房”以及“其他非正規居所”。本文關注的是自有住房流動人口的健康狀況及其影響因素,為此對上述住房性質進行劃分,將“自購商品房”“自購保障性住房”“自購小產權住房”以及“自建房”均視為自有住房。在剔除關鍵變量缺失樣本后,最終本文有效樣本為4 987個,其中自有住房流動人口樣本1 816個。上述變量描述如表1所示。

表1 變量描述

續表1
(三) 實證策略
為了考察自有住房流動人口健康的影響因素,本文使用Logit回歸模型來估計,回歸方程設定如下:

式中ln(Pi/Pj)表示第i類健康狀況和第j類健康狀況發生比的自然對數,分別從自評健康、患慢性病和患急性傷病三個維度來體現。xk表示解釋變量,分別為人口學特征、流動特征、就業特征以及影響健康的普遍因素,包括年齡、性別、婚姻狀況、受教育程度、子女個數、就業身份、居留意愿、流動范圍、流動原因、醫療保障和家庭收入情況。αi和βik表示第i類的截距項和解釋變量參數。在詢問被訪者自評健康狀況時,將回答身體“健康”以及“基本健康”的視為自評健康并賦值為1,否則賦值為0。本文通過詢問被訪者“是否患有已被確診的高血壓和糖尿病”“最近一年是否出現過腹瀉、發熱、皮疹、黃疸、結膜紅腫或感冒”以及“最近兩周是否有患病(負傷)或身體不適的情況”,分別測度流動人口患慢性病、急性病以及急性傷痛的情況。將患有一種及以上慢性病的流動人口視為患有慢性病并賦值為1,否則賦值為0;將患有一種及以上急性病以及患病(負傷)或身體不適的流動人口視為患有急性傷病并賦值為1,否則賦值為0。
三、自有住房流動人口特征與健康狀況
(一)自有住房流動人口的特征
表1報告了不同住房類型流動人口特征。自有住房流動人口中女性略多于男性,性別比為90.67%,初婚比例略高于無自有住房流動人口。從年齡分布來看,自有住房流動人口中中青年占比略低,超過95.8%的為60歲以下勞動人口,而無自有住房流動人口的這一比例為98.4%。自有住房流動人口受教育程度普遍較高,超過22.8%的自有住房流動人口受過高等教育,是無自有住房流動人口的兩倍多。從子女個數來看,超過半數自有住房流動人口有一孩,略高于無自有住房流動人口,同時多子女比例略低。總的來說,自有住房流動人口呈現出女性更多、更年長、文化程度更高、子女更少的特征。
不同住房類型流動人口的流動特征差異顯著,42.6%的自有住房流動人口市內跨縣流動,只有29.8%的無自有住房流動人口是市內跨縣流動;有42.8%的無自有住房流動人口流動原因為經商,而這一比例在自有住房流動人口中僅為24.6%;超過九成的自有住房流動人口打算繼續在本地居住,這一比例在無自有住房流動人口中略低,為81.7%;自有住房流動人口為有固定雇主的雇員的比例較高(32.1%),無工作的比例也較高(24.2%),而自營勞動者占比較低(30.7%)。這意味著自有住房流動人口更多是短距離流動,他們與雇主有穩定勞動關系或為無業人員,有強烈的本地居留意愿;而無自有住房流動人口多為經商進行跨市或跨省流動,因此自營勞動者占比較高,本地居留意愿相對弱。
在影響健康的普遍因素上,不同住房類型流動人口也存在差異。有超過24.5%的自有住房流動人口參加了城鎮職工醫保,這一比例是無自有住房流動人口的3倍多;不足半數的自有住房流動人口參加了新農合,但有73.9%的無自有住房流動人口被新農合覆蓋;同時自有住房流動人口未被保險覆蓋的比例較低。另外,自有住房流動人口家庭月均收入相對更高。可見,自有住房流動人口的醫療保障和家庭收入水平都更高。
(二)自有住房流動人口的健康狀況
不同住房類型流動人口的健康狀況存在差異,表2呈現了相關結果。總體上看,分別有2.97%、5.90%以及69.82%的自有住房流動人口自評不健康(1)此處“自評不健康”包括表中“自評不健康”和“自評生活不能自理”兩類主觀評價身體不健康的被訪者。、患慢性病或急性傷病。與無自有住房流動人口相比,自有住房流動人口自評不健康、患慢性病以及患急性傷病的比例均更高,其中在患高血壓和急性傷病上存在顯著差異。自有住房流動人口相對更年長、文化程度更高,他們可能在市內謀得一份有穩定勞動關系的工作,收入相對穩定,而且其中隨遷的女性家屬沒有工作壓力。這部分流動人口社會融入感更強,社會經濟地位更高,但由于體力勞動強度下降,日常膳食中脂肪供能較高,逐漸形成不健康的生活行為方式,直接增加慢性病患病風險[13]。較高的家庭收入增強了自有住房流動人口醫療可及性和支付能力,相比無自有住房流動人口,他們能夠更及時就醫處理急性傷病,由此表現出較高的急性傷病患病風險。

表2 不同住房類型流動人口的健康差異 %

續表2
四、自有住房流動人口健康影響因素分析
自有住房流動人口健康影響因素的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總的來說,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流動原因、就業狀態、居留意愿和家庭收入水平均顯著影響了自有住房流動人口的健康狀況。

表3 自有住房流動人口健康影響因素分析(N=1 816)

續表3
(一)人口學特征與自有住房流動人口健康
從人口學特征來看,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顯著影響自有住房流動人口健康狀況,婚姻狀態和子女個數的影響不顯著。相比于女性自有住房流動人口,男性慢性病患病風險顯著增加43.6%,急性傷病患病風險則顯著下降29.6%。隨著年齡的增加,自有住房流動人口各維度健康狀況逐漸惡化,自評不健康、患慢性病和急性傷病的概率分別顯著增加5.5%、10.4%以及1.5%。受教育程度影響了自有住房流動人口的健康自評,與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自有住房流動人口相比,大學畢業自有住房流動人口自評不健康的概率顯著下降了43.2%,但受教育程度對慢性病和急性傷病的患病風險并未產生顯著影響。教育本應通過影響個體的健康認知和健康行為進而提升健康人力資本的生產和配置效率[14],但或許潛在的不健康生活行為方式抵消了自有住房流動人口在防范患病風險上的優勢。
(二)流動特征與自有住房流動人口健康
流動特征對自有住房流動人口的自評健康產生了顯著影響,但并未影響慢性病和急性傷病的患病風險。相比務工的自有住房流動人口,因其他原因流動的自有住房流動人口自評不健康的概率顯著增加了52.6%。流動人口動態監測進一步詢問了“其他流動原因”的具體內容,對自有住房流動人口來說,占比排在前三的原因分別是照顧自家小孩、婚姻以及投親靠友。這意味著,其他流動原因的自有住房流動人口并沒有因為在城市擁有自有住房而提高健康狀況的主觀評價,他們更像是被動甚至被迫流動,社會經濟地位并沒有顯著提高。另一方面,相比沒有打算繼續居住本地的自有住房流動人口來說,有長期居留意愿的自有住房流動人口自評不健康的概率顯著下降34.4%。這些沒有長期居留意愿的自有住房流動人口很可能對現有生活狀態不滿或是近期遭遇變故,才導致今后一段時間可能繼續流動到其他地區,因此他們的主觀健康狀況評價較差,但客觀患病風險并未顯著增加。
(三)就業特征與自有住房流動人口健康
就業特征顯著影響了自有住房流動人口健康自評和急性病患病的概率。相比有固定雇主的雇員,無固定雇主的雇員和無工作的自有住房流動人口自評不健康的概率分別顯著上升了125.8%和38.4%。這說明穩定的勞動關系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提高流動人口的社會經濟地位。與此相反的是,對失業風險的擔憂增加了流動人口的社會隔離,并進一步導致其對自身健康狀況的主觀評價降低。而雇主、自營勞動者和無工作的自有住房流動人口急性病患病風險分別顯著下降了50.5%、35.7%和34.8%。可能是由于雇主和自營勞動者能夠自主選擇工作場所,避免在潮濕陰暗和有噪聲污染的環境下工作,這種干凈安全的工作環境減少了其急性傷病的患病風險,暫時無工作的流動人口更是如此。
(四)影響健康的普遍因素與自有住房流動人口健康
在影響健康的普遍因素中,醫療保險并未對自有住房流動人口的健康狀況產生顯著影響;但隨著家庭平均收入的增加,自有住房流動人口急性傷病患病風險顯著增加了18.9%。醫療保險本應該通過提高醫療可及性、形成健康行為生活方式和降低預防性儲蓄改善健康狀況[15],從回歸結果上看也確實降低了自有住房流動人口自評不健康、慢性病和急性傷病的患病風險,但影響均不顯著。家庭收入的增加使得自有住房流動人口能夠提高健康投資的預算[16],但同時由于行為生活方式的改變增加了他們患慢性病的風險,兩種效應疊加后回歸結果顯示為影響不顯著。對急性傷病患病風險的影響可能是因為較高的收入導致醫療可及性和支付能力的提高,急性傷病發生后能夠及時就醫。
五、結論與討論
不同住房類型流動人口存在怎樣的健康差異?相關因素對自有住房流動人口健康的影響效應和內在機制如何?這是十分重要但較少被關注的學術話題。本文基于2017年湖北省流動人口動態監測數據以及Logit回歸模型實證分析了上述問題。研究發現,從人口學特征、流動特征、就業特征和影響健康的普遍因素來看,自有住房流動人口具有鮮明特征,他們是介于城鎮居民和傳統流動人口之間一個更年長、文化程度更高、子女更少的群體。他們往往短距離流動,從事有穩定的勞動雇傭關系的工作或無業在家,有強烈的長期居留意愿,醫療保障和家庭收入水平更高。正是基于以上特征,與無自有住房流動人口相比,自有住房流動人口自評不健康、慢性病患病以及急性傷病患病比例均更高。進一步Logit回歸結果顯示,性別、年齡、受教育程度、流動原因、就業狀態、居留意愿和家庭收入水平顯著影響自有住房流動人口的健康狀況。其中,男性的慢性病患病風險較高,但急性傷病患病風險較低;隨著年齡的增加,各維度健康狀況逐漸惡化;大學文化程度的自有住房流動人口自評健康狀況更好;除經商、務工以及家屬隨遷外因其他原因流動的自有住房流動人口自評健康狀況較差;有長期居留意愿的自評健康狀況較好;無固定雇主的和無工作的自評健康狀況較差。
《健康中國行動2019—2030年》強調“共建共享、全民健康”,要將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在“健康中國”戰略下,如何促進流動人口健康,助力健康中國行動是一個亟待解決的難題。在影響健康的諸多因素中,社會經濟地位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就本文實證分析結果來看,對流動人口而言,要通過提高其社會經濟地位促進健康狀況。針對性的政策建議包括:減少居住隔離以增加流動人口的社會融入程度,提高流動人口的健康主觀評價和期望;提倡健康膳食模式,形成健康行為生活方式;針對性改善就業環境和勞動條件,鼓勵雇傭單位簽訂長期勞動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