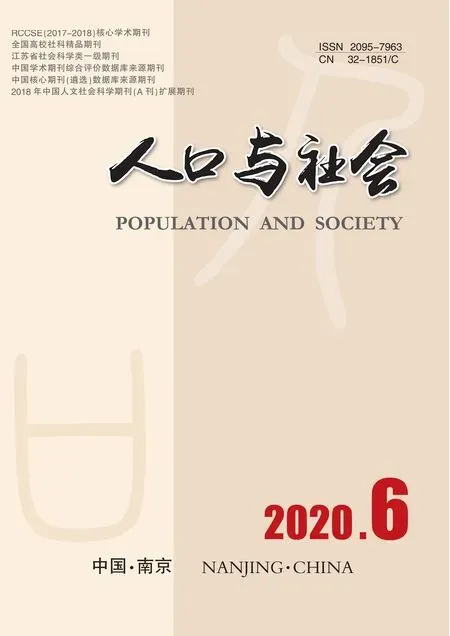中國居民幸福感的時代變化
——基于世代再分析
劉洋洋,王俊秀
(1.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 社會學院,北京102488;2.中國社會科學院 社會學研究所,北京100732)
幸福感是對社會福利最終結果的測量[1],改革開放四十余年,中國經濟迅速發展,隨著人們生活質量的改善,我國居民的幸福感提升了嗎?本文利用CGSS2005、2010和2015年全國調查數據,從人口更替的視角重新審視十年間人們幸福感的變化情況。
一、文獻回顧與問題提出
(一)文獻回顧
主觀幸福感既反映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也體現人們的精神滿足感,是衡量人們生活質量的重要綜合性心理指標, 包括生活滿意程度、積極情緒體驗與消極情緒體驗等因素, 具有主觀性、整體性和穩定性的特點[2],是能夠全面衡量個人的生活滿意度及其福利水平的綜合指標。關于幸福感變遷的研究,有較大影響力的是美國經濟學家伊斯特林提出的論點。伊斯特林對美國居民進行實證研究后發現幸福感并不會隨著經濟的增長而增長,即使人均收入呈增長趨勢,但一個社會的平均幸福水平是恒定不變的,這就是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論”[3],大量研究證實了這一論點[4-6],也受到了諸多挑戰[7]。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很多國家民眾的幸福感一直在上升[8],一些國家的相關數據也顯示,收入和幸福感之間存在穩健的正向關系[9-10]。
一些學者認為“伊斯特林悖論”在中國同樣存在。有研究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并不意味著國民幸福水平同步提高[11];有研究認為與絕對收入相比,相對收入對幸福感的影響更大,引入相對效用理論可以更好地解釋“伊斯特林悖論”[12];有學者認為高收入并不會帶來更大的幸福感,因為物質欲望會隨著收入的增加而增加[13];伊斯特林研究發現,近二十年中國的人均產出顯著增長,但幸福感卻呈現U型曲線變化,1990—2005年間趨于下降,2005年以后緩慢回升。還有學者認為經濟轉型發展使得人們的收入差距增大,部分低收入人群的幸福感下降了,所以經濟增長并不意味幸福感提升[14];邢占軍分析了山東省居民2002—2008年的相關數據,發現人們的幸福感并沒有隨人均GDP和居民收入增加而相應增長[15];朱建芳、楊曉蘭利用世界價值觀調查數據發現,中國人1999—2001年間的幸福感平均值有所下降,因為雖然中國經濟水平不斷提升,但是各種差距同樣在急劇增大[16];還有學者認為失業率的增加和社會保障體系的弱化,會導致居民生活滿意度下降[17]。
但也有學者認為中國居民的幸福感在逐步提高,并不存在明顯的“伊斯特林悖論”。劉軍強等認為在控制性別、年齡、城鄉、收入、教育、社會地位等因素后,國民幸福感仍呈上升趨勢[18];李婷基于CGSS 2003—2013年的數據進行分析,認為受經濟發展的推動,我國居民的總體幸福感在近十年內呈現單調上升的態勢,且人均GDP增長是人們幸福感提升的重要影響因素[19];零點調查公司經過調查發現,2000—2009年城鄉居民的生活滿意度基本呈上升趨勢,中國公民的幸福感隨著經濟發展和收入增加而上升[20];世界幸福感數據庫數據也顯示,2001—2012年間中國公民的幸福感有所提升[21-22]。
(二)問題的提出
針對我國居民幸福感變化的研究結論不同,而伊斯特林后期也對其提出的“伊斯特林悖論”進行了修正,認為短期內幸福感可能會與經濟走勢相關[23]。通過文獻回顧,我們發現認為幸福感提升與經濟發展沒有顯著關系的研究大多基于調查時間較短或者局部地區的樣本,可能存在代表性不強以及觀察時期過短的缺陷,而利用全國性、時間跨度較大的重復調查數據進行研究,則發現中國居民幸福感是波動上升的。基于已有文獻和所使用數據,我們提出假設:
假設1:中國居民十年來的幸福感呈上升趨勢。
雖然關于我國居民幸福感變化的研究較多,但是以往研究忽視了人口出生世代更替對社會整體主觀情感結構和變遷的影響。世代可以定義為在相同時間間隔內經歷相同事件的個體的集合[24],而出生世代則是出生在同一時期的群體,比如我們常說的“80后”“90后”。
卡爾·曼海姆和諾曼·萊德都認為,世代在生命的早期發展出特有的世界觀定義,而這些看法似乎將持續人們的整個成年期,年齡較大的人比年輕人更堅持自己原來的看法,因此社會自身的變遷更容易影響年輕人的價值觀。而且隨著受教育內容的變化、同齡人的社會化以及特殊的歷史經驗的影響,每一個出生世代的成員組成及其特征都具有獨特性,反映了其獨特的成長和生活環境,這導致了社會成員之間的主觀情感及社會態度存在差異[25]。
當年長的出生世代被年輕世代所取代,世代的“特有的世界觀定義”就會發生變化,并引起社會情感、社會態度等發生結構性變遷。這也解釋了孔德強調的“我們的社會過程依賴于人們的死亡”[26]。相關變化的動力來自“人口新陳代謝”的雙過程——持續的年長世代的逝去和年輕世代的加入[27]。不同出生世代的成員經歷的不同社會環境使他們擁有不同的主觀情感和社會價值觀,形成獨特的“世代效應”。
因此,人們的社會態度和價值觀的變化有可能源于社會總人口出生世代的更替。即使某個特定群體的主觀情感靜止不變,但隨著出生世代的后延,整個社會群體的主觀情感仍舊會出現結構性變化。如果世代內的相關變化與總體變化保持一致,那我們就可以推論,社會變遷源于個人變化的凈效應(時期效應);但是如果出生世代內成員的某種主觀情感并沒有隨著時間而發生明顯變化,我們就可以推論說,總的變化實際是由人口更替造成的(世代效應)。當然更常見的情況是時期效應和世代效應共同造成了人們社會態度和價值觀的變化。
幸福感常常通過情緒和社會認知來對個體進行測量[28]。人們的幸福感會受到人格特質的影響,性情論就持有該觀點,強調人的遺傳、生物因素和人類進化過程中先天性情的作用。還有另一種視角是情境論,認為個體的幸福感取決于環境[29],該論點已經得到了大量的研究論證[30-31]。波爾提出人是關系性存在的“人際與社會模型”[32],認為人們的幸福感依存于情境,社會環境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人們的幸福感。Diener等人也認為幸福感需要人格和環境相結合才能產生,環境是塑造人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33]。不同出生世代的成員所處社會環境的不同會導致他們的幸福感存在差異,這在我國尤為明顯。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不同的社會政策塑造了不同出生世代的“公共生命歷程”[34]。每一代人都經歷了獨有的歷史過程,其面臨的大環境及政策差異可能導致不同世代幸福感的差異。隨著人口出生世代的逐步后延,整個社會群體的幸福感不僅隨著時間變化,也隨著人口結構的更替發生改變。因此幸福感與社會環境的依存關系為世代更替效應提供了理想的研究視域。我國居民幸福感總體變化趨勢是否受到社會環境的影響,有沒有摻雜人口更替效應,此方面研究還很少。基于上述相關理論,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設:
假設2:由于所處歷史過程及社會環境的差異性,不同出生世代居民的幸福感及幸福感的變化情況存在差異;
假設3:幸福感的變化不單純是個體幸福感的變化所造成的,社會成員的出生世代更替也是導致幸福感總趨勢變化的原因。
二、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一)數據來源與變量
本文利用CGSS2005、2010和2015年三期全國性調查數據,構造跨度為十年的重復調查數據。本文的因變量是我國居民的幸福感。其中2005年的問卷問題是:“總體而言,您對自己所過生活的感覺是怎樣的呢?您感覺您的生活是?”2010和2015年的問題是:“總的來說,您認為您的生活是否幸福?”,三期調查數據的問題具有一致性。問卷回答為1~5賦分,得分越高,幸福感越高。本文主要目的是分析時期效應(個體幸福感變化)和人口更替效應(世代間的幸福感差異),因此核心自變量是調查年份和出生世代。為了保證模型的穩定性,本文剔除了樣本量過少的出生世代,最終獲得樣本量31 579個,包含出生于1930—1997年、年齡在18~85歲的樣本。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沒有包含其他人口或社會經濟變量,因為與幸福感相關的因素在年長世代和年輕世代中是有區別的,加入這些變量可能會干擾世代更替作用[35]。比如不同世代的受教育水平差異較大,而這種差異可能就是導致不同世代幸福感差距較大的原因之一,因此在模型中加入受教育程度變量會改變世代更替的總效應值。(1)實際上在加入性別、戶籍、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社會地位、地區等因素后,世代系數有顯著改變。本文關注的核心是人口更替和時間發展對居民幸福感變化的作用,而無意解釋其背后機制,因此后續分析中沒有納入其他影響幸福感的變量。
(二)分析方法
1.代數分解
將社會情感發生變化的原因分解為世代更替和世代內改變兩部分,常用的有兩種方法。一種是代數分解方法,另一種是基于回歸的線性分解方法。考慮到我國居民幸福感的變化趨勢,用P代表整體幸福感的平均值,Pj代表世代j的平均幸福水平,pij代表世代j中個體i的幸福感得分。給定重復截面數據的幸福感平均得分,如公式(1):
(1)
公式(1)即計算重復數據總體均值的標準計算方法。fj表示nj/N,即世代j的樣本量占總樣本量的比重。Pj通過fj進行加權,各個世代的加權平均值之和就是重復數據總樣本的幸福感平均得分。因此P是Pj和fj的函數,fj指的是世代更替所造成的變化,而Pj則指的是世代內(個體)的變化。Pj的變化與個體態度變化有關,而fj的變化與世代更替有關,是分解社會變遷趨勢的關鍵,當Pj或fj發生變化或者兩者同時發生變化時,總體幸福感均值P便會發生變化。
Kitagawa證實了可以用代數分解的方法將總體幸福感變化趨勢分為兩個部分,一個反映均值差異,另一個是組間構成[36]。對應到趨勢分析中,組間構成代表了世代更替效應,而均值差異則反映了世代內個體幸福感的變化。令P1和P2分別代表時點1和時點2的幸福感平均得分,那么根據公式(1),P從時點1到時點2的變化為:
P2-P1=∑jP2jf2j-∑jP1jf1j
(2)
進一步將公式(2)進行代數分解,可以變為:
(3)
其中P2j-P1j表示對世代j在時點1和時點2的樣本量加權平均后的時期效應,即幸福感變遷總趨勢中由個體幸福感變化引起的部分;f2j-f1j則表示對世代j在時點1和時點2的平均幸福感得分加權平均后的世代更替效應,即幸福感變遷總趨勢中由人口更替所導致的部分。將樣本中所有世代的時期效應和世代效應分別進行加總,以此獲得幸福感總體變化中世代和時期各自的效應值[37]。
2.線性分解
代數分解的方法簡單易行,但它得出的分析結果是一種粗略估計;其次,由于人口更替可能會導致一些世代退出或進入樣本,代數分解方法會錯誤地將這些世代的變化全部歸于世代效應,容易高估世代更替效應[38]。因為調查年份之間的間隔是定量間隔,Firebaugh提出了另外一種可行的分解方法——基于回歸的線性分解,將調查年份的出生世代作為變量納入模型,將出生年看成連續變量,而不需要合并成幾個世代大類,并用此方法分析了美國種族歧視現象減弱的過程中,個體態度改變和世代更替各自起到的作用。
線性分解第一步是利用回歸估計世代內的時期變化,這里假定世代內的斜率是線性和平行/疊加的,所以我們用以下方程來估計相關變化:
Yit=b0+b1YEAR+b2COHORT+e
(4)
其中Yit表示在第t次調查中第i個受訪者的幸福得分,b1是在控制了世代變量后,不同調查年份我國居民幸福感的變化(即個體幸福感的變化);b2是在控制了調查年份之后,我國居民幸福感在不同世代間的差異(世代更替作用)。
線性分解的第二步是利用公式(4)中的斜率來估計不同調查年份中世代內的改變和世代更替對總體幸福感變遷的貢獻。因為b1估計的是每一調查年份中世代內的改變(時期效應),為了估計其對居民幸福感變遷的總體貢獻,我們需要將b1乘以第一次調查年份到最后一次調查年份的間隔年數:
估計時期效應=b1(YRt-YR1)
(5)
其中YRt是最后一次調查年份的幸福感均值得分,YR1是第一次調查年份的幸福感均值得分。同樣為了估計世代更替的貢獻(世代效應),我們把b2乘以從調查年份1到調查年份t之間樣本出生年的均值改變:
估計世代效應=b2(Ct-C1)
(6)
其中Ct是最后一年調查樣本中的平均出生年,C1是第一次調查樣本中的平均出生年。由于方程中誤差的存在,這兩部分加起來不會恰好等于總變化,但差別不大。如果差別很大,則“線性-疊加”假設就有問題,我們只能夠采用代數分解方法而非線性分解方法。(2)方程(5)和(6)兩部分相加等于總的社會變遷的證明請參見格倫·菲爾鮑《分析重復調查數據》。
三、分析結果
要研究世代更替對人們幸福感變遷的影響,首先要確保調查數據具有人口更替性質,即不同世代的樣本在總樣本中的比例會因為人口出生和死亡的影響而不斷變化,且不同世代之間的幸福感具有差異[39]。表1展示了三期調查數據的出生世代變動情況。在間隔十年的調查數據中,除了“40后”群體在三次調查中的比例沒有顯著變化外,其余出生世代的比例都有明顯變化。其中1930、1950、1960、1970年代出生的人口所占比例顯著下降,而“80后”“90后”的比例則顯著提升,且“90后”所占比重提升了8.71%。CGSS跨度10年的數據表現出了明顯的世代更替現象,因此符合分解世代效應的數據條件。

表1 CGSS2005—2015年調查數據人口出生世代構成及變化 %
(一)幸福感總體變化趨勢
圖1展示了十年來我國居民幸福感的平均得分及回歸趨勢線,可見我國居民幸福感一直處于上升趨勢,這與一些使用全國性、跨度較長數據的研究結論相似,同時初步驗證了我們的假設1。但需要注意的是,我國居民2005—2010年幸福感的增長速度明顯高于2010—2015年,前五年我國居民幸福感提升了0.36分,而后五年僅提升了0.1分,提升速度明顯放緩。

注:實線表示幸福感均值得分;虛線為擬合回歸線
(二)不同出生世代的幸福感構成
那么不同出生世代的幸福感是否存在差異呢?我們首先通過世代表加以分析。世代表中將世代作為行變量,代表了個體幸福感的真實變化,而行與行之間的差異則來源于世代差異。表2展示了不同出生世代的幸福感構成,可見各個出生世代不幸福、幸福感一般以及幸福的比例構成存在差異,其中1960年代出生的群體選擇不幸福的比例最高,選擇幸福的比例也最低;“80后”“90后”自認為幸福的比例明顯高于其他出生世代,且感覺不幸福的比例也最低。

表2 不同出生世代的幸福感構成 %
表3展示了不同出生世代幸福感的構成變化。首先,所有世代成員感到幸福的比例都有了明顯的增長,但感到不幸福的比例也沒有明顯下降。不僅2005—2010年間所有世代感到不幸福的比例都沒有顯著下降,且1960和1970年代出生的群體感到不幸福的比例分別提升了1.94%和1.95%;在2010—2015年間,僅有1940和1950年代出生的群體感到不幸福的比例有所下降,其余世代的幸福感則沒有顯著變化。從整體上看,2005—2010年間,居民感到不幸福的比例僅下降了0.57個百分點,且不具有統計顯著性,2010—2015年間下降的比例為2.13%。
各出生世代選擇幸福感一般的比例在2005—2010年間迅速下降,感到幸福的比例則大幅度提高,但2010—2015年間選擇幸福感一般的比例下降緩慢,而選擇幸福的比例上升幅度也均低于10個百分點。
其次,各個世代各項選擇比例的變化也具有差異性,其中1930、1940和1950年代出生的群體幸福感提升明顯,十年間選擇幸福的比例分別提升了32.98%、39.63%和36.01%,而1980年代出生群體選擇幸福的比例提升24.77%。“90后”在2010—2015年之間選擇幸福的比例僅提升2.34%,且不具有統計顯著性。不同世代幸福感比例結構及其變化存在的差異表明不同出生世代的幸福感比例結構變化,可能造成調查樣本的總體幸福感發生變化。

表3 不同出生世代幸福感構成變化 %
(三)不同世代幸福感的均值變化
通過世代表的幸福結構分解,可以得知不同世代幸福感的構成及變化存在明顯差異。為了進一步探索世代間的幸福感差異,我們將幸福感賦分1~5,計算不同世代的平均幸福感得分。圖2展示了不同出生世代成員幸福感平均得分的變化。從1930年出生的群體開始,隨著出生世代的后延,幸福感一直在緩慢下降, 1960年左右降到了最低值;之后幸福感隨著新的出生世代的加入開始較快提升。我國居民幸福感與出生世代間并不是單調的線性關系,而是先單調線性遞減,后又變成單調線性遞增。(3)本文亦對三期數據子樣本分別進行了分析,均得到與總體數據變化趨勢一致的結論。圖3則進一步展示了不同出生世代群體的幸福感變化情況。除了“90后”之外,其余世代群體的幸福感都呈現遞增趨勢,不過“90后”的幸福感均值明顯高于其他群體,“50后”“60后”以及“70后”的幸福感得分明顯低于其他出生世代群體。我們進一步對各出生世代之間的幸福感差異做方差分析,其中 F=61.57,P<0.001,總體上有顯著差異。除了“30后”與“40后”“30后”與“70后”“50后”和“60后”“40后”和“70后”群體之間沒有顯著差異外,其余出生世代的兩兩比較檢驗均有顯著的統計學差異。幸福感世代變化趨勢以及方差分析的結果同幸福感的世代表所得結果一致,再一次表明世代更替是影響人們幸福感變化的原因之一。
通過分析世代表和幸福感平均得分,假設2得到了驗證,即不同出生世代之間的幸福感構成及變化存在差異。雖然圖1顯示十年來我國居民整體的幸福感一直處于上升趨勢,但要確定幸福感整體的上升趨勢有多大成分是由世代更替所造成的,則必須將相關變化總趨勢加以分解。

圖2 不同出生年份群體的幸福感

圖3 各出生世代十年間的幸福感變化
(四)幸福感變化趨勢分解
由前文可知,不同世代的幸福感變化并非單調趨勢,這不符合線性分解的要求(線性和疊加性假設),因此我們首先使用代數分解方法,大致分解世代內成員幸福感變化和世代更替作用。其次由圖2觀測可知, 1960年之前出生群體的幸福感隨著世代后延而呈現線性下降趨勢,而之后的出生群體則隨著世代后延呈現線性上升趨勢,因此本文將總樣本一分為二,即1960年之前出生的群體作為一個子樣本,之后出生的群體作為另一個子樣本,分別進行線性分解。
1.代數分解
我們以10年為時間間隔標準,將總樣本劃分為1930、1940、1950、1960、1970、1980、1990七個出生世代,并通過公式(3)進行計算,得到公式(7):
(7)
公式中j表示七個世代。通過代數分解計算得出,我國居民整體幸福感從2005—2015年間提升了0.36分,其中因個人幸福感變化提升了0.3分,世代更替導致幸福感提升了0.06分。通過計算得知世代更替效應比重為0.167,即十年來世代更替效應為我國居民幸福感上升總趨勢貢獻了16.7%。
但如前文所述,代數分解的結果比較粗略,通過代數分解得出我國居民十年來的幸福感得分提高了0.36分,而通過計算2005年和2015年樣本的幸福感均值,得出十年來我國居民幸福感上升了0.45分。代數分解可能高估了世代更替作用,因此仍需要使用線性分解方法進行更精確的估計。
2.線性分解
本文采用線性回歸模型加以分析[40],并將OPROBIT模型的結果予以同時呈現,以驗證線性模型的穩定性。
表4呈現了基于回歸模型的線性分解趨勢,其中OLS結果與序次模型結果保持了一致性。為了利用線性分解方法,我們對OLS回歸模型結果做進一步分析。首先看總模型,在控制了世代差異后,我國居民幸福感隨著年份的增加而提升,這進一步驗證了我們的假設1,即近十年來我國居民幸福感總體上呈上升趨勢;在控制了年份后,隨著世代的后延,幸福感越強。但從不同世代幸福感得分趨勢圖可知,人們幸福感的變化與世代并非單調關系,因此總樣本的結論只是表明世代更替整體上與幸福感為正相關關系,但幸福感與世代間仍有細微的結構關系。因為幸福感隨著世代變化呈現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趨勢,我們在模型中加入世代的二次項,通過模型計算可知,趨勢拐點出現在1959.46年,這也表明把1960年作為兩個子樣本劃分界限的適宜性。1960年以前的出生世代中,幸福感與世代呈現顯著的負向關系,即隨著出生年份的后延,人們的幸福感逐步下降;但1960年以后出生群體的幸福感與世代更替又呈現正向關系,出生越晚的群體幸福感也越強。總模型以及分樣本模型都證實了不同出生年份的群體幸福感存在顯著差異。調查年份的變動(個體幸福感的變化)和出生世代(世代更替效應)均在幸福感總的變化趨勢中發揮了作用。但我們仍然不清楚個體幸福感改變或世代更替效應哪一個更重要。

表4 線性分解趨勢
為了驗證這一點,我們利用公式(4)和公式(5)分別計算個體改變和世代更替作用,并將結果呈現在表5中。無論是總樣本還是子樣本,我們利用線性模型所計算得出的幸福感總體變化與幸福感十年的均值變化得分幾乎相同(均在98%以上),證明了線性分解在研究我國居民幸福感變化方面的適用性。

表5 居民幸福感變化分解表
具體看,總樣本中世代更替效應在人們幸福感上升過程中的貢獻為1.8%(0.008/0.008+0.45),因此世代更替對幸福感起到了一定的提升作用。我們知道幸福感與人們出生世代的關系并非單調線性關系,總樣本的分解可能會掩蓋真實的世代效應。首先看1960年以前出生的群體,其幸福感上升是個體變化所致,世代更替反而降低了幸福感。而1960年以后的出生世代中,世代更替效應在人們幸福感提升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也就是說出生世代越晚幸福感越高,隨著晚出生世代的樣本量逐漸增加,提高了總樣本的幸福感。
通過代數分解和線性分解,我們獲得了一致的結論。居民幸福感十年間的上升趨勢主要源于人們幸福感的真實提高,但世代更替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不過這種作用并不是連續的,因為世代更替其實降低了1960年代之前出生群體的幸福感,而1960年以后的出生世代,由于后出生世代的幸福感本身就高于前出生世代,因此隨著后出生世代樣本量的增加,幸福感也提高了。這就驗證了我們的假設3,即社會成員的出生世代更替的確會導致人們幸福感發生變化。
(五)城鄉居民幸福感的異質性分析
由于我國城鄉二元結構的社會慣性,使得在經濟轉型過程中,城鎮和農村居民在就業類型、社會保障以及福利分配等方面都存在諸多差異,這可能使得城鄉居民幸福感及其變動趨勢產生分化,因此我們也將樣本分為農村和城鎮兩個子樣本,以驗證兩個群體在幸福感變化方面的差異。由于線性分解比代數分解結果更為精確,且更具有穩定性,因此我們利用線性分解方法對城鄉模型予以分析,見表6和表7。
由表6可見,在1960年以前出生的群體中,城鎮居民十年來的幸福感增長速度明顯高于農村居民,然而1960年以后出生的群體中,城鎮居民幸福感增速卻低于農村居民,但差距非常小;從出生世代角度看,無論是城鎮還是農村居民,在1960年之前出生的群體中,隨著出生世代的后延,幸福感呈現下降的趨勢,在1960年以后的出生世代中均呈現出生越晚,幸福感越高的趨勢。由表7可見,1960年之前的出生世代中,世代更替效應對農村和城鎮居民幸福感的影響都不顯著;1960年以后的出生世代中,世代更替效應對農村居民和城鎮居民幸福感提升的貢獻相差不大,這與總樣本的結論保持了較高的一致性。盡管城鄉經濟發展存在差異,然而在解釋居民幸福感變化趨勢方面,世代更替效應沒有明顯的城鄉差異。

表6 城鄉居民幸福感線性分解趨勢(OLS分析)

表7 城鄉居民幸福感變化分解表
四、總結與討論
本文通過CGSS2005、2010、2015年三期全國調查數據,從世代更替視角對十年間我國居民幸福感的變化趨勢進行了分析。通過代數分解和線性分解兩種方法,我們了解到了居民幸福感變化趨勢中個人改變和世代更替各自起到的作用。得出以下結論:
通過CGSS數據比較發現,隨著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我國居民十年來的幸福感持續上升,并且個人幸福感的增強是十年來人們幸福感上升的主要原因,不過世代更替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具體來看,1960年以前出生群體的幸福感增長主要源自個體幸福感的提升;1960年以后出生群體除了個體幸福感提升,世代更替對于他們幸福感的增長也貢獻了較為明顯的力量。因此,如果不考慮人口世代更替的影響,會略高估我國居民幸福感的上升態勢。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2005—2015年十年調查數據的人口更替水平仍然偏低,2005—2015年樣本的人口平均出生年僅增加了4.14年,因此我們的樣本可能低估了世代更替效應。其次,限于篇幅,本文的著重點是從方法上分解人們幸福感的轉變和世代更替的各自作用,沒有對相關的發生機制進行探討。第三,世代表和代數分解均以十年為一個世代,我們假設世代內的群體具有同質性,但世代內的個體仍然會存在異質性,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研究的精確性。因此本研究僅是一種開始和嘗試,也期待后續研究能夠進一步揭示影響幸福感世代差異的深層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