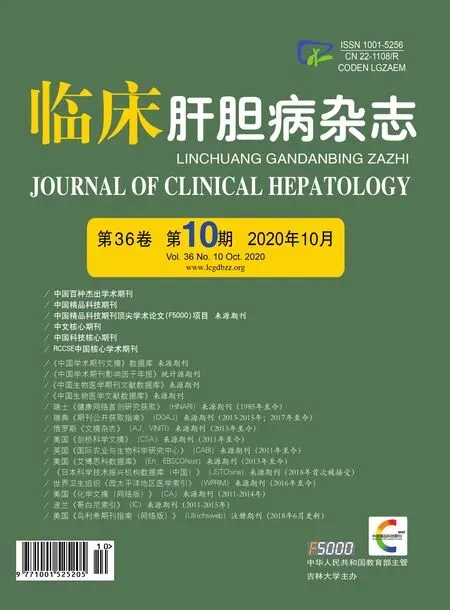疾病譜進展背景下脂肪性肝病診斷的重新審視
牛春燕, 劉 勤, 羅曉春
1 南京市溧水區人民醫院(東南大學附屬中大醫院溧水分院) 消化內科, 南京 211200;2 西安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 消化內科, 西安 710077; 3 廈門大學 醫學院, 福建 廈門 361102;4 廈門大學附屬翔安醫院 消化內鏡中心, 福建 廈門 361101
脂肪性肝病目前分為酒精性肝病(alcoholic liver disease, ALD)和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 NAFLD),二者代表了全球比例最高的慢性肝病。ALD定義為女性飲酒≥20 g/d、男性≥30 g/d,合并ALT升高(女性>19 U/L、男性>30 U/L),低于上述飲酒量則屬于NAFLD范疇。但隨著肥胖、飲酒和代謝綜合征(metabolic syndrome, MetS)呈世界性流行,代謝性疾病譜也在逐漸演變,近年大量研究顯示,相當比例的個體既具有MetS的各項表現,又合并低于ALD診斷值的飲酒量,二者在病理生理過程、組織學特征、發病機制、腸肝軸、腸道微生物叢、臨床表現等多方面具有共同或類似特征即ALD與NAFLD重疊存在,同時又存在明顯的個體間異質性。越來越多觀點認為,飲酒與MetS以相互和協同作用的方式促進肝損傷,并且每種因素的存在或暴露均會提高肝臟對另一種因素損傷效應的敏感性,最終促進肝臟疾病進展及肝臟不良結局的發生。明確飲酒和熱量過剩與代謝風險對于肝病的相互/協同作用將使脂肪性肝病的診斷更加精確,治療更加遵循個體化原則。
1 流行病學
自1970年以來,全球超重和肥胖發生率升高了2倍[1],目前全球平均超重率為39%,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國中肥胖率為23%,其中美國超重和肥胖率高達61%和38%[2]。NAFLD影響到全球25%的成人,在亞洲地區患病率已升至29.6%[3],在病態及嚴重肥胖者中高達90%以上。歐洲及美國成人飲酒占60%~70%,其中美國重度飲酒者高達8%~10%,年均消費純酒精10.9 L/人[4]。在過去25年中,成人人均飲酒量增長了約10%,大部分源于亞洲(特別是中國和印度)和非洲的增長[5]。ALD是西方國家人群中肝病相關死亡的最常見原因,以及歐美肝移植的主要適應證。持續酗酒者肝硬化和肝癌的終生風險分別為8%~20%和3%~10%[6]。全球疾病負擔項目(Global Burden of Disease)估計2016年肝硬化和慢性肝病死亡中,27%歸因于酒精,酒精相關肝細胞癌(HCC)死亡占所有HCC死亡的30%;飲酒率的分布及飲酒作為危險因素對ALD發病和死亡的影響呈地域性差別,酒精對肝硬化的貢獻率占所有肝硬化死亡因素的47.9%。近年研究[7]發現,ALD與NAFLD并存使ALD患者肥胖和MetS患病率正在全球范圍內增加,在1994年-2014年的20年間美國ALD患者超重(BMI≥25)、肥胖(BMI≥30)、嚴重肥胖(BMI≥40)以及中心性肥胖的患病率分別增加了14.6%、17.9%、5.8%及16.4%[8]。
2 飲酒、MetS、NAFLD之間的相互及協同作用
2.1 飲酒與代謝紊亂對肝病的作用 歐洲肝病學會和美國肝病學會定義安全飲酒量為男性<30 g/d、女性<20 g/d,亞太肝病學會采用較保守的閾值即男性<20 g/d、女性<10 g/d。少量-適度飲酒(主要為葡萄酒和啤酒)可能與體質量增加無關,與增重、肝脂肪變及進展、炎癥和纖維化風險降低有關[9],機制包括:通過葡萄酒和啤酒中所含的苯酚類和多酚類物質介導改善胰島素敏感性、抑制血小板活化、降低纖維蛋白水平、抗炎效應。最早關于酒精與體質量增加對肝脂肪變協同作用之一的DIONYSOS流行病學研究[10]顯示,肝脂肪變患病率在>60 g/d的飲酒者中增加到46%,在肥胖者中增加到76%,而在瘦者中僅為16%;并且肥胖合并飲酒>60 g/d者肝脂肪變高達95%。之后的研究[11]進一步證實了中-重度飲酒與增重和肥胖的相關性。瘦者飲酒≥40 g/d及肥胖者不飲酒或每天僅飲1份酒者OR值分別為2和3, 而肥胖合并飲酒>40 g者OR接近9,明確提示酒精和肥胖對肝細胞損傷的協同作用,以及肥胖和瘦者對酒精的易感性差異[12]。法國的一項1970年-2018年人群統計[5]顯示,北美/南美和歐洲地區人群飲酒率下降可能使肝病相關死亡下降3.5倍。以上結果表明,中度以下及中度以上飲酒量對肝臟的影響不同,存在劑量-效應關系。酒精的肝毒性除依賴于飲酒方式、飲料類型外,還受遺傳、性別、環境因素、飲食、腸道菌群和包括肥胖和代謝風險在內的共病的影響。
現代社會中,飲酒的同時往往會攝入較多高熱量食物,在社會活動進餐時也常伴有飲酒(社會性飲酒)。純酒精可產生約7.1 kcal/g的熱量,顯著促進熱量過剩。在預先存在代謝危險因素包括肝脂肪變情況下,合并飲酒對肝臟的損傷顯著增加,產生超加性相互作用,成為全因死亡中的重要因素[13-15]。具有一種危險因素的個體可能對另一種因素誘導的肝損傷更加敏感,間歇性飲酒可作為“二次打擊”加重肥胖性脂肪變肝臟的氧化應激,促進脂肪肝和肝纖維化[16]。反之,代謝危險因素在酗酒、長期飲酒者中也很常見,并導致或加重肝臟疾病的進展[17],飲酒和肥胖共病顯著升高糖尿病(diabetes mellitus, DM)的發生風險。酒精、肥胖和DM均為慢性肝病發生纖維化 、肝硬化、HCC、肝功能失代償以及肝病相關死亡發生和進展的獨立危險因素[18]。飲酒量與肝病之間存在強烈的劑量-效應關系,當飲酒>10 g/d時酒精的肝毒性效應呈劑量依賴性遞增,且晚期肝病的風險隨之增加[19]。由于危險飲酒和肥胖之間的相互作用,肝酶升高的風險升至26%~88%,臨床肝臟不良結局的風險升至25%~67%[14],普通人群中腹型肥胖男性酒精性肝病風險較非肥胖者增高4倍[19]。?berg等[14]認為約50%的肝病過度風險來源于危險飲酒與肥胖的協同作用和二者之間的相互作用,另50%是由于酒精和肥胖的獨立效應。肥胖和飲酒協同代謝危險因素促進肝病的發生與進展,較非肥胖者HCC風險顯著增加,而且兩種因素病理機制的協同作用比任一單獨因素造成的損傷效應更大[20]。大部分ALD患者具有MetS的某些特征,因而MetS可能參與ALD的發病機制和疾病進展。美國男性中酒精性肝硬化是肝移植的最常見原因,其次為NAFLD,隨著ALD與MetS共病率的升高,這類患者對肝移植的需求很可能會增加。
2.2 脂肪性肝病與飲酒、代謝紊亂之間的相互作用 飲酒與肥胖之間存在很強的因果關系。美國第三次全國健康與營養調查(NHANES Ⅲ)[21]提示,肥胖和MetS對ALD的共同損害導致ALD患者肝病相關死亡增加。來自英格蘭、蘇格蘭、芬蘭、德國和中國臺灣的研究[14,22]發現,人群中有17.5%的成年男性同時符合NAFLD和ALD標準(肥胖合并飲酒>30 g/d),ALD患者與NAFLD患者同樣容易肥胖,甚至ALD患者MetS的出現頻率高于NAFLD。越來越多證據支持一種觀點,胰島素抵抗(insulin resistance, IR)和2型糖尿病(diabetes mellitus type 2, T2DM)與NAFLD和ALD均密切相關,可能促進ALD和NAFLD的發生及進展[23],IR/T2DM是ALD和NAFLD全因及肝病相關死亡的獨立預測因子。高胰島素血癥和IR已被證實是酒精中毒并發DM、肝硬化的病理生理基礎。肥胖或超重、高BMI是脂肪肝和各期ALD纖維化的獨立危險因素,超重10年以上者,脂肪變、酒精性肝炎和肝硬化的風險比不超重者增加2.5、3.0、2.15倍[24]。在NAFLD合并MetS患者中,過量飲酒與死亡率增加有關,相反,無MetS的脂肪肝患者,即使過量飲酒也不能預測死亡率,提示MetS與過量飲酒對NAFLD的超加效應。NAFLD患者在肝移植后大部分會復發,因此肝移植不能治療脂肪變;ALD患者肝移植后盡管戒酒,脂肪變發生率仍然很高,進一步表明ALD患者也存在導致NAFLD的潛在危險因素[25]。
3 飲酒和代謝紊亂協同作用導致肝損傷的機制
飲酒與肝病的關系可能主要由IR所介導[26]。酒精和MetS兩種病理機制的協同作用比任一單獨機制的危害更大,合并飲酒可使預先存在的肝病惡化。動物實驗[27]表明,高脂飲食(high fat diet, HFD)誘導的中度肥胖合并暴飲可導致酒精劑量依賴性的協同性脂肪性肝炎,與加重的纖維化、一氧化氮合酶的誘導以及活性氮簇(即氮化應激)有關;細胞色素P4502E1的誘導和致癌DNA損傷的產生導致病理惡化;酒精和HFD聯合作用顯著增加小鼠SREBP-1和FAS基因的表達;在HFD誘導的NASH基礎上,即使額外低度飲酒也可引起炎性病灶和細胞凋亡數量的增加;HFD合并“社會性飲酒”可使體質量增加[14]。體外研究[28]發現,長期大量脂肪酸和乙醇誘導釋放自由基相關的酶,可引起脂質過氧化和肝損傷,在乙醇和過量游離脂肪酸的存在下,這些機制協同增強,并誘導脂質過氧化、氧化應激和促炎基因表達;CYP2E1活性的誘導乙醇和細胞甘油三酯的協同病理效應(因此藥物抑制CYP2E1已成為治療酒精性肝損傷的策略);細胞色素P450通過自由基形成和脂質過氧化在ALD中發揮作用;此外,乙醇和細胞脂肪變還可協同介導CYP2E1而誘導細胞內自噬,改善乙醇和油酸對肝細胞脂質積累和炎癥基因表達的共同作用。酒精和肥胖/DM還可通過改變腸道微生物叢數量和質量及削弱腸屏障功能促進肝臟炎癥、纖維化和肝癌發生[29]。乙醇可擾亂肝外脂肪組織功能,誘發脂肪細胞死亡和繼發性炎癥反應及脂解增加,而高脂肪飲食使脂肪組織對乙醇誘導的脂解敏感性增加,參與肝損傷[30]。內臟肥胖者脂質過氧化和炎性細胞因子產生增加,參與NAFLD和ALD進展為肝硬化及其并發癥,包括HCC[31]。除脂質過氧化和促炎細胞因子外,PNPLA3(含patatin樣磷脂酶結構域3)也參與脂質代謝,影響脂肪變、脂肪性肝炎和纖維化嚴重程度,促進肝病進展[32],其變體rs738409為ALD和NAFLD疾病進展的重要因素,與NAFLD和ALD相關HCC的風險增加有關[33]。腸-肝軸已被普遍認為是NAFLD發病機制中的關鍵因素,腸菌產物進入門靜脈循環可能觸發先天免疫,進而導致肝細胞脂肪變、炎癥級聯反應。 此外,肝損傷患者腸道營養不良患病率、內源性乙醇的產量以及腸道通透性和細菌移位增加的發生率更高[34]。近年研究發現了ALD與NAFLD腸道微生物叢及其病理機制相似的改變,腸道微生物區系被確定為ALD肝損傷嚴重程度的關鍵因素。ALD與NAFLD的共同特征包括腸道上皮緊密連接蛋白表達降低,黏蛋白生成和抗菌肽水平降低。腸屏障受損是ALD的先決條件,導致細菌產物進入血流(內毒素血癥)。 此外,細菌代謝產物如短鏈脂肪酸、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和膽汁酸也是ALD及NAFLD的共同病理學機制[35]。
4 關于對脂肪性肝病診斷和治療的重新認識
約40%的進展期非病毒性肝病患者同時存在代謝風險和規律飲酒,其風險特征既不符合典型NAFLD表型,也不符合典型ALD表型[14,36],但二者在臨床表現(包括肝臟結局)、發病機制、病理生理、治療等多方面存在共同特征,因此對進展期肝病中酒精的影響很難與代謝紊亂的影響區別開來。當前嚴格基于純NAFLD或純ALD危險因素的非此即彼的診斷策略可能會低估由酒精和代謝紊亂協同/相互作用對肝病個體的風險,從而遺漏超過1/3的進展性肝病患者[14]。飲酒和MetS各組分(包括NAFLD)都是連續變量,現有診斷體系已經不能適應當前脂肪性肝病疾病譜演變現狀以及對發病機制的深入理解,不能滿足對脂肪性肝病治療策略制訂以及個體化診療的需求,因此迫切需要更新脂肪性肝病的診斷體系,早期明確高危飲酒者,以及肝臟疾病在不同程度上受酒精和代謝紊亂的共同影響,從而在發展為終末期肝病之前進行風險分層和優化干預措施[24,36]。2020年4月-5月,JournalofHepatology和Gastroenterology相繼刊發了將NAFLD更名為代謝相關脂肪性肝病(metabolic-dysfunction-associatedfatty liver disease, MAFLD)的國際專家共識意見[37-38],提出了診斷標準,舍棄了排除法,使脂肪性肝病的診斷更加準確,同時為相關臨床研究和藥物研發提供了依據。此外,筆者支持“雙病因脂肪肝”可以作為一個同時具有ALD和MAFLD特征的診斷范疇,可以反映NAFLD與飲酒因素的共存,以及飲酒量高于推薦值但又不符合ALD診斷標準者[24],這樣在慢性肝病人群中,同時考慮飲酒和代謝因素共同和/或協同作用,而不是ALD或NAFLD單獨作用的結果,或許更加合理。
5 總結與展望
多項研究發現了飲酒、MetS與NAFLD的共存,而且隨著飲酒、MetS的流行,這一人群的比例正在上升,飲酒與MetS的協同/相互作用導致肝病的進展和惡化,肝臟不良結局隨之增加。因此,ALD與NAFLD重疊現象日益突出,或許成為脂肪性肝病疾病譜中的新成員,需要重新認識并且重視,在脂肪性肝病的診斷和治療以及相關研究中,應注意評估飲酒和代謝因素相互和/或協同作用。除飲酒量外,飲酒模式、生活方式和飲食脂肪類型在代謝性肝病中同樣有重要意義。迄今NAFLD患者飲酒與臨床結局之間關系的高質量數據僅來自于觀察性研究。未來需要大樣本基礎研究、隨機對照研究和前瞻性隊列研究,以及對MAFLD危險因素的分層研究,進一步闡明飲酒與MetS相互/協同作用的確切結局以及病理機制,為脂肪性肝病的個體化預防、治療和預后提供更高價值的數據。
作者貢獻聲明:牛春燕負責課題設計,資料分析,論文撰寫;劉勤參與收集和整理文獻數據;羅曉春參與文獻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