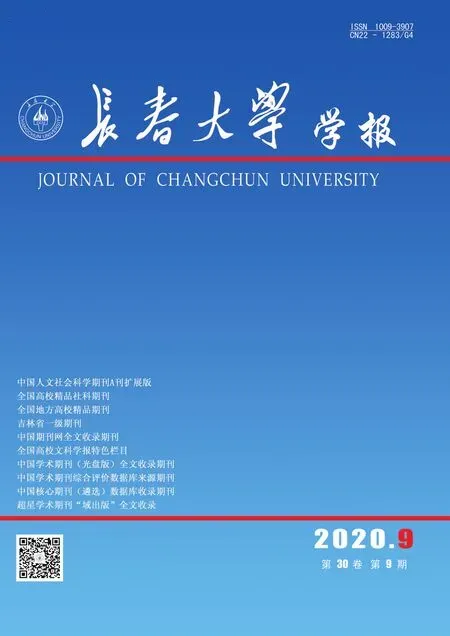《野叟曝言》的儒家經權思想與貞節觀書寫
璩龍林
(東北財經大學 國際教育學院,遼寧 大連 116025)
《野叟曝言》是清代乾隆時期夏敬渠所著的儒家言志傳統的長篇敘事小說。全書154回,約140萬字,描寫了吳江名士文素臣一生的英雄業績。小說主人公文素臣完美超凡、無所不能,因而顯得太理念化而不近情理,使他成為類型化、扁平化的文學形象。不過,盡管文素臣算不上一個成功的文學形象,然而若從考察儒學特別是理學實踐者的心態和理想藍圖的角度出發,《野叟曝言》未必不是一個極為有用而詳盡的文本。情欲觀與貞節觀,是互為表里的兩個觀念,前者的含義推衍指向后者,在小說中,通過經權思想的強勢介入而得以充分表現。
1 理學家的情欲觀與“卻色”
男女關系是人倫關系的起點。《周易》中便明確說,有天地然后有萬物,有萬物然后有男女,夫婦父子君臣上下之道都是由此衍生而來。但是,因為“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為防微杜漸,自先秦始,圣賢便制定了頗多禮儀,以此規束男女之間的行為舉止。如《禮記》一再強調“男女有別”,對各種男女嚴防的規定言之綦詳。歸其一點,就是《禮記·坊記》里的那句“男女授受不親”,成了中國傳統社會倫理之“經”,對華夏民族的文化心理影響至深。反之,男女若在特殊情況下,需要“授受有親”,則是反經行權。《野叟曝言》中的文素臣是一個罕見的理學家形象,這種思想理念使他面對困難始終無所畏懼,具有超人的力量,能夠承擔征服人和妖魔邪惡的英雄使命,成了文能提筆安天下、武能上馬定乾坤的“古今無雙”的“儒家超人”[1]。
文素臣肩負著宣揚婦德禮教的重大責任,勸風塵女子知曉廉恥。如對原本是良家女子不幸落入萊州府豪紳李又全手中已然喪失廉恥之心的隨氏,他用儒家的一些理論感化了她。他有意顯示無論他離女人多近都對她們無所欲求,也不因她們的誘惑而感到痛苦。他的痛苦只表現在他作為忠實的儒教徒卻要被迫視聽這些“非禮勿視,非禮勿聽”的東西,從而受到良心的自我譴責。在本質上這其實是一種理學觀照下自我節制的炫耀。
小說中有大量描寫情與欲的對立。夏敬渠反對除卻為生育行房之外的男女媾合,因此文素臣謹遵母命,從不貪戀床笫之歡,和每一位夫人睡覺都是按預定計劃進行。多數時候,他是靠理念來征服自己欲望的。素臣的這種極度理性的男女觀念,顯然影響到幾位妻妾的態度,她們個個貞節無比,而且這種貞節不是在道德輿論束縛下的自我壓抑,而是一種發自內心的從感性上升到理性的認識。理學最為關注的便是修身養性的問題,通過正心誠意達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一過程中,關鍵的途徑就是如何正心誠意,如何化解過度的欲望,即朱熹所謂的“私欲”或“人欲”,這其中便包括夫妻之情以外的色欲或者肉欲。夏敬渠是個典型的理學教徒,他極為服膺程朱理學,將宋哲的不少情欲思想加以發揮,來塑造文素臣這一理學圣人和超人形象。素臣將私欲尤其是肉欲克制到極致,達到常人所無法企及的高度。
作者對情欲的態度,就總體而言持崇情黜欲的觀點。在第八回中,作者借素臣教誨璇姑之言來說明性與情之間的互相排斥:
男女之樂原生乎情,你憐我愛,自覺遍體俱春。若是村夫俗子不中佳人之意,蠢妻呆妾不生夫主之憐,縱夜夜于飛,止不過一霎雨云,索然興盡。我與你俱在少年,亦非頑鈍,兩相憐愛,眷戀多情,故不必赴陽臺之夢,自能生寒谷之春。況且男女之樂原只在未經交合以前,彼此情思俱濃,自有無窮樂趣。既經交合,便自闌殘。若并無十分恩愛,但貪百樣輕狂,便是浪夫淫婦,不特無所得樂,亦且如沉苦海矣。[2]352
有趣的是,璇姑并未經歷男女云雨之事,她也仿佛過來人一樣說出一通情欲之道:
竊以為樂根于心,以情為樂,則欲念輕,以欲為樂,則情念亦輕。即如前日,自覺欲心稍動,便難消遣,情之一字幾撇天外。今因相公稟命之言,欲念無由而起,情念即芊綿而生。據此時看來,相公已怡然自得,小奴亦窅然如迷。挨胸貼肉幾于似片團成,交股并頭直欲如膠不解,床幃樂事,計亦無逾此者。恐雨云巫夢,真不過畫蛇添足而已。[2]353
換言之,情與欲二者之間是相互排斥的,要想體驗真正的“情”之樂,就必須“滅欲”。因此,作者認為“雨云巫夢”不過是“俗子但知裙里物,佳人能解個中情”。在這一理念下,水夫人讓家中的幾位媳婦全都習武練兵,不讓一個閑著,以防安逸過度,滋生淫泆之心。
作者對男女之欲的觀點并非一貫不變,而是有相當的矛盾和游移。第九十四回,夏敬渠借苗地的土圣人之言表達了他心中另一套“情”與“欲”的理解:
況天地之道,陰陽而已;天氣下降,地氣上升,謂之交泰;若天地不變,謂之否塞。峒里女人,與男子拉手、搭肩、抱腰、捧臉,使地氣通乎天,天氣通乎地,陰陽交泰之道也。若像中華風俗,男女授受不親,出必蔽面,把陰陽隔載,否塞不通。男女之情不暢,決而思潰,便鉆穴逾墻,做出許多丑事;甚至淫奔拐逃,爭風護奸,謀殺親夫,種種禍端,不可救止;總為防閑太過,使男女慕悅之情,不能發泄故也。至婚家之禮,又只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許男女自主,兩情豈能投合?若再美女配著丑夫,聰男娶了蠢女,既非出彼自愿,何怪其參商而別求茍合!若像峒中風氣,男女唱歌,互相感慕,然后成婚;則事非出于勉強,情自不至乖離;遇著男子,又得拉手搭肩,以通其志;心所親愛,復得抱腰捧臉,以致其情;其氣既暢,不致抑郁遏塞,一決而潰為鉆穴逾墻等丑事矣!人心不可能強抑,王道必本乎人情;故合九州風氣而論,要以葵花峒為第一。[2]852
陰陽對照是中國文化的傳統,一陰一陽謂之道,二者相倚相成,不可完全相離。但在多數時候,陰,代表寒冷和邪惡的一面,陽,則象征著溫暖和浩然正氣。文素臣在小說中的巨大能量和神奇稟賦,源于他作為“陽”的化身。他能夠百般卻色,往往處于極其艱難的“欲望”之境況下,其艱難程度遠超柳下惠,但他依然輕松挺過,正在于他“純陽”化身的作用。事實上,作者完全將素臣塑造成一個“純陽”的化身,這一點在他出生的時刻便已顯現出來。他母親在生他時夢到一個巨大的太陽,而這通常是“帝王”出生之兆——素臣盡管不是帝王,但他的功業已遠超帝王,從小說中他所取得的功業來看,雖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亦不能過。小說中,就連他的尿都是一種純陽之物。在第六十五回,李又全認定素臣是純陽之身,要吸他的精液來修身,而他的一幫姬妾和侍女卻爭飲素臣的尿液,倍覺“甘甜”,李又全認為可以“過仙氣”,功效異乎尋常。在第十八回中,其妾素娥病危,飲他的尿而得救。在第八十三回中,文素臣往草席裹著的尸體上小便,使死人復生。文素臣的陽氣極其壯旺,他的4位妻子在10日內為他生育了4個兒子。第九十四回和第九十五回中,文素臣為治好一個石女的病,和她同床,用體內陽氣熏蒸和手淫的辦法對她進行治療,治好了她的病,且具有了旺盛的生育力,她后來生育了28個兒子。
不過,小說中有一個吊詭的現象:他越是卻色,卻越是遭遇各種性場面。據王瓊玲研究,《野叟曝言》一書的性場面描寫大約占到全書百分之五的篇幅[3]。總之,卻色英雄素臣卻有無數的桃色艷遇,總是不停地有各種美女要投懷送抱,當然大多是因為他英雄救美。他相繼救得美貌才女鸞吹、璇姑、素娥和湘靈,后三人皆納為側室,而鸞吹后來嫁給了一位正道直行的君子儒,她丈夫雖然知曉她和素臣之間的事,也不以為嫌,夫妻甚是恩愛。素臣本人又偉岸俊美,加之救命時總難免肌膚相觸,也犯了“男女授受不親”的儒家規條,這些女子于情于理都要委身于他,甚至在得知他已經有了家室,還照樣要死要活地嫁給他。這自然可以視為這些閨中未字年輕女子的貞節觀念,如鸞吹以為男女不相親授,但在落水被素臣救命時難免沾皮著肉,這應該算是某種程度上的“失貞”,按照道理,素臣娶她是應盡的義務和責任。但她們如此不計妾之地位而要拼死嫁他,甚至違背父母之命非他不嫁,這至少也是對傳統的婚姻倫理某種程度的違抗。
2 貞節觀與經權思想
在《野叟曝言》中,出現了大量的經權思想。所謂經權思想,就是守經與行權的思想理論,簡單說就是原則性與靈活性的關系。在古人看來,要很好地達到目標,需要經權結合,常時守經,變時行權。儒家傳統講究男女授受不親,這成為倫理之“經”,但一些思想開通的大儒并不泥守此條,特別是孟子提出“嫂溺叔援”的著名悖論,他認為以經權思想便可輕易化解這一尷尬的倫理難題。
《野叟曝言》對經權思想的運用特別多。經權思想特別突出原則的變通和靈活性,顯示了對傳統和規則的突破和反動,因此,這種思想運用和凸顯的地方,常常也是規則遭到破壞、傳統倫理受到考驗的時候。貞節觀念和經權思想都屬于儒家傳統思想的范疇,只不過一個是儒家道德倫理觀念,一個是儒家思想觀念,都會對實踐發生作用,影響人們的現實生活。當原本平行的兩個觀念交叉的時候,必然會發生交涉,在明清通俗小說中,主要表現為經權思想對貞節觀念的調控和支配,使得貞節觀念發生轉折變化。其具體表現為,小說作者和主要人物經常以經權思想為“情”放行,給本屬“不貞”“不節”的行為作出合乎儒家倫理的解釋,提供理論依據,從而緩和小說人物的內在倫理緊張,推動小說情節的發展,同時也釋放了作者可能面臨的倫理壓力。在明末清初的不少才子佳人小說中,年輕的男女主人公一見鐘情,兩情相悅,在沒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情況下,情不自禁地走到一起,甚至發生了關系,這種行為無疑有違倫理道德,不合儒家禮教,要面臨巨大的輿論壓力,甚至會受到嚴厲的懲罰。但這些小說中的年輕主人公們往往會抬出經權思想這面大旗,來論證特殊情況下行權結合的必要性[4]。如《好逑傳》中的女主人公水冰心便以孟子對行權的辯解為依據,提出可以允許年輕的學子在她家中養病,盡管沒有別的女伴在場。原本心虛理虧的人物,因為占據了儒家先賢的理論制高點,轉而理直氣壯。正心誠意與修齊治平中間的溝壑被經權思想填平化解。
文素臣是一個開拓各類權宜情境的能手,“《野叟曝言》中令人驚訝的性事描寫是被用以討論行權的合法性的經典語匯的副產品”[5]199。如前所述,《野叟曝言》雖然是一部正義感和道學氣十足的小說,全書充滿了道德說教和禮教規劃,但同時又是一部具有濃厚春宮氣的小說,書中遍布赤裸裸的色情描寫,充滿性的挑逗和壓抑,不少淫穢情節和場景與《金瓶梅》相比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儒家王道倫理本與色情淫欲沖突,但是,書中卻密布了此種淫蕩而誘人墮落的氣息,這就需要從作者的敘事理念出發,實則作者是將這些作為“反面教材”,用來考驗人物的道行、修為和定力,恰恰證明一個真正的儒者所能夠擁有的巨大能量。
事實上,每當文素臣與正派年輕女子有身體接觸和撫摩甚至性接觸的時候,都是他在治病救人的時候,而拯人于危難、濟人于困厄,本就是儒教徒的必備功課之一。這種男女之間的零距離接觸,按照正常倫理是斷不能容許的,正因如此,先秦的孟子才為“嫂溺叔援”的正當性而辯論不休。在《野叟曝言》中,諸多類似男女授受不親的情形,毫無疑問也是完全有礙貞節觀念的,因此,這些年輕的女子才會如此拘謹、不自然,甚至因此要嫁給文素臣。
而素臣自己也并非完全心安理得,坦然面對,只不過一方面救人治病,危在旦夕,刻不容緩,無法顧慮太多,素臣自然可用經權思想來說服女子和女子家人,通常她們心悅誠服;另一方面即使在危病的女子已然脫離險境時,素臣仍然需要與之近距離接觸,而女子需要某種程度的“裸裎”,這種情形之下更非尋常女子所能接受,而素臣猶能坦然處之,且依舊以處變行權來寬慰女子和自己。比如他在救了落水的鸞吹之后,二人生火取暖,因為顧及鸞吹穿厚衣服會導致熱氣攻心致病,素臣勸她解下里衣烘烤。陌生青年男女單獨相處已然屬非禮之行,且親密接觸,還要女子解下閨中獨見的極為私密而“性”色彩極強的里衣,這在傳統社會簡直是不可想象的荒唐行為,與儒家貞節觀念鑿枘不合。此時,素臣化解不雅舉止和氛圍的利器依然是經權思想。而鸞吹竟然再次被他的理論和諄諄教誨所打動,不再因為自己與之授受有親而要求嫁給他。
他經常采取一些新奇甚至看似荒唐的手段,諸如用令女人赤身裸體的方式來達到“驚嚇”的醫療效果,或用他自己赤裸的身體來溫暖女性病人以治病,而素娥在文素臣病中也同樣用自己赤裸的身體溫暖他。這些情節都是為了證明“權”的重要意義[6]217。在第六十七回至第七十回,更是集中體現了作者在男女關系上的經權思想。這四回淫褻場面描寫過多,因此頗遭詬病。但若從經權思想的角度考慮,便可發現其中寄寓了作者的意旨:實際上這些描寫不過是給文素臣提供一個背景,以襯托他為了能盡忠孝之“大經”而善于權變處之的真儒高大形象。這幾回敘寫文素臣被萊州府豪紳、景王叛黨李又全捉住,要他服參藥以積精進獻,李的十幾個姬妾同他裸體洗澡摟抱,備極淫褻丑態。文素臣起初備感恥辱,欲尋一死以全清白,但是,因為他具有強烈的經權思想,于是緊接著便有以下的想法來自我慰解:
這是飛來橫禍,非我自招。我的身命,上關國家治亂,下系祖宗嗣續,老母在堂,幼子在抱;還該忍辱偷生,死中求活,想出方法,跳出火坑,方是正理!招搖過市,圣人尚且不免于辱;我豈可守溝瀆之小節,而忘忠孝之大經乎?[2]817
非夫妻之禮的男女關系,已非儒家之禮所能容納,如此淫亂的場面,自然更屬嚴重“非禮”之行,但素臣是不幸陷于此境,而非“自招”,故他能行權反禮。這四回當中,文素臣類似的想法處處涌現,以此來自我慰解。
他常常在淫褻羞辱之境下,想起“豈可守溝瀆之小節,而忘忠孝之大經”。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一再以“溝瀆之小節”與“國家之大事”對舉,如:
豈可守溝瀆之小節,而忘忠孝之大經乎?[2]817
匹夫溝瀆之小節,使老母無侍奉之兒,祖宗絕顯揚之望,非特不忠不仁,亦且不孝。[2]833
事有經權,拘溝瀆之小節,而誤國家之大事,又斷乎不可![2]844
不敢拘溝瀆之小節,而誤國家之大事,是以舍經為權,任其侮辱。[2]858
在作者看來,孔子所云“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顏淵》),原本屬于“經”的范疇,在忠孝面前顯然成了“溝瀆之小節”。也就是說,作者眼中的那些禮,就算是“經”,也屬于經之小者,為了不悖“大經”而舍“小經”,這就是行權合道。
《野叟曝言》的作者骨子里很注重女子貞節,卻本質上放松對男子的貞節要求(當然,這在古代男權社會并不特別)。不過,為了迎和男子的情欲要求,需要女子相應的突破貞節廉恥的行為。這實際上有兩種情形:一是邪惡女人的行為。她們原本就是淫蕩邪惡的代表,自然不需要任何道德掩飾,徹底撕碎貞節倫理道德。李又全的姬妾侍女給文素臣服下名為“催龍湯”的藥,讓他手足癱軟,全身上下只有陽具可以動,目的是為了集聚他的作為“純陽”的陽精供自己吸取。這種情形之下,身不由己的文素臣只好眼睜睜地看著這些淫蕩之極的婦人賞鑒和淫褻自己,他只能集中精力,設想自己變成土木形骸,對一切視而不見。二是正派女子甚至是純潔女子,她們本來貞節觀念極重,如何突破這道心理防線和觀念底線。作者的做法是讓她們處于極端狀態,或者是遇難危急,如鸞吹、湘靈,或者即提供經權思想的理論依據之時。這種描寫,難免讓人感覺作者是披著卻色的外衣或者在放煙霧彈,內里其實是窺陰癖和色情狂的變相滿足[7]。盡管每次文素臣與別的女子貼近或交合,但是都迫于無奈,這樣實際上是為作者的情欲心理提供了一個道德的安全避風港。
很多時候,小說中經權的概念因過于延展而顯得寬泛,兩個愛人間的肉體接觸太過親昵,以致“情”和“欲”變得難以區分,盡管小說堅持認為二者互不相容[6]217。例如,當原本極其貞節的素娥誤服了春藥“補天丸”后,她感到自己欲火中燒。這引發了小說中關于“情”與“欲”的最具有戲劇性的沖突之一。素娥緊抱素臣并央求他與自己發生性關系。有趣的是,素臣通過用嘴哺住素娥之口、又撫摸她的全身甚至私處的方式來拒絕她的性請求。按照一般的標準,這樣的親昵已屬“性欲”的范圍。但是,小說作者卻堅持認為素臣的舉動是“情”的行為,因為他的意圖是與性欲或者“欲”毫不相關的。他是在治她的病,因此這是一個出于“情”的行為,他的諸般撫愛都是去性欲化的。頗為諷刺的是,這些關于“情”的“去性欲化”的行為似乎最為有效地抑制了素娥看似難以控制的肉體欲望[6]220。
這些理論支撐下的行為由于顯得匪夷所思而變得非常荒唐,荒誕的把戲甚至鬧到天子宮廷里面。在一百零七回中,妖僧以烈火地獄來襲,各種大小火球爆響燒來,妃子宮女“周身衣服燒毀,有光了上身,捧著兩乳,有赤了下身,掩著陰戶,又羞又痛”[2]1034。文素臣又解下半桶小便,將草薦浸濕,攤放在門檻上,將翻滾的火球擊退。第一百零八回中,素臣還在每個妃子的心額前和每位宮女的胸前題寫“邪不勝正”,當素臣考慮到男女之嫌、宮闈之地表示不敢奉命時,太子也抬出經權思想:
急難之時,又當行權,且先生何人,何嫌可避?即正妃心額,尚欲求書!孟子云:‘嫂溺不援是豺狼也!’況宮人乎?[2]1057
這些荒唐無稽的淫思奇想,難免會褻瀆朝廷尊嚴,可見作者對經權思想的自恃之深。
而在文素臣遇到反面邪派女子的時候,比如李又全的多位淫蕩不堪的姨太太,素臣心中當然逆反,會生起種種厭惡之心和抵抗之情。但是,他顯然是身不由己,被她們捆縛,被迫聽到她們一系列下流惡心的笑話故事,看到她們種種極其淫蕩穢褻的表演,還要感受體驗她們全裸的各種性的激發和色情挑逗。作為一個正派的儒教徒,這些場景早已越過倫理底線,無疑是挑戰他的思想根基,按理他沒有活下去的理由,確實他也想到一死了之。但是,一方面他完全被縛,根本無法尋死,另一方面,他想到了自己作為國家棟梁的重大意義,忠孝大經,才是自己要追求和踐行的,自己任重道遠。這時,他又以經權思想來為自己的“性的饕餮”開脫、慰解,因為“非自己所招,迫不得已”,終于他將這些淫蕩的尤物視為土梗動物,心安理得地享受激情,體驗快感。甚至,在李又全的寵妾隨氏,原本一位美貌的良家女子,卻白沙在涅徹底喪失貞節羞恥之心來陪睡的時候,他還盯視她的生殖器,來考驗自己的定力。而隨氏要慕名賞鑒體驗他巨大的陽物的時候,他才又想起用經權思想來說服“淫穢”的美人來恢復羞恥心。觀念一變天地寬,正是有了所謂的經權思想,素臣擁有了一種理論優越感,從而在各種淫境險局中讓心靈穿行自如,輕松卸下任何思想輿論的壓力,甚至因此成為別人的思想導師,不停地給這些女子灌下一碗碗的“心靈雞湯”。
更重要的是,因為有經權思想作理論支撐,評點者(很可能就是作者自己)驕傲地宣稱:
設局騙人,食精采戰,微特天壤不容是人,即十六姨娘與歌姬、丫鬟一輩人物,要他聚在一處做一日把戲,也覺無此情理。作者特地拈此數回,淫褻極矣!然十六姨中偏有一貞烈之三姨,與九姨同為又全心上人之隨氏為素臣感化,則辟邪崇正本旨自在言外,不比金瓶等書專描淫褻,不愧第一奇書之目。[2]819
明知“淫褻極矣”,還敢如此大張旗鼓地自我稱許,似乎有悖于理。但我們可以反過來設想,假設沒有這種理論作為思想支撐,作者還能這樣堂而皇之地自負為“第一奇書”么?由此可見,“‘權’可以使人在‘情’與‘禮’之間找到最佳的平衡,特別是在極其無奈而又非常緊急的情況之下”[6]217。經權理論成了作者宣淫導褻的一大障眼法,從而在小說思想主旨的確立和故事情節的設定上都起了相當大的作用。這個“禮”便包括貞節觀念[8]。
3 結語
《野叟曝言》一書對經權理論使用過多,并且使用者常常恃此教訓別人,仿佛真理在握的派頭,也不免令讀者產生理論圖解的感受,說理小說的特色和缺陷并見于此。不過,凡事皆可作兩面觀,正如譚正璧所說:
清代的理想小說卻不然,他們都利用它來為庋藏他們博學的工具,將他們一生所得,完全借小說發抒出來。這種文字本來算不得是文學,但因為他們大多天才頗高,描寫手腕亦靈轉,使讀者不覺其為賬簿式的百科全書,而為有趣味而又動情的故事。在這一點上,他們就亦得在小說史上占一席之地了。[9]
這是為《野叟曝言》等小說說好話,《野叟曝言》是否當得上“有趣味而又動情”,見仁見智,但說“不覺其為賬簿式的百科全書”畢竟不算過分,書中不少情節還是頗有可讀性的。經權思想本身屬于理論,重在權變,可以看作是對宗經征圣傳統的翻新出奇,而又經歷代大儒暢發厥旨,卻闡發未盡,常論常新,知不足齋主人序云夏氏“抱奇負異”,則其對經權學說之類的可歸入“奇異”的學說備感興趣,并視此為才學之一,以盡情顯露,也就無足奇怪了。
不過,經權思想中有一個盲點:何時行權,誰才有此資格行權,其中的度和標準又是什么?完全守經,固然會滯礙不通甚至會造成人間悲劇,但行權思想一旦完全放開,又往往會讓小人“假權之名,行詐之實”,從而在封建倫理綱常上敲開一道思想的裂縫。可見,經與權的取舍,在作者心中也是一大疑問,這在文素臣的行為中也有表現。如第二十五回中,石氏和鶼鶼為素臣所救,晚上旅店只有一間空房,二人見素臣在外邊坐守,便勸素臣歇息,她們則在炕邊坐守,素臣于是正色道:
常則守經,變則從權。到不得不坐懷之時,方可行權;今日乃守經之日,非行權之日也。若自恃可以而動輒坐懷,則無忌憚之小人矣![2]326
總之,小說里文素臣不斷通過男女關系來體驗和實踐經權思想,也通過經權思想來重新詮解男女關系,來達到“對于性貞潔作為一種基本道德界定——特別是對婦女而言——的中心位置的解構”[5]199,正如第六十八回總評中所云:“非褻之也,蓋堅其崇正辟邪之心。”[2]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