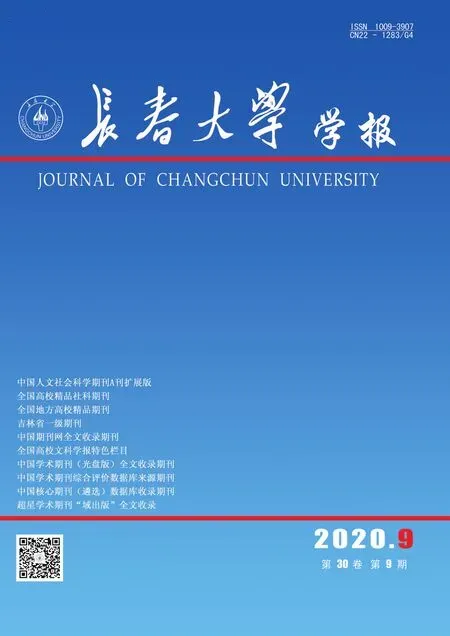從深層生態學視角看琳達·霍根的《太陽風暴》①
陳 征
(福建師范大學協和學院 外語系,福州 350108)
琳達·霍根(Linda Hogan, 1947—)是美國本土裔契卡索女作家,其作品曾獲得美國圖書獎、美國本土裔作家團終身成就獎等諸多獎項。其代表作品小說《太陽風暴》曾獲得科羅拉多圖書獎。無論是詩歌、小說、散文,還是戲劇、傳記,霍根的作品都集中關注了環境主題,從本土裔族群傳統文化的視角控訴美國社會發展過程中對環境的破壞和殖民暴力,揭示了本土裔遭受的苦難經歷,透露出強烈的社會責任感。
1973年,挪威哲學家阿爾內·納斯在《淺層和深層孤獨生態學運動:摘要》一文中首次使用了“深層生態學”一詞。深層生態學反對人類中心主義,認為人類與自然地位平等,人類只是參與者不是操縱者,因而無權處置自然。深層生態學涉及多樣性、復雜性、共生和平均主義的原則,“倡導重建人類文明的當前秩序,并使之成為自然和諧的組成部分”[1]。
霍根的小說《太陽風暴》(SolarStorm, 1995)講述了17歲的印第安女孩安琪拉(Angela)從白人寄養家庭重回出生地的尋源歸家之旅。小說描寫了由于白人殖民者獵殺動物、修建大壩、砍伐森林等對環境的摧毀行為,部落自然環境遭受前所未有的破壞,繼而導致印第安人民的身份迷失和精神創傷。小說在批判人類中心主義生態思想的同時,呼吁人類與自然的平等和諧共生,展示了作家深層生態思想,揭示了人類與自然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融合的生命共同體的關系。
1 生物中心主義下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
“生物中心主義平等”是深層生態學的最高標準之一。深層生態學認為,在這個相互聯系的世界中,所有自然事物(生態系統,生命和景觀)都具有同等價值,并享有生存和繁榮的平等權利。
在白人社會入侵之前的亞當肋骨鎮(Adam’s Rib)上,人與動物是和諧共生的。在印第安文化傳統里,人對于自身的認識與對動物的認識密切相關,彼此有著天然的親緣關系。在動物的引導下,人類學會探尋水源、辨別方向、預測氣象、躲避災害,印第安人對動物心存敬畏和感激,并形成視其他物種存在為平等互惠的動物倫理。印第安人的許多神話傳說和口述部落故事也是以動物為主題的,涉及宇宙的發源、部落的歷史發展和文化傳承。霍根在小說中也講述了海貍創世的故事:海貍創造了人類,并與人類“訂立盟約,承諾要彼此幫助。海貍提供魚、水鳥和動物,人類則相應地要看顧好世界,并與神靈和萬物對話”[2]239。深層生態學的代表人物阿爾多·利奧波德在其著作《沙鄉年鑒》中也提到“大地倫理學”,認為山川河流、鳥獸蟲魚、花草樹木等和人類共同組成了一個有機整體[3]。因此,自然環境不是供人享用的資源,而應當是被保護的主體,與人類平等共生。印第安生態意識中,人類只是自然活動的參與者,而不是操縱者和支配者。正如小說中部落的長者們認為,“我們的生命被鳥兒、蜻蜓、樹木和蜘蛛見證著。不僅動物和蜘蛛見證著我們,甚至深度空間里鮮活的銀河系和北方吹來的冰雪也一同見證著我們”[2]80。印第安人崇敬自然,認為動物同樣具有靈魂、主體意識以及神圣力量,體現了印第安人對動物的道德認同和倫理關懷,表達了人類與自然萬物相互依存、平等和諧的理念。
印第安人把土地尊稱為大地母親,體現了人與大地和諧親密的關系。印第安文化意識里,大地不但提供了豐富的物質資源,更代表了無窮的生命力和創造力,具有神奇的治愈力量,因此,人類應對大地母親的奉獻和眷顧心懷感激和崇敬之情。“人們講述土地的故事,因為這些地方自身具有能量,它們是有生命的,石頭、泥土、云母、礦物或者其他種類的東西,它們都具備治愈的能力。”[4]印第安人認為,人和土地是相互依存的關系,“沒有土地就沒有生命,就沒有人類合理的社會和文化觀念,也就不存在維持生命的土地”[5]。美國印第安評論家波拉·甘·艾倫也曾論及:“我們就是土地,這是滲透在美國印第安生活中最基本的概念,土地和人民是同一的。”[6]正如霍根所說,“這個世界在我們的血液和骨頭里,我們的血液和骨頭就是土地”[7]。對小說中亞當肋骨鎮的印第安人來說,離開部落的土地無異于死亡,因為土地承載了部落的歷史文化和傳統信仰,是印第安人獲得自我身份認同以及構建自我與宇宙關系的根本。
印第安人的傳統認知里,水即是大地母親的血液,與土地共同構成人類生存的基本物質基礎,具備無窮的精神力量。印第安人推崇水的神圣性,視其為孕育生命的靈性物質。他們保護淡水與海洋,堅守著人與自然互惠的原則,體現了平等和諧共存的宇宙整體觀。霍根在小說中借用水的意象強調主人公安琪拉重建與“自然母親”的聯系。身心備受痛苦且迷失自我的安琪拉回到故土,在養祖母布什的幫助下,學會親近“自然之水”,重拾游泳、劃船和捕魚等部落傳統技能,并逐漸感受到自己在宇宙萬物中的歸屬感。水成為她與自然萬物之間密切相連的紐帶:“我生活在水中。我們之間不可分離……我一生都在尋找我曾經迷失的古老世界,只有我的身體不曾遺忘它,在那一瞬間,我明白了我和鳥兒、雨水一樣都是它的一部分。”[2]79通過回歸部落故土的自然水域環境和印第安生態文化,安琪拉最終擺脫了白人文化的束縛和壓制,跨越了人與自然的疆界,其自我意識得以喚醒,身心得以療愈,自我身份得以重構。
2 人類中心主義下自然的災難與人類的創傷和迷失
人類中心主義是西方文化在人與自然關系問題上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一種價值取向。居于中心地位的人類被賦予對自然界一切生命和非生命物質的絕對支配權力。人與自然是利用與被利用關系,隨著經濟與社會的發展,環境惡化和生態危機也不斷地加劇。
人類中心主義的思想,讓人類背離了與自然的互相依存關系,造成環境的悲劇。在小說中,為了解決紐約居民的用電問題,白人政府強行要在印第安人生活了數千年的土地上修建大壩。大壩的修建導致了數千公里的土地被淹沒,嚴重破壞了當地的生態環境,“馴鹿和鵝以及人們需要的用于治療的植物都遭受到了影響”[2]36,印第安人民流離失所,印第安部落賴以生存的文化根基和精神信仰也被破壞殆盡。“挪威和瑞典的伐木工人砍伐了森林;加拿大人和美國人都渴望獲得水力;法國的獵手捕撈海貍和狐貍,直到它們都消失了”[2]108。在人類中心主義文化下,為了所謂的文明進程和社會發展,自然成為僅具有物質價值的商品遭受盤剝,自然的巨大毀滅給人類留下了永不磨滅的創傷。
在人類中心主義思想引導下,白人對自然無節制的掠奪和破壞,不但讓印第安人失去了家園,更讓他們遭受了身份的迷失和精神的創傷。小說中,法國毛皮獵人在亞當肋骨鎮上肆意捕殺動物,“海貍和狼消失到幾乎滅絕時,男人們(白人貿易商)遷移到其他未被損毀的地方,把他們的女人和孩子留在身后,好像他們也是被耗盡了的動物”[2]28,淪為被拋棄的人,而原本是白人尋找毛皮和財富的“生意貿易之地”,最后成了“一片孤立的土地”[2]65。土地被掠奪和生態環境被破壞所導致的身份迷失和精神創傷,在安琪拉和她的母親漢娜以及安琪拉的外祖母洛瑞塔三代印第安女性的經歷中都有著深刻的體現。歐洲的皮貨商和捕獵者通過毒餌獵捕動物的同時導致饑餓的印第安人在吃了下過毒的獵物后大量死亡。洛瑞塔雖然僥幸存活卻遭受了精神上的傷害,漢娜從母親洛瑞塔那里得到的只有她憤怒的情緒和仇恨的發泄,卻沒有絲毫的母愛。幼年的漢娜身上遍布戳傷、燙傷等各種傷痕,在承受著身體和精神的雙重折磨下,漢娜的軀體里也僅有麻木、仇恨和暴力。因此,當漢娜成為母親時,她將還是嬰兒的安琪拉塞進木柴堆里差點凍死,用牙撕咬安琪拉致使她臉上留下永遠的傷疤,最后又遺棄安琪拉使其輾轉寄養在不同的白人家庭。這一切都是自然的悲慘命運在印第安女性身上的創傷書寫,正如小說所說,“我們擁有相同的歷程,生命被摧殘,動物被虐殺,樹林被毀壞,我們的命運同這片土地緊緊相連”[2]96。主人公安琪拉童年時期痛苦的遭遇以及成長的經歷使她的心靈受到嚴重創傷,她缺乏安全感,與他人分離和疏遠,深陷于生存危機和身份危機的困境中。
人類中心主義宰制下的印第安部落,不但被剝奪了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更深陷于喪失文化和傳統的精神危機。面對土地被掠奪、資源被剝削、婦女被遺棄、種族將被滅絕、白人主流社會的文化滲透,印第安部落的文化傳統和精神信仰逐步地分裂瓦解。印第安人幻想著能重新奪回土地和家園,回歸原本的部落生活,卻承受著現實和幻想撕裂的精神創傷,沉浸在絕望與麻木之中。小說中,安琪拉和祖母們回到故土小鎮上,看到的是“部落的年輕人整日酗酒,跌跌撞撞,醉倒在街頭巷尾……酒精似乎成為醫治痛苦的唯一解藥”,“沒有酒的人們則更窮苦潦倒,不停地悲傷哭泣,并試圖自殘”[2]226。一方面,白人主流社會對自然的貪婪與物化的態度,導致“大地母親袒露著傷疤”[2]224;另一方面,大地母親滿目瘡痍的傷痛進一步印刻在部落人民身上。霍根借小說揭露白人主流社會對土地的暴行,更控訴其對印第安人民殖民式的宰制。正如她本人所說,“這里正發生的一切是對靈魂的謀殺,但兇手卻無需承擔任何后果”[8]。自然環境的破壞讓印第安部落群體不但失去生命的延續性,同時失去了傳統的信仰、身份的根基和精神內核,最終導致“集體性的經驗消亡”[9]。
3 生態自我的重新實現
米切爾·托馬斯豪指出,“生態自我”或生態身份描述的是個人與自然環境的聯系和態度,“生態自我是指我們如何建立自我意識與自然之間的聯系,而身份的建立是需要每一個人付出努力”[10]。馬休斯在《生態自我》一書里指出,人類的自我實現應當與非人類自我乃至整個宇宙自我相關聯,參與宇宙自我的自我實現,唯有如此,人的存在意義才能得到充分完美的實現,而生態的“大我”(Ecological Self)也只有建立了人主體與自然主體和諧共生的關系才可能實現[11]。小說的主人公安琪拉因被母親遺棄并不斷流離失所的經歷,導致自我身份的迷失,在追尋自我身份的過程中,她努力實現自身與自然萬物的融合依存,通過重建與自然的親密聯系,從“小我”成長為“大我”,最終實現了“生態自我”的回歸。
部落故事幫助安琪拉加深了自我與土地和族群身份的認同。印第安人的口述故事講述了美洲原住民的創世開源,與大自然的互惠共生的生活方式以及對自然的尊重和敬畏,歷史與傳統文化通過口述故事傳統世代相傳。安琪拉從部落長輩們的故事里了解自我與部落的關系,感知到自己的生命個體融入到部落群體的彼此關聯之中。“我現在認為她(曾祖母朵拉魯杰)是根,我們像是一棵樹的家庭,在地下相互連接,老樹滋養幼枝,讓其發芽成長,正是在這個古老的世界里我開始綻放,她們的故事召喚我回家。”[2]48安琪拉在與部落文化和歷史的重新連接中完成了生態自我的實現和身份的認同。印第安文化認為,人類的自我意識與物種起源的久遠記憶以及所有生物的存在共享相互聯系的記憶,失去生態記憶也就失去生態自我,因此,恢復生態記憶是人們恢復其生態自我的關鍵。
通過重建與自然的親密聯系,安琪拉重拾她的生態記憶并重建其生態自我。由于多年被寄養在白人家庭里,安琪拉受到西方人類中心主義主流價值觀的影響,將自然界視為“他者”。回到家鄉亞當肋骨鎮后,她開始感受到與自然之間的內在聯系:“(我)會聞到新鮮的空氣,在我的皮膚上感覺涼爽的微風,聽著隆隆聲和水聲。所有這些使我感到安慰”[2]43。有時她會想象著“我就像夜空的星星穿越時空時落下來,就像狼和魚一樣來到這里……我像狼一樣美麗”[2]54。隨著時間的流逝,她逐漸習慣了與自然融為一體。在養祖母布什的引導下,她開始在花園里工作,在水中劃槳,砍柴,捕魚,聆聽動物和風雪的歌唱。隨著安琪拉與自然的互動越來越多,她內心體會到更多的舒適與自在,對自然的偏見逐漸瓦解,她尋回了內心的寧靜與平衡,重建與自然的聯系,實現了生態自我,重新獲得對世界的歸屬感。
夢境地圖的重現預示了安琪拉重建與自然的聯系,實現了生態自我。印第安的文化認知中,夢境根植于大地,記錄了部落的歷史、傳統、文化,體現了人類與宇宙萬物的動態聯系,是人類與靈性世界溝通連接的路徑。小說中,安琪拉的曾祖母朵拉魯杰憑借“活地圖”的本領,一種“以口語敘述的方式匯聚印第安人的自然地理知識、地方的歷史與文化,融記憶圖、體驗圖與夢境圖為一體”[12]的印第安生態智慧,在從亞當肋骨鎮到雙城泛舟北上的旅行中,引領大家取道古老水路穿越荒野,安琪拉從中感受到萬物靈性的智慧,認同了土地的記憶與意識。在朵拉魯杰的幫助下,安琪拉逐漸恢復了夢境的能力,重建與自然的親密關系,“我遺失了生命的亮光,現在我再次找到它,夢境改變了我”[2]170。她意識到“在夢境里,人的內心可以與土地對話,找到自己的方向。人們夢見大地和水流,夢見食用的動物居住的地方,根據夢境地圖便可找到獵物。這是動物和人類共同的語言,人類以同樣的方式找到自我的療愈”[2]170。同時,有關植物的夢境喚醒了安琪拉。她感到內心里對于自然的記憶被喚醒并像“野生固有的,等待萌發的”種子一樣強勁生長。“也許夢的根源在日常的土壤中,或在心中,或在無法言說的地方,但是當它們聚在一起生長時,它們就像氫的種子和氧的種子,共同創造了海洋、湖泊和冰。這樣,我和植物彼此融合了。它們把我纏在莖和藤上,那是一個美麗的交融。”[2]171植物夢境加深了安琪拉對自然萬物的認知和敬畏,感受到自然豐富的靈性和無窮的生命力,自我與自然萬物的界限消解并融合為一體。
4 結語
在小說《太陽風暴》中,琳達·霍根通過書寫印第安部族的命運,表達其深層生態的理念,揭示了人類對自然環境與土地倫理的背離,不但造成了生態危機,更導致人類身份的迷失和精神的創傷。人類應擯棄人類中心主義的生態觀念,建立生物中心主義的平等生態觀,重建與自然的親密聯系并恢復生態記憶,才能重建生態自我,建立文明持續發展的生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