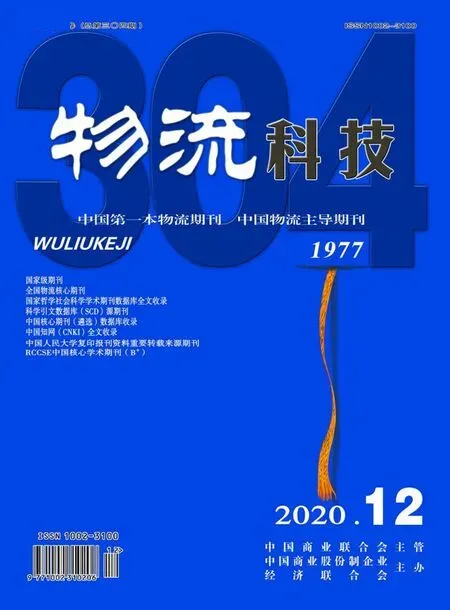基于超越對數成本函數的航空公司延誤成本測算
朱 江,黃建偉,亓洋洋,王樂樂 ZHU Jiang, HUANG Jianwei, QI Yangyang, WANG Lele
(上海工程技術大學,上海201620)
(Shangha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cience, Shanghai 201620, China)
0 引 言
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民航運輸業發展迅速,快速增長的市場需求同民航有限的資源之間的矛盾導致我國航班延誤現象日益嚴重。如圖1 所示,從2011 年至2015 年,國內主要航空公司航班正常率不斷走低,2015 年正常率僅為68.90%,在國際上處于落后水平。經過不懈的治理,近年來航班延誤率有所減少。2016 回升至76.54%,2017 年又跌至71.25%,2018 年正常率增至79.95%,但仍未達到民航管理當局設定的高于80.00%的目標,航班延誤問題仍然嚴峻。

圖1 國內主要航空公司航班正常率
航班延誤將導致航空公司運營成本的增加,包括航空器消耗更多的燃油,飛機等高價值設備資產的利用率降低,機組等人員工資支出增加等。都業富、田振才(2004)[1]通過研究測算1992 年至2002 年航班延誤的成本,并預測了2004 年至2020 年航班延誤成本,指出我國航班延誤成本呈逐年上升的趨勢,值得引起重視。但是基于20 年前數據對未來十余年的航班延誤成本所作的長期預測,通常很難確保預測精度。因此,對航班延誤問題建立數學模型,通過定性和定量分析較為準確地估算航班延誤對航空公司帶來的成本負擔,將有利于航空公司發現經營管理中的薄弱點,并針對出現的問題采取相應改善措施。為了測算航班延誤給航空公司所帶來的損失,本文將構建航空公司航班延誤Trans-log 成本函數模型,并將包含有航班延誤架次的航空公司經營過程中的眾多解釋變量納入,研究航空公司航班延誤對航空公司運營成本的影響,并針對研究結果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
1 文獻綜述
航班延誤引起的航空公司成本估算方法通常分為兩類。第一種是從航班運行的角度將航班運行的各個環節進行分類,分別計算各環節中航班延誤引起的損失,最后將其匯總估算出航班延誤總損失。李雄、劉光才等(2007)[2]通過將航班延誤損失劃分為航空公司損失、旅客經濟損失以及非經濟性的隱性損失,結合各環節各類損失計算公式,測算了2004 年及2005 年航班延誤的經濟損失。趙文智、劉博(2011)[3]通過將航班延誤成本劃分為常值費用、油費和時費三類,構建航班延誤成本模型,對B737-800 與A320-200 兩種常見機型進行延誤成本測算,指出在長時間延誤下,旅客的食宿費占比會隨著延誤程度逐步上升。
第二種是從宏觀的角度構建相關模型,將航班延誤或其它延誤相關變量作為模型的解釋變量,通過模型的擬合結果以及航班延誤相關變量在模型中對應系數的二者關系,從而估算航班延誤對航空公司運營成本的影響。2010 年,美國NEXTOR 研究了2007 年航班延誤對美國航空公司的影響,運用了超越對數成本函數測算了航班延誤造成的航空公司損失[4]。武勇彥、魚海洋(2017)[5]采用對數函數建立了航班航程與航速之間的關系,測算了2005 年中國航班時間延誤損失。馮敏、李鶴等(2007)[6]通過構建柯布—道格拉斯成本函數模型進行了估計,綜合考慮了各類影響,指出此模型適用于大規模、長時間的延誤成本測算。陳俁秀、于劍(2016)[7]通過將航班延誤時間作為模型的解釋變量之一,構建航空公司的成本函數模型,測算了2013 年國內航班延誤的航班計劃時刻延誤損失與航班計劃緩沖時間損失。
以上第一種方法不適用于長時間,全行業大規模的航空公司延誤成本測算,第二種測算方法大多只考慮到延誤時間這一解釋變量,而本文提出的延誤架次對比延誤時間有著更好的數據可獲得性和驗證性。因此,本文針對如上情況將航班延誤架次作為解釋變量,且以近年航空業的實際數據作為基礎,構建航空公司Trans-log 成本函數模型。該模型從宏觀的角度整體測算航班延誤對航空公司成本的影響,為航班延誤的治理打下理論基礎。
2 模型構建
2.1 影響因素選擇
企業的成本函數被定義為:在給定的投入要素價格Pit下,生產一定數量的產品Qit(i表示特定的航空公司,t表示時間),其成本:Y=f(Qit,Sit,Pit)。這表明可以通過構建航空公司成本函數模型來反映和研究航空公司的生產全過程,其中Qit表示航空公司的產出,本文選擇收入噸公里(RTM,Revenue-Ton-Miles) 來表示航空公司產出;Sit表示投入資本;Pit表示投入要素價格,航空公司的投入要素價格主要有三種,即燃油價格、材料價格及勞動力價格。
航空公司的成本也取決于航空公司產出的性質、質量及數量,因此在構建成本函數時需要考慮網絡經濟對航空公司的影響[8]。網絡經濟性包含密度經濟性和范圍經濟性,密度經濟性指航空運輸在保持平均航程、平均載運率及通航城市數量的基礎上,由于航空公司客貨運輸量的增加導致的單位運輸成本的下降;范圍經濟性指航空公司增加通航點擴大通航范圍時獲得更廣的輻射范圍,在維持航班平均航程、平均載運率和平均通航點運輸量不變的情況下,航空公司運輸的單位成本的下降。因此需要在成本函數模型中考慮航空網絡運營特點Nit,即Y=f(Qit,Sit,Pit,Nit)。Nit主要包含該航空公司的平均航程、平均載運率和通航城市數量。
航班延誤是航空公司生產活動中難以杜絕的擾動因素,天氣情況、空域管制、航空公司以及旅客等造成航班延誤的原因,航班延誤的發生則會增加航空公司的運營成本。因此,航空公司成本函數又可以擴充為Y=f(Qit,Sit,Pit,Nit,Dit),其中Dit表示航班延誤情況,本文模型中的延誤情況主要指航班延誤數量,模型相關解釋變量如表1 所示:

表1 解釋變量
2.2 模型構建
超越對數成本函數(Trans-log Cost Function, TCF)[9]實際上是Cobb-Douglas 成本函數的擴展,與Cobb-Douglas 成本函數相比,Trans-log 成本函數不以固定彈性為假設前提條件,其參數更容易通過標準統計方法進行估計。
模型使用的數據類型為面板數據,因此模型中包括了時間虛擬變量Tm及橫截面虛擬變量Ln,目的是為了表示隨著時間而發展的技術變化及某一航空公司對成本的特有影響;Pi(i=1,2,3)表示航空公司第i種投入要素的價格,分別是燃油價格、人均薪酬及材料價格[10];Ni(i=1,2,3)表示航空公司第i種網絡運營特征,分別是平均載運率、平均航程及通航城市數量;D表示航班延誤架次,為了使得平航班延誤架次能夠取到0,取其狀態值。
本文基于超越對數成本函數(Trans-log Cost Function, TCF) 構建航空公司成本函數模型,如式(1) 所示。

Trans-log 函數需要滿足投入要素價格的線性齊次性[11],因此,本文所建立的公式(1) 需要滿足以下的條件:

Shephard's lemma 指出投入要素的成本分攤份額方程可以用成本函數求出投入要素價格的偏導數得出[12-13],以所建立的模型求投入要素價格Pi(燃油價格P1、人均薪資P2、生產價格指數P3) 的偏導數,結果如式(3) 所示:

一般對成本函數(1) 與成本份額等式(3) 聯立求解以增加求解效率,聯立求解采用似無關回歸(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 SUR)[14]方法進行估計。并且為了克服異方差奇異矩陣問題,一般在使用SUR 方法求解之前去掉一個成本份額等式[15]。
3 數據及其描述性分析
本文采用2014 年至2018 年國內主要的4 家航空公司的面板數據(中國東方航空公司、中國國際航空公司、中國南方航空公司、海南航空公司)。2011 年至2018 年4 家主要航空公司運輸總周轉量均達到國內全部航空公司總周轉量的85%以上。
數據主要來源于各大航空公司年報、官方網站、中國統計局以及中國民航局年度報告。其中主營業務成本、收入噸公里、人均薪酬、平均航程、通航城市數量及平均載運率均來源于航空公司年報。平均燃油價格鑒于數據可獲得性,因此采用了布倫特原油價格作為參考。航空公司投入資本主要包括飛機及發動機、地面房屋建筑及高價周轉件的價值。由于航空公司投入要素價格中的材料價格獲取有難度,因此本文采用了扣除通貨膨脹因素的生產價格指數(PPI) 表示材料價格的變化。國內航班延誤架次可通過民航局年度報告與航空公司年報數據計算獲取,相關數據描述性統計如表2 所示。

表2 變量描述性統計
4 航空公司航班延誤損失測算
本文建立的Trans-log 模型求解是基于公式(1) 和公式(3) 聯立方程組,而在實際的數據搜集過程中會出現同一航空公司前后年份數據不全、不同航空公司數據口徑不一致等問題,因此本文統計搜集了2014 年至2018 年4 個主要航空公司5 年共計20 個樣本(4 個截面單位的5 年數據)。因為Trans-log 成本函數是由Cobb-Douglas 成本函數利用泰勒級數的二階展開式推導出,以取得更高的近似精度。因此,在本文數據量有限的情況下采取一階展開式對模型進行擬合。
運用EViews10 軟件建立4 個航空公司2014 年至2018 年的面板數據,運用似無關回歸對模型進行擬合。取a=0.05,在模型擬合結果中去掉了t-統計量不顯著的平均航程和員工平均薪資兩個解釋變量,之后再次嘗試擬合,最終建立的Trans-log 成本函數模型回歸結果如表3 所示。

表3 似不相關回歸(SUR) 結果
除了延誤架次以外所有納入的變量均取其對數值,為了使延誤架次能夠取值為0,因此取其狀態值納入。最終模型的R2為0.985,具有相當高的解釋力,證明了Trans-log 成本函數模型具有相當強的理論基礎,在樣本量較少的情況下仍然能夠有著相當高的擬合精度。
表3 中的所示解釋變量均通過了5%顯著性檢驗,說明航空公司主營業務成本與收入噸公里、投入資本、平均載運率、通航城市數量、燃油和PPI 指數有著顯著的相關性。最終構建如式(4) 的航空公司成本函數模型:

當航空公司在其他變量保持不變時,收入噸公里每提高1%其成本提高0.706%;投入資本每提高1%時其成本提高0.09%;當航班平均載運率每提高1%其成本降低0.542%;當通航城市數量每提高1%其成本增加0.242%。模型中關于航班延誤架次的系數則表明延誤的航班架次每增加1 千架次,其主營業務成本則增加0.0521%。
將航班延誤架次降低至0 時,保持其他變量不變,可測算出在無延誤情況下航空公司主營業務成本數值,航班延誤引起航空公司的損失即為:

根據以上模型,測算得到2018 年航班延誤共計給國內4 大主要航空公司帶來的成本增加約720.93 億,占當年主營業務成本的17.76%。2014 年至2018 年航班延誤成本及其占總成本比例結果如圖2 所示。

圖2 2014~2018 年航班延誤成本及其占總成本比例
5 結論與建議
本文通過構建航班延誤的Trans-log 成本函數模型并引入延誤航班架次作為解釋變量之一,間接地測算了航班延誤對航空公司的影響。2018 年航班延誤對我國4 家主要航空公司合計造成的成本增加達720.93 億元。由于延誤成本是通過增加航油、人工成本等項目隱性的增加,因此更容易被忽視。總結全文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1) 降低延誤成本為航空公司節約運營成本提供了一個有吸引力的潛在途徑。如能有效降低此項成本,對于航空公司節約成本提升盈利能力意義重大。
(2) 航班正常率與延誤成本/主營成本之間表現出一定的反向關系。對比圖1 和圖3 有關航班正常率和延誤成本占主營成本比率的數據,正常率相對較高的年份,其延誤成本占主營成本的比例較低。這意味著航空公司提高航班正常率有助于降低延誤成本。
(3) 降低航班延誤成本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各方協調運作和軟硬件共同投入。降低航班延誤需要加強民航監管機構、航空公司、機場、空管,甚至空軍的協調溝通,進一步提升管理水平[1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