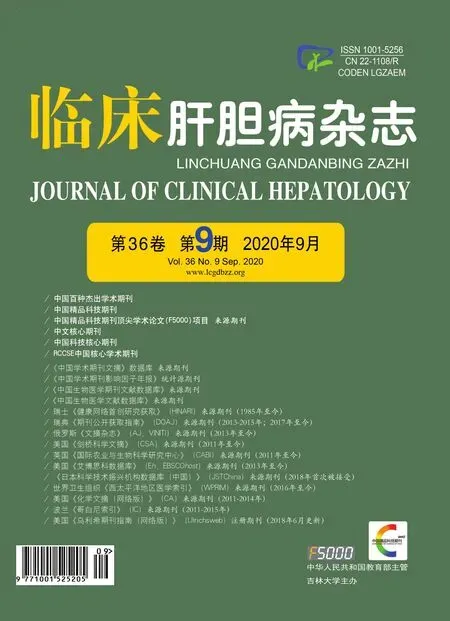腫瘤相關(guān)中性粒細(xì)胞在肝癌發(fā)生發(fā)展中的調(diào)控作用
胡 雷,高 麗,Dirk Hermann,陳艾東,
1 貴陽市婦幼保健院,貴陽 550003; 2 南京醫(yī)科大學(xué),南京 211166;3 西德腫瘤研究中心,杜伊斯堡-埃森大學(xué),德國 埃森 45122
肝癌是我國發(fā)病率較高的一種惡性腫瘤,預(yù)后差,近年來肝癌的發(fā)病率與病死率均呈上升趨勢。盡管手術(shù)技術(shù)、化療藥物和分子靶向藥物在不斷進(jìn)步,但由于大多數(shù)肝癌患者發(fā)現(xiàn)都是中晚期,容易惡化、進(jìn)展和遠(yuǎn)處轉(zhuǎn)移,治療效果并不理想[1-4]。因此,探索肝癌微環(huán)境中腫瘤惡化和轉(zhuǎn)移的發(fā)生機(jī)制,將有助于找到相關(guān)的治療靶點(diǎn)。
1 腫瘤相關(guān)中性粒細(xì)胞(tumor-associated neutrophils,TAN)
許多研究已經(jīng)通過免疫組織化學(xué)分析證明,作為另一種白細(xì)胞群的中性粒細(xì)胞混合在各種癌組織中。趨化因子是與G蛋白偶聯(lián)受體結(jié)合的小肽,可誘導(dǎo)化學(xué)吸收、炎癥和(或)血管生成[5]。它們是促進(jìn)癌癥轉(zhuǎn)移的關(guān)鍵因素之一。腫瘤細(xì)胞通常會(huì)產(chǎn)生幾種炎癥趨化因子,包括吸引中性粒細(xì)胞的CXC趨化因子[6]。中性粒細(xì)胞向腫瘤的遷移主要由與CXCR1和(或)CXCR2結(jié)合的CXC趨化因子介導(dǎo)[7]。中性粒細(xì)胞最初被視為先天免疫系統(tǒng)抵抗細(xì)胞外病原體的第一反應(yīng)者。然而,最近的證據(jù)證實(shí)了中性粒細(xì)胞的新功能。中性粒細(xì)胞參與先天性和適應(yīng)性免疫系統(tǒng)的調(diào)節(jié),并且可以響應(yīng)環(huán)境信號而極化為不同的表型。其特征是基于它們誘導(dǎo)吞噬作用、釋放裂解酶和產(chǎn)生活性氧(ROS)的能力[8]。在腫瘤微環(huán)境中,中性粒細(xì)胞在腫瘤浸潤中發(fā)揮重要作用,可以促進(jìn)腫瘤生長、侵襲、血管生成和轉(zhuǎn)移[9]。
最近的研究表明TAN具有相當(dāng)大的可塑性,能夠極化為抗腫瘤發(fā)生的“N1”表型或促腫瘤發(fā)生的“N2”表型[10];其表面標(biāo)志物,轉(zhuǎn)錄調(diào)節(jié)因子和細(xì)胞因子譜仍有待進(jìn)一步研究。中性粒細(xì)胞可分泌炎癥、免疫調(diào)節(jié)和血管生成因子,包括中性粒細(xì)胞彈性蛋白酶、基質(zhì)金屬蛋白酶(MMP)、血管內(nèi)皮生長因子(VEGF)和肝細(xì)胞生長因子[11],它們可以反映旁分泌對腫瘤微環(huán)境的影響。 “N1”中性粒細(xì)胞可通過產(chǎn)生TNFα、細(xì)胞間黏附分子(ICAM)、ROS和降低精氨酸酶表達(dá)而表現(xiàn)出增加的細(xì)胞毒性和降低的免疫抑制力。相反,“N2”中性粒細(xì)胞可通過表達(dá)精氨酸酶、MMP-9、VEGF和多種趨化因子(包括CCL2、CCL5和CXCL4)來促進(jìn)腫瘤轉(zhuǎn)移[12]。研究表明TGFβ信號傳導(dǎo)作為N1和N2表型之間的調(diào)節(jié)因子發(fā)揮作用。腫瘤內(nèi)的TGFβ使向N2表型的分化傾斜,而抑制TGFβ信號傳導(dǎo)誘導(dǎo)抗腫瘤N1表型[13]。總之,TAN的表型取決于腫瘤微環(huán)境中遇到的信號分子。TAN具有驅(qū)動(dòng)腫瘤血管生成的潛力。在小鼠模型中,TAN是MMP-9的主要來源,通過其細(xì)胞外基質(zhì)降解特性促進(jìn)血管生成[14-15]。CXCR2及其配體(即CXCL1、CXCL2、CXCL3、CXCL5、CXCL7和CXCL8)負(fù)責(zé)在正常生理?xiàng)l件下募集嗜中性粒細(xì)胞,并參與TAN的動(dòng)員。在攜帶腫瘤的小鼠模型中,靶向CXCR2介導(dǎo)的TAN動(dòng)員可增加腫瘤浸潤和淋巴轉(zhuǎn)移細(xì)胞的數(shù)量并增強(qiáng)抗凋亡。TGFβ參與了TAN兩種亞型之間的轉(zhuǎn)換,可以將TAN轉(zhuǎn)化到促腫瘤發(fā)生的N2表型;反之,抑制TGFβ,則可以誘導(dǎo)其向抗腫瘤發(fā)生的N1表型轉(zhuǎn)化[15]。綜上所述,可以通過阻斷TGFβ發(fā)揮對TAN靶點(diǎn)的干預(yù),進(jìn)而實(shí)現(xiàn)對肝細(xì)胞癌的治療。在肝癌微環(huán)境中癌細(xì)胞會(huì)生成多種趨化因子和TAN細(xì)胞表面的受體結(jié)合,啟動(dòng)其向N2表型轉(zhuǎn)化,進(jìn)而促進(jìn)腫瘤發(fā)生發(fā)展、侵襲和轉(zhuǎn)移,因此,干預(yù)TAN,阻止其向N2轉(zhuǎn)化,成為抗腫瘤治療的重要思路。
2 TAN是肝癌治療的潛在靶點(diǎn)
TAN作為潛在治療靶點(diǎn)的作用仍在評估,因?yàn)槠湓诎┌Y發(fā)展和轉(zhuǎn)移中的作用尚不完全清楚。考慮到TAN在腫瘤進(jìn)展中的作用,靶向癌癥中的中性粒細(xì)胞可能是一種潛在的新型抗腫瘤療法。然而,對于中性粒細(xì)胞的過度殺傷,可導(dǎo)致免疫抑制,因?yàn)橹行粤<?xì)胞是人體防御感染所必需的。因此,阻斷特定的中性粒細(xì)胞群,尤其是TAN,可以促進(jìn)腫瘤消退或抑制其轉(zhuǎn)移和擴(kuò)散,在此過程中還不會(huì)影響抗感染免疫。最新研究[16]表明,TAN可在肝癌微環(huán)境中促進(jìn)腫瘤增殖、血管生成和上皮-間質(zhì)轉(zhuǎn)化,TAN浸潤是疾病預(yù)后不良的重要指標(biāo)。另一個(gè)團(tuán)隊(duì)的研究[17]表明TAN可以將腫瘤相關(guān)巨噬細(xì)胞和調(diào)節(jié)性T淋巴細(xì)胞(Treg)募集到肝癌腫瘤微環(huán)境中,以促進(jìn)癌細(xì)胞生長、進(jìn)展,并產(chǎn)生對索拉非尼的抗藥性。招募來的腫瘤相關(guān)巨噬細(xì)胞,通過釋放細(xì)胞因子促進(jìn)腫瘤發(fā)生、發(fā)展和轉(zhuǎn)移[16]。研究[17]表明肝癌患者Treg的水平明顯增加,其與腫瘤細(xì)胞的侵襲性密切相關(guān)。免疫系統(tǒng)是一個(gè)重要的網(wǎng)絡(luò),如果想獲得很好的靶向治療效果,可以通過系統(tǒng)干預(yù)TAN、腫瘤相關(guān)巨噬細(xì)胞和Treg,取得綜合治療效果,但其相關(guān)療效和分子機(jī)制有待進(jìn)一步研究。
由于TGFβ調(diào)節(jié)中性粒細(xì)胞的促腫瘤表型和抗腫瘤表型,因此TGFβ阻斷可能是一種潛在的重要治療策略。趨化因子阻斷可能是導(dǎo)致中性粒細(xì)胞向腫瘤募集受損的另一種有效策略。肝細(xì)胞癌與CXCL8的過度表達(dá)具有高度相關(guān)性,從健康供體分離的人Treg可以分泌高水平的CXCL8,并促進(jìn)中性粒細(xì)胞的募集。由于從肝臟分泌的CXCL8募集中性粒細(xì)胞,通過中和抗體阻斷CXCL8軸可能是一種很好的治療方法。然而,其對肝癌微環(huán)境或腫瘤內(nèi)中性粒細(xì)胞表型的影響仍需要更深入的研究。此外,TAN的存在被證明是肝癌復(fù)發(fā)的獨(dú)立預(yù)后因素,和整體存活率相關(guān)[18]。在復(fù)制的肝細(xì)胞癌的腫瘤微環(huán)境中,TAN 會(huì)釋放很多小分子和細(xì)胞因子,影響腫瘤進(jìn)展和惡化。研究[18]發(fā)現(xiàn),肝癌細(xì)胞可以通過激活TAN,進(jìn)一步激活趨化因子配體2 (CCL2),而CCL2被證實(shí)和腫瘤大小、血管浸潤、分化程度和惡性分期等密切相關(guān)。而且,他們可以通過影響腫瘤相關(guān)巨噬細(xì)胞和Treg,發(fā)揮腫瘤細(xì)胞的遷移活性。這些被招募來的促進(jìn)腫瘤進(jìn)展的免疫細(xì)胞,如TAN、巨噬細(xì)胞和Treg,成為促進(jìn)癌細(xì)胞侵襲和轉(zhuǎn)移的影響因素。
3 中性粒細(xì)胞與淋巴細(xì)胞的比值(NLR)是肝癌預(yù)后的生物標(biāo)志物
中性粒細(xì)胞對腫瘤的發(fā)生、發(fā)展和預(yù)后有著一定的影響,其與肝癌的關(guān)聯(lián)性也不斷地被研究和證實(shí)。NLR是全身免疫系統(tǒng)功能的評價(jià)指標(biāo),是影響腫瘤患者預(yù)后的獨(dú)立因素。肖維木等[19]選取149例肝癌手術(shù)患者,將其分為高NLR組(63例)(NLR≥2.37)和低NLR組(86例)(NLR<2.37),比較兩組的總膽紅素、甲胎蛋白等預(yù)后評判相關(guān)指標(biāo),發(fā)現(xiàn)NLR對患者的預(yù)后有很好的預(yù)測價(jià)值。何朝濱等[20]回顧分析了216例接受經(jīng)肝動(dòng)脈栓塞化療(TACE)的肝癌患者的資料,多因素分析顯示NLR≥1.77與TACE術(shù)后較差的預(yù)后相關(guān),是TACE治療后影響患者生存的危險(xiǎn)因素。鄧國榮等[21]根據(jù)NLR將387例患者分為低NLR組(NLR<2.0)和高NLR組(NLR≥2.0),比較分析兩組患者的臨床特點(diǎn)和預(yù)后,發(fā)現(xiàn)低NLR組患者5年生存率明顯高于高NLR組,分別為31.6%和7.3%,術(shù)前NLR水平與預(yù)后呈負(fù)相關(guān),對接受根治手術(shù)的原發(fā)性肝癌患者,術(shù)前NLR水平與預(yù)后呈負(fù)相關(guān),術(shù)前NLR水平為其獨(dú)立預(yù)后因素。研究表明術(shù)前NLR與肝細(xì)胞癌患者的預(yù)后顯著相關(guān)[22]。綜上所述,NLR是肝癌患者預(yù)后評判的理想生物標(biāo)志物。
4 總結(jié)
越來越多的證據(jù)表明,肝癌中性粒細(xì)胞在腫瘤微環(huán)境中起著重要作用。 TAN表現(xiàn)出抗腫瘤發(fā)生的N1表型或促腫瘤發(fā)生的N2表型之間的可塑性,并由來自組織的信號分子確定其表型變化。大量研究證明了中性粒細(xì)胞促進(jìn)肝癌惡化和轉(zhuǎn)移的潛在機(jī)制,干預(yù) TAN可能成為肝癌治療的新靶標(biāo)。但肝細(xì)胞癌微環(huán)境中存在腫瘤相關(guān)巨噬細(xì)胞、Treg和多種細(xì)胞因子等,可能會(huì)影響免疫治療的抗腫瘤活性,系統(tǒng)干預(yù)和綜合治療可能會(huì)獲得滿意的療效。隨著對腫瘤微環(huán)境的深入了解,開發(fā)針對性的綜合靶向治療方案,可為肝細(xì)胞癌的治療帶來曙光。
作者貢獻(xiàn)聲明:胡雷負(fù)責(zé)綜述文獻(xiàn)收集和撰寫;高麗負(fù)責(zé)修改論文;陳艾東和Dirk Hermann負(fù)責(zé)擬定寫作思路,指導(dǎo)撰寫文章并最后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