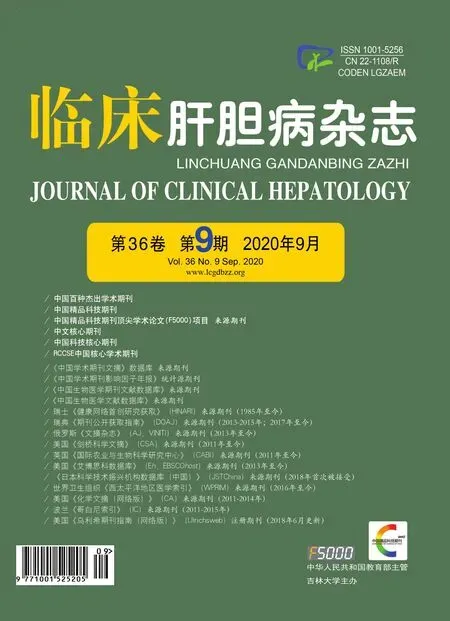原發(fā)性膽汁性膽管炎高危因素的研究進展
廖海玲,楊晉輝
昆明醫(yī)科大學(xué)第二附屬醫(yī)院 消化內(nèi)科,昆明 650000
原發(fā)性膽汁性膽管炎(PBC)是一種慢性膽汁淤積性疾病,PBC可以發(fā)生在各個年齡段的成人中,但是以中老年女性最為常見,其特點是慢性非化膿性破壞性膽管炎、肝內(nèi)肉芽腫形成、膽道上皮細(xì)胞變性、肝內(nèi)小膽管消失,導(dǎo)致慢性進行性膽汁淤積、肝纖維化[1]。起初患者的主觀癥狀不明顯,多數(shù)患者都是在偶然間發(fā)現(xiàn),隨后患者會出現(xiàn)乏力、瘙癢、黃疸、腹水等癥狀。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例如干燥綜合征、類風(fēng)濕關(guān)節(jié)炎等常與PBC并存[2]。隨著疾病進展,最終導(dǎo)致肝硬化和肝衰竭。單核細(xì)胞向肝內(nèi)小膽管中的大量浸潤,高滴度疾病特異性自身抗體[即抗線粒體抗體(AMA)]的存在以及常作為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合并癥均表明自身免疫在疾病發(fā)病機理中發(fā)揮著至關(guān)重要作用[3-4]。
與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一樣,PBC也是一種多因素疾病,其病因可能與遺傳學(xué)和環(huán)境因素有關(guān),具有遺傳易感性的個體可能會因為環(huán)境觸發(fā)因素而發(fā)展為PBC[4-5]。目前大量的病例分析和實驗室研究[6]表明,細(xì)菌感染是破壞PBC線粒體自身抗原耐受性的最重要環(huán)境因素之一。
1 AMA表位
AMA是一種高度特異性的自身抗體,大約95%的PBC患者有AMA,因此為該病提供了一種標(biāo)志物。其主要識別位于線粒體內(nèi)膜的一類酶,即2-羥基脫氫酶復(fù)合物(2-OADC),主要包括:丙酮酸脫氫酶復(fù)合物E2亞基(PDC-E2)、支鏈2-羥基脫氫酶復(fù)合物(BCOADC-E2)和2-羥基戊二酸脫氫酶復(fù)合物。這些E2酶都共享一個共同的蛋白質(zhì)結(jié)構(gòu),由一個含有單個或多個脂基的N端結(jié)構(gòu)域組成,與脂酸的賴氨酸有一個或多個連接位點[7]。AMA表位特異性在PBC患者2-OADC-E2酶脂質(zhì)體結(jié)構(gòu)域內(nèi)的唯一性提示脂質(zhì)體結(jié)構(gòu)域可能是PBC病因?qū)W的關(guān)鍵[8]。PDC-E2是一種主要的人類抗線粒體自身抗原,在多種物種中具有高度保守性,與許多微生物的PDC序列具有高度相似性[9]。感染或接觸與人類PDC-E2有密切同源性的微生物,可作為啟動PBC發(fā)展的免疫學(xué)觸發(fā)器。線粒體自身抗原PDC-E2天然脂酰部分的異種生物修飾,可能導(dǎo)致自身耐受的丟失,最終發(fā)展為膽道病變[10]。有數(shù)據(jù)[10-12]進一步表明,PDC-E2脂酸的化學(xué)修飾,通過對脂酸二硫化鍵的親電攻擊,導(dǎo)致對PDC-E2失去耐受。
2 PBC的危險因素概述
目前,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PBC的發(fā)生發(fā)展中存在許多危險因素。1984年Burroughs首次發(fā)現(xiàn)了尿路感染可能與PBC有關(guān)聯(lián)。當(dāng)時Burroughs發(fā)現(xiàn)在87例PBC女性患者中有17例(19%)有細(xì)菌尿,此外89例其他類型的慢性肝病女性患者(7%)中也同樣發(fā)現(xiàn)了顯著的細(xì)菌尿(P<0.05)[13]。大腸桿菌是最常見的分離生物,在70%的感染者中都能被檢測到。1989年,F(xiàn)loreani等[14]進行了一項研究,選取了160例PBC患者,140例其他慢性肝病患者以及28例干燥綜合征患者檢測細(xì)菌尿的發(fā)生率。研究發(fā)現(xiàn),在PBC中,細(xì)菌尿的總體患病率為11.2%,慢性肝病為12.1%,干燥綜合征為10.7%,該研究證明PBC與細(xì)菌尿之間沒有特定的關(guān)聯(lián)。盡管這兩項研究規(guī)模較小,且缺乏與年齡等因素的對照組,但還是沒有阻礙研究人員將尿路感染納為PBC重要環(huán)境危險因素之一。
21世紀(jì),美國和歐洲進行了幾項大規(guī)模的病例對照研究以調(diào)查PBC的危險因素。Howel等[15]基于英格蘭東北部的人群進行了一項病例對照研究,這項研究招募了100例1993年-1995年的PBC患者,以及223例年齡、性別均匹配的對照組。研究發(fā)現(xiàn)PBC與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僅存在弱關(guān)聯(lián),而與手術(shù)程序、妊娠事件、既往感染、疫苗接種和藥物沒有顯著關(guān)聯(lián)。10年后,Prince等[16]在Howel等進行的同一地理區(qū)域內(nèi)進行了病例對照研究,他們從地理上定義的流行病學(xué)研究(n=318)和從英格蘭東北部國家支持小組的調(diào)查(n=2258)中識別出兩組PBC病例,其數(shù)據(jù)表明,在單變量分析中,與對照組相比,PBC與吸煙、染發(fā)劑使用頻率、既往的尿路感染史、牛皮癬病史、帶狀皰疹病史和先前的自身免疫疾病病史之間存在顯著相關(guān)性,這是流行病學(xué)病例和基礎(chǔ)病例中PBC的危險因素。2001年,Parikh-Patel等[17]招募了241例PBC患者及其261例兄弟姐妹,以及141例沒有PBC的普通人。他們評估了女性的尿路感染或陰道感染與PBC的相關(guān)性,結(jié)果具有統(tǒng)計學(xué)意義(校正后的OR=2.12,95%CI:1.10~4.07)。且他們發(fā)現(xiàn),在多變量模型中吸煙的重要性支持了先前研究的結(jié)果,并提出了吸煙對輔助性T淋巴細(xì)胞1反應(yīng)的影響問題。另一項美國有史以來最大規(guī)模的病例對照研究[18]選取了1032例PBC患者和1041例對照者,數(shù)據(jù)表明,與PBC有一級親屬關(guān)系[調(diào)整后的優(yōu)勢比(AOR)=10.736,95%CI:4.227~27.268]、尿路感染史(OR=1.511,95%CI:1.192~1.915)、過去吸煙(OR=1.569,95%CI:1.292~1.905)或激素替代療法(OR=1.548,95%CI:1.273~1.882)與PBC風(fēng)險增加顯著相關(guān)。2010年法國的一項研究[19]從2006年到2007年選取了22例PBC患者,證實了先前報道的一些PBC危險因素,即疾病的家族史、個人吸煙史、尿路感染和自身免疫性疾病,并進一步確定了口服避孕藥作為推薦的保護因素,但是由于樣本較小,統(tǒng)計意義水平相對較低,因此需要謹(jǐn)慎的結(jié)論。
綜上所述,各種細(xì)菌感染、香煙煙霧中所含的化學(xué)物質(zhì)、女性化妝品(染發(fā)劑)中的某些成分可能在遺傳易感人群中誘導(dǎo)PBC。
3 細(xì)菌感染
3.1 大腸桿菌感染 大量流行病學(xué)證據(jù)表明PBC與細(xì)菌感染有關(guān),尿路感染復(fù)發(fā)史與PBC的相關(guān)性已被大規(guī)模的病例對照研究頻繁證實。大腸桿菌是一種主要的致病菌[20],尤其是在女性患者中,而復(fù)發(fā)性尿路感染的新感染是PBC的特征之一。Burroughs和Baum于1992年提出PBC和復(fù)發(fā)性尿路感染之間的聯(lián)系可能是由于人和大腸桿菌PDC-E2表位之間的分子模擬[21]。該研究還提出,來自大腸桿菌的B或T淋巴細(xì)胞PDC表位可模仿人PDC或BEC表位,從而異常表達(dá)人類白細(xì)胞抗原(HLA)-DR抗原。與對照相比,PBC患者中抗人PDC-E2對大腸桿菌PDC-E2的親和力高100倍。
3.2 新鞘氨醇桿菌屬溶芳烴單胞菌 新鞘氨醇桿菌屬溶芳烴單胞菌(N. Aromaticivorans)是一種革蘭陰性需氧菌,歸類為鞘脂單胞菌科α-變形菌綱[22]。這種微生物無所不在,可以存在于全球的土壤、水和沿海平原沉積物中。研究認(rèn)為N. Aromaticivorans可以通過兩種方式打破自我耐受性:即通過亞臨床感染引起的分子模擬和異源生物的代謝。N. Aromaticivorans在已知微生物中與線粒體自身抗原之間存在最高的同源性,有研究證明,AMA與N. Aromaticivorans的兩種已知的脂酰化細(xì)菌蛋白具有較高的交叉反應(yīng)性,這種效價比大腸桿菌高100~1000倍。此外,N. Aromaticivorans還具有代謝異生物素的能力,這些異生物素被證明對PBC患者的血清具有反應(yīng)性[23],而這些異生物素中有一些與硫辛酸免疫相關(guān),硫辛酸是PDC-E2活性中心的輔因子。
3.3 其他細(xì)菌 在一項研究中,幾乎在所有PBC患者的肝臟中都檢測到了類似幽門螺桿菌的DNA,但只有1例非膽汁淤積性肝病患者和正常對照中均未檢測到[24]。 有研究認(rèn)為在PBC患者中出現(xiàn)的由幽門螺桿菌感染引起的分子模擬[25]可能是與膽管抗原的交叉反應(yīng)而引起自身免疫反應(yīng)有關(guān)。而研究顯示,幽門螺桿菌在PBC的發(fā)展中并沒有起因果作用。因此,就幽門螺桿菌是否為PBC潛在致病因素還存在較大的爭議。
Bogdanos等[26]發(fā)現(xiàn)德氏乳桿菌保加利亞亞種可能通過破壞線粒體自身抗原的耐受性從而觸發(fā)PBC。德氏乳桿菌保加利亞亞種是在酸奶生產(chǎn)中用于發(fā)酵劑發(fā)酵的益生菌微生物。研究[27]發(fā)現(xiàn),德氏乳桿菌β-半乳糖苷酶的SxGDL[ILV]AE基序的IgG3抗體可以存在于AMA陽性PBC患者的血清中,并與人PDC-E2發(fā)生交叉反應(yīng)。 Abdulkarim等[28]研究發(fā)現(xiàn),PBC患者肝組織中存在肺炎衣原體抗原和RNA,但不存在沙眼衣原體,提示肺炎衣原體抗原可能會觸發(fā)基于分子模擬的免疫反應(yīng)。而有的研究結(jié)果并不支持肺炎衣原體感染可能是PBC的觸發(fā)劑的假設(shè),另有研究表明肺炎衣原體感染可能導(dǎo)致大多數(shù)PBC患者中IgM水平升高[29]。
4 病毒感染
目前的研究表明,某些病毒可能與PBC的發(fā)病有關(guān)。在PBC小鼠模型中,人乙型逆轉(zhuǎn)錄病毒和與之密切相關(guān)的小鼠乳腺腫瘤病毒分別與膽管炎和AMA產(chǎn)生有關(guān)[30]。早在1992年,Morshed等[31]就發(fā)現(xiàn),PBC患者肝組織和唾液中愛潑斯坦-巴爾病毒(EBV) DNA的水平明顯升高,他們認(rèn)為早期PBC患者血清中EBV抗原滴度升高表明它可能觸發(fā)PBC。
5 異生物素
研究表明,異生物素在PBC發(fā)展中發(fā)揮著重要作用。異生物素是一種外來化合物,它可以替代、改變自身蛋白,從而誘導(dǎo)自身蛋白結(jié)構(gòu)轉(zhuǎn)變?yōu)榛越Y(jié)構(gòu),然后打破耐受,這種反應(yīng)會因天然肽的持續(xù)存在而持續(xù)。眾所周知,PBC中的AMA和細(xì)胞應(yīng)答主要針對PDC-E2的脂酰結(jié)構(gòu)域。硫辛酸對于PDC-E2的識別至關(guān)重要,并且暴露于復(fù)合物的外部,因此構(gòu)成了異生物素修飾的理想目標(biāo)[32]。有研究對107種潛在的外來生物模擬物與PDC-E2內(nèi)脂酰域免疫顯性15-氨基酸肽賴氨酸殘基偶聯(lián)進行了詳細(xì)的定量結(jié)構(gòu)-活性關(guān)系分析,結(jié)果表明,化妝品、口紅和一些口香糖中含有的2-辛烯酸偶聯(lián)物2-辛烯酰胺,其定量結(jié)構(gòu)-活性關(guān)系分析與PBC血清的反應(yīng)性均較好[33]。此外,有研究[34]發(fā)現(xiàn)頻繁使用指甲油會稍微增加患PBC的風(fēng)險,但患病風(fēng)險概率很低,因此下結(jié)論時應(yīng)謹(jǐn)慎。
有研究[35]提出了許多其他可以增加PBC風(fēng)險的環(huán)境,例如暴露于環(huán)境污染物和輻射中。在日本進行的一項研究中,長崎原子彈幸存者中的PBC患病率高于一般人群。在有毒廢物堆積的地方發(fā)現(xiàn)了大量PBC患者,這表明毒素暴露可能是PBC的危險因素[36]。但是,這些發(fā)現(xiàn)很難得到驗證。
6 遺傳因素
PBC具有很強的遺傳基礎(chǔ),一級親屬的相對風(fēng)險比普通人群高50至100倍。有研究[37]評估了具有遺傳定義的雙胞胎患PBC的一致性,研究發(fā)現(xiàn)在8個單卵雙胞胎中,有5對雙胞胎,兩個人同時患有PBC(成對一致性率為0.63),且其中有4對雙胞胎發(fā)病年齡相似。但是,自然病史和疾病嚴(yán)重程度存在差異。然而,在同卵雙生子中(n=8),未發(fā)現(xiàn)PBC的一致性。關(guān)于女性更易患PBC的原因,已經(jīng)提供了幾種假設(shè)。在PBC中已經(jīng)確定了更高的X-單體分離率[38],暗示了X染色體上存在一種免疫調(diào)節(jié)蛋白基因。此外,多項全基因組關(guān)聯(lián)研究表明,HLA-DR * 7、* 8等位基因多態(tài)性,HLA Ⅱ類、IL-12A和IL-12RB2基因座的常見遺傳變異與PBC存在顯著關(guān)聯(lián),并提示IL-12免疫調(diào)節(jié)信號軸與PBC的病理生理學(xué)相關(guān)。而DR * 11、* 12、* 13和* 15等位基因多態(tài)性是某些人群的保護因素[39-40]。有趣的是,全基因組關(guān)聯(lián)研究參與PBC發(fā)病機制的許多基因也已報道于其他免疫介導(dǎo)的疾病中,因此,更大范圍了解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發(fā)病和發(fā)展機制可能會相應(yīng)地揭示PBC中的某些機制。
7 總結(jié)與展望
目前,環(huán)境因素和遺傳因素是公認(rèn)的影響PBC的重要因素,但是仍需要進行大規(guī)模、多中心的病例對照、流行病學(xué)研究以及內(nèi)容豐富的基因?qū)W研究去評估各個因素的作用,以明確其作用機制,更好的預(yù)防和治療P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