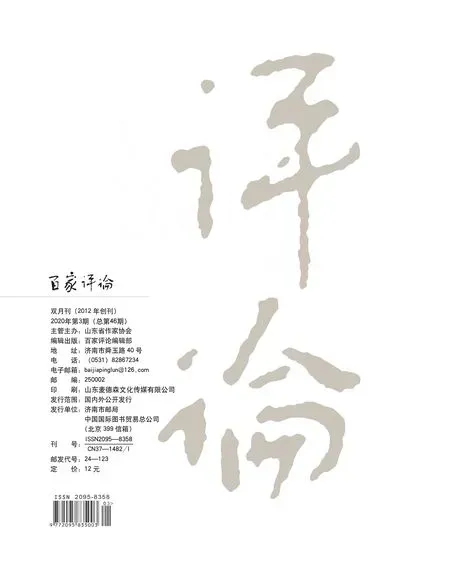小說意象世界的建構與探索
——評房偉長篇新作《血色莫扎特》
內容提要:《血色莫扎特》是房偉新近創作的長篇小說。該小說是房偉在現實主義創作路徑上進行的個性化探索。在突出故事性敘事特征的同時,小說運用“音樂”“刀子”與“蛇”三個意象對主題話語進行豐富和深化,并產生了強烈的藝術沖擊力。“音樂”意象構成人物情感發展的媒介,主導了小說敘事的情感基調。“刀子”意象指向深刻的時代困惑,有效呈現和表現了時代的某種癥候。“蛇”意象成為當下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注腳,為小說主題話語增加了懲罰和救贖的復雜元素。三個意象的內涵層層深入,具有鮮明的意象審美特征,并顯示出獨特的創新品格。
房偉的小說創作愈來愈引起讀者和批評界的關注。繼短篇小說集《獵舌師》后,房偉推出長篇新作《血色莫扎特》。從批評家向小說家的“轉換”中,房偉的每一次創作總能給讀者帶來新閱讀體驗。《血色莫扎特》也是如此。房偉這次是想在現實主義的創作路徑上進行個性化探索。《血色莫扎特》寫了一個謀殺案的故事,很像慣常的“懸疑小說”。故事發生在一座北方小城,從“兇手還鄉”開始敘事。小說采用了多視角敘述的結構,五個好朋友,除去“一死一逃亡”以外,剩下的三人輪流講述,追索真兇的敘述時間中交織著故事時間,敘述線索中散落著無數回憶碎片。小說中每個人都有訴說機會,每個人都有難以啟齒的秘密,這對“懸疑”氛圍的營造恰到好處。但房偉顯然沒有把小說敘事停留在故事和結構的淺表層面。小說中,房偉注重“虛實相生”敘事效果,在清晰的敘事表征之中賦予主題話語更多復雜性,從而形成了宏闊的藝術境界,正如宗白華所說:“化實景為虛境,創形象以為象征,使人類最高的心靈具體化、肉身化,這就是‘藝術境界’。”①這個過程中,意象具有了獨特藝術作用。對其中意象的理解就成為走近該小說世界的重要通道。在《血色莫扎特》的情節推進過程中,“音樂”“刀子”與“蛇”三個意象讓人印象深刻,它們支配著整個小說的敘事基調,意象內涵層層深入,形成了強烈的藝術沖擊力。我們就從這三個意象開始,討論《血色莫扎特》的意象特征,從而走進其豐富的小說世界。
一、音樂:情感的基調和媒介
首先是“音樂”意象。從小說命名中的“莫扎特”一詞,讀者就可以感受出來“音樂”意象的某種特征。從小說的整體敘事來看,“音樂”意象貫穿始終,并蘊含了多種闡釋的可能性。無論是人物之間的聯系,還是人物命運的發展,音樂都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影響要素,對故事氛圍的形成和人物情感的聯結都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
一是“音樂”意象決定了小說敘事情感的基調。小說題目中的“莫扎特”,一方面指美妙的音樂,另一方面成為一種隱喻——即“莫扎特”這一偉大音樂家人生遭遇的隱喻,如小說最后所注“莫扎特之死,是音樂史上的謎團”,指出有研究者認為莫扎特死于謀殺,其死亡與婚外情和音樂都脫不開關系。這顯然為小說定下了悲劇的基調。小說正是在這個基調中形成了整體的敘事情感,并在其中推進故事的發展。這個情感基調,我們從主人公葛春風的敘述語氣中就能明顯感受出來,比如他認為:“‘明亮耀眼’的東西,都是害人的。比如,音樂,舞蹈,友誼,愛情,刀子。”葛春風將“明亮耀眼”和“害人的東西”畫上等號,這近乎是一種病態的傾訴,呈現出某種壓抑的悲傷語調。葛春風正是以這樣的語調進行敘述,回憶曾經的莊嚴歌劇和優雅的鋼琴曲,再從幻想中的維也納金色大廳回到現實中的“苗苗的客廳”,從而形成小說的傷感敘事氛圍。
如果說夏冰和韓苗苗的情感敘事是這種基調中主要展開的對象,那么夏冰和女學生馮露的遭遇則形成了敘事情感中最低沉的部分。情竇初開的少女戀慕年輕有才華的鋼琴老師,盡管這位老師是有婦之夫,她還是無法克制自己的情感。音樂引導著兩個人彼此靠近,迸發出道德之外的情感。這種愛情也是音樂的劊子手,馮露葬送了夏冰的“音樂生涯”:“他的手在糞池里,他的頭腦中卻響徹著莊嚴的音樂劇。”這種相遇打擊了一個“鋼琴王子”的自尊心,并因此摧毀了他的音樂世界。正是在這一刻,那些音樂大師一個個從夏冰的頭腦中“告別”式地掠過,這宣告著夏冰音樂夢想的終結。從此,夏冰認為自己無法再用這雙“骯臟”的手撫摸琴鍵了,他不愿再去“褻瀆”大師的作品。馮露用這段畸形的愛情毀掉了夏冰充滿浪漫想象的音樂世界,同時也使她失去了自己的“音樂夢”。在這里,音樂不僅形成一種“事件”,而且也使人物的心理和觀念形象化,形成了“音樂”意象,從而強化了故事的悲劇氛圍。
二是“音樂”意象構成人物情感發展的媒介。“藝術的生命不是‘物’,而是內蘊著情意的象(意象世界)。”②小說中,主要人物的情感發展正是通過“音樂”媒介來完成的。大學時代,葛春風因為好奇結識了“鋼琴王子”夏冰,繼而認識了韓苗苗。青春時代的單純美好就像一首悠揚的鋼琴曲,音樂也成為青春、自由和激情的象征。韓苗苗是只“高貴的天鵝”,然而她的舞蹈也離不開“麋鹿”夏冰的音樂配合,音樂成就了這對校園里的“金童玉女”,而悲劇也從這里開始。值得注意的是,幾次大型的文藝演出不僅推進了小說的情節,而且也是人物情感建立和發展的支點。在故事情節中,人物往往在充滿音樂的場景中相聚,譬如,在畢業后的演出現場幾個主要人物的相逢,等等。人物的每次相聚都會出現不同往昔的情感交流,產生新的情感況味,形成新的情感線索,而此時音樂不僅是情感發展的媒介,也是人物精神世界的某種象征,形成顯著的審美意象特征。
“苗苗的客廳”是小說中突出描寫的場所。這個場所實際上是一個家庭聚會的地方。幾個好朋友在閑暇之余,相約在韓苗苗的客廳組織音樂沙龍,音樂是失意青年們的情感寄托。走出象牙塔之后的夏冰和韓苗苗,也只能在自己的客廳“施展才華”。他們在這里放縱歌舞,訴說或者傾聽對方未曾實現的夢想,在音樂中進行嘲笑和自嘲,安放理想或釋放欲望。在這個“烏托邦”的世界里,他們分享著不同風格的音樂,用音樂的在場來淹沒和實現一切。在這個過程中,理想與現實、真實與荒誕、欲望與情感、物質與精神在狹小的空間中混雜、融合,這個空間就是這些青年的精神王國。房偉濃墨重彩地描寫了“苗苗的客廳”,在敘事中顯得自然順暢,同時又呈現出別具匠心的藝術效果。“苗苗的客廳”是邊緣的和壓抑的,也是放縱的和自由的,它與外部的環境相望和對峙,并以音樂混響的形式與環境對抗,從而形成了強烈的藝術感染力。音樂已經被“抽象化”,形成了一種復雜的時代精神象征。
人物情感的終結甚至是死亡也都有“音樂”意象的在場。譬如,小說最后對夏雨的死亡描寫。夏雨選擇和母親韓苗苗一樣,決定在音樂劇的旋律中了結所有的情感,走向生命的終結。死亡是一種抗爭,“在文學的視野里,死亡本身不再是只具有社會認識價值而變得毫無意義,死亡本身還是另一種方式的抗爭,是世界的另一種真實”。③房偉對其死亡方式的安排也充滿了更多的意味。夏雨在音樂中生,也在音樂中死,音樂在其生死之中形成一種尖銳而又沉悶的力量,生成了震撼人心的藝術力量。在這里“音樂”意象已不再停留在某種觀念的具象化,而是上升到審美層面,有效參與了小說主題話語和藝術內蘊的建構。
當然,“音樂”意象也并沒有失去對“美”的一種象征。它在小說的敘事中也指代了美好的青春、夢想與追求,對葛春風、韓苗苗、夏冰等人物的精神世界也涂抹了一層絢爛的浪漫色彩。這種色彩與灰暗的現實色調調和在一起,共同形成了“音樂”意象的復雜內涵。在這個基礎上,小說對“音樂”意象包裹著的世界進行了深入的探尋,探尋的結果則是“刀子”意象所指涉的對象。
二、刀子:命運和時代癥候的一種指涉
“刀子”意象在《血色莫扎特》中呈現出獨特藝術內涵。與“音樂”意象一樣,“刀子”意象同樣推動了故事情節發展。同時,“刀子”意象指向更深入的時代困惑。“刀子”意象首先以“實物之形”——作為“兇器”,推動了小說的情節發展。刀子作為兇手的作案工具,是追捕真兇的一個重要線索。呂鵬通過對刀子多次仔細的觀察,逐漸辨別真兇,找到了“案中案”的突破口,查到真兇,還原了真實的夏冰。實際上,小說中不只是一把刀子,而是出現了多把刀子,并逐漸形成了對人物某種“意念”的象征。韓苗苗被殺現場里第一把“刀子”是馮露拿起來傷害自己的,在夏冰、韓苗苗和馮露三個人的激烈爭吵中,夏冰失手用刀割傷了韓苗苗。刀子是馮露拿的,她也割傷了自己的脖子。
這里還有一把刀子,在暗處等候、伺機行兇的郝大志手中。在兇殺案之后,“刀子”留在了馮露的心中。在以后的生活中,心中的“刀子”成為馮露重要的精神支撐,她甚至感謝兇手郝大志“幫助”自己殺死了韓苗苗:“等我醒過來,警察已經站滿了我的家。我沒看到那個郝大志。但是,他做了我想做,可是沒做成的事。我要感謝他。”“刀子”的意念支配了她所有的行動,推動她幫助夏雨復仇。馮露以“忿怒蓮師”的名義“伸張正義”,“讓所有‘不義’的人都下地獄”,也向葛春風寄發了“死亡請柬”。此時馮露所有的欲望都由心中的“刀子”發出,這種極端的意念已經是一把鋒利的“刀子”。“刀子”還是人物命運和生命的象征。小說中主要的女性形象如韓苗苗、馮露、鄒紅玉都具有“刀子”般鋒利、剛硬的性格特征。小說尤其突出了對韓苗苗的塑造,指出她是一個像“清水里的刀子”的女人,葛春風、薛暢、呂鵬在各自的敘述中都反復強調了這一特征,從而把刀子這個物體與韓苗苗的性格、命運和生命都緊密聯系在一起,刀子也因此具有了顯著的意象特征。
從閱讀感受來看,“刀子”意象的意義還不僅如此,它指向更深刻的時代困惑,這是這個意象最重要的審美內涵。我們看到,《血色莫扎特》中幾乎所有的人都不是快樂的,葛春風、薛暢、呂鵬、夏冰、韓苗苗、馮露、夏雨等都充滿了憂慮,這種憂慮來自于不同的方面。小說在此基礎上只是建構了“刀子”意象,而把對這種普遍憂慮的追問留給了讀者——這也是“刀子”意象內涵的一種延伸。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把這種精神狀況稱為時代的憂懼,并指出它無處不在:“憂懼與每件事都擺脫不了關系。所有的猶豫不定都沾染上了憂懼的成分,除非我們能忘掉憂懼。牽掛使我們無法適當地保護自己的生命。”④《血色莫扎特》中表現的情況甚至超過了這種憂懼,而是時代的“傷痕”。
小說中“傷痕”是普遍的,每個人都傷痕累累——肉體或精神上的。譬如,葛春風在麓城的失意和愧意地離開,以及最后面臨死亡的選擇;夏冰“音樂之夢”的破滅,生活所迫和尊嚴的喪失,以至“負罪”逃亡,最后成為枯井下一個“傷心至死的靈魂”;韓苗苗家庭的困頓,被誘受辱以至被殺;薛暢經營仕途負罪累累,最后也死于復仇之刀;呂鵬生活在案件的血腥和世情變幻中,內心的傷害也使他暗自傷神、感喟不已。正是種種“有形之刀”和“無形之刀”使每個人留下傷痕甚至失去生命,幾乎沒有人能夠刀俎余生。更可怕的是,這些“刀子”可以傳遞下去,繼續給人帶來新傷痕。譬如,作為下一代的夏雨和馮露就接過了這些“刀子”,并且讓它們變得更加鋒利,上演著詭異、殘酷的兇殺劇目。從這個意義上看,“刀子”的意象就具有了更加“形而上”的意味,具有更加抽象的審美特征,指向了“世界的本質”,即“傷害”是世界的本質。
從“刀子”的意象不難看出房偉對社會現實的深刻反思。房偉的思考并沒有從現實的“擠壓”和人生的“窘迫”這樣的角度展開,而是在“傷害”和“毀滅”的維度上把握和表達對世界的認知,并以“刀子”的意象來呈現這種反思和理念,這大大拓展了小說的思想深度。而且,“刀子”的意象是對“音樂”意象的一種遞進,這增強了小說敘事的節奏感和豐富性。“音樂”意象營造了敘事的整體氛圍,鋪墊了情感的基調,也預示了曲終人散的結局。而“刀子”意象則指向這個氛圍中的世界深處,指出這個世界某種“傷害性”的本質。從這個意義上說,“刀子”意象也集中體現出房偉現實主義的創作訴求,并呈現出房偉獨特的審美旨趣。在喧囂斑駁的世界中,“刀子”意象以一種犀利的力量有效擊中時代的癥候,形成小說最震撼人心的藝術力量。
房偉的思考遠沒有結束。在“傷害”本質的世界中,人又如何存在?如何安放自己的精神?房偉把“救贖”作為答案的一個選項,并運用“蛇”的意象來表達這種思考。
三、蛇:時代背景中欲望和救贖表達
“蛇”的意象對于《血色莫扎特》主題話語和藝術魅力的形成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小說中關于“蛇”的敘寫主要有兩處,一處是呂鵬所說的“貪食蛇”游戲,一處是夏雨敘述中內心深處復仇的“大蛇”。這兩處的“蛇”,顯然都具有象征意義。重要的是,這種象征意義契合了小說中人物的行為和命運的發展,成為人物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復雜注腳,表達了時代背景中的欲望和罪惡,在很大程度上增強了小說的現實批判力量。同時,小說中“忿怒蓮師”的咒語“愿狼口蛇心者地獄永不超生”,這使得“蛇”意象具有了一種神秘的色彩,也使得小說主題話語中具有了懲罰和救贖等復雜的元素。
小說中作為刑警隊長的呂鵬,既是兇殺案件的偵辦者,又是葛春風、夏冰、韓苗苗、薛暢等人物的朋友,他洞察著案件進展的一切,也感受著案件中人的欲望和罪惡。他感概人們都是“貪食蛇”游戲中的大蛇,不停地吃東西,不停地長大,最后咬掉自己的尾巴。呂鵬的那句“我們都是那條貪心的大蛇”,實際上指涉了每個人欲望化的精神世界,以及不擇手段貪婪攫取的罪惡。譬如,葛春風、夏冰、韓苗苗貪心于“三人愛情”,夏冰、馮露貪心于不屬于自己的情感,薛暢貪戀于仕途的經營,鄒紅玉、陳副市長在自己的貪欲中不斷地膨脹等等,他們最后都如同“貪食蛇”咬掉了自己的尾巴,宣告了“人生游戲”的結束。可以看出,“蛇”的意義在故事的推進中就是一種觀念,它指向對時代精神中某種病癥的表現和詰問,它的意象審美性也從中產生。
“蛇”意象的意義還不僅僅如此。貪欲的膨脹帶來不斷的傷害和毀滅,由此又埋下復仇的種子,產生連環的傷害效應,這使得“蛇”意象的內涵不斷擴大和深化。小說中的夏雨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形成的“復仇者”,正如他的自述:“一個人心里,有了一個致命秘密,就如同養大了一條蛇。”夏雨還不到九歲時,就開始養大這條“蛇”。他裝作患有自閉癥,默記母親在日記本中留下的秘密,與馮露共同實施復仇計劃,并早就預料這條讓他痛苦多年的“蛇”早晚會與自己同歸于盡。夏雨的人生是一個“殺手”的成長和毀滅過程,是什么造就了他的一生,這是小說留給讀者的問題,也是“蛇”意象的深層內涵。
小說中葛春風的精神世界也是“蛇”意象中的重要內涵。葛春風是小說中最為復雜的人物形象,他有熱情和良知,同時也怯懦和冷漠,考到省城做記者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種逃避。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他能不斷地反思和自省,并處于長期精神的壓抑和痛苦之中。葛春風回到麓城是看望生病的母親,但顯然這不是一次普通的返鄉旅程。從整個小說的敘事來看,葛春風的這次返鄉更像生命的最后一次釋放,是一種終結也是一種開始,正如小說題記所說:“每個人內心都有一個‘致命的秘密’。它藏在心靈深處,等待著唯一,也是最后的危險綻放。”小說結尾是一個開放式的結局:“陽光下,我舉起手掌,托著那藥片,好似托著一個即將誕生的奇跡。”馮露準備的這幾粒毒藥無論葛春風是否吃下,這一刻都成為他新的開始。葛春風被抑郁癥折磨多年,他正期待著這樣一個新生——心中的“蛇”將走向滅亡。或者相反,葛春風拒絕死亡救贖,怯懦逃離,這也將是另一個新的開始。因此,“蛇”的意象就具有了原罪與救贖的豐富內蘊。
在“蛇”的意象中,小說完成了葛春風“救贖”的意義表達,提供了現代人心靈安放的一個路徑。當然,葛春風的“救贖”行為是極端的,是以生命的可能終結作為代價的。房偉正是在生存的這一悖論中展開反思,拓展了對于現代知識分子心靈的表現空間。小說并沒有給葛春風更多的選擇方式,一開始就安排他踏上返鄉之路,最后也沒有讓他走出麓城,這個安排是耐人尋味的。進一步說,葛春風的省城“逃離”并不能開始“新生”,他必須“折返”,在自己的歷史中找到真正的自己,并付出相應的代價才能獲得靈魂的安寧。顯然,房偉對當代知識分子的認識是清醒的,情感是復雜的。在欲望化的時代中,即使知識分子的靈魂發生了扭曲,但房偉依然努力發現他們內心深處不曾泯滅的良知,讓讀者在其生死之間看到了人性的些許光輝。從這個意義上說,葛春風是當下時代背景中新的知識分子形象,小說對其返鄉的敘寫也是知識分子一種新的“返鄉模式”。
可以看出,“音樂”“刀子”與“蛇”三種意象都具有心理意象特征,是在作家現實體驗基礎上形成的感性形象。這些意象呈現出房偉對現實社會的復雜感知,如此“立意于象”也體現出獨特藝術悟性和藝術表現力。同時,三種意象在不同人物敘述中形成,因而也是人物自己的觀念意象。黑格爾指出:“象征一般是直接呈現于感性觀照的一種現成的外在事物,對這種外在事物并不直接就它本身來看,而是就它所暗示的一種較廣泛較普遍的意義來看。因此,我們在象征里應該分出兩個因素,第一是意義,其次是這意義的表現。”⑤作為“意義表現”的“音樂”“刀子”和“蛇”,融入小說敘事,給讀者以哲理性思考,產生了強烈藝術沖擊力。當然,象征性也是現代小說重要藝術品格,如杰姆遜所說:“現代主義的必然趨勢是象征性。”⑥值得注意的是,房偉并沒有把《血色莫扎特》寫成處處隱藏著隱喻、象征的具有現代或后現代特征的文本,而是突顯了小說故事性,這并沒有削弱小說的象征性品格。上述分析可看出,這與房偉對意象的獨特處理密切相關。“音樂”“刀子”與“蛇”三種意象無疑增強了小說的表現力,它們形成的過程也是意象審美的過程,“表現力是經驗賦予任何一個形象來喚起心中另一些形象的一種能力;這種表現力就成為一種審美價值。”⑦
作為一位“70 后”作家,房偉的寫作呈現了這一代作家對這個世界的整體感知:“強悍的現實、無序的情感、鮮活的欲望,總是以各種難以回避的方式,與一個個卑微的個體緊密地糾纏在一起,形成了種種錯位、分裂乃至荒誕的生存景象。”⑧房偉顯然并不滿足于此,他一直在追求藝術的創新——正像他在《血色莫扎特》中對意象世界的探索一樣,這將使其在創作之路上走得更遠。
注釋:
①宗白華:《美學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59 頁。
②葉朗:《美學原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版,第245 頁。
③冉小平,劉志華:《死亡意識:文學創作徘徊不去的結》,《求索》2003 年01 期。
④[德]卡爾·雅斯貝爾斯:《當代的精神處境》黃藿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2 年版,第59 頁。
⑤[德]黑格爾:《美學(第二卷)》,朱光潛譯,商務印書館1981 年版,第10 頁。
⑥[美]弗·杰姆遜:《后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唐小兵譯,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86 年版,第154 頁。
⑦[美]喬治·桑塔耶納:《美感》,繆靈珠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 年版,第132 頁。
⑧洪治綱:《中國新時期作家代際差別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 年版,第189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