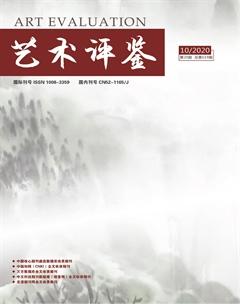淺析威爾第歌劇《游吟詩人》角色唱段
劉博
摘要:《游吟詩人》是威爾第杰出的歌劇作品。在這首作品中,人物形象唱段一直被作為演唱與教學中的范本被后世不斷地學習與研究。本文將圍繞作品中阿蘇切娜作的唱段進行分析,從人物性格到演唱方式,從音樂本體到風格特征,以求管中窺豹的反映出整部歌劇的創作與表達思維。
關鍵詞:威爾第? 《游吟詩人》? 女性? 阿蘇切娜
中圖分類號:J805?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 ? ? ? ? 文章編號:1008-3359(2020)20-0167-03
一、《游吟詩人》與阿蘇切娜
(一)背景介紹
歌劇《游吟詩人》于1853年問世,并在作曲家的親自指揮下進行首演,取得了極大成功,這也是繼歌劇作品《弄臣》之后又一史詩性力作,與其后創作的《茶花女》并稱為威爾第“三大歌劇杰作”。在歌劇《游吟詩人》中我們能夠看到,他將當時意大利歌劇以炫耀演唱技巧為主的表達方式進行極大改革,開始強調歌劇中人物的鮮明性格、戲劇性沖突以及戲劇化的演唱方式,讓觀眾欣賞專注聆聽演唱技巧的同時也能夠清晰的辨別出故事發展的方向以及人物的性格特征,這就讓音樂服務于故事情節,故事情節依托于音樂得以表現的歌劇創作模式得到了極大發展,筆者認為此為該歌劇能夠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這部歌劇共分為四幕,每幕都有標題。故事以西班牙的比斯開與阿拉貢兩地為背景,講述了15世紀封建社會中被統治階級迫害吉普賽人復仇的故事,故事內容相對復雜,以復仇為主題,以愛情為主線并穿插親情的故事鋪述方式構成故事脈絡。劇中女中音阿蘇切娜作為主線牽引著故事的發展,故事所有的愛恨情仇或多或少的都與其有著一定的聯系,這也讓故事的內容和表現力得到了極大提升,讓人們在欣賞聲樂藝術的同時也能夠在邏輯上思辨故事所要表現的思想。而作為故事中的“靈魂“阿蘇切娜在音樂演唱上又有著什么樣的特點呢?下面筆者將對此進行一系列的相關研究以及敘述。
(二)阿蘇切娜的人物性格
在這部《游吟詩人》中,對于阿蘇切娜人物性格刻畫的鋪墊并不是很多,更多的是將一些故事情節隱藏于不存在的故事開端中,后續在歌劇故事情節發展過程中能夠看出阿蘇切娜具體的人物性格。阿蘇切娜由于要為其親眼目睹慘死的母親報仇,決定把魯那伯爵的兒子抱到刑場燒死,但是卻在恍惚中錯將親生兒子丟到火堆中,至此在喪母與喪子的雙重打擊之下阿蘇切娜被摧毀,之后阿蘇切娜抱著伯爵的兒子回去撫養并堅信這個孩子能夠在將來幫她完成復仇。在此期間阿蘇切娜的詠嘆調《火焰在燃燒》則充分體現出當時阿蘇切娜的心理狀態以及人物性格。從以上人物的經歷所導致的變化來看,阿蘇切娜本身是一個孝順的女兒并且也是一個善良的母親,但是她偏激的性格以及不計后果的做事方式導致她注定是一個悲情人物。而后一系列復雜的情節轉換以及意想不到的發展結果也將阿蘇切娜這個人物推到了整部歌劇的中心點,同時將阿蘇切娜從歌劇人物升華到了歌劇形象的位置上來。當我們了解了阿蘇切娜的悲情性格以后在演唱過程中將人物的性格融入到演唱中,以設身處地的方式進行演唱則能夠讓音樂表達更具感染力,同時也讓演唱者表演更加自然、深入。
(三)阿蘇切娜的音樂形象特征
威爾第的《游吟詩人》不同于其他歌劇一個主線的戲劇發展原則的是,該劇不僅有“愛情”這條主線,更有“親情”這條主線。而“親情”這條主線的代表人物阿蘇切娜由于帶有明顯的悲情性格,所以在她的詠嘆調中充斥著悲情的色彩,演唱時旋律特征也與人物痛苦,絕望又帶有復仇情節相吻合。在《火焰在燃燒》中,附點音樂的節奏型始終充斥于全曲之中,音樂語言簡單明了,在詠嘆調的終止部分使用了有力而穩定的表情記號并在b1音上以顫音的形式延長十三拍,最后將音樂推至g2音上干脆的結束。從這里我們就能夠看出阿蘇切娜的音樂形象具有壓抑且灰暗的一面,復仇的怒火已經完全充斥了她的內心,這讓她的音樂形象得到了充分展示。另外一首詠嘆調《他雙手戴著沉重的枷鎖》是一首難度較大,篇幅較長的女中音作品,在這首詠嘆調中主人公阿蘇切娜的情感波動較大。這首作品基本節奏速度較快而且強弱變化對比極其明顯,所以對演唱者的演唱要求較高,只有自如的運用演唱技巧才能夠把這段阿蘇切娜憤恨、痛苦絕望以及飽含對孩子深深的愛這種復雜的音樂形象表達清楚,讓音樂的整體更加豐滿。
對于阿蘇切娜人物性格以及音樂形象的研究不僅能夠幫助更加深入的了解作品,同時也是演唱技巧運用的前提。因為樂譜的樂音是固定客觀存在的,如何將這些樂音轉化成優美的音色并感染觀眾,這就需要演唱者對人物性格以及音樂形象有著明確深刻的認識,在演唱時把自身融入到角色中去才能讓技巧發揮更加自如,讓戲劇情節更加貼切,讓音樂形象更具感染力。
二、阿蘇切娜演唱技巧分析
(一)音樂旋律
阿蘇切娜的第一首詠嘆調《火焰在燃燒》出現在第二幕中,屬于敘事性詠嘆調。該作品e小調,3/8拍,中板速度,復二部(A+B)曲式結構,旋律進行平穩且流暢。A段部分是單三部曲式(A+B+A),旋律整體一附點切分音的形式進行。這里筆者認為威爾第想通過切分音的節奏型來表現火焰燃燒時的律動感,也從側面反應出了主人公阿蘇切娜憤怒且有略帶顫抖的心理波動。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這首作品中大量使用了顫音來突出主人公心理上的變化,尤其是最后長達13拍由弱至強的顫音更是將阿蘇切娜的憤怒和仇恨推向了頂點,也為后續他的種種表現和人物形象埋下伏筆。
阿蘇切娜另外一首獨唱詠嘆調《她雙手戴著沉重的枷鎖》也是出現在第二幕,比《火焰在燃燒》篇幅更加長大,作品a小調,分為三個部分,每一個部分都會進行一次節奏上的變化。第一步部分樂曲采用了速度稍快的6/8拍,開始弱起的3拍長音表示了主人公的無奈和心情的沉重,其后的旋律進行主要是以級進上行和跳進下行為,伴隨著兩音之間的“f-p”或是“f-pp”產生了強烈的對比,表現了阿蘇切娜內心起伏不定、充滿憤恨的心情。
第二部分節奏轉為3/8拍,音樂速度加快,伴隨著敘述回憶的歌詞讓阿蘇切娜的情緒上升到了極點。最后一部分節奏變成了很快的2/2拍,這部分采用了《火焰在燃燒》的主旋律,其后音樂伴隨著歌詞不斷的重復“我的孩子,媽媽竟然將你燒死”這句話表現出了阿蘇切娜心中承受的痛苦與煎熬,將憂傷、昏暗的氣氛渲染到了整個作品中來。
(二)演唱技術
當演唱者掌握了阿蘇切娜的人物性格以及音樂形象以后則需要使用貼切的演唱技巧來詮釋作品。這里指的演唱技巧不僅僅是單純的發聲、咬字以及氣息幾方面,還要注意到節奏、音量、以及音樂與戲劇結合方面,這樣綜合在一起才能讓作品詮釋的更具感染力和表現力。
1.音色和氣息
音色和氣息的運用是分不開的。在《火焰在燃燒》開始部分,伴奏帶入人聲,演唱者的氣息要吸的較深一些并保持在胸腔部分,在演唱時通過“以氣帶聲”的方式把音放在高的位置保持共鳴,以便接下來的音始終保持在這個位置上并且持續進行。
在演唱附點切分音的時候要控制好氣息輸送的強弱以及靈活性。此外,由于要與戲劇內容相符合,在一些強弱變化比較頻繁的地方對于氣息的控制更是需要多加練習。值得一提的是最后部分的13拍長音演唱者要將激動的氣息牢牢控制在小腹部分,保證嘴部放松以及保持音高的持續、平穩,最終逐漸將主人公激動悲憤的情緒推到頂點。
2.節奏與音量
這兩首詠嘆調整體節奏風格都是三拍子速度較快的規整結構。我們在演唱時要注意的是節奏要與旋律進行以及戲劇發展保持平穩一致,這樣才能夠表現出阿蘇切娜受到打擊以后出現的恍惚幻覺,另外也能夠表現出諸如模仿火苗律動的場景環境,讓單純的演唱變得更加立體、豐富。
在音量方面也是需要演唱者多加注意的,在這兩首詠嘆調中為了表現阿蘇切娜起伏不定的情緒變化,威爾第使用了很多對比強烈的表情記號,這就需要演唱者對于音量的變化與氣息的配合更加協調,也要做到強弱對比分明。例如在《火焰在燃燒》中阿蘇切娜唱到“一陣陣狂笑,伴隨著喊叫”時,前四個小節采用的是f力度,而后四個小節直接轉入到pp,通過演唱者對于音量上由大到小的控制使用能夠表現出一種落寞的“回聲”效果。
3.演唱與戲劇的配合
在歌劇中,音樂與戲劇情節是分不開的,相同演唱技巧的運用在不同戲劇情節發展過程中也存在一定差別。所以我們需要對不同情節的發展做出相應的應對,以便更加符合劇情需求,讓音樂與戲劇情節完美的配合。例如在阿蘇切娜錯把自己的兒子扔入火堆時連續唱了四句“我的孩子”,筆者認為在演唱這四句時應該在前三句以遞進的關系來加深她對失去孩子時的激動、懊惱、憤怒的情緒,演唱時要控制音樂的音量,要使聲音是逐漸爆發出來的,到了最后一句可以將演唱的情緒和氣息適當漸弱,以便讓阿蘇切娜在擁有以上情緒之后表現出女人的那份無奈、悲痛。這樣才能很好的將演唱者的情緒調動起來,也讓觀眾能夠隨著演唱的深入更加受到感染。
(三)演唱風格
威爾第的《游吟詩人》創作于19世紀,此時女中音在歌劇中的地位已經得到了明顯的提高,曲作者又將女中音特有的寬厚、天鵝絨般的質感充分地開發出來用以表現母愛。另一方面,威爾第又將阿蘇切娜定位成悲情角色,這就使得女中音低沉、灰暗的獨特音色得到準確的發揮,讓戲劇人物更加豐滿,真實,讓演唱者演唱更具標志性,演唱者在將兩者相融合的過程中既要發揮出女中音特有的音色美更要具有力度美。隨著劇情的發展,演唱者還需要完成較多的顫音、華麗的花錢以及美化裝飾音等等,這些都需要演唱者有很好的演唱功底才能更好的完成,同事也要理解這些裝飾音在作品中所發揮出的作用和意義。當我們演唱時要注意聲音要堅強有力,將胸腔,頭像、口鼻喉腔組合協調使用,這樣才能讓音樂的共鳴帶動起戲劇元素的共鳴,增加女中音昏暗、厚重的音色特征,也使得阿蘇切娜的藝術形象得以深化。
在阿蘇切娜的兩首獨唱詠嘆調中,筆者人物演唱技巧的運用是整部音樂發展的動力,恰當且有深入的使用演唱技巧并與人物性格,劇情發展相結合才能夠讓作品表達的更加完整,讓音樂因為演唱技巧而鮮活,讓演唱技巧因為音樂而生動。
(四)戲劇化的演唱特征
所謂“戲劇性”指的就是人物性格在劇情發展中所產生的矛盾沖突,這也是歌劇除了音樂之外最具表現力的表達方式之一。對于阿蘇切娜的這個人物性格以及劇情變化時時刻刻都在表現出她是一個矛盾的綜合體,正因為繁復的矛盾疊加在她一個人身上才使得這個人物更加生動,感染力更加強烈。首先:阿蘇切娜的矛盾集中在她與伯爵之間。看到自己慘死的母親之后,她希望通過燒死伯爵兒子的方式來報復伯爵以便達成報復的目的。在這種矛盾的驅使下,讓她錯將自己的親生兒子丟入火中燒死。在這種矛盾中她唱出的《火焰在燃燒》生動表現了他看到兒子被燒死時的無能為力的那種悲痛、憤恨以及復仇的心理狀態。而此時女中音圓潤、柔和、豐滿的音色則很好的表現了一位母親喪母喪子的感情色彩。但小調音樂的昏暗、深沉也將阿蘇切娜的矛盾淋漓盡致地展現了出來。其次,阿蘇切娜的矛盾在于她發現了自己的親生兒子被她親手扔入火堆之后卻又帶著伯爵的兒子回去撫養,雖然她帶有想利用伯爵兒子幫他復仇的心思,但是曲作者又賦予了她光輝的母愛一面,最終將伯爵的兒子當成自己的兒子來撫養。長久之后復仇的心理隨著孩子的成長逐漸淡化最終將其視為己出。這種矛盾的產生賦予阿蘇切娜高大光輝的一面。最后,阿蘇切娜被捕之后,伯爵將自己的親生兒子綁在柱子上準備火刑的場面,讓阿蘇切娜與伯爵以及自己的矛盾達到了頂點,一方面他既希望為母報仇,另一方面也對養子曼里科表達出了不舍。阿蘇切娜注定是一個悲情的人物,諸多矛盾施于一身也讓阿蘇切娜的戲劇性特征發揮得淋漓盡致。在阿蘇切娜表現戲劇性音樂元素時,演唱者大多通過抒情風格、戲劇風格以及華麗風格等演唱技巧來詮釋作品內容以求更加符合內容需要。在這三種風格使用中演唱的音量要較大,并且要充分發揮出女中音音域寬、爆發力強、富于變化的特征,讓演唱的旋律能夠與伴奏中柱式和弦豐滿的表現力形成高度的統一,最終達到表現作品風格的演唱目的。
三、結語
綜上所述,威爾第的《游吟詩人》之所以能夠成為世界最為著名的歌劇作品之一是有其必然性的。其中阿蘇切娜作為劇中二號女主人公以其復雜、糾葛的劇情、豐富、悲情的人物性格與極其符合女中音音色特點的演唱特征成為了《游吟詩人》的標志性人物。整部歌劇雖然是“愛情”與“親情”兩條主線來發展劇情,但是我們不難看出阿蘇切娜的“親情線”更加戲劇沖突強烈,人物性格鮮明突出。正是在這種戲劇情節的前提下,注重音樂與戲劇并重的威爾第將阿蘇切娜的兩首獨唱唱段《火焰在燃燒》和《她雙手戴著沉重的枷鎖》的音樂描繪的充滿仇恨、憤怒和母愛。所以,筆者認為在演唱這首作品之前一定要深入了解阿蘇切娜的人物性格以及劇情發展,其次才能將演唱方法很好地融合到人物中去,這樣我們才能夠讓音樂充滿戲劇魅力。在演唱方法運用方面要求演唱者聲音豐滿、宏大、激情有力,表現出戲劇沖突中的斗爭性與仇恨感。在氣息方面更要求演唱者要圓潤連貫,在平穩的基調下盡量讓共鳴集中、明亮以便更好表現出阿蘇切娜憤恨、復仇的演唱情緒。
參考文獻:
[1]金雷.歌劇《游吟詩人》中女性人物形象塑造及演唱特點的研究[D].長春:東北師范大學,2009年.
[2]高瞻.愛恨交融的悲歌——對《游吟詩人》中阿蘇切娜詠嘆調《火焰在燃燒》演唱風格的分析[J].藝術研究,201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