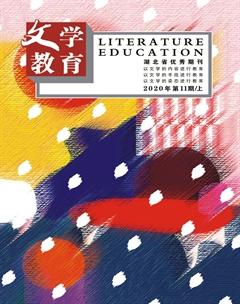傳統與現代的雙重接駁
“70后”始終被歷史、傳統等問題所困擾。這是喝“狼奶”長大的一代,他們的成長期并不匱乏現代藝術的滋養,卻幾乎完全地與傳統割裂。因此,就小說技藝而言,他們基本上都有著較為成熟的掌握,而且在向世界文學、向本土先鋒文學學習的基礎上發展出了自己的美學特征:魏微的莊重優美、盛可以的誚薄凌厲、金仁順的淡然清雅、戴來的簡潔中性、李浩的倫理哲思、肖江虹的邊地古風、魯敏的精神暗疾、曹寇的“無聊現實主義”、付秀瑩的古典氣質、梁鴻的中原風范……
然而,人到中年,他們越來越無法避免地要面對一個問題:如何與自己的土地、民族、文化傳統進行接駁。徐則臣以他一直以來方向明確的努力作出了回答。一方面,他通過閱讀和學習古代文化、藝術、歷史、考古等典籍進行彌補;另一方面,他一直在思考、在尋求如何將“中國經驗”納入到一個適當的敘事外殼之中,使之既鮮明又妥帖。
《虞公山》是一個近乎完美的嘗試。小說在主題和精神上是“傳統”的。故事發生在鶴頂。鶴頂是離花街不遠的運河邊上的一個小鎮,在《輪子是圓的》《最后一個獵人》等小說中出現過。這次它是以徐則臣正在構思和書寫的“鶴頂偵探”系列中的背景出現的。小說通過中學生吳極“盜墓”的故事,引出了一個國人隔膜已久的問題:家譜。它曾經是鄉土中國的“命根”。中國人無論走到何處開花散葉,只要有家譜,便能找到自己的根,他們的離鄉背井便有了一個安然堅固的底子。然而,隨著現代性和全球化的發展,世界性的離散、漂泊越來越普遍,以致于今天的中國人早已忘記了自己的祖先和來處。家譜更是無蹤可尋,甚至不曾在人們的思念中占有一席之地。
但徐則臣偏要逆風而動,將一個“古老”的詞語和現象重新牽引回我們的視野。他將吳極(這個名字本身也很“中國”)置于內在的誘惑和外在的脅迫之中:在內,父親吳斌告訴他,他們不姓吳,本姓虞。老祖宗虞鳳常是康熙的愛臣,隨皇上沿運河南巡時意外在鶴頂病逝,就地下葬,埋在了虞公山,隨之下葬的還有一部家譜。在外,吳極與一個吳姓同學發生爭吵,對方說“有種別姓吳”。為了撇清跟對方的關系,吳極決定到老祖宗的墳墓里尋找“吳自虞來”的鐵證。
小說在形式和結構上又是很“現代”的。“要從一個鬼魂說起”,這個開頭一下子將我們帶回到了魔幻現實的氛圍之中,回到了馬爾克斯筆下那個瘋狂的馬孔多小鎮。但是,倘若現在還有哪個作家要執著地來一個“魔幻現實”,無疑已經相當地不合時宜。作者設置這么一個煞有介事的鬼魂故事,實則要寫的是一個少年委屈的、怯生生的“尋根”故事。這個“尋根”又與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大舉朝向傳統進行挖掘和“鍍亮”的尋根文學不同。吳極要尋的只是家族的根、自我的根。由“鬼魂”牽出“盜墓”,由“盜墓”留下的“藍旗”煙頭,派出所的人尋蹤到了常年跑船的煙酒大戶吳斌家中。
這是一個擾亂現世秩序和時間順序的敘事。這種方式對于“70后”當然不是難事,不過是信手可拈的雕蟲小技。小說將吳極、安大平、吳極母親、船老大、派出所、縣公安局、考古專家等多線索進行了有條不紊的編排。在復雜而邏輯清晰的敘述中,一個影影綽綽的人、一個眾說紛紜的人,始終飄蕩在文本中,那就是吳斌。他在老婆口中是一個不著家、不顧家的自私浪蕩子,在兒子眼中是一個會講故事的幽默高手,在船老大眼中是個聰明的有才華的人,跑船屈了才,應該“能干很多高級的事”。這是吳斌的“羅生門”,他始終未曾正面出現過,這讓“破案”的過程蒙上了飄忽不定的色彩。一直到最后,故事也沒有給出確切的答案。吳斌成了一個永遠上不了岸的人:就像《河的第三條岸》中那個遙遠而陌生的父親,向子一代發出了充滿魅惑的召喚,而他自己則永遠地留在了河上。
《虞公山》的主題何止于此,我們還可以從這萬字短篇里讀出更多的故事、更多的內涵:吳極子虛烏有的尋祖,卻坐實了虞公山的考古工作;吳極對于“姓氏”的尋找和對于“父親”的追隨,無疑可構成一個代際性的命題;個體身份的尋求與認同,可擴展之視為一代人的身份困惑;一代人對文化和文明的回返,亦可視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世界中”的自我辨認……
《虞公山》在徐則臣的創作中是一次重要的轉型。這一次,他筆下的人物不再如花街少年那樣著了魔似地要“到世界去”,而是一門心思地返向了自己生命和血脈的來處。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種“認祖歸宗”的行為也可視為“70后”一代向著傳統進行的追溯與回返。而這,僅僅只是一個開始。
曹霞,著名文學評論家,現居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