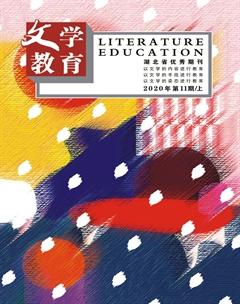唐宋嶺南詩詞中的“芭蕉”意象寫作
內容摘要:唐宋嶺南詩詞中的“芭蕉”意象有側重外在形態(tài)描寫而不注重內涵寄托的特點,較為常見的有“蕉林”“蕉和荔”“紅蕉”這三種表現內容。造成唐宋嶺南詩詞中“芭蕉”意象數量少且內涵沒有進一步拓展延伸的主要原因,一是這一意象在唐宋時期的泛南方化傾向;二是受到南貶文人復雜內心感受的影響。
關鍵詞:唐宋 嶺南詩詞 “芭蕉”意象
嶺南,又稱嶺表、嶺外,概指五嶺i山系以南地區(qū)。嶺南是一個歷史概念,其具體所指隨各朝代的行政建制不同而有所差別。大體而言,唐代嶺南地域范圍包括今廣東、廣西大部及越南北部,而宋代嶺南區(qū)域則包括廣東、廣西及海南一帶。由于五嶺的交通阻隔以及惡劣的自然環(huán)境,唐代之前的嶺南鮮少進入以中原為主流的文化視野中。唐宋之際,隨著大批中原人士因著各種原因流寓嶺南,嶺南在文學作品及文化典籍中出現的頻率有了大幅度提升。本文提及的唐宋嶺南詩詞,即是指唐宋期間流寓嶺南文人所做詩詞及其他文人以嶺南為題材的詩詞作品。
芭蕉是熱帶、亞熱帶植物,常見于我國南方大部分地區(qū),其中尤以嶺南地區(qū)最為繁多茂盛。早在西漢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中,就出現了“諸柘芭苴”的記載,由此可知,我國栽種芭蕉的歷史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芭蕉以其寬大優(yōu)美的葉片及油亮翠綠的色澤贏得了人們的喜愛,并一再出現在文學作品中。及至唐宋,有關芭蕉意象的文學作品數量已經蔚為可觀,同時,經過長時期的文化積累,這些詩詞作品中的芭蕉意象的內涵意蘊也呈現出多元化的態(tài)勢。最為常見的意象有:“雨打芭蕉”,如杜牧的《雨》:“一夜不眠孤客耳,主人窗外有芭蕉”;“蕉葉題詩”,如岑參《東歸留題太常徐卿草堂》:“題詩芭蕉滑,對酒棕花香”;“芭蕉喻空”ii,如白居易《逸老》:“筋骸本非實,一束芭蕉草。”又或者以芭蕉之卷舒寫歡欣或憂愁的情緒,如李清照《添字丑奴兒》:“葉葉心心,舒卷有余情”,等等,不一而足。
唐宋嶺南詩詞中的芭蕉意象總的呈現出側重外在形態(tài)的描寫,而不重內在意蘊寄托的特點。大致說來,較為常見的有以下三類描寫:
一.蕉林
從大量唐宋文人的詩詞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芭蕉是作為園林景觀植物,為滿足人們的視覺及聽覺審美需求服務的。如杜牧《芭蕉》就有云:“芭蕉為雨移,故向窗前種。憐渠點滴聲,留得歸鄉(xiāng)夢。夢遠莫歸鄉(xiāng),覺來一翻動。”又如宋代王十朋的《書院雜詠·芭蕉》中云:“草木一般雨,芭蕉聲獨多。主人栽未足,其奈客愁何。”出于這種訴求,芭蕉栽種只求其有,并不求其多。然而唐宋時期的嶺南地區(qū)則不然,芭蕉在這里是作為一種經濟作物成片種植的。據《元和郡縣圖志》記載,早在唐太宗在位之時,廣州進貢給朝廷的貢品中就有蕉布。iii宋代周去非在《嶺外代答》花木門·水蕉條中記載道:“水蕉不結實,南人取之為麻,縷片,曝干,灰煮,用以績,布之細者,一匹直錢數緡。”可見當時嶺南人有種植一種不結果實的芭蕉品種以供紡織用。
因此,唐宋嶺南詩詞中“蕉林”出現的頻次不低。如歐陽炯《南鄉(xiāng)子》其二:“畫舸停橈,槿花籬外竹橫橋。水上游人沙上女,□回顧,笑指芭蕉林里住。”摹寫具有濃郁地域色彩和生活氣息的嶺南風情畫,借岸邊女子的笑談引出芭蕉林里有人家的炎方景象。無獨有偶,我們在稍后北宋黃庭堅的《謝陳正字送荔支三首》其三中也可以看到相近的描述:“齋馀睡思生湯餅,紅顆分甘愜下茶。如夢泊船甘柘雨,芭蕉林里有人家。”“甘柘”即為甘蔗,與芭蕉同屬嶺南常見經濟作物,甘蔗雨和芭蕉林交織成典型的南方物候。向子諲《西江月·番禺趙立之郡王席上》中也寫道:“風響蕉林似雨,燭生粉艷如花。”寫風吹過蕉林發(fā)出的如下雨般的聲響,獨具嶺南風味。
二.蕉和荔
芭蕉果實形似月牙,皮薄而果肉飽滿,味清香而略甜,自古以來就是嶺南常見的水果之一。唐宋嶺南詩詞中,文人們常常將其與頗負盛名的嶺南佳果——荔枝相提并論。實際上,唐宋文學中荔枝的書寫是跟隨著它的進貢地點改變的,其中心經歷了由唐代巴蜀到宋代閩地的轉移,但嶺南作為荔枝的重要產地之一,隨著南來文人的吟詠,嶺南荔枝也逐漸聲名鵲起。其中最廣為傳唱的無疑是蘇軾的“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食荔枝二首》其二)
在對蕉和荔的吟詠中,有本土人士不無驕傲的介紹,如田開的《臨封雜詠》:“我愛臨封好,詩人興味長。嶺南蕉子國,海上荔枝莊。民有百年壽,家藏十種糧。宦游無遠近,樂處是仙鄉(xiāng)。”田開是恭城(今廣西恭城)人,此詩作于詩人知封州(今廣東封開)任上。雖不免有溢美之詞,但也真實反映了當時嶺南這兩種作物種植之廣;也有南貶文臣滿是感慨的向往,如李綱的《次貴州二首》其二:“懷澤為邦古郁林,江邊邑屋樹森森。山連八桂峰巒秀,地近重溟霧雨淫。歲久承平消瘴癘,時危爭戰(zhàn)覺幽深。試謀十畝膏腴地,丹荔青蕉獲我心。”貴州即今廣西貴港,時局動蕩,一貶再貶、壯志難酬的遭遇讓身衰心疲的李綱在遍植蕉荔的嶺南陋鄉(xiāng)萌發(fā)了歸隱山林的念頭;還有未至嶺南者對未知之地的遐想,如薛敏思《送歐陽令之任粵中》:“大隄二月柳初舒,秣馬飄然別故廬。自取通才分劇邑,誰憐修路奉除書。綠蕉丹荔千山度,瘴雨蠻煙百粵居。此去縣中花事好,早將佳績報雙魚。”送別將至嶺南赴任的朋友之際,遙想彼處應有設色分明的滿山綠的芭蕉、紅的荔枝,卻也有對瘴雨蠻煙的擔憂。芭蕉與荔枝一道,建構出了詩人們的嶺南印象。
三.紅蕉
紅蕉是我國栽培歷史悠久的芭蕉科植物,相對于其他芭蕉品種,紅蕉的花色艷紅,與青翠的葉片形成鮮明對比,更具觀賞價值。周去非在《嶺外代答》中描述道:“紅蕉花……色正紅,如榴花、荔子,其端各有一點鮮綠,尤可愛。”[1]然而紅蕉喜溫不耐寒,因此其栽培難度較大,唐宋時期以嶺南最為多見。唐劉昭禹在《送人紅花載》中寫道:“世上紅蕉異,因移萬里根。艱難離瘴土,瀟灑入朱門。葉戰(zhàn)青云韻,花零宿露痕。長安多未識,誰想動吟魂。”可見這個品種移植之不易。
紅蕉以其獨特的外形成為嶺外之人對嶺南遐想中的一抹固有的亮色。唐代王建的《送鄭權尚書南海》中寫道:“七郡雙旌貴,人皆不憶回。戍頭龍腦鋪,關口象牙堆。敕設薰爐出,蠻辭咒節(jié)開。市喧山賊破,金賤海船來。白氎家家織,紅蕉處處栽。已將身報國,莫起望鄉(xiāng)臺。”于送行的美好祝愿之中構想嶺南處處紅蕉的美麗景色。殷堯藩在《送韓協(xié)律勝起容府幕》中也有詩句云:“云收碧海連天水,風動紅蕉滴露光。”設想海上云彩消散,碧水藍天相接,一望無際;清風吹拂,紅蕉像露滴花心那樣光彩奪目,美艷無比。它同時得到了南來文人的矚目,李紳在《逾嶺嶠止荒陬抵高要》中描寫這種讓他印象深刻的植物道:“嶺頭刺竹蒙籠密,火拆紅蕉焰燒日。”極寫其顏色之艷,仿佛灼燒烈火直逼紅日。
顯而易見,唐宋嶺南詩詞中的芭蕉意象從內在蘊含上而言并不深刻。而且從數量上而言,它在唐宋嶺南詩詞中的眾多植物意象中為數也并不多。這與唐宋芭蕉在嶺南的廣泛種植似乎并不匹配。究其根本,原因大約有如下:
其一,與其他更具嶺南特色的植物意象相比,唐宋嶺南詩詞中的芭蕉意象地域從屬性并不那么分明。這些植物意象是指一出現就往往能讓人直接聯想到嶺南的,如李珣《南鄉(xiāng)子》:“相見處,晚晴天,刺桐花下越臺前。”歐陽炯《南鄉(xiāng)子》:“路入南中,桄榔葉暗蓼花紅。”孫光憲《菩薩蠻》:“木棉花映叢祠小,越禽聲里春光曉”李珣《南鄉(xiāng)子》:“曲岸小橋山月過,煙深鎖,豆蔻花垂千萬朵。”提到的刺桐、桄榔、木棉及豆蔻皆屬此類。
而芭蕉,由于其栽培區(qū)域的不斷擴張,到唐宋時,已經能夠在南方大部分區(qū)域乃至北方部分區(qū)域成功存活了。芭蕉種植區(qū)域的擴大,與唐宋園林藝術的長足發(fā)展有關,受到當時經濟發(fā)展及社會思潮的影響,人們對園林造景藝術手法、建筑與山水花木的搭配融合以及動植物的畜養(yǎng)栽植有了更高的認識和追求。芭蕉的外形優(yōu)美、生長周期短,又富于文人雅趣因此廣受歡迎。唐宋時期,隨著經濟重心南移,江南富庶的城市經濟使得園林造景需求倍增,芭蕉種植地由前朝的皇家苑囿普及到了民間園林。據《玉堂閑話》描述:“天水之地,邇于邊陲,土寒不產芭蕉,戎師使人于興元求之,植二本于庭臺間,每至入冬即連土掘取之,埋藏于地窖,候春暖即再植之。”[2]天水,即今甘肅天水市,位于我國西北地區(qū),氣候比較寒冷,常態(tài)下芭蕉難以過冬,然則在此時就已經摸索出窖藏過冬的法子。可見其栽種范圍的不斷擴大。隨之而來的就是這種植物的地域屬性變得模糊化,唐宋時期芭蕉變得隨處可見的結果,是使它在唐宋詩詞的書寫中成為泛南方化的植物意象,從而更多地與“江南”“南方”而非“嶺南”捆綁在一起構成人們的刻板印象。比如徐波在《論古代文學中的“雨打芭蕉”意象》一文中就認為,在中國的文化傳統(tǒng)中,雨打芭蕉是江南水鄉(xiāng)典型的景象。在他看來,江南不僅是一個地域概念,更是一個文化概念。江南易使人產生清秀、空靈、溫柔、婉雅的聯想,而“雨打芭蕉”這一文學意象本身所具有的柔美、輕盈、清婉的風味比較能體現江南的美學特點,因此,在人們的審美體驗中,雨打芭蕉是屬于江南的。[3]
其二,唐宋嶺南詩詞中的芭蕉意象的復現頻次不高,內在蘊含不深刻還與南貶文人的心態(tài)有關。時至唐宋,作為“教外之地”的嶺南成為朝廷安置逐臣的聚集地。清代郝玉麟纂修《廣東通志》,于該志《謫宦》前言道:“仕宦謫籍嶺南尤眾,豈非以古荒服地而蠻煙瘴雨之鄉(xiāng)歟。”[4]宋沈晦詩云:“五嶺炎熱地,從來著逐臣。”據統(tǒng)計,唐代289年中,有姓名及貶地可考的貶官共2456人次,其中嶺南到高達436人次,為南方諸道之最,僅盛唐玄宗一朝,貶赴嶺南者即高達71人次,遙遙領先于其他地域。而宋代謫宦嶺南之人,載入史籍者達499人次。湮沒無考者,則更是不計其數。[5]這些卷入政治斗爭旋渦,成為權力較量下的犧牲品的逐臣貶官,帶著對嶺南瘴癘地的恐懼,以及未卜前途的擔憂,還有從高位墜落的不適感與失落感,交織成了復雜的心理感受。如同受傷后不停舔舐傷口的困獸,他們很難全情投入于嶺南的奇花異草,秀美風光,這些現實層面上的感官刺激也往往要服務于內心情感抒發(fā)的需要,作為其興發(fā)的鋪墊。如李德裕的《謫嶺南道中作》云:“嶺水爭分路轉迷,桄榔椰葉暗蠻溪。愁沖毒霧逢蛇草,畏落沙蟲避燕泥。五月畬田收火米,三更津吏報潮雞。不堪腸斷思鄉(xiāng)處,紅槿花中越鳥啼。”他固然也注意到嶺南獨有的桄榔、椰樹、紅槿及越鳥,但這些不過是引發(fā)他斷腸思鄉(xiāng)情思的外在導索罷了。又如宋代洪皓《芭蕉》:“芭蕉非一種,南粵競成叢。結實聯房綠,舒花焰火紅。 ?象蹄形甚偉,筒葛纴尤工。羈旅牽愁思,秋窗夜雨中。”即使也描寫到芭蕉的美麗外形,終究還是落在羈旅愁思的情感表述上。
綜上所述,唐宋嶺南詩詞中的芭蕉意象數量不多,意蘊不深刻,往往止步于對芭蕉外形的簡單摹寫。這與唐宋時期芭蕉種植范圍的擴大,芭蕉意象的泛南方化地域屬性有關,也與這一時期南貶文人的沉重心境下的情感表達述求有關。正因如此,唐宋嶺南詩詞中的芭蕉書寫無法得到進一步的拓展和延伸。
參考文獻
[1]周去非著;楊武泉校注.嶺外代答校注[M].北京:中華書局,1999:327.
[2]李昉等著,《太平廣記》.卷140(引述《玉堂閑話》,中華書局,1961.
[3]徐波.論古代文學中的“雨打芭蕉”意象[J].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學報,2011(3):79-83.
[4][清]郝玉麟《廣東通志》卷262, 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5]侯艷.唐宋歷史地理與詩歌地理中的嶺南[J].廣西社會科學,2014(11):105.
注 釋
i五嶺:一般認為指越城嶺、都龐嶺、萌渚嶺、騎田嶺及大庾嶺。
ii芭蕉喻空:陳寅恪先生認為,受印度佛學比人身于芭蕉等易于解剝之植物影響,魏晉文人往往以芭蕉中空說明陰蘊俱空,肉體可厭之意。見陳寅恪《禪宗六祖?zhèn)鞣ㄙ手治觥贰?/p>
iii見《元和郡縣圖志》第三十四卷至三十八卷。
基金項目:本文系2017年度廣西高校中青年教師基礎能力提升項目“宋詞嶺南意象研究”(項目編號:2017KY0641)成果。
(作者介紹:梁歡華,賀州學院文化與傳媒學院講師,研究方向:古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