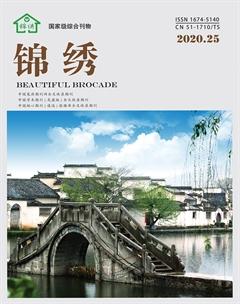生生之萬物的橫向感通如何可能
吳雙


摘要:張載以“太虛即氣”建立了儒家哲學的本體論,以‘一本散為萬殊,而立于萬殊中之氣,不僅在縱向上成為太虛與萬物形上形下縱向貫通的根據,橫向上更是成為了主體與主體之間橫向感通函攝的根據,回應了儒學天人同構而導致的主體萬物間彼此孤立、難以聯系為整體的挑戰。以“太虛”中未顯的陰陽動靜交通互感之性,上乘儒家生生傳統,體現為“至善的流行”,而不致使氣化流行淪為萬物的“大輪回”;下啟氣學辯證法路徑,為王廷相王夫之辯證法之精進提供理論涵養。
關鍵詞:張載;太虛即氣;氣化流行;生生之幾;辯證法
一、導言
儒學的核心問題是性理問題,從心性闡發天理。儒家心性之學的源頭可追溯到孔子的“仁”,表現在生命的原初就是對“性”善的肯定,表現在宇宙萬物運動法則就是“理”的生生流行。一方面從生命的原初性來看,儒家以積極正面的態度對宇宙化生和人的本性,對天道與人道的開端都以“生生之仁”的“善端”加以肯定。另一方面,從生命的運動性來看,儒學認為從開端化生萬物,生命流轉運動的過程中都在展現和擴充生命存在中最初的善性。1具體說來,大至從天地渾元到形成萬物,小至一粒種子發芽生長,其有和諧有序的運行背后,有某種連續性、無限制、不停止的功能原則。這就是“至善的流行”,本源之善、善的流行以至生生不息的思想脈絡貫通先秦儒學、宋明理學,以至對現代新儒家也有深遠影響。儒學重視由人即天、由天而人的縱向感通,人–天、性–理,是一種同構關系。儒學(尤程朱陸王)立足自身,是一個由己看天的路向,哲學思想內收于人本身。
但這面臨一個問題,如果只聚焦于個體與天道的貫通,那么如何實現人與人的感通呢?建立在人人之心的先驗同構(人人之心,皆同此心)上,或許能解釋這個問題,但過于主觀臆測,只能說是一種假設,沒有堅實的形而上的哲學理論依據。再者,這種孤立性不僅僅存在于人與人之間,更重要的是體現為萬物的孤立無感。物與物、事與事之間如何呈現出整體性、聯系性、協調性呢?
筆者秉持這個核心問題——如何在儒學萬物生生縱向感通的傳統上,解決物物之間的孤立性而打通萬物橫向的感通涵攝?——對宋明理學進行考察,并于張載“太虛即氣”的氣化流行觀入手探究。
二、張載“太虛即氣”感通萬物
1、“太虛即氣”解析
首先,張載闡釋了太虛和氣的關系問題。這里有兩個要義:
一是,太虛與氣不是二物,反對“虛能生氣”的說法。張載雖說“太虛無形,氣之本體”2,深層意義在于“氣之聚散于太虛,猶冰凝釋于水,知太虛即氣則無無”3,太虛通過氣展示出來,氣是太虛的體現,太虛是氣的一種特殊狀態。所以不能將二者當作兩種事物分開來看,也不能單純認為氣生于虛。如果虛能生氣的話,就會出現有限與無限的矛盾,即張載所說的“體用殊絕”的困境。
二是,二者并不等同。雖然二者不離不分,甚至可以說本質上是同一物,但是二者在運動聚合中處于不同位置(后面將進行詳述)。以馮友蘭和張岱年為代表的學者持一種唯物的觀點,認為,太虛和氣是同質的關系,將太虛和氣一起作為形而下的物質論述之,二者的差別僅在于存在狀態的不同。這種觀點雖然符合了張載太虛和氣的同質關系,但是將太虛和氣作為物質固化了。一來違背“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4所強調的,太虛中動靜交通、陰陽交感的特性。二來,如果把“氣”視作形而下的物質,就違反了氣作為太虛生生顯化可形可象的流行功能,變得死氣沉沉、機械而無生生之意。自然,氣化過程之“道”也無從顯露。這種違背儒學核心生生之幾的“太虛”與“氣”必不是張載所立足的天道論。
其次,“太虛”和“氣”形而上的實在性。從形上性來說,從上段分析得出,“太虛”因其內含陰陽動靜、交感互動之性,“氣”因其生生顯化可形可象、可聚可散的流行功能,而都不可視作形而下的物質。從實在性來說,“氣”作為流行聚散的載體,其實在性不必多言。“太虛”一來指的是萬物渾元、虛寂無形的狀態,包含著天地萬象未顯之形,蘊含著陰陽動靜、交感互動之性,因此不是“無”,具有實在性。二來“太虛” 不是“氣”的衍生源泉,而是“氣“的聚合之處,因此張載反對在“氣”之上懸設一個“太虛”的本原。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太虛也具有不可否認的實在性。
最后,萬物如何化生——氣化流行。張載在《正蒙》中談到“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成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5。“太虛”中天地萬象未顯之形通過 “氣”的陰陽交感聚成萬物,萬物演化最終仍以“氣散”的形式散歸于“太虛”,從而再次化生為他物。這種太虛、氣、萬物的流通演化過程,以“氣”的聚散為核心的思維(如下圖6所示),就是張載的氣化流行觀。
2. 橫向感通萬物之可能
從對張載“太虛即氣”的理解出發,看“氣化流行”的宇宙模型,從中我們可以發現,如果把具有形而下氣質的氣學完全地限定在“材質”“物料”層面,實際上與中國傳統的“天—人”感通所建立的宇宙論模型相悖,而且也無法解釋張載氣之聚散流行的無限性問題。持這種理解思想的馮友蘭、張岱年的唯物說,以及牟宗三的“體用圓融說”都無法好似細水流淌一般順暢自然的“萬物感通”之可能。
唐君毅先生在這里從張載“兩一”思想出發,認為應該跳出唯物或唯心的詮釋框架,將太虛和氣都視作一種“存在地流行”和“流行的存在”,認為“虛氣不二”。他從縱橫兩個不同角度來證明“虛氣不二”:縱向來看,氣以其虛,故能消融已然凝聚之形,再次生化為其他物。橫向來看,正因為氣虛不二,物是從萬象未顯之太虛中,經氣之聚合流行而顯為此象或彼象,由于“氣”于各物流行的普遍性,“一本散為萬殊,而立于萬殊之中”,物與物之間才獲得了得以相互感通與攝涵的根據和先天條件。唐先生在解析張載的太虛即氣時評點道:
“在濂溪之系統中,有一太極之誠,立于萬物之各自正命處,然未嘗言萬物之間,皆原有一依其氣之清通,以相體合一之性。此中便只有‘一本散為萬殊,而立于萬殊中之一度向,而無‘萬殊間,亦彼此能依其氣之清通,而互體,以使萬物相保合,為一太和之一度向。此即橫渠言性與天道之進于濂溪者也。”
——《中國哲學原論·原性篇·由佛再入人之性論》
《張橫渠之即虛以氣以體萬物謂之性,及氣質之性之名之所以立》7
中國傳統思想從《易經》以來的自然觀都包含了物與物之間相互影響的關系,但直到張載,才明確地指出萬物之間感通而相攝涵的可能本于氣之虛,由此‘一本散為萬殊,而立于萬殊中,張載哲學的本體(氣)不僅使形上形下縱向貫通的根據,更是主體與主體之間橫向感通函攝的根據。這正是張載之氣學思想所以過周濂溪氣學以及程朱天道本體論的地方。
三、萬物橫向感通中的生生之幾
二程與朱熹對張載的“氣化流行觀”并不認同, 認為張載天道觀中“太虛”中天地萬象未顯之形通過 “氣”的陰陽交感聚成萬物,萬物演化最終仍以“氣散”的形式散歸于“太虛”,從而再次化生為他物的“氣化流行”不過是一種萬物的輪回。“橫渠辟釋氏輪回之說。然其說聚散屈伸處 ,其弊卻是大輪回。蓋釋氏是個個各自輪回 ,橫渠是一發和了 ,依舊一大輪回。”8氣作為“存在的流行”,只能完成流行的功能,在氣化的過程“道”中,沒有實現自我超越的動力,不過是圓圈式的循環往復、無限輪回,有違儒學生生之傳統。
對此,筆者認為,張載“氣化流行觀”的橫向感通與其同時貫徹儒學生生之幾并不矛盾。
原因一,張載天道論實現萬物生生的關鍵不在于“氣化流行”的過程,而在于“太虛”所含的陰陽動靜交感之性。在“氣化流行”中,氣將“太虛”中未顯的象,聚合為已顯的象。這個過程確實沒有萬物生生、自我超越的可能。這是為什么程朱批判張載“氣化流行”為一大輪回的原因。但實際上,這是一種片面解讀,只看到了“氣化流行”中沒有生生的動力,卻忽視了“太虛即氣”的另一重要環節——“太虛”。張載的“太虛”蘊含動靜交通、陰陽交感,不是“空寂”、“死寂”。“太虛”里,是活的、隱隱運動著的,因而將形成生生之幾,生生之幾進一步通過可形可象、可聚可散的流行功能顯為萬物。由于太虛中蘊藏的“生生之幾”,氣化功能每次都有新意、新象,雖然這種思想還在張載自身“不失吾常”,靜為絕對、動為相對的統攝之下,但也絕不是程朱所批判的大輪回。因此,在湯勤福張載“太虛即氣”思維圖的基礎上,應該再進行如下增益:
原因二,張載的“太虛”中蘊含著辯證法的思想,一定程度上為王廷相、王夫之所發展,開啟氣學辯證法之路。
張載認為,“一物兩體”是宇宙間的普遍規律,陰陽二氣的聚散推移成為一切事物運動變化的內在根據。《正蒙·太和篇》寫道“氣之為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為有象,不失吾常”9,所謂變,是講陰陽二氣的恒久變化運動;所謂常,是講本原之氣的永恒性。由此可見,氣之動而生萬物其實是“不失吾常”,靜是絕對的,動是相對的,強調動為“靜之動”,這已然具有了辯證法的思路。
王廷相把生生的運動變化的特性從“太虛”釋放到“氣”本身上,使動靜互涵。 “靜而無動則滯,動而無靜則擾,皆不可久,此道筌也,知此而后謂之見道”10(《慎言·見聞》),動與靜應該是共同作用,也就是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張載尚靜,故而忽視了動,王廷相能發展之,使動靜互涵。
王夫之意識到變動之中也有相對的靜止,即變中有常,常是變的某一種狀態。概括起來講就是王夫之以運動為絕對,以靜止為相對,把氣學一派的辯證法發展到一個較為科學的新高度。他首先突破張載的“不失吾常”,“太虛者,本動者也。動以入動,不息不滯。”11認為作為本體的特殊狀態的太虛本身是變動的,而氣化流行化生萬物就成了“動以入動”而非“靜之動也”。
從張載的“不失常”到王廷相的“動靜互涵”再到王夫之的“動靜皆動”,展現了中國古代辯證法思想發展演變的脈絡。張載能自覺地將辯證法與本體論結合起來討論,可以說是為后來二王辯證法思想地精進打下一定基礎,同時也證明這他的本體論思想中蘊含著儒家生生之意。
四、總結
張載“太虛即氣”的本體論思想可以說處理了兩大難題。一是自儒學取得官學地位后,漢儒建立的天人合一觀以災異譴告為特征的讖緯之學玄而難知,粗糙且不具備本體論的支持。二是在貫徹儒家積極生生的傳統基礎上,消解佛老喜談空無、以解脫游覽、因果緣起解釋世界的整體感通,對世界的縱橫感通給出一個儒學解釋。
張載正是把“知天”作為其理論的突破口,從天道問題入手,先“為天地立心”,再“本天道為用”,直面漢唐以來儒學哲學之弊端,回應佛老如幻如化的宇宙觀,建立了儒家哲學自己的本體論,縱橫感通之間最終由天道進入儒家真正關?的?道問題。他以‘一本散為萬殊,而立于萬殊中的氣之虛,不僅在縱向上成為太虛與萬物形上形下縱向貫通的根據,橫向上更是成為了主體與主體之間橫向感通函攝的根據。以“太虛”中未顯的陰陽交通之性,上乘儒家生生傳統,體現為“至善的流行”;下啟氣學辯證法路徑,為王廷相王夫之辯證法之精進提供理論涵養。如此觀之,張載打通形上形下、萬事萬物的縱橫感通,上繼往圣之絕學,下啟后世氣學辨證之法,以其為中國氣學發展史上承上啟下的關鍵性人物,可謂名實相符。
參考文獻
[1] 王夫之.張子正蒙注[M].北京:中華書局.1975
[2]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原性篇[M].香港九龍:新亞書院研究所.1974
[3]谷繼明.王船山《周易外傳》箋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4]侯外廬.王廷相哲學選集[M].北京:中華書局.1965
[5]王夫之.船山思問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6]邸利平.牟宗三對張載“太虛即氣”的詮釋[J].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38(03):87-91
[7]湯勤福.太虛非氣:張載“太虛”與“氣”之關系新說[J].南開學報,2000(03):53-59
[8]徐洪興.“太虛無形,氣之本體”——略論張載的宇宙本體論及其成因和意義[J].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03):125-131
[9]曾振宇.從張載到王廷相:中國古代氣學的超越與回復[J].齊魯學刊,2010(03):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