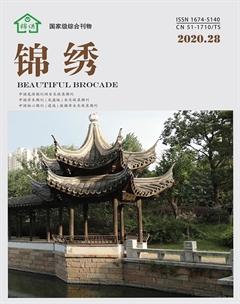我的一個道姑朋友
那年,洛道的春意正濃,閑月人倍忙,處處是繁華的縮影。
怎料,長街落雨,滴破萬千好景,頓時人影疏散,我一人一馬,煙雨如夢。身邊無傘,只好牽馬奔竄。雨勢見急,打花了妝、打濕了人和馬。我本想找一處屋檐避雨,卻被滾滾悶雷慌亂了手腳,還在觀望,身邊卻帶過了一陣風,帶著朦朧的暗香,一把傘遮在了我的頭上。你一襲白衣、佩劍秀利。我抬頭觀望,卻望進了你深邃的眼眸。
雨絲微涼,你攬我入懷,宛如華山夾著細雪的微風,帶著些朦朧的醉意。本是采藥換錢買來的桂花糕,一直藏在懷里,我將它贈與你,溫度應該剛好才是。
你的眼里似有柔情萬種,暖化了我內心的冰雪融融。
自那日一別,我日思夜念,強歡無味,思君采花花無意,念君弄水水無情。我不盼飽腹裹衣之日,卻盼與你相見之時。
我自幼孤身一人,不曾上過學堂、不曾沾染陳世,可我也懂些男女相戀之事,也羨驚鴻照影釵頭鳳,臨邛宴上鳳求凰的愛恨情愁。我想以一紙書信表達自己的愛慕之心,又難狀內心所想。
是否情字寫來都空洞?是否誓言想來都由衷?愛恨本是平常事,從古到今人有之,可愛是何物,只教人,百思想,千系念,萬般無奈把君怨。我斟酌著每一筆一畫,慎重每一字一句。
后來,我每次上山都會刻意看他,他也每次都會送我下山。耳邊的鈴聲輕晃輕晃,我們在山下一起騎馬、一起游玩,像是游作人間的龍與鳳,不羨鴛鴦不羨仙。
他說會保護我一生一世,我想他是喜歡我的,而我也應該是喜歡他的。
一日天降大雨,吹壞了我早已破舊的房子,我亦喜亦悲,悲是晚來風寒無處歸,滿紙柔情化作煙;喜是情愫覺醒意以深,留有嬌靨待君會。我意已決,即使當一道姑,能永遠的陪著意中人,我也愿意。
于是,我帶著他送我的傘和為數不多的行李上了山,可惜世事弄人,他偏偏有事不在觀中。另一道長問我,你是否愿意看淡得失心,不問浮生事;是否愿意終日尋道,即使踏破芒鞋;又是否愿意了卻紅塵舊時事,終生不嫁。我皆回答愿意。從此便白衣素裝成了一名道姑,但是一入道門深似海,從此蕭郎是路人,要守得中級三百大戒,待三年,才可冠巾出游。
之后的日子里,我們每天都能相見,他還是和原來一樣陪我嬉鬧,只是外出的次數愈漸頻繁。他每次下山回來都會送給我東西,有時是餅酥糕點、有時是紅妝胭脂,我都開心極了,但是我害怕被別人看到,他卻說只管收著就好。就這樣過了一段時間,突然有一天晚上,他問我,思念一個人是什么感覺?還沒等我回答,他就轉身離開了,我的心中一陣悸動,可他從此卻再也沒有回來過。
后來我聽別人說,他早已有了塵緣,時間到了,便還俗下山了,我想和他當面對質,可我欲見君,山無棱,江水為竭。
猶記當年洛道春,
花隔云端玉樓人。
而今為姑遺郎恨,
瞞心數載負玄門。
再后來,三年期滿,我冠巾下山,去給一家人做婚事。
禮堂上樂奏蕭韶、燭影搖紅、佳人在側、牲肥酒香。婚禮順利的進行,可恍然間燈火繾綣,映照出一雙如畫面容,宛如豆蔻枝頭溫柔的舊夢。他同他的意中人向我走來,對面不識,卻道:這是我的一個道姑朋友。
頓時間,我思緒翻涌,酒沉頭昏。多年不見,卻是喜宴重逢,望你白衣如舊,神色幾分冰凍。旁人都說,你們是天生的一對,我也覺得你們般配極了。我用假笑扮作從容,只默默飲酒,側耳去聽那些情深意重,裝成你的道姑朋友,可誰知我心惶恐。也許我應該趁著酒醉裝瘋,借你懷抱留下一抹唇紅,再將舊事輕歌慢誦,任旁人驚動。
本是喜宴眾歡時,不料舊人相逢我獨悲,再留于此,也是多幾分無動于衷罷了。
若你早與他人兩心同,又何苦惹我錯付了情衷。我無言辭去,只當做了一場夢,往后以長劍為碑,以霜雪為冢,再不留余情與欲。山門外,雪拂過白衣,又在指尖消融。負長劍,試問江湖偌大,我該何去何從。憶此生,像個笑話一樣,連自己都嘲諷。癡情人,罪是一廂情愿,有始亦無終。
此生若是錯在了相逢,只求能有一個善終。
回去時,我孤身打馬從南屏舊橋邊走過。山雨下,橋上霧蒙蒙,恰如此生,南柯一夢謠,夢醒后跌落粉身碎骨,無影亦無蹤。
作者簡介:屈慶燁(2000—)男,漢族,山東濟寧人,本科,江蘇海洋大學在校學生,長河詩刊簽約作家,青郎研習社入駐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