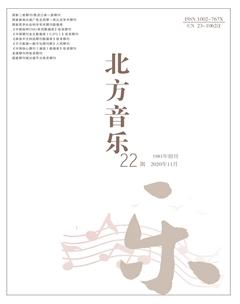山西山曲的文化釋義及其傳承


【摘要】山西山曲作為黃土高坡人民的文化符號,是傳達人們精神意象的載體,與人們的生活緊密相連。可在經濟高速發展的今天,在各種文化現象的擠壓之下,我們卻忽略了身邊的傳統民間音樂,從而導致在傳承與發展上出現了較為嚴峻的問題。要想真正解決這一問題,除了政府的宣揚與號召,最為關鍵的還是需要依靠教育與民間藝人甚至是我們的共同努力。
【關鍵詞】文化傳達 ;審美表達;傳承;發展
【中圖分類號】J632.3?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 ? ? ? ? 【文章編號】1002-767X(2020)22-0037-03
【本文著錄格式】崔蕓.山西山曲的文化釋義及其傳承[J].北方音樂,2020,11(22):37-38,68.
民歌是一個民族社會生活和文化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時代精神、生活風貌和審美情趣的最直接的表現。山西山曲是黃土高坡獨特的民間傳統文化,它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會時期山野的呼喚,雖然吶喊不能算是唱歌,但它卻是山歌最原始的狀態,無疑也是孕育山曲的種子。然而,真正意義上的山曲應該從黃土高坡人們的生產勞動開始說起。
山曲作為一種特定的文化符號,它的形成與流傳必定體現著相應的行為方式和情感思想。正如美國人類學家梅里亞姆所提出的三元分析模式—“概念-行為-音聲”,以及它們之間的互動關系而獲得對人類文化或“人”的宏觀認知。因此,我們要想在山曲這個領域獲得一個宏觀的整體性認知,就必須從“思想-行為”的研究角度出發。
首先,音樂作為人類精神意象的載體,必然承載著一種思想觀念與認知。而山西山曲作為黃土高原人的精神載體,又傳達著怎樣的思想呢?
山曲是由上下句構成的單一部曲式,結構較為簡潔。山曲的上句和下句一呼一應,同時形成一種對稱的美,符合了人類本能的審美需求。
例如:《腳夫調》和《不愛銀子不愛錢》。
正如譜例所示,大跨度音程(如四度音程)的連續跳進以及切分節奏的使用,使得曲調跌宕起伏,從音樂本體感受到了他們的內心訴求,從而揭示了黃土高坡人的審美心態,將他們的自由奔放與豪邁展現無遺。而律動的走向讓人感受到了黃土高原的溝溝坎坎和坡坡嶺嶺。正因為大自然生態的貧瘠,所以黃土高原的人必須擁有更為頑強的意志去戰勝大自然。因此,歌曲的曲調與自然環境形成一定的反差,從而揭示了高原人的精神訴求。像“陽”“喲”之類的延長音,是抒發情感和宣泄情緒的一種自然流露,是山曲中特有的一種吶喊腔。而滑音的出現使得山曲特別符合山西當地的方言腔。正是這些勞動人民想要樸實地表達他們內心情懷的這種思想與需求,才出現了唱山曲這一行為。
其次,對于任何音樂的理解,都不只是對音樂結構的認識,更為關鍵的是要挖掘隱喻其后的象征性闡釋。而藝術人類學對藝術作品的解讀也不僅僅是對藝術作品本身的關注,更是通過對藝術作品形式與文化的整體分析。那么,山西的山曲與山西信天游、內蒙古爬山調又有何淵源呢?
喬建中在他的著作中這樣論道:“以北方而論,四種有代表性的山歌,‘信天游‘山曲流行于黃河中游兩側的黃土高原;‘爬山調在其北部的陰山山地及河套平原,三者的流傳呈焦灼狀態,因此結下了親近的血緣關系。”由此可見,環境、地理對于音樂的起源、音樂風格的形成、音樂的傳播和擴散、發展等有重大的影響,不同環境下形成的原因、風格都不一致。山曲植根于山、陜、蒙地區,體現了民族交融,但又有其獨特個性的風貌。因此,要研究山曲,就必須研究其形成的歷史背景與其產生的文化基礎。
每一種藝術的產生,都有其獨特的歷史文化背景。山西山曲作為一種特定的人文符號,是自然時間與社會記憶有機結合的產物,以“年”為時間向度,以民眾生產生活的進程為空間緯度,構成了人們的整體場域。
首先,從民眾生產生活談起。說起“大花襖”,可能會馬上在眼前呈現出一個黃土高原婦女的形象。沒錯,這已然成為了黃土高原的一大象征。紅色和綠色的搭配,格外搶眼。可為何這樣的“大花襖”會出現在此地而不是江浙一帶呢?這或許就是山曲與穿著需求的異質同構了。不僅穿著如此,炕頭的紅綠被面,掛在房梁上金黃色的玉米,貼在窗戶上的艷麗的大紅花,無不反映著黃土高坡人的審美需求。正是因為黃土地的貧瘠,人們才會需要這樣豐富的、明亮的色彩來填補內心精神的空缺。而山曲的出現與此現象或許是同一緣由了。因此,山西山曲作為“感自然規律而成,蘊人文精神而豐”的時空文化點,是民眾集體智慧的結晶,是生命意識的物化。在長期的文化積淀進程中,山曲就是這樣簡單、樸實地反映著黃土高原人文情懷、精神信仰、文化倫理和審美追求。
對于民間音樂的理解最重要的不是對音樂曲式和聲的分析,而在于對音樂意義“前置結構”的預設,而這種預設需要伴隨文化的經驗才能實現,體現出外向性的民俗場景。山西山曲作為一種最接近人的內心世界抽象性的“心聲”,可以體現出人們精神性的表達,它不僅表現出人們自我審美的行為方式,同時也反映了人們的審美情趣。正如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在《美學》中寫道:“人類本性中就有普遍愛美的要求。”生活就是美,美就需要歌唱,愛美是人的本性,生活需要美,而山西山曲來源于生活,是黃土高原人們真實生活的體現,他們生活中質樸的美正體現于此。
作為人類精神文化的本體象征,任何一種音樂風格的存在,首先是人本的體現,是反映人的精神的。再如江浙一帶的音樂,早在20世紀60年代初,就有金祖禮在其論著中提出“小、輕、細、雅”四字概括其音樂風格。當我們對比《茉莉花》和《腳夫調》時,會有怎樣的心理形態呢?山曲之所以如此粗獷豪放,正是因為它匯集了黃土高原一帶自然與人文的生活精華,所以山曲作為一方土地的傳統文化遺產,其人文價值是不可估量的,因為這是一個民族社會生活和文化傳統的真實映照,是一個地區特有的生存方式和需求的文化傳達。
而現如今,在科技飛速發展、經濟全球化的今天,各種文化現象相互沖突、相互交集,從而導致我國民間音樂文化的傳承與發展面臨著更為嚴峻的挑戰。山西山曲曾作為黃土高原人精神文化的食糧,是不可或缺的。可是現如今呢?是因為經濟的高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所以不需要唱山歌了嗎?它沒有所謂的功能意義了嗎?其實并非如此。
很多土生土長的山西人,從小就開始接觸音樂的學習,但是他們對山西民間音樂了解的卻是微乎其微。這一現象無疑說明了一個真實但又非常不樂觀的事實:民間音樂藝術在傳播與教育上存在著很大的弊端。要想解決這一問題,除了政府需要正確的引導、確立民間藝術文化建設的關鍵地位以外,還應該適時加大宣傳和保護力度、廣度,創新民族民間藝術的傳播方式和體制,共同促進民族民間藝術的傳播、傳承以及創新。
我們經常這樣說,傳統文化中既有精華也有糟粕。當今,我們應當認真思索的是,傳統民族民間音樂的精華是什么?民族民間音樂怎樣科學合理的傳承?不能無原則地留戀傳統音樂,也不能主張復古的歷史倒退,應該在精心鑒別與篩選的基礎之上,對傳統民族民間音樂藝術進行選擇性的繼承和發展,又要避免單純形式上的“創新”,必須注重作品形式與思想內涵的共同創新、健康發展。
音樂離不開功能,任何一種民歌都有其特定的功能性,某些音樂形式的消失,是因為失去了它的功能和意義。在當前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過分拘泥于所謂的原生態,強調“原汁原味”“不走樣”傳承,也是有悖于音樂藝術發展規律的。而山西山曲在某種程度上來說,不但具有功能性還有很強的娛樂性。就如阿寶演唱的《想親親》,就是山西山曲河曲的民歌,他的這一唱,并非是原汁原味、一成不變的照搬照抄,雖然有一定的表演性和舞臺化,但這卻真正意義上推進了山西山曲的傳承,讓這首山西民歌家喻戶曉。所以,在未來的民間音樂傳承與發展過程中,我們應該以一種更為開放的胸襟和眼界來看待傳統文化以及傳統音樂的傳承與發展。我們應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學校音樂美育教育相結合,特別是在中小學音樂教育中的傳承,這是對中小學生進行本土音樂文化熏陶和教育,加強民族團結和愛國主義教育的良好時機。
試想,如果國家教育部頒布一些關于“讓民間藝術走進校園”的條例和規定以作為音樂教育和美育教育的導向的話,一定可以促進民間傳統文化的傳承與發展。讓傳統文化以走進課堂,不僅可以讓孩子們感受到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形式多樣、精彩紛呈,還可以讓他們更加熱愛自己的本土文化,增強民族自豪感,加速優秀民族傳承。云南大學馬居里教授曾這樣說過:“本民族的文化還是需要本民族的孩子來傳承。”我認為非常之對。我們山西地區的音樂,如果讓一個別的地區、別的民族的人來接繼,不僅傳承的不徹底,而且會顯得“不地道”。正如美國人類學家索爾說的:“一個特定的人群,在其長期生活的地域內,一定會創造出一種適應環境的文化景觀和標志性的民俗符號。”所以,我們自己的文化需要我們自己傳承。
雖然社會經濟正在飛速發展,但我們的民族民間藝術似乎也在飛速地消失。每一年、每一月、每一天、每一小時都有可能有一個優秀的樂種、一首民歌、一個藝術形式徹底消失在我們的世界里。就如二胡曲《二泉映月》,如果沒有楊蔭瀏老師發現并極力促成這首曲子的錄制,那今天的我們就難以聽到這樣美好的撼動心靈和靈魂的曲子,日本指揮家小澤征爾跪著聽完《二泉映月》被感動得泣不成聲。如果當年楊老師沒有發現或者發現了也不作為,抱著事不關己的態度以對之,此曲或已絕響了。阿炳只演奏過一次嗎?只是楊老師一個人聽過嗎?非也。所以,當我們在面對我們自己優秀的傳統民間藝術,面對那些優秀的民間藝人的時候,我們是不是應該除了有心靈上的的觸動,還應該有某種意識上的覺醒?
我們中國自己的傳統民間藝術,在社會政治建設的同時,也遭受過幾次重創。“文革”時期,藝術是政治的工具,“文革”中紅衛兵“破四舊”,對于民間藝術的打壓野蠻粗暴、不計后果;還有在改革開放中,對于傳統民族民間文化和藝術造成了一定程度上“建設性的破壞”。然而這些破壞之后,還是可以挽救的。但是,當我們自己的傳統民間文化和音樂被我們自己認為是“落后”的、“愚昧”的、“out”的時候,那才是真正危機的開始。所以,對于傳統文化和民間音樂最可怕的顛覆就是民眾對自己文化的忽略遺忘、自卑甚至是鄙視。
山西山曲是山西人自己歷經時事變遷、被歷史巨浪篩選并傳承下來的優秀傳統民族民間音樂,作為一名身處高校的音樂藝術工作者,深深地覺得承載傳承祖輩們智慧的結晶,讓其在藝術的殿堂里發光發熱,責無旁貸。雖力量綿薄,或許也做不了什么大事,但深深地覺得自己要從具體的點滴做起,認真學習并承擔起傳承和傳播優秀民族民間音樂藝術的責任,廣聞博學,積累知識,積極投身于鄉野民間,集大地精華于視聽,豐盈和提升自我的同時,極力為優秀的民族民間優秀音樂藝術的傳承和發展做一點小事,實為我之幸事!
參考文獻
[1]馮寶志.三晉文化[M].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
[2]山曲民歌合唱曲集[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00.
[3]申波.審美意識與音樂文化[M].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2005.
作者簡介:崔 蕓(1979— ),女 ,云南財經職業學院基礎教育部講師 ,研究方向:音樂表演(聲樂演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