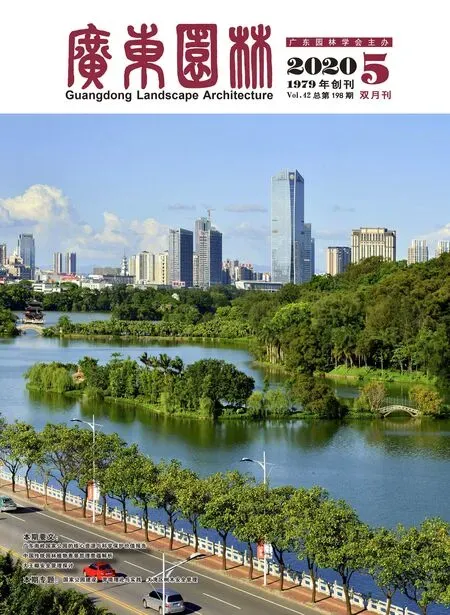星球時代下的專業認同與設計文化:對話查爾斯·瓦爾德海姆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Design Culture in Global Age: Dialogue with Charles Waldheim
嘉賓介紹:查爾斯·瓦爾德海
姆(Charles Waldheim),美 國-加拿大籍建筑師與都市主義者。瓦爾德海姆探索景觀、生態及當代都市之間的關系,同時是多部被廣泛翻譯與出版的著作作者與主編人。他是哈佛大學設計學院約翰·E·歐文教席教授,兼任城市化辦公室主任,是羅馬美國學院會員,加拿大建筑研究中心訪學基金獲得者,萊斯大學庫利南主席,及密歇根大學桑德斯基金會員。
導讀:廣東園林雜志海外風景園林思想專欄的首篇訪談有幸請到了哈佛大學風景園林系前系主任,同時也是景觀都市主義理論的提出者與主要倡導者的查爾斯·瓦爾德海姆教授。星球城市化與景觀都市主義都是以城市環境為主要研究對象,建立在對20世紀中期以來社會與經濟發展模式的反思和批判上發展起來的理論,兩者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系。瓦爾德海姆作為景觀都市主義的主要研究者,對星球化議題同樣有著深刻的見解。本次訪談集中探討了星球化與在地性的并存性及其關系、風景園林學科自身折射出的社會不公平性、景觀都市主義者的身份與責任、多學科協作中風景園林的角色與潛力,以及學科內核從生態規劃往設計文化轉向的趨勢等。
蔡淦東:最近出版的一期《New Geographies》(新地理)雜志取名“Extraterrestrial”(地球之外)①《New Geographies》是由哈佛大學設計學院出版的設計研究刊物,自2008年創辦至今,主要關注設計學科與地理空間的關系。,反映了設計學科的關注點延伸至外太空的最新學術思潮。伴隨著星球化研究的進行,一系列以星球為設計尺度的競賽也盛行起來,例如設計人類在火星上的棲居地。您如何看待星球議題對風景園林學科的影響?
查爾斯·瓦爾德海姆:在過去的十年當中,來自設計學科的多位學者,包括建筑師、城市設計師和風景園林師,從不同的角度思考了全球或星球議題。20世紀展開了來自規劃和社會科學領域的“全球城市”討論,這可以認為是對星球城市化批判性討論的開端。全球城市理論關注的是作為社會與經濟網絡核心的大城市,而星球城市化則認為整個星球都已城市化。近年來對星球城市化探討得最深入的當屬追隨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研究成果的尼爾·布倫納(Neil Brenner),他的研究與資本經濟網絡、氣候變化、物理環境構成等議題相關,同樣認為地球上的每個角落已經城市化。關于你問題里提到的另一個話題—地球以外,我認為這需要追溯到1968年阿波羅8號太空船的宇航員拍攝的“地出”(Earthrise)照片。在那之后的20世紀70年代我們可以看到全球意識與星球意識的出現,隨之而來的則是對資本主義的批評以及對環境問題的關注。回到過去十年設計學科的討論中,來自麻省理工學院的Hashim Sarkis、哈佛大學設計學院的Toshiko Mori以及布倫納都提出了諸多有關全球性和星球化的探討②Hashim Sarkis,現麻省理工學院建筑規劃學院院長。Toshiko Mori,哈佛大學設計學院建筑系教授。。長期以來,風景園林學科善于為特定場地輸出知識,而建筑與城市學科則在思考全球問題上更得心應手。這樣的情況隨著風景園林逐步地適應以星球化為核心的理論框架而得到改善。
蔡淦東:這與您提出的景觀都市主義者的概念相符,即風景園林師在更大的星球尺度上實踐,而非僅僅關注于場地尺度。
查爾斯·瓦爾德海姆:對的,這與風景園林師如何看到他們自身的工作,以及誰來委任工作有關。在過去,相比起由工程師負責基礎設施建設,規劃師進行城市規劃,建筑師提出城市設計構想,風景園林師往往是最后被委任的,而這個情況因環境保護思潮的盛行而有所扭轉,越來越多風景園林師得以介入到場地組織及基礎設施的建設當中。
蔡淦東:而另一方面,美國風景園林協會基金會(Landscape Architecture Foundation)最近公布了本年度“研究與領導力獎”的6位獲得者,其中至少有3份獲獎提案都涉及到在地性的問題:深入地區與場地,與當地居民互動且傾聽其聲音,用設計的方法嘗試解決明確存在的本地問題。盡管設計地球乃至太空的熱情高漲,與之相對的對在地性議題的深入關注似乎也是當下的一大趨勢。您怎么看待這兩個看似背道而馳,但同時出現在我們專業討論熱潮當中的議題?
查爾斯?瓦爾德海姆:你提到的兩個趨勢的確是并行的。我認為啟蒙運動是不完整的,它具有全球的影響力,但卻沒有體現出社會階層間的流動及地理上的遷移,這兩者往往需要依靠教育來實現人與人的連接①啟蒙運動一般指發生在歐洲17到18世紀的一場涉及哲學、文化、科學等方面的運動,但也有學者認為,啟蒙運動的影響力是全球性的,并不局限于歐洲。瓦爾德海姆這里提及的啟蒙運動也是基于這樣的視角。。我成長于一種不依靠出生地而是遷移地來定義自我的文化,在這里你作為美國人或加拿大人的居民身份無關種族,我認為這是一個明顯充滿問題的歷史。得益于啟蒙運動我們才能跨語言和文化地進行全球性的連接,但它同樣帶來了地方文化與認同感的丟失。我堅信只有通過教育、交流與分享,人文精神才能跨越種族得以延續。我們正在向自己—既是作為哈佛設計學院也是作為風景園林學科,提出一個艱難的問題,不僅關乎在地性,也關乎個人認同和群體認同。毫無疑問,風景園林、城市規劃、都市設計與建筑學自古就是權力表達的工具。設計并建造世界本身即是權力的表達。一個種族主義的社會能產生種族主義的設計,一個種族主義的學校則會延續這狀況。回溯在北美大陸上發生的對原住民的屠殺以及黑奴歷史,我們仍然在尋求方法應對這種狀況。問題是風景園林學科如何向這一段種族主義歷史作出回應,以及如何提出具有批判精神的問題。這同時也塑造了另一個有關我們學科未來的問題:依靠作為西方帝國主義產物的現代風景園林解決上述困境是難以想象的,又或者說,我們該如何為學科進行去殖民化,才能以一種后帝國主義或后資本主義的學科姿態出現?我認為關于這個問題的討論有很多。而這也是我們目前最感興趣的議題之一。
我不認為星球化與在地性之間存在矛盾,這兩者只關乎我們的工作對象和方向。我們學科的歷史建立在特定的國家與地區認同感之上,或為特定文化所服務,在整個工作生涯當中我都致力于超越這種族群主義。我們用教學作為媒介,通過知識的教育與環境的營造改善人們的生活質量。談到個體認同,我認為我在哈佛設計學院的同事提出了諸如新人種學(New Ethnography)或新人類學(New Anthropology)的研究課題,皮埃爾?比朗格爾(Pierre Belanger)和加雷斯?多爾蒂(Gareth Doherty)在各自的研究領域提出了關于風景園林學科建構人類主體性的新思考②皮埃爾·比朗格爾成立了非盈利設計研究工作室OPSYS,長期關注于設計學科與社會生態學、地緣政治學的關系。加雷斯·多爾蒂在哈佛大學設計學院的主要研究方向為風景園林與人類學,并深入研究伊斯蘭地區、西非及拉丁美洲的風景園林發展。。誰是土地的擁有者?如果說西方現代景觀是精英群體通過資本主義把自我表達于建成環境、花園、莊園或公園,那么這些建成空間的主體性該如何理解?又該如何被用于對學科進行批判性思考?這些正是當下最有趣的學科議題。
蔡淦東:我們已經談到了系統性種族主義,我想進一步跟您探討關于不公平性的話題。我注意到最近哈佛設計學院舉辦了一個名為“Architecture, Design,Action”(建筑、設計、行動)的訪談,您也參與其中。盡管訪談內容是關于系統性種族主義,我認為其中同樣涉及到了全球與本地的問題,例如訪談中有關“美國建立于竊取而來的土地之上”,“我們應更多地向少數族裔建筑師學習”,“我們建造的世界是以系統性種族主義與資本主義為基礎”等討論。您認為系統性的不公平性跟星球化與在地性之間的鴻溝有關嗎?風景園林又是否可以充當二者間的調和者?
查爾斯?瓦爾德海姆:這是可能的,但我更想聽聽你如何思考它的可能性。最近圍繞不公平性以及學校內部存在的結構性種族主義等討論,與美國的原住民群體問題息息相關,這部分源自白人優越性思維作為定義“美國夢”的標準已滲透到各個族群當中。我完全贊成我們應重新思考自身的歷史,并承認黑人景觀一直被低估、被忽視、缺乏理論化與系統記錄。因此,在我想象風景園林能解決什么問題之前,我們應首要思考的問題是風景園林在上述問題中都扮演了什么角色。一方面,我通過歷史和理論課程上向學生介紹風景園林在過去如何通過建成作品與學科建設鞏固了白人階級的權力,另一方面,我提出了這樣一個質疑:倘若風景園林的內核是白人優越性,我們該如何克服它而前進?也許這個問題是如此嚴重以至于更好的解決方案是尋找一個新的領域以及創造新的詞匯。當現代風景園林學科的概念在19世紀被發明時,倡導者們正是宣稱著當時的專業分工已不足以應對社會的變化。我們正面臨著類似的時刻,人們向建筑與風景園林提出了是否可以做到去殖民化的質疑。
從這點出發,我們現在的討論應該是全球化議題如何符合并促進解決以上問題。剛才提到的群體認同感與資本主義之間的關系,學術圈中有一個共同的認知,即這是由經濟系統導致的結構性問題,而非單純的意外或危機。如果將所有事物擺在一起,無論是族群認同、帝國主義、去殖民化還是資本主義,毫無疑問一切都是相互連接的。全球化就是一個人類在全球尺度互相連接的概念,同時也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延伸。把全球與本土聯系在一起思考可能會出現一個問題,即我們可能會因此喪失了對資本主義及結構性種族主義的政治批判力。
蔡淦東:在《New Landscape Declaration》(新景觀宣言)①《New Landscape Declaration》于2017年出版,收錄了2016年美國風景園林協會基金會組織的一次活動中的重要發言。2016年是由麥克哈格為首撰寫的景觀宣言發布的50周年。一書中,理查德?韋勒(Richard Weller)提醒我們在1966年宣言的第一個版本是由5名白人撰寫,關注點僅在北美,也沒有涉及社會公正問題、物種瀕危問題以及氣候變化問題。50年后的新宣言有超過600名參與者以及32名演講者,涉及的專業議題也比當年廣泛得多。然而當我翻閱所有演講者背景的時候發現,其中僅有兩位來自拉丁美洲,兩位來自中國,還有一位來自印度。剩余的演講者都來自西方國家。不難想象,仍然有許多聲音未被聆聽,許多實踐與想法沒被發現和重視。您認為如果要撰寫2066年版的景觀宣言的話,它應當包含哪些內容?
查爾斯?瓦爾德海姆:把時間線拉長是一個有趣的思考方向,尤其考慮到氣候問題的時間性。我不清楚我能否看到那一天,但我拭目以待。我認同你說的投入更多注意力到發展中國家(Global South)②Global South屬于社會經濟學與政治學范疇,國際上使用該詞一般泛指發展中國家與地區,并非指代地理學中赤道以南區域。,并且我會提出這樣的問題:發展中國家的上述問題可以通過我們學科的發展而解決嗎?盡管現代風景園林是一個西方世界的概念,但它從歐洲出發輸送到世界各地后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尤其在東亞地區的快速成長是令人驚嘆的。然而風景園林學科作為一種媒介可以一直向不同的觀念和聲音保持開放嗎?抑或是我們該發展出一種新的思考、工作或描述方式?我堅信依靠教育與文化分享,大學作為一種機制可以幫助人們脫離貧困,實現階級躍升,并融入到全球網絡之中,這也是我來到哈佛設計學院的原因之一。當然有人持反對意見并認為我們需抵制全球化以捍衛當地文化。我認為兩者兼得是可能的,這并非簡單的零和游戲。拓展風景園林學科意味著承擔更多的責任,我們依然任重而道遠。不過我對是否需要新的詞匯這一觀點依然保持開放態度。
蔡淦東:這與專業身份認同有關。在您的著作《Landscape as Urbanism》(景觀都市主義)中,您提出了風景園林師作為時代的都市主義者的口號。在2016年的新景觀宣言會議上您也提到了這一點。景觀都市主義者(Landscape Urbanist)的專業身份與責任是什么?它與風景園林師(landscape Architect)的區別又是什么?
查爾斯?瓦爾德海姆:我的觀點是,西方的風景園林學科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階段扮演的角色更多是像音樂劇一樣為上流社會和精英階層服務的城市化副產物。從未有人期待或渴望風景園林成為人人都能享有的資源。從繪畫題材、花園形式到公園發展模式,作為媒介的風景園林一直改變著自身的出現形式。當我在25年前第一次創造“景觀都市主義”這一術語時,我希望憑借這一修辭行動提醒人們,我們必須調整實踐的方向。我一直使用這樣的觀點嘗試引起更多人思考我們學科究竟能做些什么。在我第一次接觸風景園林時,它是關于植物材料以及如何利用植物進行設計的。這在某一時期是正確的理解,但我認為對我們學科而言完全不夠。因此,景觀都市主義所倡導的是風景園林師取代規劃師、城市設計師以及建筑師而被雇傭,因為后三者還未發展出一套完整的環境應對策略。在北美,大多數的風景園林項目并非建立在設計學院之內,而是在林學院、農學院以及自然科學學院,這使得許多人依然認為風景園林是關于花園設計以及環境管治、保育及林學的。我尊重這一觀點但我不認為它是我們學科的未來。景觀都市主義在過去的25年中一直宣稱風景園林師應重新武裝自身并如一名都市主義者般工作,這恰恰是當年學科被創立時奧姆斯特德的想法。奧姆斯特德深知我們學科是關于如何塑造城市、整合基礎設施與自然系統的。最近我們更頻繁地使用生態都市主義(Ecological Urbanism)一詞③生態都市主義可以被看作景觀都市主義的批判性延伸。相關理論著作包括莫森·莫斯塔法維與加雷斯·多爾蒂于2010年合著的《Ecological Urbanism》(生態都市主義)。,因為我們發現在實際操作中它具有更好的精確性。
有一個有趣的爭論:一方面,如果你從不質疑、批判或重命名自己的專業或學位,你將無法對外部情況進行回應并與社會脫鉤。另一方面,我不建議每次遇到一個新議題便更換學科的名字,例如一次颶風、一場流行病,或一場大火災。已被認可達數個世紀的知識突然被認為并不完善的例子屢見不鮮,19世紀下半葉的風景園林學科就是針對已有的建筑、工程、花園設計與藝術等學科不完善而被發明的。隨著時間流逝,我們學科逐漸變得熱衷于懷舊,而喪失了原有的激進性。20世紀第一個10年創立的城市規劃學科,50年代創立的城市設計學科以及25年前創立的景觀都市主義,都是試圖通過重塑專業實踐與討論,來為風景園林學科帶來相關性的嘗試。關于風景園林師是否有足夠的社會身份認同以面對今日的挑戰,我認為仍沒有明確答案。
蔡淦東:我認同我們應努力保持專業的靈活性并使之能更好地應對世界變化。風景園林在20世紀中期曾受到生態規劃與環境科學學科的深刻影響,20世紀末則是建筑師產生了對風景園林的興趣,并通過一系列重要的競賽帶來了建筑理論與策略。我一直在思考的一個問題是:我們是否應減少對外部學科的吸納,而是通過自身技術提升與理論發展以建設更明確的專業身份?又或者我們應保持風景園林的“模糊身份”,以更好地發揮風景園林學科的綜合性特點,從而更好地粘合各個學科?
查爾斯?瓦爾德海姆:我認為將“模糊性”解讀為一種潛在的“靈活性”來討論這個問題是個有趣的角度。我注意到許多人都認為我們專業缺乏強有力的地位,實踐中也有不少人提出工程師在20世紀占據了風景園林師的地位。我認為在這樣的挑戰下風景園林才能顯示出最有趣和價值的一面。景觀都市主義思想的出現并非因為我,而是主要因為一系列的機遇、空缺被證明與風景園林息息相關,我們需要做的就是把注意力放在最有價值的技能上。我要額外提到幾點:首先,我不認為整合所有知識是可能的。我們必須做出選擇,決定該吸取多少的科學知識、植物知識、歷史理論知識以及城市知識以塑造我們的專業領域。學校里關于此的爭論每天都在進行,而我個人反對風景園林師融合一切知識的想法。我認為最首要的是設計文化的問題,即景觀都市主義者該如何扮演引領建筑師及城市設計師的角色問題。這與我們上一代同行有根本性的區別,他們是提倡運用科學知識到規劃而摒棄設計的一代生態規劃師。我認為這是一個重大的錯誤。第二,景觀都市主義者需在設計場地尺度而非區域規劃尺度上熟悉生態系統策略。第三,景觀都市主義者需要具備與多種應用型學科協作的能力。
在我看來把風景園林或景觀都市主義看作一個解決問題的工具是錯誤的,它必須是一個關于文化、想象力,以及對新生活與工作概念思考的活動。如果把我們的工作降低到純技術性的程度,我們將在與其他領域的競爭中處于不公平的劣勢,包括房地產、市政工程,以及其他相關領域。有鑒于此,設計文化以及風景園林作為一種文化形式的概念是我的思想核心。因此,我在書中與教學中提出的建議是減少對技術層面的過度關注,而更關心風景園林師的價值。我們能為社會帶來的將越發與技術無關,而與想象力、提出構想的能力以及描繪世界的能力有關。從這點來看,風景園林學科正在變得越發強大與備受矚目,并且這一切并非發生在某個具體的地區,而是通過風景園林教育在全球范圍內發生。因此可以認為,景觀都市主義者作為全球性設計師這一概念,是建立在對傳統風景園林師定位的批判上。
蔡淦東:您剛剛反復提到了“設計文化”這一概念。在《景觀都市主義》一書中,您認為與當代風景園林更密切相關的是設計文化,而非科學導向型的環境規劃。在另一本著作《Cartographic Ground》(土地的表達)中您同樣提到了空間精確性與文化想象力的問題。我認為設計文化是您的學術思想中十分關鍵的一個概念。這讓我想起最近一個流產了的Sidewalk Toronto城市設計項目①Sidewalk Toronto是由美國Sidewalk Labs負責的位于多倫多濱水區的城市設計項目,因在城市設計中大量引入技術創新而備受業界矚目,但于2020年5月宣布項目終止。。盡管項目遇到的問題很多,如新冠病毒的爆發,而一個無法被忽視的問題是項目過度強調技術導向與智慧城市概念而非文化概念。人們的注意力被過多地集中到對信息安全和全球共享系統的討論中,本土文化與認同卻遭到忽視。您怎么看這一項目?
查爾斯?瓦爾德海姆:毫無疑問,多倫多是全球范圍內一座重要的城市,也是北美少數的幾個實踐景觀都市主義的城市。他們聘請一流的風景園林師重塑城市的濱水區,WEST 8、MVVA、JCFO等事務所在那里實踐著由風景園林引領的城市項目。Sidewalk Labs的失敗之處部分來自于對公眾想象力的忽視,以及對當地文化的錯誤理解。作為一名移民到加拿大的美國人,我生活在兩個國家,我認為Sidewalk Labs是一個非常典型的美國式新自由主義與放任主義的產物,即由技術方和私人企業完全接管數據。這引起了所有關于公共領域隱私權的尖銳問題。我把這看作是一種文化上的錯誤理解,一種把美國思考公共空間的政治模型移植到一個有著迥然不同的文化政治背景環境中的錯誤操作。我同意你說的缺乏空間想象力和高水平的設計同樣是這個項目失敗的癥結所在。
蔡淦東:非常感謝您在今年特殊背景下的繁忙開學季抽空接受了這一次的采訪!
查爾斯?瓦爾德海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