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知筆墨的客觀性
王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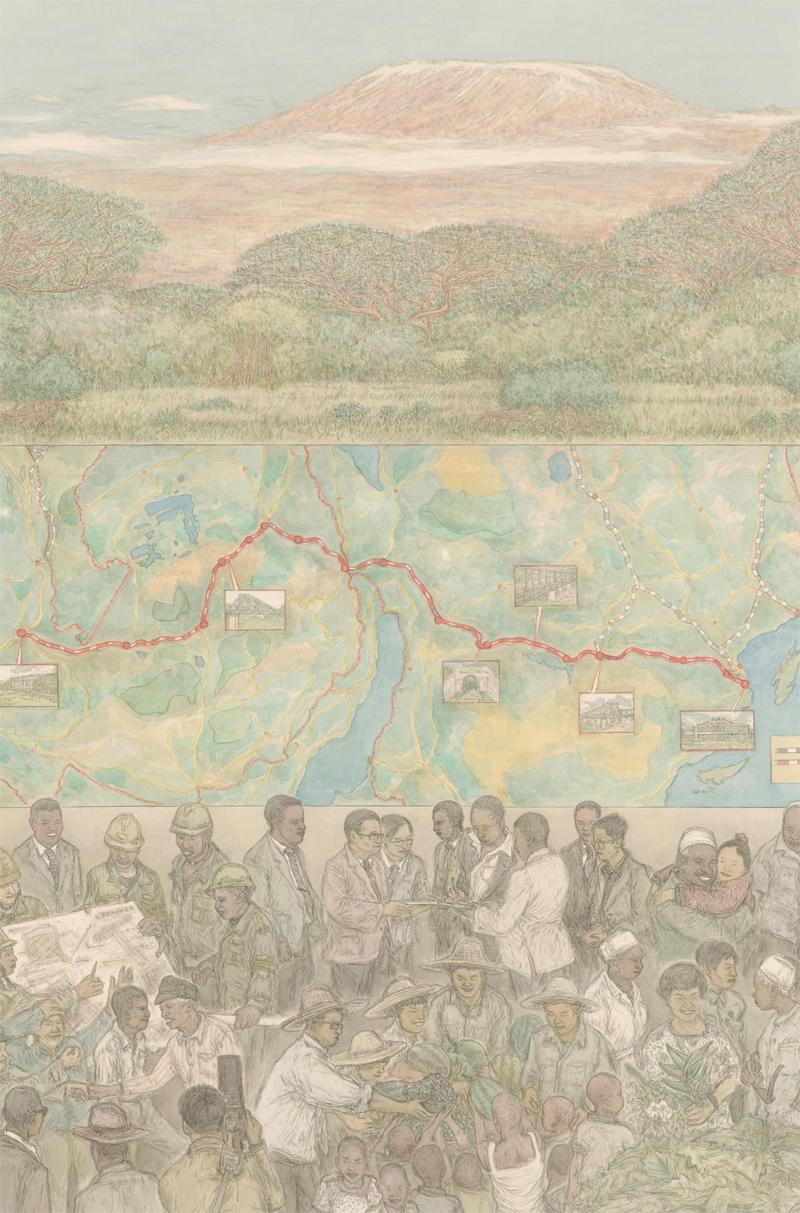

關于筆墨問題的爭論,在中國畫再認識的進程中不斷被關注。有的認為筆墨是主觀產物,是中國畫成立的根,是與中國畫的審美屬性相匹配的標準之一,是中國畫意象審美實現的載體。有的認為筆墨應是具體的產物,是因地制宜的,是由客體生發的。“筆墨是中國畫造型的精神實質。……筆墨的運用不是先定的,是從對象來的,氣韻生動也不是先定的,也是從對象來的。”蔣兆和先生所說的對象就是客觀,對于水墨人物畫來說就是具體的人,對于人的認知是前提。對于蔣兆和先生的《流民圖》來說,直接感動觀者的,是經由造型和筆墨處理的活生生的震撼人心的感人形象,筆墨與造型在此都退居其次。形象的感人是首位。筆墨與造型都是實現形象的方法與工具。觀者只有在感動之余,才能感受筆墨精妙與造型的精彩。由此可見,筆墨的地位屬于技術認知的層面,對于藝術整體的感知層面是從屬的。這樣,“唯筆墨”者也許會不太認同此觀點。繼而,帶來了“客觀的筆墨性”與“筆墨的客觀性”的問題,以及兩者的關系與意義。筆墨從來不是獨立存在的,也不是純粹主觀的產物。早期的中國畫,由于材料的限制,多在絹帛上繪制,以線的勾勒為主,墨的運用只在渲染的部分出現,可見筆與墨的關系又有分層與從屬。“筆以立其形質,墨以分其陰陽。”(韓拙)此時,筆是主體,線是筆的顯現;線是骨,是支撐畫面的主導;墨是附屬,是烘托線的地位與畫面整體氣氛的附庸。筆墨是手段,而非目的。筆墨具有成就造型、構成意象、生成意境的功用價值。
客觀的筆墨性在于筆與墨的實施應是客觀的、精準的,不是濫觴的、無節制的,不應成為僅僅為了發揮筆墨語言的筆墨游戲。筆墨語言一直被當作中國傳統文人畫成立的最為主要的評判標準。筆、墨、水、紙的有機交融與配合,而產生多變性,在可控與不可控之間帶來水墨韻味的審美結果。大家對于審美結果的認同,背后是千百年來的一整套的審美機制的要求與審美范式的支撐。在大部分審美認同的同時,許多人也會把筆墨神圣化、中心化,認為沒有筆墨的中國畫不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中國畫。筆墨語言在此時喪失了客觀性,失去了其應有的價值與意義歸屬。“中國文人水墨畫作為傳統中國畫的一種,堅持以筆墨為中心,無可非議,但是與此同時,不要忘記這筆墨規范有恒定的一面,也有變化的一面。而作為‘中國畫這個大傳統,就很難用‘筆墨中心來概括它的基本特征了,不論從美學的角度,還是從技巧、技法的角度。”由此可見,筆墨問題是客觀的、發展的,不是一成不變的。筆墨問題也是時代性問題,是隨著不同載體、不同時代審美變遷而變化著的,進而產生不同的審美認知與意義。單就水墨人物畫來說,人物的時代性凸顯無疑,無論人物的服飾、環境、器物、飲食,還是人的審美品位與精神氣韻等,都有異于古人,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審美變遷,而且此種變化還在過程中,是現在進行時。筆墨此時應有其客觀性的一面,是針對現實客觀物象而產生的屬于現代人特有的筆墨語言。筆墨的方式方法,可以是傳統的,而經過新的載體(現代人)的碰撞,就會產生不同于傳統要求的筆墨范式。這也是新的筆墨規范生成與建構的過程,舊有的筆墨規范被激活了,同時延續了傳統的筆墨價值,筆墨語言得到了良性的傳承與接續。經由具體的現代人作為客觀表現的對象,筆墨的表現同時也具體化了。人的具體而微的結構特點、服飾特征、環境道具的特質等,對于筆墨來說,都是具有新意的載體,筆墨此時是客觀的、具體的。筆墨對于整個水墨人物畫來說,是更好地實現人物畫人本精神的工具,不再具有中心的主導地位與位置,是具有客觀性的產物。
筆墨的客觀性是指筆墨的出處是客觀的、具體的。在水墨人物畫中,筆墨是隨著客觀造型的形體而生成的,不是主觀任意為之的產物。筆墨的好壞,也不是獨立判斷的。筆墨如果失去載體,將會失去其本身的意義。誠然,如觀宋人山水,每一筆、每一墨,都在其合適的位置上。宋人山水的筆法墨法也皆來自大自然,如斧劈皴、豆瓣皴、解索皴等,都是借用筆墨之法,比擬大自然的生長規律,概括總結出來的法則,是一種與自然的肖似。此時的筆墨對于宋畫來說也是一種客觀性存在。經由客觀性的筆墨來表達畫者對于自然的客觀性的敬畏與認知。由此,來表達畫者宏大的宇宙觀與寬博的生命意志。
“至于山石竹木水波煙云,雖無常形而有常理。”(蘇軾)由于“理學”觀念的盛行與廣泛傳播,宋代鑄造出具有客觀意識、具體而微的審美精神。宋代的繪畫,無論是花鳥畫、山水畫還是人物畫,都代表了中國繪畫的寫實高度與特質。由此看來,筆墨的客觀性在宋代繪畫中表現得淋漓盡致。筆墨的客觀性不是完全沒有主觀的成分,一張作品的出現,一旦有了形象的注入,就會有主觀的處理與安排。就現代水墨人物畫來看,我們面對活生生的人,怎樣來面對他,通過怎樣的筆墨與造型的方式轉化到畫面當中,都會成為現代水墨人物畫面對的實際問題。筆者認為,畫者應放下頭腦中慣有的概念式的筆墨與造型的認知,樸實地平視客觀對象,從對象中發現特質,并生成與之匹配的筆墨,此時的筆墨是優質的、精準的、客觀的。筆墨有了客觀的載體,載體經過筆墨的造化而具有生命感。了解筆墨的客觀性有助于我們敬畏自然與客觀,避免陷入主觀任意妄為的惡性循環。“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發現。”(羅丹)我們的盲目自信與自大,會使我們喪失觀察的動力與發現的能力,如果沒有發現、尋找、探究的動力,繪畫也就失去了意義。面對新鮮的客觀對象,我們稍有心,就會發現客觀的生生之意,而“寫生”的“生”,恰有此意,生生不息之意。此時,筆墨的實施,一定要伴隨著“生意”,新鮮的筆墨感覺也會帶來新的方法與規則,舊有的程式化的筆墨在新的客觀面前會統統失效。正如前文所說,具有時代性的筆墨也許會出現,變化著的筆墨方式也會出現,水墨人物畫的歷史也會經由新的筆墨介質出現而傳承有緒、延綿不絕。筆墨的客觀性的認知有利于中國水墨人物畫教學體系的完善與建構,培養學生對于客觀的興趣與發現,運用客觀的筆墨語言表現客觀精神,避免過于主觀表現,進而形成良性的客觀的筆墨觀,有助于水墨人物畫教學的現代性轉化與發展。
對于優質筆墨關系的理解也是必要的。筆墨長期以來一直作為中國畫(文人畫)的魂與根,繪畫以筆墨的優劣為評判標準,講究見筆見墨、筆清墨潤,用筆須“平、圓、重、變、留”,用墨“清、潤、沉、和、活”,而“板、刻、結、滑”皆為敗筆,“濁、漬、死、污”皆為庸墨。同時,筆墨也具有形而上的價值體現,好的用筆要求有四勢—“筋、肉、骨、氣”,好的用墨講究“水墨淋漓”“渾厚華滋”,由此帶來了筆墨的文化審美象征意蘊。筆與墨對于畫面來說不是分離的,“筆與墨會,是為氤氳”(石濤)。筆中有墨,墨中見筆,筆靠墨生輝,墨借筆出韻,兩者并生互載、相映成趣。誠然,優質的筆墨會帶來優良的畫質,好的繪畫是筆墨混合而成的,同時也是與造型、繪畫精神等混合一體,并非獨立存在。筆墨應是性情之產物,是跟隨主體精神而生發的,主體精神隨著客觀的物象被激活而發生,在這里主客觀進行有機的碰撞與融合。“筆墨之道本乎性情”(沈宗騫)。所謂的性情也是有載體的,是有的放矢的,不是所有放浪形骸、解衣盤礴才叫性情。同樣,對萬事萬物的細膩關懷也是一種性情。“一沙一世界,一歲一枯榮”,經由客觀展現體察萬物之心,窺見對待萬物的終極關懷,這也是藝術的功用所在。而中國畫的筆墨語言恰好是展現性情與內心最方便與簡潔的工具。“以一管之筆,擬太虛之體”,是以少勝多的代表。“筆精墨妙,這是中國文化慧根之所系。”(張仃)筆墨上升至形而上的美學機制層面,大而廣之地看,筆墨似乎是可以代表中國繪畫的審美規范和文化品格,繼而由物質層面上升為精神表征。同時,筆墨的精神特質,一直與中國傳統哲學系統緊密相連,以至與鑄造人格的道德理想息息相關。也許對于傳統繪畫來說,筆墨可以作為繪畫的重要審美標準,甚至可以作為底線守護。但對于現代中國畫,特別是水墨人物畫來說,筆墨不是繪畫判斷的唯一標準。成就繪畫的要件元素有很多種,由造型要求、筆墨要求、構成要求、結構要求、色彩要求、情感要求等一系列要素構成,而且要素之間的比例成分也不是量變的、可計量的,最重要的是各種要素之間的協調與統一關系。畫面直接的視覺力度、傳達的感受性與圖像結構似乎更為重要。筆墨對于開放與多元的時代性要求,評判不再是唯一,不再是主導。“隨著現代社會的日趨開放和多元,隨著水墨材料的現代性探索日益成為中國人賴以區別西方普遍主義藝術觀的獨特意義世界,筆墨對于現代人的‘現在時和‘將來時價值,必將在一部分注重藝術深度的藝術家那里得到更加自覺和多樣的體現。”(盧輔圣)
綜上所述,對于客觀的筆墨性與筆墨的客觀性的認知,就水墨人物畫而言,使筆墨的價值得到充分而合理的利用,有利于形成良性的筆墨觀,在水墨人物畫教學中引領認知的示范作用,為水墨人物畫教學體系的建構夯實寬厚、客觀的認知基礎。如何更好地運用傳統的筆墨語言來表現日新月異的新時代,是水墨人物畫的現代性的任務與出路。人物具有時代感,筆墨同樣具有時代性。筆墨本身應順應時代而進行更新性改變。筆墨會根據客觀物象的特質,生成既能表現物象質感又具獨立審美意義的新筆墨語言。客觀地認知筆墨性,不放大化,不神圣化,把對于筆墨的認知還原到其應有的位置上。特別是對于水墨人物畫來說,應把集中的表現力聚焦在人本身,筆墨是表現人的工具,筆墨語言應準確地符合現代人的氣質與特征。筆墨語言不是孤立存在的,是依附于人的載體、形的特質、神的需求。隨著時代的變遷,現代人的生活環境、自然環境、生活方式、思維方式、行為方式都異于古人,筆墨也遭遇了時代多元化的問題,有了新的水墨要求,在與造型語言共生的基礎上,不應失去筆墨的傳統語言優勢、直覺優勢、變幻優勢,不斷演進新的筆墨語言形態、標準、性質等,解決新時代介質的問題。同時,我們應該更宏觀地看待筆墨語言,筆墨語言是在發展的、更新的,是與時代同步的。“不執著于古典筆墨的外在形態,而在更深更廣的層次上去延展作為傳統繪畫語言的筆墨,或許才是當代中國畫的最好出路。”(林木)
當代水墨人物畫教學是現代中國畫學院的教育主要構成部分,我們應正確地理解筆墨語言的客觀性與當代性,以及筆墨語言從古典形態向現代形態的轉換與應用,進而樹立客觀的筆墨觀。在當代水墨人物繪畫中,筆墨的優質與否,不會決定一張優秀繪畫作品的成敗,但好的筆墨語言有助于成就一張好的繪畫。筆墨語言客觀性存在著,如何認識,以至如何運用是關鍵。再好的筆墨語言也抵不過帶有繪畫欲望的訴說,對于繪畫,情感是前提,一切的表達都應圍繞情感來進行,繪畫也是傳遞的工具與手段。在感人的繪畫面前,我們會忽略掉技術與方法,同時也會忽略掉筆墨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