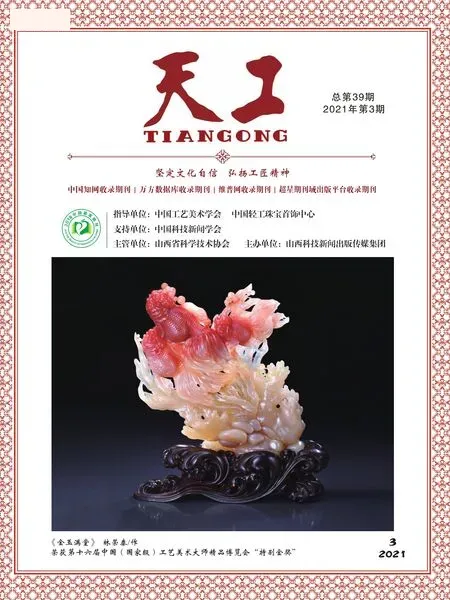內(nèi)蒙古召?gòu)R高等級(jí)彩畫初期特征研究
——以美岱召高等級(jí)彩畫為例
文 王智睿
一、美岱召建筑彩畫概況
美岱召原名“靈覺寺”或“靈照寺”,是阿勒坦汗的家廟,坐落在內(nèi)蒙古包頭市土默特右旗美岱召鄉(xiāng)境內(nèi),是土默特蒙古部順義王阿拉坦汗及三娘子主持興建,建于明萬(wàn)歷三年(1575)。
美岱召建筑彩畫主要繪于梁、枋、柱子等大木構(gòu)件上,其中主要建筑的大木構(gòu)件上的彩畫構(gòu)圖多以官式和璽彩畫為藍(lán)本。和璽彩畫在官式彩畫中象征皇權(quán),等級(jí)最高,運(yùn)用嚴(yán)格且不可隨便逾制。美岱召雖不是敕建,卻出現(xiàn)和璽彩畫構(gòu)圖形制的召?gòu)R彩畫遺存,是因?yàn)槊泪氛僮畛跏亲鳛橥聊夭堪⒗仗购沟恼沃行亩ㄔ斓模峭聊睾箛?guó)的汗廷所在地,必然要求裝飾其上的彩畫是象征皇權(quán)的彩畫。
二、美岱召高等級(jí)建筑彩畫的構(gòu)圖特點(diǎn)
美岱召中軸線上的主體建筑是內(nèi)蒙古地區(qū)召?gòu)R中典型的將漢藏建筑特征交融一體的漢藏結(jié)合式建筑,此類建筑單體結(jié)構(gòu)還是采用抬梁式木結(jié)構(gòu),因而建筑中彩畫裝飾的位置著重在梁、枋、檁、檐墊板等大木構(gòu)件上,這些大木構(gòu)件上繪制的高等級(jí)建筑彩畫以官式和璽彩畫為藍(lán)本,構(gòu)圖一般為三段式。為了方便理解與敘述,本文采用清官式和璽彩畫中各結(jié)構(gòu)稱謂,即主要由中間的方心、兩端的箍頭、找頭三部分構(gòu)成。通過實(shí)地調(diào)研中軸線上主要殿堂大雄寶殿及琉璃殿中現(xiàn)存彩畫實(shí)例發(fā)現(xiàn),按照建筑構(gòu)件的不同以及用料的長(zhǎng)短,依具體情況在基本的三段式構(gòu)圖框架下采取了以下幾種靈活的變化方式:遇到較短的建筑構(gòu)件采用取消盒子、找頭等方式進(jìn)行構(gòu)圖繪制,碰到像主梁這類較長(zhǎng)的建筑構(gòu)件則通過增加方心的數(shù)量來調(diào)整構(gòu)圖,最多的甚至出現(xiàn)三方心的構(gòu)圖。由此可見,美岱召建筑上高等級(jí)彩畫構(gòu)圖雖與官式和璽彩畫構(gòu)圖相似,但構(gòu)圖靈活,不似官式彩畫嚴(yán)格按照三停[1]進(jìn)行布局。(見圖1)

圖1
三、美岱召高等級(jí)建筑彩畫圖案紋飾的藝術(shù)特征
美岱召是藏傳佛教、漢地文化以及蒙古族文化的交融之地,因而其建筑彩畫的內(nèi)容也具有多種文化雜糅的特點(diǎn)。
(一)方心紋飾特征及施畫特點(diǎn)
美岱召高等級(jí)建筑彩畫方心的圖案紋飾內(nèi)容多以龍、鳳、吉祥草、藏傳佛教法器、草原上的花草等為題材,除了皇權(quán)等級(jí)的象征,更多地融入了藏傳佛教教義與游牧民族生產(chǎn)、生活的氣息,這正是內(nèi)蒙古地區(qū)召?gòu)R建筑彩畫區(qū)別于官式和璽彩畫的重要特點(diǎn)。在具體的施畫過程中注重與建筑的使用功能相統(tǒng)一,在相鄰的建筑構(gòu)件之間會(huì)采用具有一定寓意的方心題材內(nèi)容進(jìn)行跳接。
方心中的龍紋多為左右對(duì)稱式構(gòu)圖,兩條行云龍以中間的火焰寶珠為中軸線左右對(duì)稱。單體造型為五爪金龍,龍身一波三折,腳下騰云駕霧,張嘴伸舌,上腭突出于下顎,龍須向后彎曲,龍腿粗壯并有鬃毛向后飛動(dòng)。龍紋采用圖案形式的瀝粉貼片金的施畫手段來表現(xiàn),整體紋飾疏密合理,呈現(xiàn)出強(qiáng)烈的動(dòng)感。
鳳紋的構(gòu)圖與龍紋相同,也為左右對(duì)稱式構(gòu)圖,雖然整體也是對(duì)稱的雙鳳朝陽(yáng)構(gòu)圖,但在不同顏色的方心底色上會(huì)有所區(qū)別,通常情況下綠底方心繪制降鳳,紅底方心繪制升鳳。單體鳳凰身體與鳳尾各占二分之一,形成均衡態(tài)勢(shì)。頭部造型如錦雞上的鳳冠呈如意形,翅膀舒展呈大鵬展翅狀,纖細(xì)的仙鶴腿,為了增加韻律感,3根形似孔雀尾造型的鳳尾彎向不同方向且非常靈動(dòng)。整體圖案紋飾同樣采取瀝粉貼片金的施畫手段來表現(xiàn)。

圖2
方心圖案中最具特色的要數(shù)吉祥草圖案,又稱關(guān)東楞草(見圖2)。吉祥草的紋飾特點(diǎn)是整體構(gòu)圖為左右中心對(duì)稱的大型卷草紋樣,花型碩大、卷草壯碩,非常具有力度感,輪廓線以彎曲的弧線條為主,使整體造型消弭笨拙之態(tài),更顯自由靈動(dòng)。吉祥草圖案在官式和璽彩畫中非常少見,是原就流行于內(nèi)蒙古地區(qū)的裝飾圖案,帶有強(qiáng)烈的草原文化裝飾藝術(shù)特點(diǎn)。其施畫方法為輪廓瀝粉貼金,圖案則采用退暈的技法進(jìn)行繪制,花朵與卷草為五彩顏色,裝飾性非常強(qiáng)。除方心紋飾外,還有山水花鳥及錦紋圖案的使用,體現(xiàn)了漢地文化對(duì)其的影響。值得一提的是,山水花鳥方心底均為黃色,構(gòu)圖自由。施畫方式采用墨色工筆國(guó)畫技法,與其他主題的方心紋飾構(gòu)成強(qiáng)烈的對(duì)比,形成層次豐富的視覺感受。錦紋方心同官式彩畫一般,圖案用色采用平涂方法。方心紋飾無論是哪種題材內(nèi)容,或多或少都會(huì)采用瀝粉貼金的技法,用以突出彩畫的高等級(jí)。
(二)箍頭、找頭等紋飾特征及施畫特點(diǎn)
美岱召高等級(jí)建筑彩畫的箍頭分為無紋飾的死箍頭和有紋飾的活箍頭兩種形式。死箍頭構(gòu)圖如同官式和璽彩畫,一般采用藍(lán)或綠色兩退暈色帶作為基底色,正中以壓黑老線區(qū)分,箍頭線以較粗黑線和較細(xì)的白粉線繪制。活箍頭的構(gòu)圖呈連續(xù)不斷的紋樣,圖案內(nèi)容為蒙古族最為喜愛的硬萬(wàn)字紋,本地又叫“拉不斷”紋,采用藍(lán)綠攢退的施畫技法表現(xiàn)。
盒子的岔角圖案通常為簡(jiǎn)化的小圓點(diǎn)或四分之一野菊花紋飾圖案,盒子本身的題材內(nèi)容有與官式和璽彩畫相同的卷草西番蓮,更多的則采用蒙古族最喜愛的哈木爾紋(云紋)、法輪以及牛頭等反映藏傳佛教教義及蒙古族游牧生活特征的內(nèi)容,采用瀝粉貼片金的施畫方法。
找頭一般繪制在較長(zhǎng)的建筑構(gòu)件上,其中線光心構(gòu)圖一般為一整兩破的形式,在中間完整的線光心內(nèi),繪制有草原上最普通常見的格桑花圖案。找頭圖案題材主要是龍紋、吉祥草兩大類,找頭中龍紋除了與方心相同的行龍,還有一種尾部翻折至頭頂?shù)慕谍埿蜗螅@與官式和璽彩畫的降龍完全不同,體現(xiàn)了地方召?gòu)R高等級(jí)彩畫中的靈活性。吉祥草的構(gòu)圖與方心構(gòu)圖不同,以左花右卷草的布局形成均衡的構(gòu)圖。找頭部分的圖案同樣為了提高彩畫的等級(jí),通常采用片金或輪廓瀝粉貼金彩色退暈的施畫方法,基底設(shè)色規(guī)律為:圭光線為綠色兩退暈,線光心則為藍(lán)色或反之,行龍和吉祥草的基底色均為紅色,降龍則為綠色基底。
四、美岱召最高等級(jí)建筑彩畫的色彩搭配
官式和璽彩畫中設(shè)色規(guī)矩嚴(yán)格,按口訣“青箍頭青光線青楞線”“綠箍頭綠光線綠楞線”“青箍頭綠(三綠)岔角”“綠箍頭青(三青)岔角”[2],方心按照規(guī)則運(yùn)用大青、大綠設(shè)色。通過實(shí)地調(diào)研可以看出,美岱召高等級(jí)建筑彩畫中的顏色應(yīng)用較為靈活,雖是以官式和璽彩畫設(shè)色為藍(lán)本,以藍(lán)、綠色調(diào)為基本的基底色,但方心顏色搭配靈活多變,在藍(lán)、綠兩色的基礎(chǔ)上大量采用紅色、黃色進(jìn)行跳色,并且在施畫過程中利用金色、黑色、白色這類中性色進(jìn)行輪廓的勾描,增加整體彩畫的明暗層次。整體建筑的設(shè)色方法與官式和璽彩畫一致,立面由檁至枋,水平方向自明間(山面亦同)起做對(duì)稱軸,向左右對(duì)稱展開。在這樣的大前提下,再以各建筑構(gòu)件中的箍頭顏色為基點(diǎn),以實(shí)現(xiàn)各個(gè)部件顏色相間的設(shè)色。整體來看,美岱召高等級(jí)建筑彩畫的色彩以大面積藍(lán)色使用為主,這也反映出了蒙古族對(duì)藍(lán)色的偏愛,方心底的顏色擺脫官式彩畫規(guī)矩的青綠跳色,跳色中加入黃色、紅色這樣的暖色調(diào),反映出顏色的選擇更多地將藏傳佛教中色彩的象征及蒙古族本身的顏色喜好雜糅于官式彩畫設(shè)色中,體現(xiàn)出特有的民族特色。
五、結(jié)語(yǔ)
綜上所述,從美岱召高等級(jí)建筑彩畫來看,內(nèi)蒙古地區(qū)召?gòu)R高等級(jí)建筑彩畫初期特征保留了官式和璽彩畫整體華麗莊嚴(yán)的特征,雖受明、清官式彩畫的影響較大,卻仍具濃郁的游牧民族地方特色。其構(gòu)圖、色彩的運(yùn)用自由靈活,不似官式和璽彩畫形制嚴(yán)格,圖案紋飾亦獨(dú)具游牧民族傳統(tǒng)裝飾的特點(diǎn),反映出蒙古、藏、漢各族文化交融之特點(diǎ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