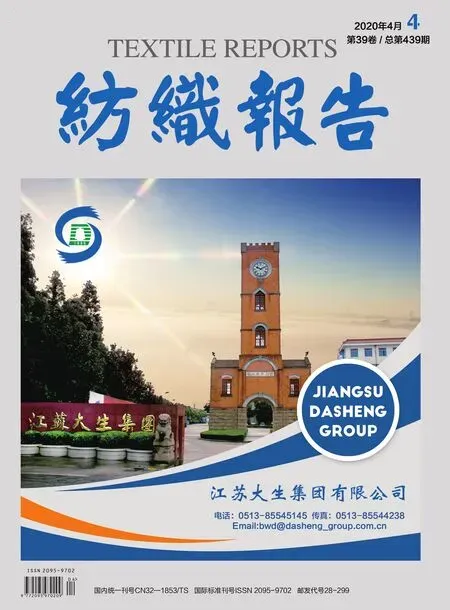淺談類型學的影像研究方法在少數民族服飾研究中的運用
——以二連浩特蒙古族服飾為例
胡鉞涵,張 寧
(大連工業大學 服裝學院,遼寧 大連 116034)
中國歷史源遠流長,文化積淀深厚。但是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的迅猛發展,外來文化瘋狂涌入,對我國傳統的民族文化造成了不小的沖擊,其中服飾文化更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蒙古族部落性特征逐漸模糊,多樣性逐漸消失,民族服飾也在社會背景下不斷被漢化。所以,通過類型學攝影的影像拍攝,將處在消失邊緣的部落性特征定格下來,并進行分析、重組,留下民族文化的永恒檔案。
1 類型學
人類一直沒有中斷過對世界運行規律的探索,為提前知曉事物運行的軌跡和趨向,中國先祖發明的陰陽五行讓事物的運行有跡可循。古希臘的集大成者亞里士多德試圖用規律與邏輯去掌握世界。邏輯學中重要的方法就是類型學,它是將已知的內容分析、重組、歸納[1]。人們也在無形中運用著類型學。它源自于考古學,分組歸類是類型學的一大體系。19世紀,德·昆西于他的著作《建筑百科辭典》中提出了目前為止接受度最廣、最具權威性的類型學概念。
2 類型學攝影
類型學涉及的門類廣泛,其中,類型學攝影是指將事物通過分類重組的方式進行攝影。自奧古斯特·桑德到貝歇爾夫婦,自杜爾塞多夫學派到當代藝術,類型學攝影經歷了從單一的外在記錄到復雜繁瑣的多維度題材的討論。類型學攝影一直處于爭議中,但它并非是單純對某一事物的簡單模仿與抄襲,而是旨在探索與利用已存在的某些事物。它需要追溯對歷史的剖析與提取,是對人類“集體無意識”的記憶,其中記載了數千年來人們的文化積淀、生活方式等一點一滴的更迭與變化,運用攝影的手段、更加簡化與抽象的構圖與拍攝手法,承載厚重的歷史意義。在當代藝術領域中,類型學并非無人問津的冷門藝術[2]。
3 類型學的影像研究方法在少數民族服飾研究中的運用
中國是多民族百花齊放的國家,蒙古族以其較為悠久的歷史積淀以及獨特的草原文化在當今依舊蓬勃發展。蒙古族服飾更是蒙古族人民在長期的生產和生活實踐中創造的藝術結晶。它以蒙古族的傳統精神為內涵,以傳統審美思想為支撐,是蒙古族文化的外在表現。但在發展迅速的今天,蒙古族服飾最終也將從某種意義上消失,成為標本。選擇中國特定地區蒙古族服飾為類型學的研究對象,捕捉蒙古族服飾文化的外在特征,形成一系列蒙古族服飾區域性的類型攝影作品,并進行創作及思考。蒙古族服飾作為傳統文化,在更新速度極快的現代社會要如何以全新的視覺形式、獨特的影像風格存在于世人的面前,以平靜的二維影像傳遞信息,來感受活體的內心變化。從蒙古族服飾本身的文化價值、社會價值,到影像輸出后的文獻價值,蘊藏著諸多可能性[3]。
選題形式以1959年德國杜塞爾多夫藝術學院的伯恩·貝歇和希拉·貝歇開始合作拍攝并記錄德國日漸消失的工業建筑為基礎。他們的成功之處在于將類型學攝影理論化、體系化,使其更加成熟、更加厚重,他們的類型學攝影理論也融入了更多哲學與文化的思考。幾千年來,人類一直認為自己是最重要的,人和人的意識天然優越于其他事物,但他們超前意識到了德國和歐洲重工業發生的結構性變化所帶來的后果。
類型學影像研究是建立在貝歇爾夫婦的意識之上的。從社會文化和歷史傳統的角度著手,全面地記錄二連浩特地區即將消失的蒙古族服飾,將他們以照片的形式保存,從而留下服飾文化的影像,讓時間與時代的變遷給影像賦予全新的定義,讓這些影像彌補人類記憶中缺失的部分。
拍攝時,盡量不注入個人情感和客觀想法,現象學告訴人們要追求事物的本質,存在主義讓人們去追尋存在者存在的本質與樣式,從中引出存在的意義,這就要求創作者要把被拍攝對象,哪怕是物體放在對等的位置。故而,將服飾放在對等的位置上,充分體現出其自身的結構與存在方式。人與世界的關系便是交織于主觀與客觀之間,經過類型化后拍攝的圖片,讓圖片與人之間有了情感的交流,用情感將客觀化作自身主觀的部分,有利于加深人們對蒙古族服飾的印象,加大保護力度,提高保護服飾文化的可操作性,有利于在傳承傳統服飾的基礎上滿足人們的心理需求。
類型學記錄下來的蒙古族服飾,正如杉本博司的永恒之美《海景》系列作品,“相機雖會記錄,但卻不會記憶。留下記憶的,終究是相機背后的人”[4]。事物本身的衰落直至消亡,都是它生命本體的一部分,是龐大民族傳統文化的一部分,時間賦予它厚度,歷史賦予它意義[5]。蒙古族服飾文化的消逝與變化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類型猶如語言,語句的變化不會改變整個語意。剝開事物的表層形態,研究事物的純粹本質,形態表現了本質,本質支撐了事物本身的存在。用類型學理性的思考過程將影像的特征提煉出來,后世的蒙古族文化會在此基礎上傳承、發揚,不斷將其類型文化流傳、運用,使影像的純粹直面永恒,蒙古族服飾便以一種全新的形式,隨著漫漫的歲月長河流傳于世。
類型學為蒙古族服飾提供了可操作的研究方向和視角,通過前期文獻資料的翻閱和多次的實地調研,在拍攝前將所需素材按照3個方面形成架構:不同場合—放牧、婚慶、那達慕、日常起居等,不同年齡階段—小孩、青年、老人等,受到不同地域影響形成的部落特色。對二連浩特地區蒙古族服飾進行了大量底片素材的積累后,找出類型學的影像風格,對具有相似特征的服飾圖片進行還原、歸類,恢復和再現特定的文化,最終進行成組展示,使人們對蒙古族服飾能無意識地認識和辨別,有利于加強人們對蒙古族服飾的記憶。
4 結語
在類型學攝影方式的創作中,最難把握的其實是作品背后的理念。它是根據現象學的理念,對事物純粹的本體以及它存在的特有狀態的認識,是一個互相辯證、若有若無而又觸手不及的東西。它存在于每個人的理解之中,閱歷、對事物的理解、表達手段的不同都造就了創作的千差萬別。
所以,類型學不是表面的機械排列,照片背后的意義需要更深厚的理念去支撐,攝影師如何看待這個世界,又以什么理念去表達自我。影像的意義永遠都是多維度的表達,運用類型學進行少數民族服飾的研究,不能停留在服飾本身,而是站在前人、智者的肩膀上,去體會時代和歷史賦予它的鮮活生命,利用藝術的工具、攝影手段,去表達對于世界的體驗與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