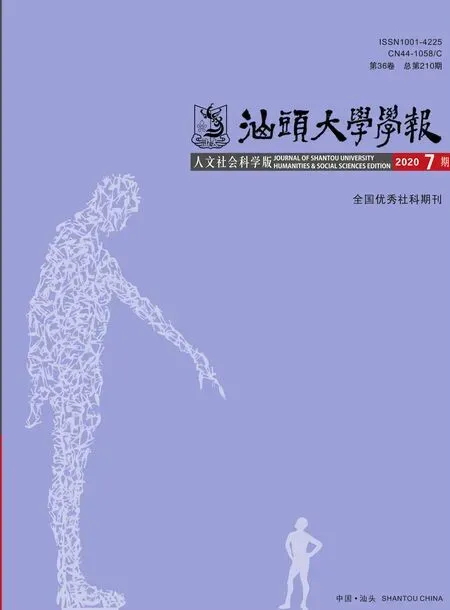所仰唯真理
——林風眠在中國現代藝術建構中的歷史地位研究
周曉平
(嘉應學院文學院,廣東 梅州 514015)
晚清至20 世紀初,西方思潮洶涌而入,中國大地發生了劇烈的社會變革。“中國向何處去?”“中國文化走向何處?”這些基本問題牽動著每一位中國知識分子的敏感神經。西潮的沖擊,改變了中國傳統文化既有的生存秩序,它深刻地影響著中國藝術的變化與演進。
“魂系織蘭彩蝶飛,林濤風嘯人未眠。”無疑,林風眠是這場藝術變革運動中的杰出代表。作為二十世紀中國乃至世界最為杰出的藝術家,“當年林先生的藝術已經越過了從主觀方面努力于極端寫意派的中國畫,和從客觀方面努力于極端寫實派的西洋畫這兩個時期,跨進了運用東西新藝術之‘素’,進行創造并且獲得了藝術成功的新階段。”[1]當中國藝術進入二十一世紀的時候,林風眠的藝術仍然是一座難以企及的高峰。
一、“五四”現代藝術與啟蒙的先驅
林風眠(1900-1991),經歷了一個劇烈動蕩而新舊交替的時期。在中國文化的大背景中,林風眠與蔡元培是忘年之交。他不僅與魯迅的思想淵源有關聯,并且與陳獨秀、李大釗的步調一致。這種契合,主要是指他們于文學、藝術在精神上的一脈相承。1927 年5 月,林風眠在北京藝術大會上,提出:“打倒模仿的傳統藝術!打倒貴族的獨享的藝術!打倒非民間的離開民眾的藝術!提倡創造的代表時代的藝術!提倡全民的階級共享的藝術!提倡民間的表現十字街頭的藝術!全國藝術家聯合起來!東西藝術家聯合起來!”這種狂飆突進的藝術口號,與“五四”初期陳獨秀所提倡的文學三大主張幾乎一脈相承。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發表的《文學革命論》,提出:“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貴族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兩者何其相似乃爾!這是文學藝術一體的繼承與發展。
“五四”新文學運動波及之廣,政治、社會、文哲、科學大都參與其中。人們常常把中國的“五四”新文化運動認作為中國的文藝復興,這是既成的事實。可是,西方的文藝復興,藝術是第一把“交椅”。在“五四”,惟有主持人類情感為文化不可缺乏的藝術似乎缺席了,或者顯得力不從心。作為“五四”新文化的推手的蔡元培不無感到遺憾。從這場新文學運動的過程而言,新藝術運動的來臨相對于新文學運動來說,顯得有些滯后。或者說由于“五四”新藝術運動初期的不足,才促使后來藝術運動的高漲。這是一個遲到的祝福!為什么呢?
十四至十六世紀,在西方意大利就已經發生了一場文藝復興運動①公認為意大利了不起的創造,包括十五世紀的最后二十五年和十六世紀的最初的三四十年。在這個小小的范圍內,像雨后春筍一般出現了一批成就卓越的藝術家:萊奧納多·達·芬奇、拉斐爾、米開朗琪羅、安德烈亞·德爾·薩爾托、喬爾喬納、提香、柯勒喬等等,這個范圍界限分明,往后退一步,藝術尚未成熟,向前一步,藝術已經敗壞,往后是作風粗糙,干枯或僵硬的探路。。它滲透的領域方方面面,在世界歷史上無與倫比。尤其在藝術方面,更是群星閃爍,光輝燦爛。而且復興藝術是作為一個最為重要的領域出現在西方文藝復興的歷史上的。達·芬奇、丟勒、荷爾拜因、米開朗琪羅……這些閃光名字代表著藝術中的盡善盡美,他們的作品至今仍備受尊崇,它提倡人文主義精神。文藝復興的精神的核心是提出以人為中心而不是以神為中心,肯定人的價值和尊嚴,啟蒙人生。主張人生的目的是追求幸福。同時,倡導個性解放,反對愚昧迷信。認為人是現實生活的創造者和主人。這種精神廣泛地波及到政治、經濟、文化、歷史、文學及其藝術的各個領域。
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北京,又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鎮北大,蔡元培營造了“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新風尚。也許是因緣際會,也許是歷史的必然,若干年后,蔡元培才在異國他鄉物色到了堪當大任之才—林風眠,一個能夠為藝術獻身的人。
林風眠曾經形象地做一個比喻,他認為藝術家就像美麗的蝴蝶,一方面蝴蝶要為自己編織一只繭,另外一方面要有破繭而出的本事。這個本事便是藝術家早年艱辛學得的技法和所受到的影響。[2]的確,在藝術上林風眠正是像美麗的蝴蝶一樣經歷了一次次的脫胎換骨的蛻變。可是,當他學成歸國試圖一展拳腳之時,他所看、所聞皆不是他所想到的。林風眠不由捫心自問:“今日的中國社會,還有一點過得去的地方嗎?”現實的困境是:
以言民情,則除朦朦無知,不知國家社會以及人類為何物者外,便只有貪狠毒辣的殘殺或被殘殺,以及血枯汗竭的斷喊凄嘶!……以言經濟,一面是貪官污吏以及軍閥走狗們的腰纏十萬,厚榨民脂,以供其花天酒地,……以言政治,在軍事則有年戰,月有戰,日日有戰,無時不戰!在政務則貪險者為民上,無所不用其極,陰謀勾結,弄得天昏地黑,一塌糊涂……(《致全國藝術界書》)
1927 年,正是“五四”運動退潮、國民黨反動派興風作浪之時。林風眠目睹國內慘狀,民不聊生,不由心急如焚。藝術家的敏感與激情迫使林風眠去尋找救治之方。他要找到社會黑暗的根本之所在,于是走上了“藝術救國”的道路。正如魯迅一樣,“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如果說,為了解救、醫治中國人心靈的創傷,魯迅是做起了遵命文學的話,那么,林風眠則是從另外一個方面——藝術,去尋找藥方,于是做起了遵命藝術。
林風眠在《致全國藝術界書》說“中國自來無所謂宗教,又無藝術以代宗教而維持其感情的平衡之故!”“像中國現刻的這種情況,我們試一留心地檢查,立刻可以發現這完全是因為感情的不平衡!”顯然,林風眠將社會這種丑惡、混沌、復雜、黑暗、頹廢、不平等歸罪于“感情”失卻了平衡,而林風眠堅信失去“平衡”的“感情”復歸平衡的責任落在了藝術的肩上。[3]林風眠認為倡導“藝術為藝術”者,那是藝術家的言論;倡導“藝術為社會”者,那是批評家的言論。兩者相互相成,不可偏廢。他看到藝術對于社會擔負的責任,并希望利用自己的藝術參與社會變革。“藝術,一方面創造者得以自滿其感情之欲,一方面以其作品為一切人類社會的一切事物之助!”“藝術是感情的產物,有藝術而后感情得以安慰!”[4]
林風眠始終沒有忘記作為一個藝術家肩上扛著的歷史使命與責任,他不負重任,不辜眾望,就任北京國立藝術專門學校校長兼教授之職。1925 年,林風眠扛起“為人生的藝術”、“為大眾的藝術”之旗,這些舉措正是“五四”新文化的啟蒙運動在中國藝術領域里繼續燃燒起來的熊熊烈火。林風眠以藝術啟蒙為己任,他確信:“藝術是一切苦難的調劑者”,而“補偏救弊在于當今的藝術家”。這樣鏗鏘有力的聲音,即使在“五四”新文化如火如荼的時候,也是不多見的。林風眠已經把藝術的啟蒙上升到一種崇高的認識。
魯迅苦于中國老百姓文化的落后,他是首先拿筆做武器,展開文學啟蒙的。他對工人、農民、知識分子、下層零余者的國民劣根性都有辛辣的揭露與無情的批判。《狂人日記》、《阿Q 正傳》正是不朽之作。然而,魯迅也清楚地意識到,他的作品是寫給“三十歲以上的青年人看的……”。這就是說,基于知識水平、社會閱歷、文化背景的原因,人們對其作品的思想蘊含作真正理解的人并不在多數。魯迅做過深刻的反省。他要尋找一切能夠為中華民族所啟蒙的“靈丹妙藥”。鑒于木刻繪畫的通俗易懂,對于普通百姓來說似乎更能通曉易懂。一旦發現,則不遺余力。他收藏過大量的木刻版畫,培養過不少藝術新人。[5]魯迅與林風眠是有過交往與交流的。其日記載述:“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五日晴,風。上午往美術學校看林風眠個人繪畫展覽會。”(《魯迅全集·日記》)但對于這次展覽會上林風眠的繪畫,魯迅有過什么評價,提出過什么觀點,則沒有記載,史料似乎也沒有任何的披露,這無疑是一種遺憾。然而,從這里可以看到,對于作為啟蒙的藝術繪畫,魯迅是很重視的。畢竟,魯迅先生是文學家,藝術啟蒙的具體實踐,恐怕還得留待藝術家們來實現。
事實上,林風眠現代藝術的啟蒙思想在很早的時候就萌發了,可謂藝術啟蒙之先鋒。1923 年在德國創作的巨幅大型畫《摸索》,林風眠大膽地采用了現實主義的藝術手法,把不同國家不同時代的詩人、哲學家、畫家、文學家,穿越時空地表現在同一畫面上。構思新奇,想象豐富,猶如達·芬奇創作的《最后的晚餐》,此乃繪畫史上的奇跡。不同的是,《摸索》帶有更為強烈的啟蒙藝術色彩。畫面上的耶穌、荷馬、莎士比亞、但丁、歌德、米開朗琪羅這些人物一個個表現得栩栩如生:或冷靜淡泊,或快樂達觀,或思辨憂郁,或急躁憤怒。讓這些哲人、思想家、詩人、藝術家聚居一堂,為人類的共同理想而探求真理,尋找人類啟蒙之光。也正是在這一年,林風眠創作了《柏林咖啡屋》、《克里阿巴之春思》、《唐又漢決斗》等油畫、國畫。林風眠以人道主義的關懷,反映德國有閑階級的頹廢的生活情緒,他要喚醒頹廢的德國人。[6]林風眠慷慨激昂的油畫力作如《痛苦》、《人道》、《悲哀》、《南方》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他關愛社會,關心貧民百姓,探討社會與人生問題。用表現主義的手法,揭示人類的痛苦與現實的困境。他的創作風格是苦澀而悲涼的。《痛苦》是林風眠得知好友熊君銳因參加共產主義運動而被國民黨當局殺害后,所發出的強烈的怒吼與痛斥。[7]
現代藝術的啟蒙是林風眠其藝術生涯中的主旋律。無論在抗戰的歲月,解放后的各個時期如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的年代,甚至在林風眠的晚年如八十年代,啟蒙藝術仍然是林風眠藝術創作中一以貫之的現代性主題。
二、現代審美結構的求新求變
(一)“以美育代宗教”的最早實踐者
眾所周知,蔡元培在“五四”時期提出“美育代宗教”的口號,是有其特殊背景的。蔡元培多次呼吁“文化運動不要忘了美育”[8],蔡元培試圖在“五四”運動中推行自己的主張,實現人生的理想。可是曲高和寡,在“五四”時期,真正能夠理解這種思想的人有幾人?能夠付之于實施的又有幾人?
當新文化運動如火如荼的時候,藝術的缺失,這是蔡元培深感痛惜之處。為了發掘人才,蔡元培把希望的目光投射到當時留學在國外的一批留學生們的身上。1924 年,蔡元培在中國學生留法舉辦的“中國美術展覽會”上見到林風眠和他的作品,其《摸索》這一巨幅油畫,則深深地感染了他。按照林文錚的話來說,這幅畫的主題“暗合蔡先生人文主義精神,可以說是‘同聲相應’”[9]。林風眠與蔡元培的思想是很吻合的,并在蔡元培思想的影響下,林風眠人文主義思想進一步得到催生。1925 年,林風眠擔任北京國立藝專校長時,發動了“北京藝術大會”,他以此來實現蔡元培“美育代宗教”的理論主張,以推廣美育運動。[10]在林風眠看來,大凡宗教是離不開藝術的。宗教是感情的表現,藝術則是最能動搖人類感情的。如果把藝術放在美的環境中,豈不將使藝術的感動更有力量嗎?
“五四”新文化運動后,社會形態發生前所未有的變化,從封建的、半殖民半封建的社會,向獨立自主的現代民主的社會轉化。自從把德先生、賽先生請進中國之后,中國追求現代化的進程已經濫觴,其實質表現為:人的現代化、思想與語言的現代化。文學藝術的現代化則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具體實踐。從二十世紀20 年代至50、60年代林風眠的思想軌跡與創作歷程來看,他把藝術實踐與美育理念完美地結合起來,從而探求中國現代美育的革新之路,他極大地拓寬了中國藝術的現代性變革與訴求—“社會藝術化”[11]。
林風眠在《致全國藝術界書》中以贊佩的語氣寫到:“在蔡元培所著《藝術起源》一文中,他說,無論在哪一個時代,藝術同社會的關系都是很顯著的。在教育主張上,從柏拉圖突出美育主義后,多數的教育家們,都認為美育是改造社會的利器。”“美育的目的,在于陶冶活潑敏銳之性靈,養成高尚純潔之人格。”可是這種“美術革命”由誰來完成呢?陳獨秀沒有做到,恐怕還得由藝術家們來付出實施。
對于積貧積弱的中國現實,林風眠深入地認識到了。要改變這種狀況,林風眠以情感為切入點,指出“像中國現刻的這種情況,我們試一留心地檢查,立刻可以發現這完全因為感情的不平衡!”。他從社會宏觀到個人微觀,大到國民革命,小到日常生活條件的改善,無不以感情為動力。他進一步談到:“中山先生40 年努力國民革命,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而以博愛之精神,企望世界之大同。……中山先生之人格偉大,其偉大亦正因建筑在能為中國人滿足其求痛快之感情。”[12]林風眠的美育思想與教育目的的產生是有歷史根源的,它體現了民國初年資產階級民主派改革中國的理想,是整個中國教育要求德、智、體、美的教育目的在美育中的具體表現。這相比于晚清“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的教育宗旨,是一種質的轉變與歷史性進步。林風眠以促進“社會美育”為出發點,不僅與中國封建社會畫院派的“忠君”的藝術思想有嚴格的區別,也與“精研古法,博采新知”、“保存國粹與時代進化”、“為國家社會謀人才,為全體畫家謀出路”(《中國美術·年鑒》)的口號相比較,同樣具有巨大的進步意義。它超越了中國傳統的教育思想,即不在于它維護國粹的純正性,而在于以新的藝術觀念沖擊國粹藝術觀念的保守性,并代之以新的西方文藝復興時期的美育思想社會的進步。[13]
不僅如此,林風眠執掌北京藝專時期,做了扎實的工作。林風眠倡導的美術教育包含著兩部分的思想構成:一是作為其核心的美術院校的專業教育和審美教育;一是作為其外圍的社會的美術教育,即“社會藝術化”。作為“社會藝術化”,又是基于林風眠既成的現有認識:一方面在于欣賞主體,是“國人亦正因為沒有東西可鑒”,而“鄙視藝術不至于談藝術”,因而中國缺少藝術的陶冶,而且這種惡性循環的情形愈演愈烈。其治療的“藥方”,第一味便是要求藝術家“肯犧牲一己名利”,創作“真正的作品問世”。他在國立杭州藝術院紀念周的講演,是專門與“諸位同學交流感情”,并向他們灌輸自己教育思想的報告。教育學生“要從享受著的實際著眼,怎樣才可以使大家了解藝術,使大家可從藝術的光明中,得到人生合理的觀念,同正當感情的陶冶。”(《我們要注意—西湖國立藝術學院紀念周演講》)林風眠試圖確保藝術這種積極的能動的社會教育功能的實現,由學校而推廣到整個社會,以實現全民的美學教育。基于這種教育理念,他著力從五個方面打造實踐環節:一是指導以積極進步的美學觀念;二是啟發以中西融合的美學宗旨;三是教授以嚴格的基本技法;四是輔導以切實的史論知識;五是循循善誘,因材施教。[14]
理想是豐滿的,而現實卻很骨感。林風眠提出的“社會藝術化”,不是為了消極避世,恰恰是為了面對現實,改造人生。美育的至善至美,它是林風眠解救日益頹變的人心的一把鑰匙,這也是理解林風眠畢生為之奮斗的美育思想的關鍵。
(二)新派畫創作的第一人
“五四”新文化運動后,它所裹挾的對傳統文化的反思與學習西方文化藝術的新潮流,由此而掀起了一場徹底改變傳統中國畫趣味與審美的新思潮。林風眠對于傳統中國畫的革新,在藝壇上形成了一股強烈的沖擊波。
首先,林風眠是不甘于重復、不甘于在沿襲守舊中完成一個藝術家的使命的。他說:
在新派作風中,我們聞到了汽油味,感覺到高速度,接觸到生理的內層,心理的現象,代表了他們這一個時代。……畢加索給了我們20 世紀上半期許多碰壁的經驗,得到了許多新形式。可是我們在藝術方面,也總是睜不開,近來作了許多新畫。使我想到了許多,這使我看見了光……[15]
林風眠所畫的山水、仕女、花卉、戲曲中,可以強烈地感受到中國繪畫藝術的深厚功底,它蘊藏著深厚的傳統韻味。林風眠在作品中絲毫不掩飾自己的情感感受,并訴之于一種新的思想意境。他與自由知識分子蔡元培、胡適等人具有同樣的特點。與傳統文人相比,他們對創建新的社會秩序、新的文化懷有極大的熱情。對于這種新思想的表現,在新派繪畫作品中,林風眠是這種獨特精神的最早訴求。早在1924 年,蔡元培在法國看到林風眠創作的《生之欲》時,感嘆“得乎技,進乎道矣!”林風眠的畫已經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中國畫,它融技術與理性、情感、妙悟、新思想為一體。他曾受教于柯羅蒙①柯羅蒙(1854-1824)巴黎高等美術學院教授,有“學院派的畫家”之稱。20 世紀著名畫家勞特累克、馬蒂斯、波納、凡高等,都在他的工作室師從過。,對印象主義、野獸主義、立體主義、德國表現主義進行了研究,磨煉出了兩種繪畫的新形式。盡管徐悲鴻及其學派開拓了20世紀中國寫實繪畫的一代新風,對補救傳統人物繪畫做了一個新的嘗試。可是,徐悲鴻始終未能把西方的寫實與中國的寫意形式、西方的色彩語言與中國的筆墨語言融匯一體,使之有機而完美地結合起來。林風眠成功地做到了。他的繪畫一直是按照這個思路進行創作的,而且越到后面,更加顯得奔放、強勁。譬如《屈原》、《惡夢》、《南天門》《火燒赤壁》等,呈現出一種創新與升華的面貌。
1925 年,林風眠來到了北京后,著手推進中國現代藝術的創新之路。他以極大的熱情投入藝術運動,力求把藝術運動與改造社會結合起來。在藝術創作實踐與理論、推進藝術運動和進行藝術教育方面,林風眠都具有現代意識與超前理念。他創作的《摸索》、《人之欲》、《人道》、《痛苦》等就是林風眠用藝術來參與社會變革的具體實踐。他強調傳統藝術的基本功,而又反對仿古、泥古的藝術行為。但是,林風眠深諳藝術的發展規律,指出唐宋之前的繪畫是“形似”高于“神似”,“狀物”高于“達意”。到了后面,元代則“狀意”,明代“狀趣”。[16]林風眠對古代繪畫藝術進行了較為全面的審視,并以此為觀照,有的放矢地進行揚棄。在《我們所希望的國畫前途》中指出:“繪畫上的基本練習,應該以自然現象為基礎,先使物象正確,然后談到“寫意不寫形”的問題。在我們的時代,這種畫匠也不是沒有;不過,他們是早已不為水平線以上的畫家所齒及,而且他們的錯處倒有我們的抄襲家那樣烈害的趨勢;于是,我們不得不努力矯正我們自己的,而不把那些畫匠置之話下。”[17]
林風眠對于西方的藝術一直持開放的態度,主張中西結合。這與魯迅先生在對待西方文化的引進上主張“拿來主義”的原則,可謂異曲同工。他對于西方藝術創作中的現代主義藝術作品很有感觸,認為中國的藝術作品中所缺少的正是這些新元素。林風眠就像一個普羅米斯修的盜火者,試圖將西方藝術中的現代因素融入到中國藝術的創作中,并提出了一些綱領性的藝術宣言。當然,林風眠對于西方過激的現代思潮如未來主義、達達主義卻是持審慎態度的。從這種觀點出發,林風眠認為中西藝術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只有中西結合,融入先進,現代藝術才能取得新的突破。然而,不思創新的傳統中國畫家,他們把自己局限在一種舊有的框架中,得不到伸展,回到百年以前的老路上去,陷入了一種藝術的怪圈。表現不出新的形式,產生不出新的語言,創作不出新的文本,整合不出新的內容。林風眠以自己的實踐創作,以敢為天下先的精神,成為了新派畫創作的第一人。
三、在中西合璧中創造時代的新藝術
林風眠深刻地認識到中國與西洋藝術的優勢與缺憾。在藝術界,正如有的學者認為,中國現當代的繪畫藝術有兩支:一是以齊白石、黃賓虹、潘天壽等為主要的,他們走的是中國藝術的傳統之路,從傳統力求突破;二是留洋歸國,或先事西畫,后轉攻西洋畫的劉海粟、徐悲鴻、林風眠,納洋以興中。這是有道理的。歷史的經驗告誡:僅靠內部機制的轉換是很難維持其持久的活力的。當既定的形式與內容到達一種極致的時候,勢必成為一種戒律。對于藝術而言,就成為了束縛:在韻趣、章法、筆畫功力……逃不出這種窠臼。[18]
如何逃出這種窠臼?林風眠的選擇,卻是站在世界文化藝術的高度去看待這一問題。他深刻地認識到,西方現代藝術正在向東方索取營養,從而才使其幾百年的傳統繪畫大河改道,走向新的征程。西方現代藝術也正是在博取眾長的藝術創作中才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基于這種思考,林風眠認為中西藝術需要相互取長補短。鑒于西方藝術中側重的描摹與東方藝術的傾向“達意”,林風眠認為這兩種表現手法都是片面的。吳冠中對于林風眠的繪畫評價如是說:“用西方的解剖刀來解剖東方”,這種概括是準確的。
林風眠藝術思想的主旨就是“中西藝術相結合,創造時代藝術”。“創造時代藝術”是其藝術人生的最高目標。他認為:“藝術對于人類生命力的滿足,是永遠不會劃地自禁地宣告休止的。”只要人類藝術存在,那么融中于西,或者融西于中的藝術永遠在動態中發展。他清楚地認識到中西藝術的現狀與本質:“西方藝術是以摹仿自然為主,傾于寫實一面。東方藝術是以描寫想象為主,傾于寫意的一面。藝術之構成是由人類情緒上的沖動,而需要一種相當形式以表現之”。新的時代孕育新的藝術,當時西方的造型藝術應運而生。譬如,1905 年出現了野獸主義、1907 年誕生了立體主義,到了1910 年則產生了抽象主義,現代思潮席卷而來,波及整個西方大地。[19]但是,西方藝術家并不以此為滿足,他們也把藝術的眼光投射到中國這個具有五千年文明的廣袤的藝術大地,試圖融中貫西,吸取中國古代的藝術文明。當年林風眠是具備一定的國畫基本功的,其之所以到德國去,正是為了增進對西方的藝術的深刻了解。那時他在藝術創作上似乎沉迷在自然主義的氛圍中而難以自拔。林風眠回憶到:“有一天,楊西施特地來看我,批評我學得太膚淺了。他誠懇地然而很嚴肅地對我說:‘你是一個中國人,你可知道中國的藝術有多么寶貴的、優秀的傳統啊!你怎么不去好好學習呢?……’還說:‘你要做一個畫家,就不能光學繪畫,美術部門中的雕刻、陶瓷、木刻、工藝……什么都應該學習;要像蜜蜂一樣,從各種花朵中吸取精華,才能釀出甜蜜來。’”[20]林風眠受到的啟發是非常深刻的,猶如醍醐灌頂。無疑,這也是林風眠堅定地走中西合璧的藝術之路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繪畫實踐中,林風眠進行了大膽的改革,在國立藝專時期,林風眠就把國畫、西畫合并為繪畫系,并進行了闡釋:
本校繪畫系之異于各地者包括國畫西畫于一系之中。我國一般人士多視國畫與西畫有既然不同的鴻溝,幾若風馬牛不相及,各地藝術學校亦公然承認這種這種見解,硬把繪畫分為國畫系與西畫系,因此涼席的師生不能互相了解而相輕!此誠為藝術界之不幸!我們加入把頹廢的國畫適應適宜社會意識的需要而另開新途徑,則研究國畫者不宜忽視西畫的貢獻;同時,我們加入又要把油畫脫離西洋陳式而足以代表民族精神的新藝術,那么研究細化這亦不宜忽視千百年來國畫的成績。(《藝術教育大綱》)
林風眠開拓了一條中西合璧藝術的新途徑,不僅如此,他大力培養的藝術人才,如王冠中、李可染、席德進等等。于當今藝術而言,現代藝術仍然是朝著林風眠既定的方向前進的。
四、“為人生的藝術”與“為藝術而戰”
(一)“為人生的藝術”
“五四”新文學運動狂飆突進之際,以魯迅、茅盾等人為代表的“文學研究會”倡導“為人生的文學”,呼喊為蕓蕓眾生的勞苦大眾而創作。如果說,梁啟超賦予了中國現代文學的“文學救國”價值取向,那么魯迅則為其創立了“文學立人”的時代命題。而1925 后,林風眠則在復雜曲折的歷史軌道中尋找民族藝術的位置,為民族藝術賦予時代的特色。林風眠在蔡元培的感召下,高舉“藝術救國”的大旗,試圖開辟一條“藝術救國”之路。“為人生的藝術”深得蔡元培的理念,但“藝術救國”又何其之難!當年蔡先生的意向是非常明了的:魯迅扛起文學的大旗,而林風眠則可扛起藝術的大旗。兩面旗幟交相輝映,則社會可以改良,民心則可救矣!因為蔡元培、魯迅、林風眠清醒地洞察到中國眼下的困境,一切在陰暗中蔓延與發霉,到處充滿畸形、病弱或流產的東西;到處流浪著窮苦的農民、瘸腿的乞丐、眼睛虛腫而癡呆的婦女、精疲力竭的趕腳人、臉色蒼白的病人;還有一切為了可怕的邪惡與欲望而魚肉百姓的地痞流氓。它就像腐爛的樹上的蛀蟲,在不斷地侵蝕著社會的文明。因此,只有替他們治病,才能拯救民生與這個社會。要達到這個目的,首先拯救的還是專制統治下的文藝。
正如羅曼羅蘭說道:
藝術正被個人主義和無治底混亂所攪擾,少數人握著藝術的特權,使民眾站在原理藝術的地位上。……要救藝術,應該挖取那扼殺藝術的特權;應該將一切人,收容于藝術的世界。這就是應該發出民眾的聲音;應該興起重任的藝術。重任的努力,都用于為眾人的喜悅。什么下等社會呀,智識階級呀那樣,筑起一階級的壇場來的事,并不是當面的問題。我們不想做宗教、道德,以致社會這類的一部分的機械。……我們所愿意作為伴侶的,是在藝術里求人間的理想,在生活里尋友愛的人們的一切;是不想使思索和活動,使那美,使民眾和選民奮力開來的人們的一切。中流人的藝術,已成了老人的藝術了。能使它蘇生,康健者,獨有民眾的力量。我們并非讓了步,于是要“到民間去”;并非為了民眾,來顯示人性之光,乃是為了人性之光,而呼喊民眾,呼喊藝術。[21]
林風眠以藝術作為人生的武器,他把深刻的哲學道理與改造社會的價值,蘊意在創作中,體現為一種深層的“美”與“力”,以奔放的情感替代生硬的說教,啟迪人生。1931 年,蔣介石和宋美齡在西湖博覽會上看到林風眠的畫《人類的痛苦》,十分不滿地質問林風眠:“光天化日之下哪來那么多的痛苦?”《痛苦》描繪了幾個痛苦掙扎的人體。它以灰黑作為背景襯托慘白的死尸,畫面陰森恐怖。林風眠嚴厲地抨擊了當時的黑暗現實。他的作品《人道》則描繪了一些橫七豎八、茍延殘喘的被殘害的同胞的畫面,其中一具冰冷的女尸和寒光凜凜的鎖鏈,畫面凸顯了鮮明的時代背景。[22]林風眠的藝術作品感染了許多人。譬如,與林風眠志趣相投的徐悲鴻,也發表了不少此類作品。也是在林風眠創作的《摸索》之后,徐悲鴻創造了一幅表達現實的巨幅油畫《傒后我》。《傒后我》取材于《書經》,描寫的是夏朝君王桀,其殘酷的統治下的“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的殘酷現實。畫面描繪了一群窮苦百姓在翹首遠方的場景:大地干裂,樹木干枯,莊稼焦萎,瘦弱的黑牛精疲力竭地低垂著頭,舔舐著土地。而老百姓的眼睛里燃燒著焦灼的期待,如同久旱甘霖。[23]
林風眠以藝術啟蒙為己任,以改造國民性素質為目標。他以“我入地獄”之精神,表示實現藝術的決心和對藝術本體精神的推崇。由于各種復雜的因素:人為的、社會的,甚至是歷史文化的,林風眠的理想要得到實現,何其之難!甚至是一種烏托邦。但他這種赤子之心是清晰可見的,林風眠要與他的同仁抱定“以挽救世道人心的衰退”[24],雖然現實是殘酷的,但人類還得在黑暗中摸索向前。而藝術作為一種精神載體,引導與改善著人生。林風眠以一種基督教徒式的虔誠,要以藝術照亮他人,因為“上帝說,要有光!”
林風眠認為:“倡‘藝術的藝術’者,是藝術家的言論,倡‘社會的藝術’者,是批評家的言論。兩者并不相沖突。……現在的藝術不是國有的,亦不是私有的,是全人類所共有的,愿研究藝術的同志們,應該認清藝術家的偉大使命。”(《藝術的藝術與社會的藝術》)林風眠深知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的文藝之所以復興,是因為它是以人為中心,而不是以神為中心,強調人性,把人放在一個至高無上的位置。林風眠秉承蔡元培的“美育代宗教”的思想,以期實現“社會藝術化”的理想。他認為歐洲文藝復興運動到達鼎盛時期后,藝術便“脫離宗教而趨于人生之表現,獨當一面地直接滿足人類的感情。”“所謂人的發現,實際上就是藝術家們如達·芬奇、拉斐爾、米開朗琪羅把活潑潑的人,從神的鐵掌下脫了出來,是他們走上活的路,便是藝術從宗教下解放出來的原動力了。”[25]
(二)“為藝術而戰”
從“為人生的藝術”到“為藝術而戰”,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事實上“為人生的藝術”實踐起來并非簡單,要付出百倍的代價。林風眠深知只有為“為藝術而戰”,“為人生的藝術”才有實現的可能。
林風眠在《致全國藝術界書》中,對中國過去的藝術進行全面的審視,大聲呼吁:
中國之缺乏藝術的陶冶,主要原因,在于沒有真正創造的藝術品。……如此,藝術既愈趨愈下!人心亦愈趨愈不肯接受藝術的陶冶,前途危殆,真是不堪設想。欲救此種危殆,則非有犧牲一時名利的藝術家,奮其腕力,一方面以真正的作品問世,使國人知藝術品之究為何物,以引起鑒賞的興趣,一方面為中國藝術界打開一條血路,將被逼入死路的藝術家救出來,共同為國人世人創造有生命的藝術品不可。[26]
這里提出了前瞻性的理論與方法,造成了一種輿論與宣傳效果。在這篇宣言書中,對于藝術的社會功能,林風眠提出了四點:第一,感情的安慰;第二,宗教的信仰;第三,藝術代宗教;第四,關于藝術的影響問題。
林風眠從孫中山致力于國民革命四十年到眼下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的各個方面,說明感情發泄的重要性。而人類的欲望又是有加無已的,于是要強調宗教信仰的維持。然而維持宗教的信仰的最有力的利器就是藝術了。藝術的重要性在于它的“美”與“力”,作為具有高級情感的人類是不能缺少的。他進一步認為,作為藝術,一方面創造者得以自滿其情緒之欲,另一方面以其作品為一切人類社會的一切事物之助。林風眠指出,文藝復興時期,宗教利用藝術的功用而深入人心,藝術大放異彩。那么,藝術替代宗教則勢所必然。但是,放眼國人與現狀,林風眠為中國的每況愈下的藝術,感到憂心忡忡。現代藝術已經失去在社會上相當的能力,中國人的生活,在精神上成為一種變態,人與人之間沒有了同情心,而被冷酷、自私所替代。社會風氣變得不可收拾!
于是,在藝術理論與宣傳方面,林風眠寫下了不少具有前瞻性的論著。他先后發表了《原始人類藝術》《我們要注意》《徒呼奈何是不行的》《中國繪畫新論》《我們所希望的國畫前途》,它們配合著藝術運動,激勵人生,賦予藝術以巨大的生機。
林風眠是一個言行一致的藝術家。更為難能可貴的是林風眠身體力行,在實踐上為中國藝術的良性互動做了大量的開拓性工作。
凡屬在藝術上產生了重大影響的藝術派別和藝術家,都是因為在藝術的思考和探索中提出了重要的文化主張。在20 世紀中國美術的歷史中,林風眠藝術的理論與實踐的目的就是要重鑄中國形象的“再東方化”[27]。他是以調和中西藝術的策略作為實踐的指南:在西方藝術的寫實與中國藝術的傳統中取長補短。他接任國立北京藝術專門學校校長職務時,“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改進校務;第二,整頓教師隊伍,增設系別;第三,舉辦藝術活動。經過一年多的教育改革、教育實踐打破了舊北京藝專的死死沉沉、平平庸庸的局面。期間,他殫精竭慮地策劃與完成了“北京藝術大會”。但是,他的藝術革命沒有成功,反而招來殺身之禍,林風眠又辭去了校長一職。[28]林風眠痛心疾首:“不期橫逆之禍,不先不后,偏于此藝術運動剛剛有此復興希望時來到,于是費盡多少心血,剛剛扶得起的一點藝術運動的曙光,又被滅裂破壞以去!這是藝術運動中多么可悲的事啊!”后來,林風眠接任國立杭州藝術學院院長一職,林風眠不分日夜地為藝術奔走,他繼承蔡元培的辦學理念:“兼容并包,藝術自由”。提倡現代的、印象的、抽象的各種風格。1928 年策劃成立了“藝術運動社”,并創辦了《亞波羅》、《雅典娜》和《車神》多種刊物。其中1929 年成立的以林風眠、克羅多為導師的“西湖一八藝社”是“藝術運動社”最為著名的一個。“西湖一八藝社”后來匯入了魯迅掀起的新興木刻運動并在上海舉辦展覽。直到1937 年,整整十個春秋,林風眠苦心經營了杭州藝專。可是代表著林風眠“藝術運動”精神的《亞波羅》終于不再出版了。各種復雜的社會背景與嚴峻的形勢,林風眠終于離開了國立杭州藝專[29]。從此,改造社會的運動對于林風眠而言又只得告一段落……“為藝術而戰”,凝結著他對后繼者的無限的希望。
結語
時至今日,林風眠離開三十年了,人們在繼續著他所開創的藝術神話。他在近一個世紀的遠足中,帶給我們如此神奇而富饒的心靈風景,開啟了一道亮麗的人性曙光。藝術是什么?現代藝術將走向哪里?林風眠苦苦以求的藝術探索,給后人樹立了一桿高高聳立的標桿,所仰為真理。同時,也留下了許多永恒的話題。從傳統到“西化”,從“西化”到“調和中西”,再從“調和中西”到“民族化”,現代藝術之路,潛在暗藏,不就是林風眠所要探尋的光明大道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