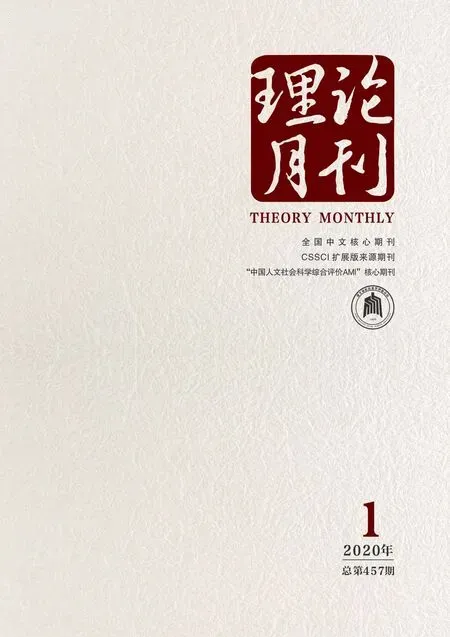東方賦權:媒介視角下東西方文化對話的機制、問題和可能
□曹志偉
(南京財經(jīng)大學 新聞學院,江蘇 南京 210023)
薩義德《東方學》中的“東方”(Orient)最準確的含義是一個想象的東方,是一個模糊的地政學范疇。狹義上,該東方是伊斯蘭和阿拉伯世界;現(xiàn)實中,它與廣義的西方相對,可以包含遠東地區(qū)的中國、日本及印度。20世紀90年代初,后殖民主義文化理論引入中國,并逐漸被人熟知。1990年代,眾多國內(nèi)文化學者將“東方主義”中國化,試圖將東方的版圖擴大,以適應中國的語境。其中就包括了劉象愚、王一川、陶東風、王岳川等著名文化學者,他們在《讀書》《文藝爭鳴》《當代外國文學》《外國文學》等期刊集中討論了后殖民主義與中國現(xiàn)代化的“碰撞”,也提出了諸多“方案”。在很多人看來,與1990年代的環(huán)境相比,現(xiàn)在再去談論“文化殖民”一詞貌似已經(jīng)過時,但事實上,后殖民主義理論并非是僵化的理論,它會隨著歷史時刻、地理區(qū)域、文化身份等諸多外部環(huán)境的變化而變化。與20多年前相比,外部環(huán)境已經(jīng)發(fā)生巨變,所以在此討論對東方主義中國化議題的更新、擴展與再思考有一定必要性。
1999年,薩義德的《東方學》首次在中國出版,距今恰逢20年。巧合的是,1999年常被業(yè)界稱為互聯(lián)網(wǎng)大潮的起始年,它與東方學傳入中國的時間偶合,這也使得當初的人們對互聯(lián)網(wǎng)這一“西洋”事物自然地與“殖民工具”相聯(lián)系。經(jīng)過20年的發(fā)展,人們也逐漸辨析清楚兩者之間的微妙關系,互聯(lián)網(wǎng)并不是“后殖民”的“幫兇”,而有可能成為“后殖民”的“掘墓人”,互聯(lián)網(wǎng)的“殖民能力”經(jīng)歷了“由盛及衰”的變化。在東方學引入中國和互聯(lián)網(wǎng)大發(fā)展20周年的雙重歷史節(jié)點上,重新思考“互聯(lián)網(wǎng)與東方學”,并在此基礎上探討東西方“和解”的可能性顯得尤為重要。
一、由盛及衰:作為“轉(zhuǎn)折點”的互聯(lián)網(wǎng)
在中國學者討論后殖民主義之前,也就是在互聯(lián)網(wǎng)成為一種“新殖民工具”之前,后殖民主義理論在西方已經(jīng)發(fā)展得非常完善。薩義德在1978年出版的《東方學》、霍米·巴巴在1990年出版的《民族與敘事》、1993年出版的《文化的定位》、斯皮瓦克在1999年才出版的《后殖民理性批判:通向正在消失的現(xiàn)在的歷史》都是在互聯(lián)網(wǎng)出現(xiàn)或興盛之前出版的論著,在這個互聯(lián)網(wǎng)“統(tǒng)治”的時代,一些論調(diào)已經(jīng)無法適應當前語境,或是完全被互聯(lián)網(wǎng)情境所顛覆。薩義德、湯林森、霍米·巴巴、斯皮瓦克等后殖民主義研究學者與20世紀90年代東方眾多文化研究學者也無法預料到,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帶來的殖民效果會如此“波動”,勢必需要重新思考東西方話語權的平衡與格局。胡翼青在提出關于“媒介技術哲學范式的興起”觀點時就強調(diào):“媒介作為當下社會的技術框架,重塑著社會的時間觀、空間觀和權力關系。”[1](p5)因此,從理論上講,通過技術哲學的角度對后殖民主義進行思考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從過去幾十年的狀況看,西方話語經(jīng)歷了一次由盛及衰的權力波動。在前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東方話語權力一再被削弱,西方文化不再是滲透和倒戈,卻是明目張膽地利用傳媒工具對東方施加影響。西方沉浸在“自我”與“他者”的身份結(jié)構(gòu)中,幻想傳媒工具(主要指傳統(tǒng)媒介)帶來永久的權力快感。隨著互聯(lián)網(wǎng)從Web2.0時代逐漸走向后期并跨入Web3.0階段,西方話語權出現(xiàn)了衰落跡象。由此可見,Web2.0時代的西方媒介生態(tài)出現(xiàn)了諸多問題,從而直接導致了“西方轉(zhuǎn)衰與東方賦權”。直觀地看,西方自媒體的低門檻、強交互特征逐漸顯現(xiàn),新媒介逐漸替代了傳統(tǒng)媒介,為此西方集中壟斷媒介資源的能力也大大削弱。當東西方都具備媒介使用權的時候,西方原先幻想壟斷情境已不復存在。現(xiàn)如今,中國、日本、韓國、印度正從互聯(lián)網(wǎng)信息凈輸入國發(fā)展成了互聯(lián)網(wǎng)信息輸出國,由逆差轉(zhuǎn)向順差,這是一個很明顯的西方話語權力衰落的跡象。早在2001年,富蘭克林的《互聯(lián)網(wǎng)與后殖民主義政治表征》與戴維·莫利的《認同的空間》中以西方視角(殖民者視角)反思了網(wǎng)絡空間中“東方崛起”,文中提道:“我們在承認一種文化壟斷的終結(jié)的同時,我們都受到來自自身發(fā)現(xiàn)的威脅。頃刻間情況變得可能是只存在他者而我們自己則是諸他者中的‘他者’。”[2](p34)這句話暗示著,從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傳到東方之日起,“西方中心主義”的架構(gòu)就不再是堅不可摧的了。
宏觀上看,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的主體性“劇變”切實影響著整個傳媒生態(tài)、權力與東西方對話。在此背景下東方被賦權,對東方來說既是機遇也是挑戰(zhàn),“東方的反抗”所帶來的文化“地域化”瓦解了文化“程式化”的單一發(fā)展路徑,但也一定程度上阻礙了文化全球化發(fā)展。現(xiàn)在東方的處境早已不是羅蘭·巴特在《Mythologies》中講述《失去的大陸》那般:“所謂‘東方’,被掠走了所有的內(nèi)容,恢復到單純的色彩。”當前的“話語規(guī)則”就不僅僅涉及文化的力量,更是社會的較量,當媒介環(huán)境發(fā)生改變、主體身份出現(xiàn)偏移、權力結(jié)構(gòu)產(chǎn)生松動的時候,那又該是重新思考東方學的時候。其實安東尼·葛蘭西在提出霸權所涉及的關聯(lián)體中時包含了政治與社會因素,往后學者受形式主義影響,漸漸忽視了諸如“互聯(lián)網(wǎng)”等工具作為的社會因素。某種意義上講,互聯(lián)網(wǎng)的作用在20年的后半段被低估了。
二、主體偏移:后殖民主義式微的媒介語境
互聯(lián)網(wǎng)對殖民主義最初產(chǎn)生的效果是“主體偏移”,主體偏移最直接地表現(xiàn)在參與主體、權利主體與主體屬性三個方面。三方面的主體偏移直接導致了西方話語霸權的削弱。
互聯(lián)網(wǎng)是21世紀的時代標志,互聯(lián)網(wǎng)的技術變革深刻影響著世界的各個方面,它能夠改變交流方式、溝通渠道、認知范圍,甚至能影響政治決策。互聯(lián)網(wǎng)早已從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美國專利品變成了當下各個國家都可利用的公共必需品,這就意味著互聯(lián)網(wǎng)的參與主體開始增多,數(shù)量上,東方的發(fā)展中國家增速明顯。由此可以判斷,主體偏移的第一方面便是參與主體的偏移,即媒介主控者從西方壟斷變?yōu)闁|西方共用。這一角度變化意味著西方媒介壟斷資源的喪失。
主體偏移的第二方面是權力主體的偏移,即媒介被賦予了主體力量。著名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批評理論家馬克·波斯特在2001年出版的《What’s the matter of the Internet?》一書中將媒介描述成一種物質(zhì),更是一種能夠改變文化的物質(zhì)力量。與此同時,他認為社會的改變需要文化層面的顛覆與重構(gòu),并且由文化自身來主導。在波斯特的論點中可以清晰地判斷文化被賦予了主體性,結(jié)合麥克盧漢“媒介即訊息”的觀點,主體功能被遷移到了媒介身上。一時間,“社會學家會有意無意地將互聯(lián)網(wǎng)當作人”[3](p12),那么這就意味著,互聯(lián)網(wǎng)已經(jīng)成為反映社會文化變遷的一種顯著核心變量。當具備主體性的互聯(lián)網(wǎng)置放在新世紀東西方對話的規(guī)則之中,東西方話語的關系網(wǎng)絡則變得比過去更加復雜。這一角度的變化意味著西方對文化及媒介的控制已失去絕對的權威。
主體偏移的第三方面是屬性偏移,即媒介的功能屬性逐漸擴大。20年來,互聯(lián)網(wǎng)從傳統(tǒng)的純技術工具演變?yōu)槿谌胝巍⒔?jīng)濟、文化、社會等各個方面的必需品。互聯(lián)網(wǎng)對傳統(tǒng)的東西方話語權格局具有非常深刻的影響,隨著參與主體與權力主體的集體偏移,互聯(lián)網(wǎng)改變了原先的傳媒生態(tài),它不僅能夠削弱西方話語的霸權地位,同時也能使東方話語迅速復興。因此,后殖民時代隨著互聯(lián)網(wǎng)工具的引入,使東西方權力格局變得紛繁復雜。盡管海德格爾曾提出了一套關于技術的本質(zhì)及其與存在史之關聯(lián)的完整系統(tǒng)論說,提出了“通過技術,整個地球如今以西方的方式而被經(jīng)驗”[4](p94-106)的論斷,并創(chuàng)造“集置”的概念,解釋可操作性的擴張壟斷現(xiàn)象,但當參與主體成為“雙方”的時候,該“集置”就不再會有“壟斷”的屬性特征。本質(zhì)上,Web2.0時代的傳媒技術回歸到了原始狀態(tài),即看作是一種“可操作的工具”,尤其是在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產(chǎn)業(yè)(Web2.0后期)出現(xiàn)之后,西方話語殖民的趨勢便逐漸減緩。
綜合以上三個方面,不難發(fā)現(xiàn),互聯(lián)網(wǎng)不再作為一種神秘的“渠道”出現(xiàn)在東西方對話的視野中,它開始變得普通和可觸及,甚至其本身就能夠代表一種意識形態(tài)力量。盡管從主體屬性的發(fā)展趨勢上可以看到對于西方國家來說操縱互聯(lián)網(wǎng)具有巨大的優(yōu)勢,但是當參與主體開始東移且其“工具性”逐漸減弱,那么后殖民主義下的媒介生態(tài)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東西方權利關系也開始步入“后”的時代。
三、惡性生態(tài):文化工業(yè)背后的程式化弊端
后殖民主義理論在近些年逐漸淡出學者視線,其重要原因在于“壟斷機制”出現(xiàn)了危機,即由“惡性生態(tài)”帶來的“由盛及衰”。互聯(lián)網(wǎng)前期(Web1.0時代)裂變式的傳播模式下,使過去文化工業(yè)隱藏的程式化弊端被無限放大,形成了最初的“互聯(lián)網(wǎng)惡性生態(tài)”,這一趨勢與當前多元化的發(fā)展理念背道而馳,長久以來也一直被東方世界詬病。不難發(fā)現(xiàn),互聯(lián)網(wǎng)對文化工業(yè)模式的延續(xù)與“主體偏移”的事實南轅北轍。在Web2.0時代,西方美好的“守權”幻想一直存在,直接導致了Web2.0時代與Web3.0時代延續(xù)了Web1.0時代繼承文化工業(yè)弊端的遺存。這些所謂的“遺存”,恰恰成了未來“東方賦權”的最佳突破口,但這些問題也是東方急需面對的:首先,互聯(lián)網(wǎng)工業(yè)使受眾意識演變?yōu)楣ぞ呃硇裕祟悊适Я颂綄の镔|(zhì)本真的原有方式;其次,傳統(tǒng)的文化范式被工業(yè)化的快餐文化擠占,唯西方標準的規(guī)則下,傳統(tǒng)文化的魅力正在消解;最后,互聯(lián)網(wǎng)新媒介通過“涵化”的方式統(tǒng)一思想,迷惑東方接受西方價值。
(一)從技術干預到文化滲透
消費文化和視覺文化興起,是21世紀初最明顯的時代特征,互聯(lián)網(wǎng)則是這種“后現(xiàn)代文化”[5](p101)的助推器。媒介化是現(xiàn)代工業(yè)文明異化世界的重要方面,工具理性取代審美感性,人們對工具的崇拜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這是惡性生態(tài)暴露出來的第一個問題,也是各個媒介理論家公認的問題。
技術理性并不是互聯(lián)網(wǎng)的“專利品”,它在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達到頂峰,因此從側(cè)面可以斷定新媒介與傳統(tǒng)媒介不是“取代”關系,而是“迭代”關系。早在18世紀60年代的第一次工業(yè)革命開始,人類就開始崇尚工具崇拜。在工業(yè)革命的影響下,特別是改革開放浪潮推動下,20世紀九十年代初的中國小說中,就具有了對工具崇拜的影子,小說中流行工具崇拜,對詩性的追求不斷弱化。“小說寫作逐漸從精神境界的對話成了急功近利的利益互動”[6](p150-155),文字作為最原始的傳播方式也被工具理性所影響。到后來20世紀90年代末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從美國迅猛發(fā)展,受眾對互聯(lián)網(wǎng)的崇拜達到頂峰,很多學者發(fā)現(xiàn)已經(jīng)回不去從前,高建平等人就直言不諱地提出:“工具理性對待效率的訴求是時代的趨勢,也適應歷史性訴求。”[7](p263)在新世紀初期,很多學者也都這么認為,因為人們很容易覺察到互聯(lián)網(wǎng)帶給東方的短期優(yōu)勢,即迅速吸收西方先進理念、文化,縮短與西方的實在差異。
精英文化、西方文化在互聯(lián)網(wǎng)發(fā)達的今日逐漸祛魅,精英文化也可以消費,西方文化對于東方人來說也不再遙遠。通俗文化、消費文化、娛樂文化、快餐文化成為當今主流的文化,精英與大眾、東方與西方的二元對立日漸消解。不論精英文化還是大眾文化、東方文化還是西方文化,都依托互聯(lián)網(wǎng)載體,唾手可得。傳媒生態(tài)系統(tǒng)的各個要素在主流文化建構(gòu)過程中發(fā)揮重要作用,特別是傳媒產(chǎn)品生產(chǎn)和傳播的過程兩個方面。崇尚媒介工具論的人們在傳媒產(chǎn)品的傳播指引下,沉浸在電視、電腦、手機等傳媒工具中無法自拔,受眾意識被傳媒工具“涵化(Cultivate)”,因此傳媒工具的發(fā)展影響受眾看待世界的視角。原先受眾看來遙不可及的文化,被圖像化、語音化、視頻化,受眾更容易接觸到精英文化和西方文化,但是與此同時帶來的問題則是文化傳輸?shù)乃槠⒊淌交酥镣ㄋ谆2⑶遥瑐髅焦ぞ呔哂羞^濾的功能,傳媒工具選擇性傳送的訊息經(jīng)過過濾和后加工,受眾看到的內(nèi)容并非真實現(xiàn)實的全部。受眾逐漸培養(yǎng)成被動接受式的習得模式,而非主動索取式的了解文化本真之方式。
受眾被培養(yǎng)工具理性的意識下,傳媒生態(tài)的三個層面也發(fā)生了改變:信息與受眾層面的生態(tài)、媒介組織層面的生態(tài)和媒介控制層面的生態(tài)。首先,受眾適應新的信息傳播體系,很大程度上不愿回到過去傳統(tǒng)的口述模式或紙媒模式。由于互聯(lián)網(wǎng)媒介高參與度的特征,受眾適應了被動接受者向主動發(fā)布者的身份轉(zhuǎn)變,便認為互聯(lián)網(wǎng)的使用理所應當,潛移默化地依賴互聯(lián)網(wǎng)媒介。再者,媒介組織層面,資金、人才、管理等要素的引入,促使傳媒生態(tài)組織化、商業(yè)化、財團化,葛蘭西所謂的媒介霸權其實就是最先是從媒介工業(yè)(商業(yè))霸權開始的。最后,有了組織化的商業(yè)霸權便可以獲取技術霸權,隨后就可對媒介控制層面的生態(tài)進行滲入,包括文化及其外圍的政治、經(jīng)濟、信息活動等方面的操控。通過傳媒生態(tài)的三個層面滲透媒介文化,對“他者”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社會的影響,揭示了西方“阻止‘主體偏移’”的“真面目”。
(二)從西方標準到生態(tài)壟斷
西方在西方發(fā)明的媒介工具中執(zhí)行西方的規(guī)則標準是必然,與此同時,西方文化的碎片化、程式化、通俗化特征與互聯(lián)網(wǎng)傳播特質(zhì)完全吻合,換句話說互聯(lián)網(wǎng)起初就是為西方量身打造的。在規(guī)則和形式都壟斷的情況下,傳媒生態(tài)就顯得保守、封閉及板滯。這種模式下,西方快餐文化得以盛行,東方傳統(tǒng)文化魅力很難顯現(xiàn)。這是惡性生態(tài)暴露出來的第二個問題,也是一個急需解決的問題。
薩義德曾就“后殖民主義”的“標準”問題展開過討論,在薩義德看來,東方學并非關于東方的真實話語,因為在一定程度上東方被西方看作是神秘、封閉、愚昧之地。西方在文化上特別注重其自身“主體性”,被“他者”化的東方何來的權力?薩義德在《東方學》中界定的東方學有三層含義:首先,東方學是作為一個學術研究的學科;其次,東方學是一種思維方式。最后一層含義則是,“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臨東方的一種方式”[8](p256)。最后一層含義表達了西方凌駕于東方之上的話語霸權,話語的載體是多種多樣的,就民間階層而言,董曉萍等學者就認為“影響最為深刻的途徑即是媒介”[9](p89)。在東方,最早接觸西方思想及媒介工具的是精英階層,精英階層直接掌控著東方的話語方向,通常連很多學者也就精英文化的標準來衡量大眾文化。西方通過建構(gòu)一個完善的媒介生態(tài),以吸引東方的精英階層的注意。19世紀六十年代的洋務派提倡“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師夷長技”,他們就是很早的一批吸收西方先進技術的東方精英階層。不論是被動接納,還是主動接受,后期的發(fā)展都帶有東方的自愿性。從被動到主動,從抵抗到接受,從殖民再到后殖民,可以說是一個東方精英階層被馴化的過程。20世紀90年代開始,互聯(lián)網(wǎng)是被西方賦予了“新興殖民工具”屬性而登上歷史舞臺的,傳統(tǒng)的后殖民理論在互聯(lián)網(wǎng)的作用下得到了更新和迭代。Web1.0時代西方絕對的信息霸權迫使東方缺少參與主體身份,使得西方繼續(xù)嘗到了文化工業(yè)的“甜頭”,但到Web2.0時代,東方揭露了互聯(lián)網(wǎng)最初產(chǎn)生的本質(zhì),西方標準和生態(tài)壟斷得以曝光于天下。
互聯(lián)網(wǎng)產(chǎn)生初期,信息殖民化的呈現(xiàn)方式依舊是法蘭克福學派阿多諾和霍克海姆所提出的傳統(tǒng)方式,即推崇標準化、規(guī)格化、機械復制、大批量、覆蓋廣的“文化工業(yè)”。這種文化工業(yè)讓受眾產(chǎn)生心理依賴,導致人性異化及審美能力退化。傳統(tǒng)的敘事內(nèi)容及其言說無法適應當前受眾的快餐化文化需求,文化轉(zhuǎn)型勢在必行。文化轉(zhuǎn)型是傳媒發(fā)展帶來的重要特征,娛樂化消費式取代原有的精英化經(jīng)典式,在有限的文學空間里,傳統(tǒng)的文化范式被擠占,文化的魅力消解。
西方的媒介生態(tài)是從過去的傳統(tǒng)歌劇、芭蕾舞蹈到電影、爵士、唱片再到現(xiàn)在的互聯(lián)網(wǎng),是一個為西方文化量身定做的媒介生態(tài)。對于東方文化來說,新事物的到來注定會擠占東方傳統(tǒng),文化的轉(zhuǎn)型也必定會失去很多原有的精粹,是被動的或是強迫的。而當前媒介生態(tài)下的文化轉(zhuǎn)型對于西方來說是西方文化發(fā)展的應有走向,是時代的必然選擇。東西方倘若建立對話的機制,在平臺上就顯現(xiàn)出差異。由此看見,制定多元化的互聯(lián)網(wǎng)文化標準和打破生態(tài)壟斷才是逃脫“程式化牢籠”最有效的方式。
(三)從文化工業(yè)到技術涵化
在印刷媒介、電視媒介占統(tǒng)治地位的年代,文化工業(yè)是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家們經(jīng)常討論的概念,文化工業(yè)的重要目的是文化商品化。互聯(lián)網(wǎng)占統(tǒng)治地位的年代,理論家將文化工業(yè)升華,開給人們自由、實現(xiàn)愿望、滿足審美等各種“快樂支票”,實際上卻使用技術涵化的手段使人們接受現(xiàn)實秩序。這是惡性生態(tài)暴露出來的第三個問題,也是一個隱藏很深的問題。
在2005年召開的“信息社會世界高峰會議突尼斯階段會議”中就有人指出西方互聯(lián)網(wǎng)“控制權”的問題:互聯(lián)網(wǎng)迅猛發(fā)展的媒介生態(tài)下,西方的話語權僅僅更換了一種方式進行殖民,傳媒作為西方話語的載體,致使爭奪話語權更有效、更高效。互聯(lián)網(wǎng)將世界各地的人連接在一起,形成地球村,該傳媒工具使用西方的先進技術傳播西方中心論的思想,潛移默化中影響“他者”,將地球村的受眾思想統(tǒng)一。互聯(lián)網(wǎng)傳媒工具出現(xiàn)后,話語權無須爭奪,因為作為“他者”的東方接受互聯(lián)網(wǎng)傳媒技術,也隨之接受這種傳媒技術帶來的價值。
“掌握技術就掌握了核心競爭力”,這話在文化研究者看來并不是他們擅長討論的范疇,但是恰恰是互聯(lián)網(wǎng)技術從根本上決定了東方的邊緣地位,并且在現(xiàn)在看來,東方文化在客觀條件下很難翻身。此種現(xiàn)象的發(fā)生歸因于強大的“意見領袖”,凱茲和拉扎斯菲爾德在對“意見領袖”的概念進行修正過程中提道:“在使用媒介過程中,角色劃分為主動接受和傳遞訊息者與被動依賴他人的指導者。意見領袖掌握媒介使用的權利,被人們認為是具有消息來源和指導角色等特征。”[10](p79)把此論調(diào)再修正,上升至國家層面上看,則吻合了席勒在《傳播與文化支配》一書中提出的“文化帝國主義”的觀點。由此看來,東方話語權在Web1.0階段的邊緣窘境就不難解釋了。在當時,西方掌握“喉舌”的關鍵技術,社交媒體討論西方的價值、理念,研究西方社會感興趣的文化,參與西方政治家所重視的議題。Facebook、Twitter、Instagram、YouTube在互聯(lián)網(wǎng)大發(fā)展的初期包攬了全球社交平臺的半壁江山,成為新時期意見領袖。通過傳媒技術的“涵化”,東方的權力根本沒有施展的空間,甚至出現(xiàn)“他者”認同西方文化。伯格納提出的涵化理論在社交媒介的運用可表現(xiàn)為:“西方通過互聯(lián)網(wǎng)社交媒介傳播特定的內(nèi)容(面向西方本國的受眾),東方受眾在長久以往的關注后,會逐漸接受西方建構(gòu)的內(nèi)容,并與自我的‘東方現(xiàn)實’相結(jié)合,認同西方文化”。特別是東方精英階層受互聯(lián)網(wǎng)傳播的影響,潛移默化地認同西方主流價值,作為東方依賴西方指導的意見領袖,從根源上截斷了東方話語權滋生的環(huán)境。
隨著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主體偏移”的顯現(xiàn),東方逐漸開始認識到技術涵化的危險,因此在Web2.0的后期東方針對性研發(fā)了微信、微博等自己的社交軟件,從技術根源上截斷了被西方涵化的可能。盡管現(xiàn)階段技術涵化的效果有所緩和,但面對長久而又鞏固的涵化秩序,東方話語權在互聯(lián)網(wǎng)媒介主導的媒介生態(tài)下,發(fā)聲依舊較為困難。
四、東方反超:生態(tài)危機化解與反技術壟斷
面對“主體偏移”的事實和“惡性生態(tài)”的困局,東方媒介話語權力的提升既有機遇也有挑戰(zhàn),機遇在于“主體偏移”帶來的客觀利好,挑戰(zhàn)在于解決西方長期建立起來的惡性生態(tài)。事實上,東方可以從“主體偏移”的環(huán)節(jié)入手,對“惡性生態(tài)”的生態(tài)危機和技術壟斷兩個方面制定針對性的“東方方案”。
麥克盧漢在《理解媒介》中指出“媒介即萬物”,當互聯(lián)網(wǎng)媒介從一種行業(yè)力量上升為一種社會元權力的時候,媒介化社會將成為一種顯在。互聯(lián)網(wǎng)媒介組織著我們的日常生活,提供給我們一個新的時空,東方尚可從結(jié)構(gòu)(空間)和變遷(時間)等角度實現(xiàn)“東方反超”。結(jié)構(gòu)上,互聯(lián)網(wǎng)媒介提供了制度的路徑;變遷中,互聯(lián)網(wǎng)媒介提供了關系建構(gòu)的路徑。
(一)生態(tài)危機的化解
基于上述“惡性生態(tài)”的剖析,不難發(fā)現(xiàn),倘若改變原有的生態(tài)危機需要改變程式化規(guī)準,讓文化奪回生態(tài)建設的主動權。生態(tài)危機的解決都是立足空間維度的,其一是針對傳統(tǒng)媒介生存危機,它要求傳統(tǒng)媒介與新媒介有一個共洽的生存空間,這個方案盡管不分東方與西方,但實際操作是有利于“東方反超”的;其二是面對東方傳統(tǒng)文化繼承危機,它要求東方文化、西方文化與互聯(lián)網(wǎng)實現(xiàn)共洽,實現(xiàn)三者的權力平等,使該空間的溝通是雙向的。
處理傳統(tǒng)媒介與新媒介的關系在過去是有實踐基礎的,尼爾·波茲曼在《娛樂至死》中就警惕電視是否會取代紙媒,波茲曼在80年代論述的觀點在現(xiàn)在看來顯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因為互聯(lián)網(wǎng)興起又再次改變了媒介生態(tài),互聯(lián)網(wǎng)扮演了80年代電視的角色。就波茲曼的論點來看,三十多年過去,紙媒并沒有消失,很多人會認為波茲曼豈不是杞人憂天,但三十多年后的今天不可同日而語,互聯(lián)網(wǎng)也許真的會顛覆趨于平衡的媒介生態(tài)。工具上的生態(tài)顛覆無東西之分,可工具層面的傳媒生態(tài)一旦發(fā)生變化,或是互聯(lián)網(wǎng)媒介占據(jù)傳媒工具主體地位,那么東方文化載體的危機便應該引起重視。波茲曼反復強調(diào)“媒介即訊息”,這就意味著媒介帶給我們的內(nèi)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媒介本身,媒介本身就作為內(nèi)容出現(xiàn)在公眾視野,它是具有意義的。我們在考察媒介的視角從工具論轉(zhuǎn)向內(nèi)容論的時候,傳統(tǒng)媒介與新媒介的不可調(diào)和狀況仿佛有所緩解。從這個角度看,東西方話語權的爭斗就不能局限在占領“新媒介地盤”之上,傳統(tǒng)媒介諸如報紙、廣播、電視都與互聯(lián)網(wǎng)同樣重要。西方在失去傳統(tǒng)媒介壟斷地位且面臨互聯(lián)網(wǎng)主體偏移與惡性生態(tài)雙重夾擊的背景下,東方傳統(tǒng)文化與媒介的結(jié)合恰逢其時。
波茲曼在《娛樂至死》中其實還強調(diào)“媒介即隱喻”,就當下互聯(lián)網(wǎng)語境來說,互聯(lián)網(wǎng)用隱蔽但有力的方式重新定義了整個世界。換句話說,互聯(lián)網(wǎng)創(chuàng)造了一個與現(xiàn)實世界呈鏡面關系的“擬態(tài)世界”。波茲曼認為“傳媒技術影響下的文化精神的枯萎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會成為一場滑稽戲。”[11](p186)在當時看作是“滑稽戲”的嬉皮士、朋克、披頭士、搖滾等青年亞文化,現(xiàn)如今早已被收編,融入西方主流文化體系。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互聯(lián)網(wǎng)傳播的“滑稽戲”卻和東方主流文化格格不入。從某種角度上來說,互聯(lián)網(wǎng)不只能與西方文化相匹配,東方同樣也能通過互聯(lián)網(wǎng)創(chuàng)造東方屬性的擬態(tài)世界,互聯(lián)網(wǎng)鏡像呈現(xiàn)的東方文化也能使之成為一場“正統(tǒng)劇”。這樣一來,東方文化與互聯(lián)網(wǎng)、西方文化與互聯(lián)網(wǎng)都有各自獨立的規(guī)則,東方與西方對話最終有所可能。
(二)反技術壟斷
反技術壟斷是實現(xiàn)“東方反超”的第二條路徑。從西方通過傳媒控制東方的方式上看,后現(xiàn)代工業(yè)社會中的電視、電影、互聯(lián)網(wǎng)等媒介實為一種編碼解碼的工具,利用傳統(tǒng)文字文本的闡釋是有邊界的,現(xiàn)代意義上的圖像或聲頻文本闡釋是無邊界的。文本閱讀的過程中,文本本身就給受眾帶來限制和約束,東德學者朗曼提到,文本中的作品是具有引導性的,文本的闡釋者帶有一種預設,闡釋者試圖通過這種預設來達到“控制”的目的。我們不禁會問,東方為何沒有用同樣的方式與西方對話?主要原因就是技術壟斷。
大眾階層認為,在當前媒介生態(tài)的發(fā)展趨勢下,給東西方文化提供一個對話平臺不無可能:工具來自西方,文化可以以新媒體作為載體,不在乎形式與外表,注重的是內(nèi)容與本質(zhì)。因此可以說當前互聯(lián)網(wǎng)引領的媒介生態(tài),為東方文明關上了一扇門,卻打開了一扇窗。
在實際操作中,東方建立一個自主的文化網(wǎng)絡平臺是十分必要的。大眾階層的想法其實與一百多年前洋務派“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方法十分類似,大眾階層沒有充分認識到技術與思想的緊密聯(lián)系,洋務運動當時也正是沒有引進西方先進制度理念而失敗的。通俗地說,互聯(lián)網(wǎng)代表的是西方技術,承載的是西方思想文化。東方欲建立平等的對話平臺,就需要擁有異于互聯(lián)網(wǎng)而又優(yōu)于互聯(lián)網(wǎng)并且與東方文化思想完美結(jié)合的技術手段。對話需要載體,東西方對話不僅是思想的碰撞,更是政治、經(jīng)濟、文化、技術諸多方面組成的一整套體系的對話。
新世紀初,在東方傳媒生態(tài)處在危機的情形之下,形成一整套自主的體系并與西方進行對話,的確十分困難。但現(xiàn)如今,微信、微博、優(yōu)酷等互聯(lián)網(wǎng)工具逐漸走向世界,這標志著東方自主的傳媒生態(tài)體系逐步形成,東西方平等對話的可能大大增加。
五、對話場域:后東方主義的再思考
互聯(lián)網(wǎng)發(fā)展對推動文化全球化有很大影響,同時對傳統(tǒng)文化正逐步消解,互聯(lián)網(wǎng)將文化置于技術之后,追求瞬時的快感,忽略永恒的經(jīng)典。海德格爾在《關于存在的問題》中提到,“全球化”直接地與虛無主義廣泛傳播聯(lián)系在一起,他更是認為“虛無主義有全球化傾向”[12](p94-106)。通過上述內(nèi)容可以看出,對傳統(tǒng)經(jīng)典的顛覆,是值得學者思考的問題。其中西方學者也認識到,對傳統(tǒng)經(jīng)典的顛覆不僅發(fā)生在東方,在西方也在發(fā)生。互聯(lián)網(wǎng)等新傳媒技術的引進,給傳統(tǒng)文化帶來的消解成了一個全球性議題。借此,薩義德在《東方學》中所提出的東西方合作成了東西方共同關注的話題。
西方話語的式微從理論上是由于西方過度使用制度學派的理論進行“殖民操作”,它的核心問題就在于將媒介作為一個無主體性的“物”植入到社會制度與文化制度的運作中,互聯(lián)網(wǎng)本身并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東方反超的方案則通過互動學派的方式將互聯(lián)網(wǎng)的地位提高,將東西方對話的環(huán)境看成是媒介與社會共同建構(gòu)的。從中可以發(fā)現(xiàn),兩者是二元對立的,沒有一個共洽的環(huán)境給予雙方對話,那么將東西方看作是兩個場域,并且雙方的博弈過程看成是一條條亞場域的力學線條,東西方對話的可能性就會大很多。
在過去,東方作為“他者”始終沒有足夠的籌碼與西方對話,話語權很難得到保障。當東方話語與西方話語形成各自的系統(tǒng)性場域的時候,媒介場域作為一個亞場域勾連起兩個元場的溝通渠道,其中就包含了相互獨立的“規(guī)則場域”(化解生態(tài)危機)和“技術場域”(反技術壟斷)。在此基礎上,后東方主義提倡的“東方對‘文化訓導’的消解和顛覆,推崇文化自尊和平等對話,重新獲得東方文化身份和文化自信”[13](p4-9)充分成為可能。
反思前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東方面對后殖民主義的方式,被西方文化思想長期壓迫致使東方對西方文化的一些抵抗存在“閉關”成分,所謂拒絕西方文化,推崇中國傳統(tǒng)經(jīng)典文化,有急需證明自我價值的民族主義之嫌。真正的后東方主義,是建立在“地球村”的概念之上,以一個價值無涉的態(tài)度去審視當前的大眾文化,擺脫原有東西方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立足整體,認識“自我”,進行兩場域間有效的文化互動。
在規(guī)則場域與技術場域的合法框架內(nèi),面對傳統(tǒng)文化被消解的問題,東西方兩場域間文化的互動更應注重歷史性的探討,而非基于新媒體的闡釋。“融合”作為東方文化的一大議題在近幾年再次引起熱議,東西融合是歷史的必然趨勢,也是解決東西方二元對立的辦法,而媒介融合更是一種將“互聯(lián)網(wǎng)文化”收編的方式。因此在“他者”的視閾下,解決西方文化上出現(xiàn)的規(guī)則霸權與技術本質(zhì)問題,往往會看得更遠。整體意識的確立,有利于結(jié)合東西方不同的優(yōu)勢,取長補短,在立足各自的“自我”時對“他者”并不施加影響。去中心化及媒介融合的方式使得各自文化得以保存,不受到使用傳媒工具帶來的侵蝕,這種模式何不叫一個新時代——“后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
六、結(jié)語
長久以來,互聯(lián)網(wǎng)建構(gòu)的媒介環(huán)境暴露出了很多問題,西方話語霸權雖依舊存在,但出現(xiàn)些許松動。“后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的“后”并非“技術之后”而是“理念之后”,媒介技術角度它本稱作“互聯(lián)網(wǎng)后時代”,而對話格局的角度它更應該稱作“后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后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更多地代表了Web3.0時代的去中心化思考。因此,“后互聯(lián)時代”概念的影響是全域性的,它同時發(fā)生在東西方兩個文化場域,它能夠充分滿足東西方話語的“求同存異”,東西方對主體偏移、惡性生態(tài)及負面效應的警惕意識正是東西方平等對話和合作的契機。在該背景下,不論傳媒技術的發(fā)展究竟如何,東西方話語權力有多么懸殊,“后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下的話語隔閡必將土崩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