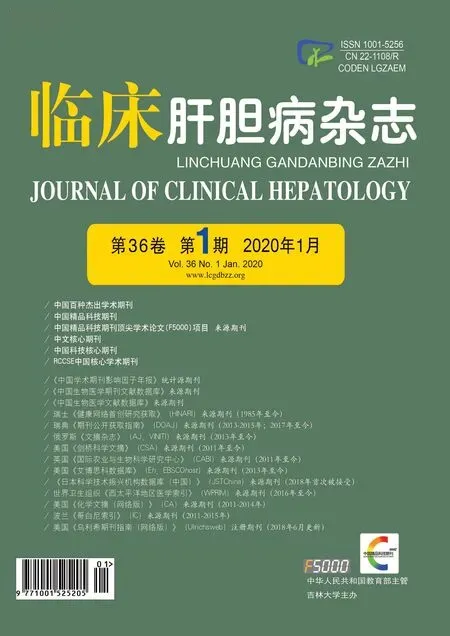中醫藥治療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重要靶位
——腸道微生態
李紅山,胡義揚
1 上海中醫藥大學 肝病研究所,上海 201203; 2 中國科學院大學寧波華美醫院,浙江 寧波 315010;3 寧波大學醫學院,浙江 寧波 315211; 4 上海中醫藥大學附屬曙光醫院 臨床研究中心,上海 201203
隨著生活方式和飲食結構的改變,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的發病率逐年上升,已成為我國重要的慢性肝病之一,帶來嚴重的經濟和醫療負擔。盡管國際上對NAFLD的機理研究逐步重視,但臨床仍缺乏有效的治療藥物。中醫藥作為我國治療NAFLD的重要手段,其療效逐步被臨床和基礎研究證實,積極研究中醫藥治療NAFLD的作用機制和靶點,具有重要的意義。
NAFLD雖然病位在肝臟,但與腸道密切關聯,腸道微生態是人體內重要的微環境之一,由人體腸道內正常的菌群、腸道分泌物、腸黏膜屏障及功能組成,腸道微生態的平衡穩定對人體健康至關重要[1],一旦微生態平衡被破壞,腸道菌群失調,腸黏膜屏障及功能破壞,就會產生多種致病作用[2-3]。腸道微生態在機體的能量平衡和代謝中具有重要意義[4],微生態的紊亂、腸道菌群失調是NAFLD發生、發展的重要病理機制[5]。調節腸道菌群、維持腸道微生態平衡是中醫藥治療NAFLD的重要策略。
1 腸道菌群紊亂與NAFLD的關系
健康成年人的腸道棲息著1000~1200種不同的腸道菌,細菌的細胞數量大約有1014(1~2 kg重),其細胞總量大概是人體自身細胞的10倍左右,此外,腸道微生物所攜帶的基因數量大約是人體自身基因數量的150倍[6]。腸道菌群的失調會引起免疫和代謝疾病,如炎癥性腸病、結直腸癌和2型糖尿病[7]。腸道菌群還能影響宿主的新陳代謝和消化,增加能量吸收、腸道通透性和慢性炎癥,從而參與NAFLD的發生和發展[8]。
研究[9]表明,腸道細菌過度生長可能增加腸道的通透性,促進細菌及其代謝產物,尤其是脂多糖的移位,后者可以誘導NAFLD的發生。腸道菌群過度增長患者的內毒素血癥可以激活Toll樣受體(TLR)4和CD14受體,進而誘導TNFα、IL-6和IL-8等炎性細胞因子的產生,這些細胞因子的過度生長可以加重炎癥和胰島素抵抗,進而誘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肝纖維化和肝細胞癌的發生[10]。
研究[11]發現,不同的小鼠因為腸道菌群的不同,喂養高脂飲食后雖然都會出現相似的體質量增加,但肝臟脂肪和炎癥變化截然不同,據此將小鼠分為responder(有反應)和non-responder (無反應),而將反應不同的小鼠腸道菌移植給無菌小鼠后,移植小鼠出現與供體小鼠類似的病理變化,移植responder小鼠腸道菌的無菌小鼠出現空腹高血糖和胰島素血癥,而移植non-responder小鼠腸道菌的無菌小鼠血糖水平正常。與供體為non-responder的無菌小鼠相比,供體為responder的無菌小鼠表現出肝大泡性脂肪變性,肝臟甘油三酯含量和脂肪合成相關基因的表達明顯增加。16S檢測結果發現,responder和non-responder小鼠具有不同的腸道菌群,在門、屬和種水平上具有明顯差異。有研究[12]表明,將肥胖患者減肥前和減肥后的腸道菌移植給無菌小鼠,無菌小鼠表現出不同的變化,移植肥胖患者減肥前腸道菌的無菌小鼠表現出肝臟脂肪變性和肝臟內甘油三酯含量升高,而移植肥胖患者減肥后腸道菌的無菌小鼠未出現上述病理變化。這些研究說明腸道菌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決定NAFLD的發生。
2 腸道菌代謝物與NAFLD的關系
越來越多的研究證據表明腸道菌在NAFLD的病理機制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其中,膽汁酸、氨基酸、短鏈脂肪酸等腸道菌的小分子代謝物起著關鍵作用,這些代謝物不僅能導致腸道的炎癥變化和功能改變,還能通過與宿主細胞受體的結合,介導肝臟炎癥和NAFLD[13]。
生理條件下的膽汁酸有助于維持肝葡萄糖、膽固醇和甘油三酯的穩態。研究[14]表明,膽汁酸可以通過改變膽汁酸受體(farnesoid X receptor,FXR)信號來參與NAFLD的發展, 初級膽汁酸鵝去氧膽酸是膽汁酸的內源性激動劑,能激活FXR信號通路,而次級膽汁酸脫氧膽酸則是FXR的內源性抑制劑,可以抑制FXR信號通路。FXR活化后主要通過多條途徑調節肝臟脂肪代謝以實現肝臟脂肪代謝平衡[15]。有研究[16]發現,FXR被膽汁酸激活后,可以減輕NAFLD小鼠的內質網應激,從而改善NAFLD。
腸道微生物和膽汁酸有著密切的關系,腸道菌群可顯著影響膽汁酸的代謝和轉運,尤其是可直接調控初級膽汁酸向次級膽汁酸的轉化,進而影響FXR的活化和功能[17]。膽汁酸激活或抑制FXR的能力與腸道菌密切關聯,研究[18]發現,奧貝膽酸可顯著改善NAFLD小鼠肥胖、代謝紊亂、肝臟炎癥和纖維化以及腸屏障損傷,降低NAFLD小鼠牛磺酸結合的膽汁酸含量,同時能顯著上調腸道布勞特氏菌屬的豐度。而用抗生素組合去除腸道共生菌后,奧貝膽酸的上述作用明顯減弱,說明奧貝膽酸調節膽汁酸治療NAFLD的作用是通過腸道菌實現的。
短鏈脂肪酸是由腸道微生物發酵產生的非消化性碳水化合物,包括甲酸鹽、乙酸鹽、丙酸鹽和丁酸鹽,短鏈脂肪酸不僅是來自腸上皮的重要營養和能量來源,還是脂肪生成和糖異生的前體,糖異生是NAFLD發病過程中一個重要的環節[19]。研究[20]表明,補充丙酸鹽能顯著降低體質量和肝細胞內脂肪含量,改善胰島素敏感性,明顯刺激人結腸細胞釋放胰高血糖素樣肽1。研究[21]發現,肥胖人群的總短鏈脂肪酸含量明顯高于非肥胖人群,并且肥胖人群的厚壁菌門和擬桿菌門的比例發生了變化。基礎研究[22-23]表明,產生丁酸鹽的益生菌可以糾正高脂飲食誘導的小鼠腸肝免疫失調和減輕脂肪性肝炎。
氨基酸在腸道被微生物發酵后可產生一些代謝物,部分代謝物表現出對肝功能的保護作用,研究[24-25]發現,谷氨酰胺能減輕高脂飲食誘導的小鼠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和肝臟氧化應激,抑制NF-κB p65的表達,改善肝臟脂肪變性。研究[26]表明,口服精氨酸可以改善西方飲食誘導的雌性小鼠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瓜氨酸可以預防高甘油三酯血癥和肝臟脂肪變性,調節肝臟脂肪代謝進而改善NAFLD[27]。
3 腸屏障結構和功能與NAFLD的關系
腸屏障包括物理屏障、生物屏障和免疫屏障三個部分。物理屏障主要由黏液層、微生物和由緊密連接蛋白連接的單層腸上皮細胞組成;生物屏障由具有抗菌特性的分子,如膽汁酸、α-防御素、β-防御素、C型凝集素、組織蛋白酶、溶菌酶和腸堿性磷酸酶等抗菌蛋白組成;免疫屏障由免疫球蛋白、淋巴濾泡及多種免疫細胞組成。腸黏膜屏障受損,就會導致細菌移位,細菌代謝物通過門靜脈循環和血液到達肝臟、腦等組織和器官,參與疾病的發生[19]。
研究[28]發現,NAFLD患兒的腸道通透性明顯增加,并且與疾病的嚴重程度密切關聯。腸道屏障功能的改變可以導致腸道促炎因子的移位,NAFLD患者的血液中細菌內毒素水平明顯升高[29]。有研究[30]表明,高脂和高蔗糖飲食可導致大鼠的脂多糖水平明顯升高,腸道緊密連接蛋白occludin的表達明顯降低,以及肝臟脂肪沉積明顯增加。
4 中醫藥療法與腸道微生態的關系
中醫認為,脂肪肝多為飲食失節,過食肥甘厚味,損傷脾胃,痰濁、瘀血阻于脅下所致。病位雖在肝臟,但病因則為脾胃功能失調,中醫的脾胃功能失調與西醫的腸道微生態失調有著密切關聯。
4.1 調節腸道菌 臨床觀察[31-33]發現,祛濕化瘀方(茵陳、姜黃、虎杖、梔子等)具有良好的治療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的作用,并且能降低NAFLD患者的血清游離脂肪酸水平和瘦素水平。基礎研究[34-36]證實,祛濕化瘀方治療實驗性NAFLD的效果十分顯著,可以改善NAFLD大鼠低脂聯素血癥,改善脂聯素信號通路,對AMPK信號通路也顯示出良好的調節作用。同時,研究[37]發現,祛濕化瘀方能糾正高脂飲食誘導的NAFLD大鼠的腸道菌群紊亂,具有良好的調節NAFLD大鼠腸道菌群、恢復腸道菌穩態的作用。筆者團隊最近的研究發現,來源于祛濕化瘀方的中藥成分復方梔子苷-綠原酸組合能明顯降低NAFLD小鼠布勞特氏菌屬、厭氧棍狀菌屬、羅氏菌屬豐度,上調NAFLD小鼠擬桿菌屬豐度,改善腸道和肝臟膽汁酸代謝,維持膽汁酸穩態,進而改善NAFLD小鼠脂肪代謝和炎癥損傷,而敲除FXR后,梔子苷-綠原酸組合對NAFLD小鼠的治療效應明顯減弱,提示梔子苷-綠原酸組合治療NAFLD的效應是通過改善腸道菌-膽汁酸-FXR軸實現的。
有學者[38]研究發現,參苓白術散能上調NAFLD大鼠的腸道雙歧桿菌和厭氧桿菌等產短鏈脂肪酸相關腸道菌的豐度,減少血清內毒素和脂多糖的水平,這是該藥物治療NAFLD的重要機制。有研究[39]表明,槲皮素能改善NAFLD小鼠胰島素抵抗,減輕NAFLD活動度積分,抑制肝臟脂肪沉積,具有良好的治療NAFLD的效果,進一步研究發現,NAFLD小鼠的硬壁菌門/擬桿菌門比率、革蘭陰性細菌和螺旋桿菌屬的豐度較正常小鼠明顯上調,槲皮素能糾正上述菌群失調,恢復腸道菌群穩態。
另有研究[40]表明,葛根芩連湯能上調NAFLD大鼠硬壁菌、梭菌、乳酸桿菌的水平,調節腸道菌群,這可能是其治療NAFLD的重要機制。研究[41]發現,茵陳蒿湯可糾正NAFLD大鼠擬桿菌門、厚壁菌門、變形菌門及放線菌門的失調,維持腸道菌穩態,這可能是該方治療NAFLD的重要機制。研究[42]表明,黃芪多糖能抑制高脂飲食誘導的肥胖小鼠的肝臟脂肪變性,上調擬桿菌門和厚壁菌門的相對豐度,下調變形菌門的相對豐度,而將黃芪多糖組小鼠的腸道菌移植給高脂飲食小鼠后,高脂飲食受體小鼠體質量出現明顯下降,一定程度上提示黃芪多糖減肥和改善肝臟脂肪變性的效應是通過腸道菌群實現的。
4.2 改善腸黏膜屏障 研究[43]發現,梔子苷-綠原酸組合能降低NAFLD小鼠腸道和血清脂多糖水平,恢復腸道緊密連接蛋白的表達,改善腸屏障功能,阻止內毒素進入誘發肝臟炎癥,從而有效的治療NAFLD,在一定程度上提示梔子苷-綠原酸組合治療NAFLD的效果與改善腸屏障功能密切關聯。另外,白藜蘆醇可以通過調節內源性大麻素系統來維持腸道屏障完整性和抑制腸道炎癥,從而減輕高脂肪飲食誘導的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44]。
有研究[45]發現,柴胡湯(柴胡、黃芩、白芍)能減少NAFLD大鼠肝組織TNFα、TGFβ、NF-κB和TLR4水平,并在一定程度上調控腸屏障功能,改善腸-肝軸,這可能是柴胡湯治療NAFLD的重要機制。有研究[46]表明,冬青皂苷D和冬青皂苷A1組合物能有效減輕NAFLD,并且能降低硬壁菌/類桿菌的比例和脫硫弧菌的相對豐度,增加阿克曼菌的相對豐度,調節腸道菌群。此外,冬青皂苷D和冬青皂苷A1組合物還能上調回腸緊密連接蛋白1和閉塞素的水平,進而改善腸-肝軸,減少循環中的內毒素水平。
5 存在問題與展望
如前所述,腸道微生態與NAFLD有著密切關系,中醫藥作為防治NAFLD的重要手段,對腸道微生態有著良好的調控作用,腸道微生態已經成為中醫藥防治NAFLD的重要靶點。然而目前中醫藥調節NAFLD腸道微生態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現象觀察階段,只是觀察一個藥物能上調或下調某一或某幾個腸道菌在門、屬、種等水平上的豐度,究竟該藥物治療NAFLD的效果是否是通過這些菌來實現的,由于缺乏相應的驗證,并不十分清楚。因此,未來基于腸道微生態研究中醫藥防治NAFLD的效應機制,需要注意幾個方面的問題:(1)要引入無菌小鼠。盡管無菌小鼠的成本非常高,飼養條件也很嚴格,但是作為腸道菌研究的重要載體,能有效的反證中藥治療NAFLD與某一種或某幾種腸道菌的關系,能保證中醫藥相關研究的規范性和嚴謹性。(2)構建成熟的抗生素耗竭的NAFLD小鼠模型,并應用于中醫藥研究。目前,抗生素組合耗竭小鼠腸道菌已被應用于多種疾病的機制研究和藥物治療研究中,然而,在NAFLD研究領域,目前尚缺乏腸道菌群耗竭和某一特定菌群缺失的NAFLD動物模型,對藥物的治療研究帶來極大困難。需在建立NAFLD動物模型后,探索耗竭NAFLD動物腸道菌群或某一特定腸道菌的抗生素組合或種類,以進一步構建特定菌群缺失的NAFLD動物模型,應用于中醫藥調節腸道菌的相關研究。(3)開展驗證研究。在中醫藥治療NAFLD的研究中,觀察到中藥對某一腸道菌有明顯調節作用后,可以運用動物實驗或者細胞實驗,驗證該細菌是否能有效干預NAFLD,從而可以佐證中藥治療NAFLD的作用是否是通過該菌群實現的。
總之,腸道微生態紊亂是NAFLD重要的病理機制,糾正腸道微生態紊亂是中醫藥防治NAFLD的重要治療策略,需加強和規范以腸道微生態為靶點的中醫藥治療NAFLD的機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