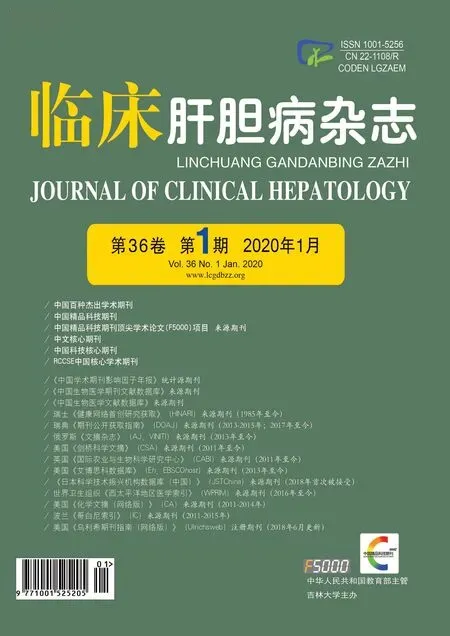門靜脈性肺動脈高壓的研究現狀
殷 鑫,張 雨,邵玥明,高 卉,秦婷婷,溫曉玉
1 吉林大學第一醫院 肝病科,長春 130021; 2 泰安市立醫院 消化內科,山東 泰安 271000
門靜脈性肺動脈高壓(portopulmonary hypertension,POPH)是與門靜脈高壓相關的肺動脈高壓,不論是否合并肝病,任何可引起門靜脈高壓的疾病,如肝硬化、膽管阻塞及膽汁淤積性疾病、先天性肝外門腔分流等均可發生POPH。POPH是由于長期門靜脈高壓引起的肺血管重構導致肺動脈高壓。根據2013年肺動脈高壓的最新分類將此種肺動脈高壓列為1組肺動脈高壓[1]。盡管POPH的發病率低、發病機制尚不明確,但其對患者的預后影響重大。近年來,隨著診斷及治療方面的逐漸進步,臨床醫生對該病的認識也不斷深入。
1 POPH的流行病學
1951年Mantz 和 Craige[2]報告了第1例尸檢發現的POPH。該病的發病率在不同研究中有所不同,在各種原因引起的肺動脈高壓疾病中占5%~10%[3],在門靜脈高壓患者中的發病率為1%~2%[4]。美國數據[5]表明在肝移植患者中POPH的發病率可增加至5%~8%。我國最新的流行病學數據[6]提示POPH患者占全部肝移植患者的6.3%,與前述范圍一致。POPH常發生在診斷為門靜脈高壓后的4~7年,且門靜脈高壓及肝硬化的嚴重程度與POPH的發生率之間無明顯相關性[7-8],但與POPH患者的預后相關[9],女性、自身免疫性肝病為該病的危險因素,丙型肝炎為其保護因素[7],脾臟切除術也可能為POPH的危險因素[10]。
2 POPH的發病機制與病理改變
由于POPH的低發生率及目前尚無相關動物模型,POPH的發生機制尚不清楚。目前研究的主要發病機制有以下幾種:(1)高動力循環狀態。晚期肝病患者血管張力失調,內臟血管舒張,總外周阻力降低,血壓降低,心臟通過增加心排出量進行代償,內臟動脈血管擴張引起的高動力循環狀態和全身阻力降低是門靜脈高壓癥的特征。隨著肺動脈血流的持續增加,肺動脈床所受的剪切應力增加,造成肺血管內皮損傷,進一步促進原位血栓形成及血管內皮細胞的增殖,使肺動脈壓力進行性升高[11]。(2)血管活性物質失調。門靜脈壓力升高及側支血管的生成使得正常情況下由肝臟代謝的血管活性物質未經肝臟處理直接隨體循環進入肺循環,導致血管活性物質失調,如血管內皮素1、IL-1、IL-6、血栓素等血管收縮因子上調,而一氧化氮、前列環素等血管舒張因子減少,縮血管物質同時參加血管增殖過程[12],使肺部血管發生重構、收縮,肺動脈壓力進行性升高。嚴重的自發性門體分流明顯與中重度POPH相關,且對治療無反應[13-14],這些研究也進一步說明內臟循環的血管活性因子可能是POPH發展的致病因素。(3)遺傳易感性。在門靜脈高壓患者中,并不是所有患者均發生POPH,故認為該病存在一定程度的遺傳易感性。有研究[15-16]表明,遺傳性肺動脈高壓患者骨形態發生蛋白(bone morphogenetic protein, BMP)9及其受體和下游效應物存在功能缺失突變,在此基礎上Nikolic等[17]發現POPH患者血漿BMP9較其他原因的肺動脈高壓患者明顯減低,因此,BMP9信號通路獲得性缺失可能也參與POPH的發病。針對POPH患者進行基因分析的結果[18]顯示ENG基因突變頻率最大,進一步證實遺傳因素在POPH的發展中起到重要作用,但很多遺傳因素需要進一步在POPH患者中得以證實以便應用于臨床,盡早篩查出易患人群加以防護,提高生存率。(4)免疫機制、雌激素及氧化應激:目前已發現POPH患者自然殺傷細胞功能減弱[19],有學者[20]認為POPH可能是一種后天獲得的自然殺傷細胞介導的免疫缺陷疾病,而病毒感染可能是導致肺動脈高壓的重要原因。POPH患者在雌激素信號通路和雌二醇含量方面存在更高的基因變異,同時女性是POPH的危險因素,以上兩者均表明雌激素在疾病的發病機制中起重要作用,針對雌激素信號傳遞及血清雌二醇水平與POPH之間的聯系為當下的研究熱點。另外,有研究[21]表明潛在POPH患者氧化應激程度升高,抗氧化系統失調,平衡氧化應激可能是預防POPH進展的治療靶點。以上各方面的發病機制為POPH患者帶來了新的治療靶點。
POPH在病理上與特發性肺動脈高壓相似,均表現為內膜增生,間質肥大,纖維化和原位血栓的形成,這些病理變化導致肺血管阻力增加,肺動脈壓力升高,部分POPH患者同時存在肺內分流,該因素使POPH患者生存率進一步降低[22]。
3 POPH的臨床表現
POPH患者臨床表現多無特異性,早期常無特殊癥狀,由于多數患者仍為肝硬化基礎上發展為POPH,故常以肝硬化癥狀為主,逐漸出現疲乏、水腫及呼吸困難,呼吸困難逐漸由勞力性呼吸困難發展為靜息性呼吸困難,同時需要排除大量腹水、肺部感染、胸腔積液等繼發因素所致。不到1/3的患者可出現胸痛、暈厥癥狀,體征上可表現為肝硬化體征,如肝掌、蜘蛛痣及右心室肥大體征(如第二心音亢進、三尖瓣區舒張期雜音)等,晚期患者可出現右心衰竭癥狀及體征,如肝頸靜脈回流征陽性等。
4 POPH的診斷及鑒別診斷
根據最新的肺動脈高壓的定義,POPH的診斷標準[23]為:(1)門靜脈高壓的臨床診斷(伴或不伴慢性肝病);(2)右心導管檢查測量滿足以下標準:平均肺動脈壓力升高(mean pulmonary artery pressure, mPAP)>20 mm Hg (1 mm Hg=0.133 kPa);肺血管阻力增高(pulmonary vascular resistance, PVR)>240 dyn·s·cm-5(=3 Wood Units);肺毛細血管楔壓<15 mm Hg。根據平均肺動脈壓力可將POPH進行分級:輕度(20 mm Hg≤mPAP≤35 mm Hg)、中度(36 mm Hg≤mPAP≤45 mm Hg)、重度(mPAP>45 mm Hg)。在常規檢查中POPH表現無特異性,在胸片上可顯示心影增大伴肺動脈主干增寬。心電圖顯示電軸右偏、右束支傳導阻滯及V1~V4導聯的T波倒置。動脈血氣可顯示輕度至中度低氧血癥及低碳酸血癥,這與肺泡-動脈氧梯度升高有關,且研究[24]表明門靜脈高壓患者動脈血CO2分壓<30 mm Hg,提示存在肺動脈高壓。
目前,經胸超聲心動圖常作為篩查肝硬化或門靜脈高壓患者中是否存在肺動脈高壓的有效工具,利用超聲心動圖提示的三尖瓣反流峰值速度可計算出右心室收縮壓。Colle等[25]發現采用肺動脈壓力<38 mm Hg作為排除POPH患者的截斷值會更準確,其最大特異度為82%,同時保證了100%的靈敏度和陰性預測值,若合并右心室擴張,這個新的截斷值的特異度甚至增加到93%,但POPH診斷的金標準仍為右心導管檢查,由其有創性及肝硬化患者的凝血功能下降使得右心導管檢查不能大規模開展并作為篩查工具,目前公認以心臟彩超篩查肺動脈壓力≥50 mm Hg的患者需要進一步行右心導管檢查來確診[26]。為了減少POPH患者的有創操作需要進一步尋找具有診斷意義的指標,最近研究[27]發現POPH患者巨噬細胞移動抑制因子(macrophage migration inhibitory factor, MIF)升高,MIF>60 ng/ml或三尖瓣返流梯度>50 mm Hg對POPH的診斷具有92%的靈敏度和特異度,陽性預測值為86%,陰性預測值為96%,因此MIF是一種有前途的新型生物標志物,可以在肝病和門靜脈高壓癥患者中預測POPH的存在及其嚴重程度。如上所述POPH患者的BMP9水平明顯低于其他肺動脈高壓患者,當BMP9的血漿濃度<132 pg/ml時,BMP9水平對識別POPH具有較高的靈敏度及特異度[17],可將其視為POPH的標志物,是無移植生存的獨立預測因子。外源性BMP9在幾種肺動脈高壓動物模型中被發現可以減輕肺動脈高壓、血管重塑和右心室肥大[28],但尚未在人體進行相關研究。以上2種生物標志物有待在前瞻性研究中進一步證實,以便于通過無創方法鑒別出肝硬化或門靜脈高壓患者中的POPH患者。
需要與POPH相鑒別的疾病為肝肺綜合征(hepatopulmonary syndrome, HPS),兩者最大的鑒別點為HPS表現為肺部血管的擴張,故當懷疑為HPS時可行發泡試驗進一步鑒別,其原理為振動生理鹽水可產生60~90 μm的微泡,外周靜脈注射直徑>25 μm的微泡在正常情況下不能通過肺泡毛細血管(直徑8~15 μm)到達左心,若右心房出現微泡后,左心房在3個心動周期內出現微泡提示心內右向左分流;4~6個心動周期后左心房微泡延遲出現提示肺內血管擴張即HPS的出現,若陰性可基本除外HPS[29]。在POPH患者中由于肺動脈直徑減小,微泡常常不能出現在左心房內,由此進行兩者的鑒別。
5 POPH的治療
POPH患者的治療目標為減輕癥狀,促進肝移植及改善預后。目前對于POPH的治療有多種,可根據患者實際情況選擇。一些非特異性治療目前已不推薦使用,具體原因如下:(1)β受體拮抗劑增加患者惡性心律失常的風險同時降低患者運動能力;(2)抗凝劑增加肝硬化患者出血的風險;(3)鈣離子通道拮抗劑增加患者門靜脈高壓及腹水的風險。TIPS手術治療因臨床療效不確切及增加患者肝硬化并發癥相關風險而不建議在POPH患者中使用。目前POPH患者的治療主要依靠肺動脈高壓的特異性治療,主要包括以下幾種。
5.1 前列環素及其類似物 前列環素是一種強效的肺和全身血管擴張劑,還具有抗血小板聚集及抗增殖的作用。近期研究[30]表明早期應用腸外前列環素治療可提高患者5年生存率并改善POPH患者的肺動脈壓力、肺血管阻力及心輸出量,其不良反應包括血小板減少、脾功能亢進和全身性低血壓。該藥物還有吸入型制劑伊洛前列素及口服的前列環素類似物曲前列尼爾,其副作用與前列環素一致。賽樂西帕是一種口服前列環素受體激動劑,可提高肺動脈高壓患者的無事件生存率[31],但該研究中未包含POPH患者,也沒有肝毒性的報告,故該藥物在POPH患者的效用及副作用尚待進一步觀察。
5.2 內皮素受體拮抗劑 內皮素1是一種血管收縮劑和平滑肌有絲分裂原,有助于肺動脈高壓的發展,內皮素有2種受體,與內皮素A受體結合會產生血管收縮及血管增殖的作用,與內皮素受體B結合會產生舒張血管的作用,阻斷內皮素受體可有效緩解肺動脈高壓。對于內皮素受體拮抗劑,有不同的口服治療選擇。波生坦是一種口服雙效非選擇性受體拮抗劑,能顯著改善肺動脈高壓患者的血流動力學及運動耐受性,但波生坦存在肝毒性[32],故患者在應用該藥物時需要密切監測肝功能。安立生坦是一種高選擇性的內皮素A受體拮抗劑,其優點為單用安立生坦治療可顯著改善肺動脈壓力和肺血管阻力,且對肝功能無不良影響[33]。馬西替坦是一種新型雙重內皮素受體拮抗劑,在POPH患者中進行了三期臨床試驗,證明該藥物顯著改善了患者的肺血管阻力,且對肝功能沒有影響[34],其主要不良反應為貧血、鼻咽炎及頭痛[35]。
5.3 磷酸二酯酶5抑制劑 磷酸二酯酶5抑制劑通過阻止平滑肌細胞中環狀鳥苷一磷酸的降解,提高了一氧化氮含量,一氧化氮是一種有效的血管擴張劑。本類型包括口服制劑西地那非、他達那非和伐地那非,該藥改善POPH患者的血流動力學及WHO功能分級[36],其作用溫和,與上述兩類藥物聯合使用均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和療效。不良反應主要與其擴血管作用相關,如頭痛、顏面潮紅等。也有研究[37]表明單靠磷酸二酯酶5抑制劑治療可能是不夠的,在嚴重POPH患者中,聯合治療能增強血管擴張和抗增殖能力。
5.4 可溶性鳥苷酸環化酶的刺激劑 利奧西呱是一種新型的口服制劑,通過增強一氧化氮的活性而降低肺動脈壓力[38]。在PATENT-1及后續2年的PATENT-2研究[39]中發現利奧西呱安全性高且該藥物有效的改善了患者的運動能力,由于藥物代謝慢會造成藥物的蓄積,故在嚴重肝損傷(Child-Paugh C級)患者中仍不建議使用,其不良反應主要為低血壓。在肝硬化大鼠模型[40]中,利奧西呱顯著降低了門靜脈壓力并延緩肝纖維化,但這一效應尚未在人類身上得到證實,需要在以后的前瞻性實驗進一步證實。以上幾類藥物的的研究往往不包含POPH患者,但小系列的POPH病例研究及相關的病例報道[41]已證明前列環素類、內皮素受體拮抗劑及磷酸二酯酶5抑制劑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5.5 聯合治療 在相關病例報道及研究[42]中均證實以上幾種藥物的聯合使用優于單藥,尤其在嚴重的POPH患者中,但具體聯合方案及原則尚不明確,有待在臨床中逐步積累經驗。
5.6 肝移植 肝移植是終末期肝病的最佳選擇,但中至重度POPH的存在使肝移植的風險顯著增加。POPH患者的死因主要為右心衰及肝病并發癥,肝移植時有多種潛在問題可導致急性右心衰,包括前負荷增加、血栓栓塞、細胞因子顯著釋放等,這些都會對已經受損的右心室造成嚴重損害,導致術中或術后急性右心衰而死亡。隨著肺動脈高壓靶向治療的發展,在肝移植術前積極控制肺動脈壓力,使越來越多的POPH患者可以安全地進行肝移植。2016年發表的國際肝臟移植學會實踐指南的最新共識聲明指出mPAP<35 mm Hg且PVR正常的患者不一定需要治療,尤其是無癥狀、右心房壓力和心輸出量正常的患者,如果mPAP升高,應啟動靶向肺動脈高壓治療,中度POPH患者經肺動脈高壓特異性治療優化肺血流動力學后可行肝移植治療,臨床療效良好。嚴重POPH(mPAP>45 mm Hg沒有或盡管進行了肺動脈高壓治療)患者是肝移植的絕對禁忌癥[43]。術前控制肺動脈壓力至關重要,在肝移植等候期間建議至少每3個月復查心臟彩超評估肺動脈壓力,亞臨床高三尖瓣反流壓力梯度是預測肝移植后生存惡化的重要指標[44]。肝移植術后血管活性藥物聯合治療POPH可使術后心血管相關病死率降低并使大多數患者肺動脈高壓正常化,是肝移植術后肺動脈高壓正常化的唯一預后因素[45],部分患者在肝移植后可停用肺動脈高壓靶向藥物而肺動脈壓力恢復正常,部分患者肝移植后仍需繼續口服藥物,停藥時間無明確截斷點。患有嚴重POPH和終末期肝病的患者可考慮聯合肺移植和肝移植,盡管這種手術稀少,來自德國的一個病例系列[46]報告了13例肺移植和肝移植患者中5例為POPH,1、3、5年生存率分別為69%、62%、49%。
6 POPH的預后
POPH患者的預后在未接受治療時生存率低,自診斷起平均生存期約15個月[47]。法國注冊中心對154例POPH患者進行回顧性分析[48],結果顯示,POPH患者的1、3、5年生存率分別為88%、75%、68%。也有研究[49]相繼報道POPH患者較家族性或特發性肺動脈高壓患者死亡風險高出3倍,并且POPH患者的2、5年生存率比特發性肺動脈高壓患者差[50],回歸分析提示POPH是死亡的獨立危險因素,但隨著肺動脈高壓靶向治療藥物的發展及肝移植技術的成熟,接受治療的POPH患者生存率較前大幅度提高。Swanson等[51]研究提示無治療干預的POPH患者5年生存率為14.2%,單純藥物治療組45.3%,單純肝移植組25.4%,藥物治療聯合肝移植組67%,故仍應加強POPH患者的聯合治療從而提高患者的生存率。
7 展望
由于POPH的相關動物模型較難誘發,故該病的發病機制研究尚不全面,許多研究結論需要大樣本的前瞻性研究進一步證實,以期待發現更多的發病機制及治療靶點。目前仍需要進一步尋找更有臨床意義的POPH診斷標志物來避免患者診斷的有創性。采用肺動脈高壓靶向治療和(或)肝移植聯合治療,可以達到POPH的穩定或可逆性,隨著肺動脈高壓治療的改善,可能需要考慮單獨使用肝移植治療POPH的適應證,特別是對于那些對治療有反應且沒有其他肝移植適應證的患者,進一步探索不同的治療途徑和POPH表型可能是未來研究的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