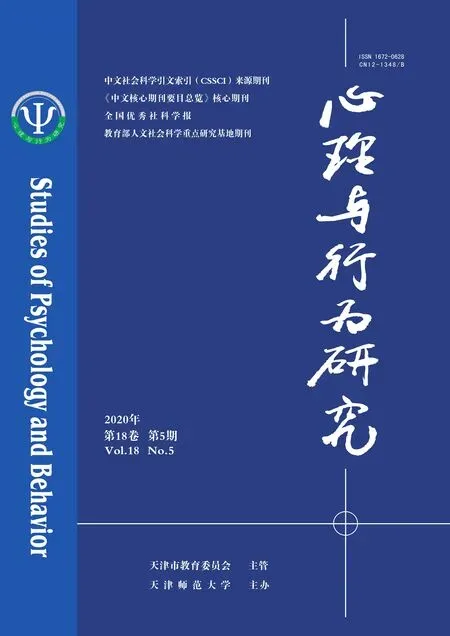中文詞匯加工過程中的無關言語效應 *
俞錦旺 孟 珠 秦 釗 鄧志洲 趙紹晨 閆國利1,,3
(1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 學重點研究基地天 津師范大學心理與 行為研究院,天津 300387) (2 天津師范大學心 理學部,天津300387) (3 學生心理發展與 學習天津市高校社 會科學實驗室,天 津 300387) (4 廣 東機電職業技術學 院汽車學院,廣州510515) (5 廣東財 經大學應用心理學 系,廣州 510320) (6 中國人 民警察大學基礎部,廣州 510663)
1 引言
在完成視覺認知加工任務時,同時呈現但要求被試盡量忽略的言語聲音會顯著降低當前加工任務的成績,這種現象稱為無關言語效應(Colle &Welsh, 1976)。在閱讀研究中,無關言語效應的機制主要存在語音干擾假說和語義干擾假說兩種不同的觀點。語音干擾假說基于Baddeley 和Hitch(1994)的工作記憶模型。該理論認為,工作記憶中的語音環是無關言語效應產生的關鍵。在閱讀中,無關言語自動進入語音環的語音存儲裝置,與閱讀過程中由視覺信息轉換成的語音信息發生混淆,從而干擾視覺信息的存儲和提取。語音環專門用于處理語音信息,非言語的聽覺信息不會進入,因此,在閱讀過程中,言語聲音會進入語音環產生干擾,非言語的聲音則被過濾掉,不會產生干擾(Salamé & Baddeley, 1987)。語音干擾假說在短時記憶的研究中得到了支持(Hanley &Bakopoulou, 2003; Salamé & Baddeley, 1982, 1986,1987; Schendel, 2006)。然而,Martin,Wogalter 和Forlano(1988)在閱讀研究中發現,有意義言語對閱讀理解的干擾顯著大于無意義言語,而無意義言語和白噪音沒有顯著差異。結果并不支持語音干擾假說。該研究提出了語義干擾假說,認為閱讀理解過程中對無關言語語義的自動加工會干擾對文本語義信息的提取,從而影響讀者對文本語義表征的建構(Vasilev, Kirkby, & Angele, 2018)。因此,語義干擾假說強調語義的重要性,有語義的無關言語才會干擾閱讀。
語義干擾假說得到了后續大量閱讀研究的支持。Venetjoki,Kaarlela-Tuomaala,Keskinen 和Hongisto(2006)對比了正常言語、模糊言語(不能識別語義內容)和連續噪音對閱讀的影響,結果發現,正常言語條件下被試校對閱讀的成績顯著更低。Oswald,Tremblay 和Jones(2000)則發現自然言語對閱讀理解的干擾顯著大于倒播言語的干擾。最近的研究則進一步揭示了無關言語的語義對閱讀加工過程的影響。Yan,Meng,Liu,He 和Paterson(2018)采用眼動追蹤技術,比較了有意義言語和無意義言語對被試閱讀過程的影響,結果發現,有意義言語顯著降低了被試的閱讀速率,產生了更多的注視和回視。Vasilev,Liversedge,Rowan,Kirkby 和Angele(2019)的研究也有類似的發現。
在閱讀過程中,詞匯識別是句法分析與語義整合的前提。盡管很多研究探討了無關言語對句子或篇章閱讀的影響(何立媛, 黃有玉, 王夢軒, 孟珠, 閆國利, 2015; 閆國利, 孟珠, 2018; Hy?n? &Ekholm, 2016; Martin et al., 1988; Oswald et al., 2000;Vasilev et al., 2019; Yan et al., 2018),但研究者對于單獨的詞匯加工任務中的無關言語效應還知之甚少。與句子閱讀中的詞匯識別不同,單獨的詞匯識別任務不會受到句法、語境及相鄰文本信息的影響,對語義信息的需要可能很少(張必隱, 1992)。有研究表明,無關言語效應受到視覺加工任務要求的調節(閆國利, 孟珠, 2018; Marsh, Hughes, &Jones, 2019)。Marsh 等發現,在詞匯的短時記憶任務中,當被試按語義類別回憶詞匯(強調語義加工)時,有意義言語的干擾顯著大于無意義言語,但是當被試按詞匯呈現順序進行回憶(強調順序記憶)時,兩者的干擾沒有顯著差異。閆國利和孟珠研究發現,無關言語的語義僅干擾了自然閱讀,對側重于檢測字詞拼寫錯誤的校對閱讀則沒有顯著干擾。基于單獨的詞匯識別與句子中的詞匯識別存在加工差異—前者較少依賴語義信息(張必隱, 1992),后者受到句法、語境及相鄰文本信息的影響,因此無關言語是否會影響詞匯水平的任務,以及特點如何,并不能以句子和語篇閱讀研究的結論來直接推論。將無關言語效應的研究拓展到單獨的詞匯水平任務中有著重要意義。探討無關言語對詞匯水平加工任務的影響既拓展了無關言語效應的研究領域,也為解決閱讀任務中無關言語效應作用機制的理論爭議提供了新的證據和視角。
為考察詞匯加工任務中的無關言語效應,并進一步探討是無關言語的語義還是語音干擾了詞匯識別,本研究比較了有意義言語(含語音、語義和噪音成分)、無意義言語(含語音和噪音成分)、白噪音和安靜環境對被試進行詞匯判斷的影響。根據語音干擾假說,只要是語音就會產生無關言語效應,因此有、無意義言語均會干擾詞匯識別,且兩種條件沒有顯著差異。而根據語義干擾理論,是語義而非語音在無關言語效應中起關鍵作用,因此,僅有意義言語能夠干擾詞匯識別,而無意義言語與白噪音相比不會有顯著差異。
本項研究包括兩個實驗。實驗1 采用真假詞判斷任務,除了控制背景聲音外,還操縱了詞匯的具體性,將詞匯材料分為具體詞和抽象詞。具體性效應的研究發現,相對于抽象詞(如“真理”),對具體詞(如“香蕉”)進行真假詞判斷的反應時和錯誤率顯著更低(即具體性效應),這與兩者的語義加工難度差異有關(陳寶國, 彭聃齡, 1998),其中抽象詞的語義加工難度更大。根據語義干擾理論,無關言語效應源于無關言語的語義干擾了閱讀中的語義提取。鑒于抽象詞的語義提取難度更大,因此,本實驗預測無關言語會顯著降低詞匯判斷成績,且有意義言語對語義提取難度更大的抽象詞判斷的影響將更顯著。實驗2 則采用語義范疇判斷任務,在與實驗1 相同的背景聲音條件下進一步考察詞匯加工的情況。與真假詞判斷不同,語義范疇判斷必須是在提取語義的基礎上完成的,這對于考察語義的作用可以提供最直接的證據。實驗2 要求被試對詞匯是否屬于動作語義范疇做出判斷(陳寶國, 尤文平, 周會霞,2007),如果被試在無關言語條件下的詞匯加工成績顯著低于安靜和白噪音條件,則說明存在無關言語效應。進一步而言,如果有意義言語下的成績顯著低于無意義言語,則說明語義在無關言語效應中起關鍵作用,支持語義干擾假說。如果有意義言語與無意義言語條件下的成績沒有顯著差異,則說明語音是產生干擾的關鍵,支持語音干擾假說。
2 實驗1:無關言語對真假詞判斷任務的影響
采用真假詞判斷任務,考察被試在有意義言語、無意義言語、白噪音和安靜的背景聲音條件下詞匯判斷的成績差異。
2.1 研究方法
2.1.1 被試
18~25 歲的大學生44 名(男生18 名,女生26 名),皆為漢語母語者,未接觸過維吾爾語,視力、聽力正常,實驗后獲得一定報酬。
2.1.2 實驗設計
采用4(背景聲音:有意義言語、無意義言語、白噪音、安靜)×2(詞類:具體詞、抽象詞)重復測量設計。實驗以正確率和反應時為因變量。
2.1.3 實驗材料
詞匯材料。從基于中國電視電影旁白的漢語詞匯和筆畫頻率語料庫中選擇了具體詞和抽象詞各150 個。將合計300 個雙字詞隨機排列編制成評定問卷。請16 名大學生對詞的具體性進行7 點量表的主觀評定,其中1 代表“極其抽象”,7 代表“極其具體”,1~7 的變化代表詞語具體性的增強。根據評定,選出了抽象詞和具體詞各80 個。入選的160 個雙字詞的相關信息見表1。

表1 實驗1 雙字詞材料的參數(M±SD)
經檢驗,具體詞和抽象詞在具體性評分上差異顯著(p<0.001),在詞頻、首字筆畫數、尾字筆畫數等因素上兩類詞差異不顯著(ps>0.05)。
干擾詞是由真字構成的假詞,為了消除假詞的筆畫數可能帶來的影響,從選定的詞匯中將首字和尾字隨機組合成160 個假詞(如“香理”)。160 個真詞和160 個假詞,再加上40 個填充詞共同組成實驗材料,材料分成四組,每組90 個詞,在實驗中分別對應四種背景聲音條件中的一種。實驗時,組間的詞語固定,組內詞語隨機呈現,被試需接受所有的詞匯材料。
聲音材料。一段普通話的敘事錄音作為有意義言語材料。將該錄音轉換成維吾爾語版本,作為無意義言語材料。兩段錄音由同一名女大學生以相同語速朗讀錄制,時長均約12 分鐘。再選擇一段相同時長的白噪音作對照(Martin et al., 1988)。四種背景聲音條件的呈現順序進行了拉丁方平衡,被試隨機分成四組,每組接受其中一種背景聲音播放順序,言語背景音和白噪音的播放音量約為75 分貝,安靜條件下的背景音的音量約為45 分貝。
2.1.4 程序
實驗程序使用E-prime1.0 編程完成,在隔音實驗室運行,被試先閱讀指導語,明白實驗程序后,戴上耳機進入練習。實驗開始時,屏幕中央呈現紅色“+”號注視點,800 毫秒后注視點消失,接著呈現刺激,被試對呈現的詞進行真假詞判斷。如果是真詞,迅速按“F”鍵反應,如果是假詞,則按“J”鍵反應。被試做出反應后空屏600 毫秒,再進入下一個試次。實驗過程中要求被試盡量忽略耳機中呈現的聲音,每個背景聲音條件下的任務完成后,提示被試休息兩分鐘后繼續。
2.2 結果
2 名被試的數據因背景聲音播放故障而被刪除,剩下42 名有效被試。有效被試數據中,大于或小于3 個標準差的極端值被刪除,占有效被試數據的1.6%。剩下的數據進入分析。
2.2.1 正確率
被試在四種背景聲音條件下的反應正確率如表2 所示。

表2 實驗1 四種背景聲音條件下的反應正確率(M±SD)
重復測量方差分析顯示,詞匯具體性差異顯著,F(1, 41)=61.94,p<0.001,η。被試對具體詞的反應正確率(M=0.98,SD=0.01)顯著高于抽象詞(M=0.95,SD=0.03)。背景聲音條件的主效應不顯著,F(3, 123)=1.88,p=0.13。詞匯具體性和背景聲音交互作用不顯著,F(3, 123)<1。
2.2.2 反應時
被試在四種背景聲音條件下的反應時如表3所示。

表3 實驗1 四種背景聲音條件下的反應時(ms)(M±SD)
重復測量的方差分析顯示,詞匯具體性主效應顯著,F(1, 41)=46.56,p<0.001,η=0.53,被試對具體詞的反應時(M=564ms,SD=49ms)比抽象詞的反應時(M=593ms,SD=60ms)顯著更短。背景聲音的主效應不顯著,F(3, 123)=2.13,p=0.09。詞匯具體性與背景聲音的交互作用顯著,F(3, 123)=6.68,p<0.001,η=0.14。簡單效應分析顯示,對具體詞來說,被試在4 種背景聲音條件下的差異均不顯著,Fs<1;但是對抽象詞來說,背景聲音的效應顯著,F(3, 39)=3.29,p<0.05。兩兩比較發現,有意義言語條件下的反應時顯著長于安靜條件下的反應時,t(41)=2.93,p<0.05,也長于白噪音條件下的反應時,t(41)=2.88,p<0.05,其余各條件下的反應時之間則沒有顯著差異,ps>0.05。
實驗1 發現,有意義言語條件下被試對抽象詞的反應時顯著長于安靜和白噪音條件,而在無意義言語、白噪音和安靜條件下,被試對抽象詞判斷的反應時沒有顯著差異,說明語義干擾了抽象詞的詞匯加工,中文詞匯加工過程中存在無關言語效應。但是,被試對具體詞的加工在各背景聲音條件下沒有顯著差異。這可能與真假詞判斷任務語義加工程度較小有關。實驗2 選擇更強調語義加工的語義范疇判斷任務做進一步的探討。
3 實驗2:無關言語對語義范疇判斷任務的影響
3.1 研究方法
采用語義范疇判斷任務考察被試在有意義言語、無意義言語、白噪音和安靜條件下的詞匯加工任務成績的差異。
3.1.1 被試
18~25 歲的大學生48 名(男生20 名,女生28 名),皆為漢語母語者,未接觸過維吾爾語,視力、聽力正常,實驗后獲得一定報酬。
3.1.2 實驗設計
采用單因素(背景聲音:有意義言語、無意義言語、白噪音、安靜)重復測量設計,以正確率和反應時為因變量。
3.1.3 實驗材料
詞匯材料。從基于中國電視電影旁白的漢語詞匯和筆畫頻率語料庫中選擇“動作”范疇的雙字詞(如“揮舞”)和非“動作”范疇的雙字詞(如“信息”)各120 個,將合計240 個詞分成四個組,每組60 個詞,其中一半是屬于動作范疇的詞,另一半是不屬于動作范疇的詞。匹配了這些詞的詞頻、首字筆畫數、尾字筆畫數以及各組屬于動作范疇的詞匯的典型性,其具體做法是讓30 名被試對含有120 個表示動作語義的合計180 個雙字詞進行范疇成員典型性評定。采用7 點量表,其中1 代表“完全不屬于動作的語義范疇”,7 代表“非常典型地屬于動作的語義范疇”。1~7 表示屬于動作范疇的語義程度依次遞增。方差分析顯示,各組材料的詞頻、首字筆畫數和尾字筆畫數、動作詞典型性之間都沒有顯著差異(ps>0.05),如表4 所示。

表4 實驗2 四組詞匯材料的參數(M±SD)
3.1.4 程序
實驗使用E-prime1.0 編程,在隔音實驗室運行。被試先閱讀指導語,然后戴上耳機進入練習。實驗開始時,屏幕中央呈現紅色“+”號注視點,注視點消失后,立即呈現一個詞語,被試判斷詞語是否表示“動作”范疇,如果是則按“F”鍵反應,否則按“J”鍵反應。實驗過程中,要求被試盡量忽略耳機中呈現的聲音。實驗分為4 個區間,每個區間對應一種背景聲音條件,每種背景聲音條件下呈現一組詞匯,每組的詞匯材料是固定的,但是組內的詞匯材料隨機呈現。每個區間完成后,被試休息兩分鐘。為避免對實驗結果造成影響,各背景聲音的呈現順序在被試之間進行了平衡。
3.2 結果
4 名被試沒有按要求認真完成實驗任務,其數據被刪除。剩下44 名有效被試,有效被試的數據中,大于或小于3 個標準差的極端值被刪除,占有效被試數據的4.9%。剩下的數據進入分析。
結果如表5 所示。

表5 實驗2 四種背景聲音條件下的反應時和正確率(M±SD)
單因素重復測量的方差分析顯示,在正確率上,背景聲音的主效應不顯著,F(3, 129)=1.32,p=0.80,各背景聲音條件下的正確率沒有顯著差異。在反應時上,背景聲音條件主效應顯著,F(3,129)=9.49,p<0.001,η2=0.18。事后檢驗發現,安靜條件下被試的反應時顯著短于白噪音(p<0.05)、無意義言語(p<0.01)以及有意義言語(p<0.01)條件下的反應時。有意義言語條件下的反應時顯著長于白噪音條件(p<0.01),也顯著長于無意義言語條件(p<0.01)。但是,白噪音和無意義言語條件下的反應時沒有顯著差異(p=0.36)。
實驗2 結果表明,背景聲音干擾了詞匯加工,且有意義言語產生的干擾顯著大于無意義言語和白噪音,而無意義言語和白噪音的影響沒有顯著差異,說明在強調語義加工的任務要求下,在無關言語效應中起到干擾作用的主要是言語的語義成分。
4 總討論
4.1 中文詞匯加工過程中存在無關言語效應
本研究采用真假詞判斷任務和語義范疇判斷任務,在詞匯水平的任務上考察詞匯加工過程中的無關言語效應,排除了語境和句法信息的影響。在實驗1 中,被試在有意義言語條件下對抽象詞做真假詞判斷的反應時顯著長于白噪音和安靜條件。實驗2 進一步采用了必須通達語義才能做出正確判斷的語義范疇判斷任務,結果發現有意義言語顯著干擾了詞匯通達,在有意義言語條件下,被試的反應時顯著長于其他背景聲音條件。兩個實驗的結果說明,無關言語干擾了詞匯加工,中文詞匯加工過程中存在無關言語效應。值得一提的是,在句子閱讀或篇章閱讀的研究中,對于無關言語是否會影響詞匯通達這一問題,目前存在著爭議。Vasilev 等(2019)在句子閱讀中發現背景言語與詞頻在首次注視時間、凝視時間等指標上交互作用不顯著,指出言語并不影響句子閱讀中的詞匯通達。而何立媛等(2015)以及Yan 等(2018)的研究則指出,無關言語不僅干擾句子整合還影響了詞匯通達。如前言所述,鑒于單獨的詞匯判斷任務與句子或篇章閱讀任務在加工過程以及復雜程度的不同,本研究并不能為“無關言語是否影響句子閱讀過程中的詞匯通達”這一問題提供實證依據。相關問題還需要進一步探討。
4.2 無關言語的語義特征是詞匯通達中無關言語效應產生的關鍵
無關言語具備語音、語義和句法等成分特征。無關言語效應研究的一個基本問題是,無關言語的哪一種或哪些成分使其對認知任務造成了干擾。語音干擾假說和語義干擾假說爭論的本質即在于此。為區別語音和語義的作用,本研究使用了有意義言語、無意義言語、白噪音和安靜四種背景聲音條件。對被試而言,有意義言語(普通話)是可理解的,具有語義特征,無意義言語(維吾爾語)對被試而言是不具語義特征的。結果顯示,兩個實驗中有意義言語條件下的詞匯加工都受到了顯著干擾。在實驗1 中,僅在有意義言語條件下被試對抽象詞的判斷反應時顯著大于安靜和白噪音條件,其他各條件之間沒有顯著差異。在實驗2 中,被試在有意義言語條件下的反應時顯著大于其他三種背景聲音條件,而無意義言語與白噪音條件下沒有顯著差異。根據語音干擾假說的觀點,無關言語效應是源于言語自動進入到工作記憶中語音環的語音存儲裝置,與視覺輸入的信息發生混淆而產生的,只要是言語,不管是否具有語義都可以進入語音存儲裝置從而干擾認知任務。然而,在本研究的兩個實驗中,無意義言語與白噪音條件下的反應時和正確率均無顯著差異,說明無意義的語音并沒有產生顯著干擾,這并不支持語音干擾的觀點。相反,在兩個實驗中,有意義言語均造成了顯著大于白噪音的干擾,說明語義是干擾產生的關鍵因素,研究結果支持語義干擾的觀點。
4.3 無關言語的語義干擾作用受到認知任務中語義加工程度的調節
在實驗1 中,詞匯具體性和背景聲音產生了顯著交互作用。被試在抽象詞上出現了無關言語效應,但是在具體詞上則沒有出現。具體詞和抽象詞存在語義加工難度上的差異,說明語義加工難度調節了語義干擾效應。前人研究表明,沒有語義加工要求的任務不引起語義干擾或只有不明顯的干擾。在采用字母序列或數字序列作為識記材料的短時記憶系列回憶任務中,無關言語的語義并不影響無關言語效應(Baddeley & Salamé,1986; Colle & Welsh, 1976; Ellermeier & Zimmer, 1997;Salamé & Baddeley, 1987)。當研究者采用詞匯作為短時記憶的識記材料時,通過要求被試按照語義類別組織項目回憶時,語義干擾的作用就會出現,但是,如果讓被試對詞匯材料按照呈現時的順序進行系列回憶時,語義干擾的作用也不會出現。研究者認為,雖然加工的刺激都是有語義的詞匯材料,但是與自由回憶或按語義類別回憶不同,系列回憶對語義加工的要求不是必要的(Marsh et al., 2009; Marsh, Perham, S?rqvist, & Jones,2014)。因此,可以理解在實驗1 中出現的背景聲音條件與詞匯具體性的交互作用。具體性效應的研究表明,抽象詞的語義加工難度大于具體詞。在實驗1 中,具體性效應非常顯著,相對抽象詞,被試對具體詞的正確判斷反應時顯著更小。同時,真假詞判斷任務的語義加工難度也較低,被試有時候不一定需要通達語義就可以做出判斷(彭聃齡, 1997)。從而可以推斷,具體詞上未產生語義干擾效應是由于在真假詞判斷任務中,被試對具體詞的語義加工程度較低即可完成詞匯判斷,無關言語語義的自動化加工與視覺材料的語義加工過程沖突較小,因而沒有產生顯著的語義干擾效應。而實驗2 采用的語義范疇判斷任務,其做出判斷必須以通達語義為前提,語義加工的程度更高,因此出現了顯著的語義干擾效應。
5 結論
中文詞匯加工過程中存在無關言語效應,無關言語對詞匯加工產生了顯著的干擾。研究結果支持語義干擾假說,是無關言語的語義而不是語音對詞匯加工過程產生影響。無關言語的語義對詞匯水平任務的影響,受任務要求下語義加工程度的調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