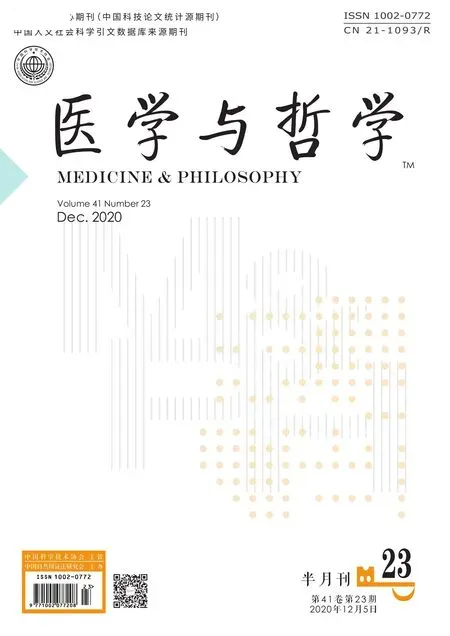感知/親歷醫療暴力醫生的內向和外向反應*
——基于浙江調研數據的分析
王淑紅 孫澤生
我國的醫療暴力發生率多年來一直居高不下[1],新近發生的嚴重傷醫案例也表明醫療暴力尚未得到有效遏制[2]。因我國尚未建立全國性的強制性醫療暴力事件報告系統,因此以已有文獻或依賴于媒體/法院披露的致醫生傷亡案例、判例數據來估計醫療暴力頻度和特征[3-4],或借助調查數據分析醫療暴力發生規律[5-6]。在反醫療暴力法律環境和醫療衛生政策情境下,探討感知/親歷醫療暴力的醫生如何做出自身的內在反應并對職業關聯的法律環境和政策做出外向反應,是治理醫療暴力的重要實證依據。本文將醫療暴力具體區分為身體暴力和語言暴力,并借助自行設計問卷來探討感知和親歷暴力的醫生的內向和外向反應特征,以增加學界對醫療暴力影響的理解。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本研究定義的醫療暴力既包括文獻強調的以推搡、毆打導致身體傷害為指征的身體暴力行為[3-4],也包括以威脅/辱罵為衡量的語言暴力。因醫生的人力資本特定性和職業鎖定[7],本文定義的內向反應主要涉及醫生自身及其家庭的行為反應,其外向反應則是對諸如政府、立法、執法和醫院對醫生安全的保護力度以及衛生政策效果等的評價。按照浙江省衛生資源下沉改革中三級醫院向二級醫院下沉的制度設計,本研究將二級和一級醫院歸類為基層醫院,以與三級醫院相對應。
本研究采用方便抽樣方法,在2018年6月~2019年3月,由經培訓的工作人員向杭州、嘉興、湖州、寧波、麗水和衢州等地共36家醫院的醫生發放調研問卷。所有醫生均對本研究知情同意。最終獲得720份問卷,其中有效問卷671份,有效率為93.19%。利用SPSS 23.0軟件和信度檢驗發現Cronbach's α系數為0.818,表明問卷及調研數據具有很好的內部一致性。
1.2 調查方法
1.2.1 問卷設計
基于5點積分法自行設計問卷。問題項包括:(1)醫療暴力,包括感知所在醫院暴力頻度以及醫生親身經歷的暴力頻度問題項,“從未”“很少”“偶爾”“經常”“頻繁”感知暴力者分別賦分1分~5分;是否親歷醫療暴力的賦值方法為:報告“從未”經歷醫療暴力受訪者賦值為0分,其余為1分。(2)暴力防控,包括醫生對防控流程的認知和所獲得的反醫療暴力培訓。二者雖有關聯,但前者強調醫院層面,后者強調醫生個體層面且不僅限于醫院提供的培訓。對前者,“使用過”“培訓過”賦1分,“聽說過”“不清楚”“不存在”則賦0分;對后者,曾在“學校”“醫院”獲得培訓賦1分,否則為0分。(3)法律環境評價,分別納入政府、立法、執法和所在醫院4個層面對醫生保護力度的評價。其中,政府保護用以評估公權力對醫生安全的總體保護,立法和執法則分別評估成文法和司法機構對醫生的保護力度。賦1分~5分分別對應評價“很低”“較低”“尚可”“較高”和“很高”。(4)衛生政策評價,結合調研地浙江正在實施的分級診療和衛生資源下沉改革,考慮與醫生工作相關且醫生均有所了解的7個方面醫療衛生政策[8]:醫療服務價格、醫保政策、職稱評審、醫學生基層工作激勵、定向生、考核評價以及下沉津補貼政策,賦分標準與法律環境問題項相同。(5)醫生內向反應,包括工作積極性、高風險患者識別意愿以及對子女學醫支持度。其中,工作積極性賦1分~5分表示“無影響”“較小”“中等”“較大”“很大”;1分~5分分別對應患者識別意愿“很低”“較低”“尚可”“較高”和“很高”;對子女學醫支持度賦1分~5分分別對應“上升”“不變”“略有下降”“明顯下降”和“大幅下降”。
1.2.2 統計學方法
使用SPSS 23.0統計學軟件進行統計分析。采用方差分析方法比較不同組別醫生間的醫療暴力認知和反應差異。差異顯著性檢驗水準為α=0.05。
2 結果
2.1 受訪者基本信息
三級醫院和基層醫院醫生所占比重分別為71.39%和28.61%。31歲~40歲年齡段占比43.52%,41歲~50歲和30歲及以下占比分別為29.51%和22.65%。本科學歷醫生占61.25%,碩士學歷醫生占24.89%。中級職稱者占34.43%,副高和正高職稱比例分別為26.23%和9.69%。3年~5年工齡醫生占比最高(41.58%),隨后是新入職2年以內醫生(21.61%)以及工齡6年~10年醫生(20.86%)。
2.2 不同等級醫院醫生的認知和反應
區分醫生對所就職醫院醫療暴力的“感知”和“親歷”,可發現感知身體暴力和語言暴力頻度均值介于2(“很少”)和3(“偶爾”)發生之間[(2.61±0.81)和(2.93±0.91)]。其中,回答所就職醫院身體和語言暴力“從未”發生的比重分別為8.49%和4.92%,回答“偶爾”“經常”“頻繁”的比重合計為59.32%和69.45%。受訪醫生親歷身體暴力和語言暴力的比重分別為45.74%和39.04%,但回答身體暴力“經常”“頻繁”發生的受訪醫生比重達到27.75%。方差分析結果顯示,三級醫院醫生認知的身體和語言暴力發生頻度之均值[(2.78±0.75)和(3.12±0.86)]均大于基層醫院[(2.19±0.80)和(2.46±0.84)],且這一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三級醫院醫生子女學醫支持度(2.78±1.05)和工作積極性(3.07±1.01)均低于基層醫院[(2.88±0.87)和(4.43±1.06)],但高風險患者識別意愿(2.84±1.06)卻高于基層醫院醫生(4.43±1.06),以上結果均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
2.3 親歷/非親歷醫療暴力的醫生認知和反應
親歷身體或語言暴力醫生認知的所在醫院醫療暴力頻度之均值高于未親歷暴力所認知的醫療暴力頻度,且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此外,親歷身體暴力和親歷語言暴力兩個變量間顯示有統計學意義的同向變動關系,即親歷語言暴力的醫生所親歷的身體暴力頻度(2.15±0.90)高于未親歷語言暴力醫生(1.14±0.43),同樣,親歷身體暴力醫生所親歷的語言暴力頻度(2.69±0.82)亦高于未親歷者(1.56±0.75)。見表1。
親歷醫療暴力的影響還反映在醫生的外向反應和內向反應上。首先,親歷語言暴力醫生對政府、立法、執法和醫院保護4個指標的評分均值都低于未親歷語言暴力醫生,且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相對照,親歷身體暴力醫生對除立法保護之外的3個法律環境變量的評分顯著低于未親歷者。其次,親歷語言暴力和身體暴力醫生對衛生政策的評價都要較未親歷者負面(P<0.05)。最后,對醫生內向反應,親歷語言暴力或者身體暴力者均具有顯著較低的子女學醫支持度和工作積極性,但高風險患者識別意愿卻顯著較低。
2.4 醫院暴力防控的組間比較結果
由調研結果可知,對醫院暴力防控流程“使用過”“培訓過”的醫生占比為53.20%(357/671);分別有0.3%(2/671)和48.29%(324/671)的受訪醫生報告其在醫學教育和所在醫院獲得反醫療暴力知識和技能。無論醫生認知醫院暴力防控流程和接受反暴力培訓與否,其醫療暴力頻度認知都不存在統計學意義上的差異,但認知流程和接受培訓者對法律環境和衛生政策評分的均值都較高(P<0.05)。在醫生的內向反應中,認知醫院暴力防控流程和接受反暴力培訓醫生的高風險患者識別意愿顯著較高,但其子女學醫支持度和工作積極性均值也較高(P<0.05)。見表2。

表1 親歷和非親歷醫療暴力醫生認知及反應的比較

表2 醫院防控認知和反暴力培訓對醫生內外向反應的影響
3 討論
本研究發現,三級醫院醫生親歷身體/語言暴力的比重顯著高于基層醫院醫生。先前的聚焦于三級(甲等)醫院醫生的文獻報道了60%左右的醫療暴力發生率[5-6],比本研究的所有醫院暴力發生率高;研究中基層醫院醫療暴力發生率低于三級醫院的結論與文獻報道醫療暴力主要發生在三級醫院結果一致[9]。除親歷之外,醫生群體還基于自身可得信息評估所就職醫院的醫療暴力狀況。方差分析發現,三級醫院醫生感知的醫療暴力發生率與基層醫院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這說明,因三級醫院有更高的診療能力但卻面臨與基層醫院相似的醫療服務價格管制,導致患者傾向于優先選擇三級醫院,使三級醫院擁堵程度更高、診療等待時間更長,患者就診體驗弱于基層醫院,發生醫療暴力的概率亦高于基層醫院。基于媒體報道和法院判例的統計數據支持這一結論[3-4]。
與以上醫療暴力發生率情境相對應,三級醫院醫生的內向反應特征是更低的工作積極性和子女學醫支持度,以及更強的高風險患者識別意愿。其解釋在于,從醫所面臨的要素特定性和職業鎖定使醫生的內向反應空間較窄。首先,為降低醫療暴力風險,需在接診時通過“小心診療”“多做檢查”和“勸說轉院”等識別和應對高風險患者,由此降低了醫療服務可及性、增加了醫療成本[7]。其次,因醫療暴力帶來的從醫效用下降,內向反應還延伸至醫生的家庭成員,使其對子女學醫支持度明顯降低,以實現跨代的職業再選擇,與已有調查結論相符[10-11]。相比較而言,醫生外向反應被證明在不同等級醫院醫生間少有顯著差異,僅在醫療服務價格和(差異化)醫保政策上,基層醫院醫生評分較高,與這兩項政策偏向基層醫院有關。
基于是否親歷暴力進行分組發現,親歷暴力醫生所感知的就職醫院暴力發生率顯著高于未親歷暴力醫生的認知。醫學文獻所稱的應激反應刻畫了親歷醫療暴力后對暴力的過度敏感和信息放大特性[12],以此加總至群體行為后,親歷暴力醫生也放大了所感知的醫療暴力發生率,其與無親歷暴力醫生的差異在身體暴力和語言暴力情境下均具有統計學意義。方差分析還表明,在內向反應上,親歷暴力醫生具有更低的工作積極性和子女學醫支持度,這與前面的討論相似;但有所區別的是,親歷醫療暴力醫生有更低的高風險患者識別意愿,且對身體/語言暴力均具有統計學意義。其解釋是,已發生的暴力反而降低了醫生面臨的不確定性并消極作用于其對患者的選擇行為,但這是以降低工作積極性為代價得到的結果。在外向反應上,親歷語言暴力醫生對包括政府、立法部門、執法部門和醫院在內的反醫療暴力法律環境均給予了顯著更低的評分;親歷身體暴力醫生除在立法保護上與未親歷者無差異外,對其余3個方面法律環境之評分也顯著較低。這表明,已有之遭際說明了法律環境在保護其安全方面的不足,未親歷者則并不知悉這一點。同時,親歷醫療暴力者在幾乎所有醫療衛生改革政策上均給予了有統計學意義的較低評分,說明他們同樣因其遭際而負向評價改革和相關政策。
按照《勞動法》,作為雇主的醫院有法定義務保護作為雇員的醫生的安全。其主要舉措包括醫院暴力防控及對醫生的反醫療暴力培訓。本文發現,獲得反暴力培訓并知悉醫院暴力防控流程的醫生均對反醫療暴力法律環境和衛生政策有更高的評價。因此,醫院方的暴力防控流程構建、落實及對醫生的信息傳遞,以及醫院組織的反醫療暴力培訓具有重要作用。其效果延伸到醫生內向反應的兩個方面:首先,它提高了醫生的工作積極性和子女學醫支持度,接受反醫療暴力教育、了解醫院防控流程醫生的這兩項反應均值顯著高于未了解防控流程和未受培訓醫生的均值。其次,接受反醫療暴力教育、了解醫院防控流程醫生的高風險患者識別意愿雖較高,但它是以工作積極性改善和反醫療暴力技能的提升為支撐,有利于其將風險進行再配置,起到帕累托改善的效果。不過,問卷調研也說明,尚有46.80%的醫生報告醫院暴力防控流程“不存在”“不了解”或者僅“聽說過”,有51.71%的醫生反映其未在醫院接受過反醫療暴力培訓,加之99.70%的受訪醫生未從入職前的醫學高等教育中獲得此類知識/技能,均使得醫生對反醫療暴力法律環境的評分下降。
需說明的是,醫生職業承擔保護公共安全的職責但卻高度暴露于風險中,承受極高的人力資本投資水平但卻面臨要素鎖定,導致醫療暴力會產生遠較普通工作場所暴力更高的社會成本[9,13]。已有醫療暴力案例表明[14],于社會而言醫療暴力會導致嚴重的醫療人力資本損失,于受害醫生而言則帶給他們職業鎖定但又發展受限的心理創傷。本文的研究表明,這一創傷和負面影響還會傳遞給醫生群體,產生更大的社會成本。要治理醫療暴力,作為雇主的醫院方的作用可能只是邊際意義上的、有限的,更根本的舉措既依賴于醫療資源的平衡配置和患者在不同等級醫院間的理性就醫選擇,以大幅降低醫療市場尤其是高等級醫院的擁堵、改善就診體驗、降低暴力發生率[15],也在于考慮醫療暴力之高社會成本后實現優化的刑罰設計和更強的執法力度,使得處于高風險暴露中的醫生群體能匹配于更強有力的法律保護[1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