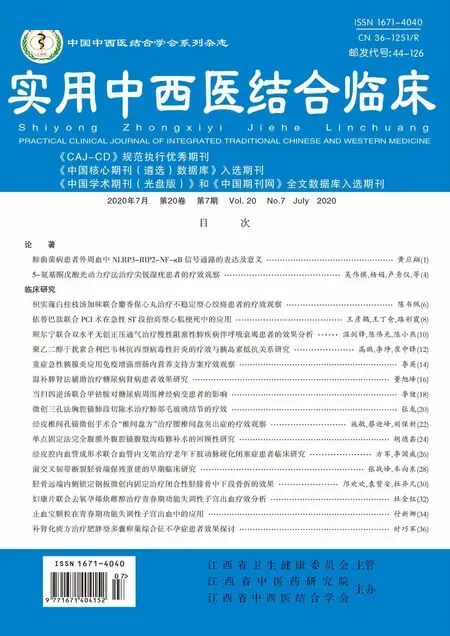探析柴胡疏肝散加減治療乳腺癌的理論淵源*
王利勤 唐曉玲 郭健 武彪 周惠芬 萬海同 王珠 熊墨年#
(1南昌大學第一附屬醫院 江西南昌330006;2江西省中醫藥研究院 南昌330046;3浙江中醫藥大學 杭州310053)
近年來,乳腺癌已成為危害全球女性健康的常見惡性腫瘤之一,而且隨著生活環境及方式的改變,該病的發病率及病死率逐年升高,且乳腺癌已位居我國女性惡性腫瘤發病率之首[1]。 6年前,國家衛計委從年鑒中統計分布結果發現,我國城市中每10萬乳腺癌患者死亡人數達4.25萬, 在農村地區每10萬乳腺癌患者死亡人數達2.83萬。新增乳腺癌患者逐年增加,而且隨著年齡的增長,乳腺癌的發病率升高,城市地區乳腺癌發病率高于農村。 可見乳腺癌對我國乃至全球女性的危害不容小覷。 迄今為止,乳腺癌的治療仍是以手術切除、放療、化療及調節內分泌等方式為主。患者術后生活質量受到嚴重影響,放化療產生的毒副作用,對患者的身體狀況有明顯影響。 臨床實踐表明,中醫藥治療乳腺癌患者從整體出發,辨證論治,可顯著提高療效并減輕毒副作用。 中醫藥治療可以減少乳腺癌的復發率和腫瘤轉移率,提高患者的生存質量,延長患者的生存時間[2~5]。 本文探析柴胡疏肝散加減治療乳腺癌的理論淵源。 現報道如下:
1 乳腺癌的中醫病因病機
乳腺癌,中醫學稱之為“乳巖”。“巖”是指石頭,巖石是堅硬的,難消散的東西,這跟臨床上癌癥的難治有異曲同工之理。 中醫基礎理論指出,乳房與五臟六腑中的肝臟關系密切。 同時在經絡上,“足厥陰肝經上膈, 布胸脅繞乳頭而行”,“女子乳頭屬肝”。從中醫生理學角度出發,我們認為女子以肝為先天,而肝主藏血及疏泄,肝本性為體陰而用陽。 若肝的疏泄功能正常,則人體全身的氣血運行正常,可充滿于沖任之中,進而起到調節乳房的功效。 乳腺癌的發病機制涉及到多種因素,西醫著重從生育史、哺乳史、家族遺傳史及性腺激素等刺激及飲食等方面闡明其病機。中醫學認為,情志內傷可導致各臟腑功能失常,主要由肝功能失調,導致氣血運行紊亂,久則出現氣滯、痰凝及血瘀相互搏結于乳絡, 而成“乳巖”。 正氣虛弱,氣血陰陽不足,臟腑功能減退,邪客于乳絡是引起此病的內因,而風、寒、暑、濕、燥、火六淫外侵,邪毒留于體內,成為主要的外在發病原因。肝主情志,喜條達而惡抑郁,若氣機運行不暢,則可致肝氣郁結,郁久可生結節。 正如朱丹溪在《格致余論》中所說,“憂怒抑郁,昕夕積累,脾氣消阻,肝氣橫逆,遂成隱核……名曰乳巖”。明代醫家陳實功在《外科正宗》 中指出:“憂思郁結, 所愿不遂, 肝脾氣逆……結積成核”,均表明肝郁可能是乳巖的主要病因之一。
2 乳腺癌與肝郁的相關性
2.1 古代醫家對肝郁與乳巖發生關系的認識 古代醫家分別從內科與外科角度分析乳巖的病因病機及診治方法,主要有兩種理論。 一是朱丹溪在《格致余論》中指出:“乳子之母,不知調養,怒忿所遂,郁悶所遏,厚味所釀,以致厥陰之氣不行,故竅不得通,而汁不得出,陽明之血沸騰,故熱甚而化膿”,“所乳之子,膈有滯痰,口氣焮熱,含乳而睡,熱氣所吹,遂生結核”。也就是說,朱丹溪從哺乳期婦女哺乳的特點,以及乳房的經絡分布特點分析乳腺疾病的發生過程。 他認為乳房是人體中陽明經繞行的氣血交匯之地,乳頭屬于厥陰肝經,而哺乳的過程主要是通過乳頭將乳汁排出,若是乳頭出現郁滯不通,導致肝經氣滯,即肝郁氣滯,久而久之可導致乳巖的發生。 同時朱丹溪也認為:“若于始生之際,便能消釋病根,使心清神安,然后施以治法,亦有可安之理”。可見他的觀點是肝屬于風木之臟,喜調達而惡抑郁,若是失于疏泄,則可引起氣運不暢,瘀堵有形之物結于乳絡,久而久之則可發展為乳巖。 在治療上,朱丹溪提出從肝胃治療為主,并給予青皮、枳殼等疏泄足厥陰肝之滯,并用石膏等以清陽明胃經之熱,根據情況加瓜蔞子、夏枯草等以消腫散結,且配生甘草以健脾益氣行肝血之濁。
另一種理論是清代高秉鈞在所著的《瘍科心得集》中提出“夫乳屬陽明,乳中有核,何以不責陽明而責肝。 以陽明胃土最畏肝木,肝氣有所不舒,胃見木之郁,惟恐來克,伏而不揚,氣不敢舒;肝氣不舒,而腫硬之形成;胃氣不敢舒,而畏懼之色觀”。 清代王洪緒在《外科證治全生集》中表明:“初起乳中生一小塊,不痛不癢……此因哀哭憂愁,患難驚恐所致”,“乳巖乃心肝二經,氣火郁結,七情內傷之病”。 清代馬文植在《醫略存真》中指出:“乳巖,乃七情致傷之癥,以憂思郁怒,氣積肝胃而成。 氣滯于經則脈絡不通,血亦隨之凝泣,郁久化火,腫堅掣痛”。 高秉鈞也認為,治肝為治乳腺癌的主要治則,調肝則乳腺腫物也可消散。 由上訴古代醫家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出,早在數百年前古代醫家就已經發現乳腺癌的發病與患者的情志因素有關,在治療上需以疏肝解郁、調暢情志為主。
2.2 現代學者對肝郁與乳腺癌發生的相關性認識乳腺癌發病與情志改變有關,而肝郁又為情志病因中的首位。 現代學者分別從痰飲等方面闡述了乳腺癌與肝郁的相關性。 比如林麗珠和周仲瑛等認為乳腺癌患者多情緒壓抑,導致氣機受阻,肝失調達疏泄,最終可致痰飲內結[6~7]。 從中醫角度出發,痰飲不僅僅屬于病因,也是疾病的病理產物。 人體長期的情緒抑郁會引起氣機失調,脾失健運,運化功能不及,可內生成痰飲,痰飲阻滯于經絡,久可內生癥瘕。同時痰阻氣機,也可使氣機壅塞,全身氣機不暢,變生百病。 可見,痰飲與肝郁相互影響,互為因果,導致乳腺癌的產生。 焦中華等[8]從臟腑病因學研究發現肝郁傷脾是乳腺癌的主要病因,患者多有情志不舒或者憂思傷脾,最終導致肝失疏泄,橫逆犯脾,致脾失健運,不能運化津液,瘀滯致痰濁,而痰濁瘀阻經絡,可聚結成塊而致癌癥。 沖任之脈為人體氣血之海,若是沖任失調,亦可致氣滯血瘀,引起乳腺經絡受阻,變生腫瘤。 雖然乳腺癌的病位僅表現在乳房,但其實它與肝、脾、沖任等其它臟腑經絡也有密不可分的關系。 宋俊蓮等[9]專家則認為,乳腺癌應屬于肝絡之病,肝病日久入絡而傷血分,血分致病有易滯易癖、易入難出、易積成形的特點,久而成積聚,即乳腺癌。 如果時常肝氣失調,導致經絡之氣機不暢,影響人體內微循環的運行, 引起乳腺組織局部的血流不通,致瘀血形成,久則癌腫生成。
中醫情志因素與現代醫學中的社會心理學內容極為相似,情志因素對乳腺癌的發生、發展與預后的影響非同小可,甚至可以說,抑郁或(和)焦慮的情緒可能是乳腺癌發病的重要影響因素。在中醫學中,情志因素屬于三大致病因素中的“不內外因”,“七情致病”是中醫病因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情志致病總病機應當歸于氣機的失常。 正如明代虞摶在《醫學正傳》中指出:“此癥多生于憂郁積忿之中年婦女”。當出現負性情緒,且該情緒存在人體內時間過長,或超出正常生理調節的范圍時,可能會引起機體的氣血失調,導致臟腑氣機失衡而致病。 而肝臟是人體調節情志的主要場所,性喜條達而惡抑郁,若機體長期氣機運行不暢,則可致氣血阻于乳絡,最終發為乳腺癌。
3 柴胡疏肝散治療乳腺癌的理論基礎
柴胡疏肝散為明代張景岳所創立的方劑, 首見于《景岳全書·古方八陣·散陣》中:“若外邪未解而兼氣逆脅痛者,宜柴胡疏肝散主之。 柴胡疏肝散,治脅肋疼痛,寒熱往來”。可見,柴胡疏肝散自古即為疏肝理氣的代表方劑, 其功用主要是疏肝解郁, 行氣止痛,臨床常用于治療消化、心血管、婦科、男科等系統疾病,以及抑郁癥、頭痛、脅間神經痛、糖尿病、頑固性失眠等疾病。從生理及病機學說方面,肝經布于胸脅、乳房,肝功能失調易出現乳房脹痛或脅痛,久而久之,疼痛可由一點發展為一塊,范圍擴大,根據氣滯血瘀理論,遂可結于乳中而成癌。 故治乳當治肝,治肝應調氣。 因此,在臨床辨證論治處方中,疏肝理氣常配合運用化痰祛瘀、軟堅散結的藥物以助于消除乳腺癌腫,從而改善乳腺癌患者的生存質量,降低復發率。
柴胡疏肝散方中柴胡、枳殼、川芎、郁金與香附等可疏肝理氣行滯,當歸、白芍可養血柔肝;桃仁、制沒藥及制乳香等可活血化瘀,配以半夏、浙貝母、瓜蔞、膽南星及山慈姑等化痰消腫散結,佐用甘草以調和諸藥。全方體現了理氣驅邪而不傷正之理,疏散中有收斂。故我們認為在臨床上,辨證屬肝郁氣滯兼見痰瘀互結的乳腺癌患者, 均可選柴胡疏肝散作為主方。
4 討論
不管從西醫還是中醫角度而言,乳腺癌的發生、發展是一個復雜的生物學過程,肝郁是其基本病機之一,疏肝解郁是其對應的基本法則,而柴胡疏肝散是疏肝解郁之基本方。 中醫藥在治療乳腺癌方面有其獨特的優勢,可通過調整機體的陰陽、氣血及臟腑功能平衡,達到治療疾病的目的。 柴胡疏肝散的應用范圍較廣,疏肝解郁散結的作用大,且毒副作用小,在女性常見的乳腺癌治療中發揮著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