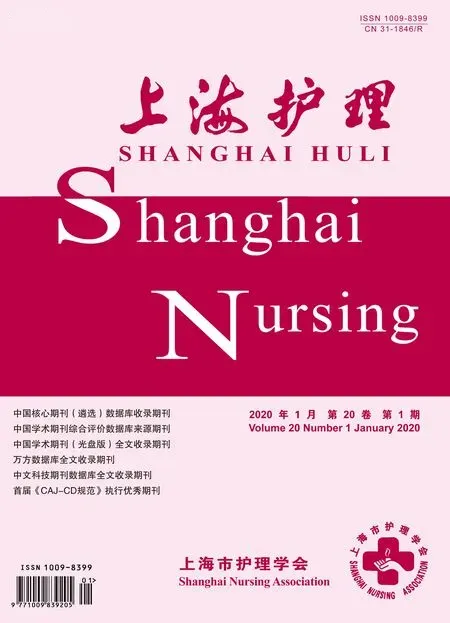患者決策輔助的臨床應用現狀與展望
李 麗
(海軍軍醫大學第三附屬醫院,上海 201805)
世界衛生組織患者安全聯盟一直在倡導患者要積極參與醫療衛生決策。患者參與、共享決策已被視為衡量醫療護理質量的一個重要標志[1]。因此,在臨床診斷和決策中,患者的知情權、自主權、話語權及參與權越來越被重視,醫患共享決策 (shared decision making,SDM)模式應運而生[2]。但有研究表明,患者疾病知識獲取不足,醫患間缺少溝通,加之患者需要面臨多樣化的治療選擇,導致患者無法真正參與決策,因此共享決策現狀并不樂觀[3-4]。患者賦權對于共享決策至關重要。決策輔助是一種可以有效促進患者參與決策、緩解決策沖突,賦權于患者,進而改善患者臨床結局的工具[5-6]。近年來,決策輔助在幫助患者參與決策方面取得了顯著成果,并對醫患共享決策起到了積極的推進作用。但目前決策輔助的應用尚未普及,導致患者參與程度依然較低[7]。決策輔助在臨床的推廣應用方面仍面臨著諸多挑戰。
1 決策輔助概述
1.1 決策輔助的定義早在1972年,醫患共享決策就在《變革年代的醫學倫理學模式:什么樣的醫生-患者角色符合倫理學關系?》一文中首次被提及[2]。在醫患共享決策理論實踐發展的過程中,患者決策輔助(patient decision aids,PDAs)也得以發展推廣。加拿大是推動決策輔助發展的先驅[8]。決策輔助是幫助患者參與決策的工具,國際患者決策輔助標準(international patient decision aid standards,IPDAS)協作組織將其定義為:根據最佳證據客觀地提供有關治療選項和結果的信息,幫助患者詳細了解不同治療方案的風險和益處,使患者明確自身價值觀和偏好,并且盡可能多地了解自己的疾病和治療選擇,平衡患者綜合需求,幫助患者確定需要做出的選擇[9]。決策輔助的發展不是為了取代醫護人員的咨詢,而是幫助醫師傾聽患者的聲音,也幫助患者做好與醫師溝通的準備。其目的是促進雙方參與,使患者和醫護人員討論治療選擇變得更加容易[10]。決策輔助的發展不僅增加了患者對決策過程的參與,使患者對治療方案的選擇更加滿意,還減輕了患者的不確定感,提高了決策質量,最終給患者帶來較好的醫療結局[11]。
1.2 決策輔助的形式迄今為止,世界范圍內針對各種疾病的決策輔助已經以多種不同的形式被開發出來[12],決策輔助實施方式逐漸多樣化,主要包括紙質版輔助手冊形式,視頻、音頻等多媒體形式,基于計算機Web網站及手機應用程序的輔助形式等。目前,基于計算機Web網站和手機應用程序的決策輔助形式應用日益廣泛,旨在節省醫護人員時間和節約醫療成本[13]。
1.3 決策輔助的內容決策輔助主要應用領域:①不同治療方案的選擇,如早期原發性肝癌患者是選擇手術切除還是保守治療[14];②疾病的診斷或者篩查方法的選擇,如篩查早期前列腺癌的幾種不同方案[15];③危重癥患者一些決定的選擇,如借助決策輔助改善長期機械通氣患者及家屬的決策困境[16];④其他,如慢病篩查與管理、是否使用某種藥物、是否改變某種生活方式等。決策輔助制訂過程和評價方法大致包含以下7個步驟:①幫助患者認識到需要作出決定,即確定決策輔助需求;②對決策輔助是否可行進行評估,主要評估患者及決策輔助本身;③確定決策輔助目標;④選擇決策支持的理論框架;⑤提供可供選擇的決策支持方法;⑥確定輔助決策的評價方法;⑦進行轉化傳播,即在臨床應用[17]。
2 決策輔助應用
2.1 國外決策輔助應用現狀
2.1.1 決策輔助的發展概況在西方國家,決策輔助伴隨著醫患共享決策的發展應運而生[18]。目前,已經有多個國家的相關機構開發了決策輔助工具。同時各國都很重視決策輔助的發展,并出臺了相應的衛生政策促進患者參與、推行決策輔助工具的使用和共享決策方案的實施。美國國家衛生政策優先發展的六大目標之一是強調以患者為中心,重視患者參與決策能力,促進患者及家屬能夠參與到決策中。英國衛生質量標準署也將共享決策納入衛生政策中[8]。加拿大是決策輔助發展最好的國家,共享決策項目基本已覆蓋本國的各個省份。加拿大渥太華決策支持網(https://decision aid.ohri.ca)是最早且最全面提供決策輔助的網絡,包括評估患者決策需求、提供決策輔助及決策評價工具等[19]。截至2018年,該網站決策輔助清單共列出200余種疾病的決策輔助。當下,國外共享決策理論體系已經逐步完善,未來研究重心將轉移到臨床實踐,即如何借助決策輔助,激發醫患雙向、準確、及時的信息交流,促進醫患共享決策在臨床實施。
2.1.2 決策輔助工具的質量評價決策輔助工具的質量評價是基于IPDAS進行的[20]。IPDAS是由IPDAS聯合會在2006年運用德爾菲法創建的一套基于國際共識、受到國際認可的國際患者決策輔助標準。IPDAS一方面用來幫助構建患者與醫師間更慎重、更平等的對話[21];另一方面確保向公眾傳播患者決策輔助是可靠和有效的衛生信息來源,使決策產生偏差的風險最小。IPDAS確定了12個維度來評估決策輔助的質量,其中一個重點也是當下熱點,即借助互聯網為患者提供決策輔助。但IPDAS的劣勢在于不能對決策輔助提供精確、定量的質量評價[22]。為此,在2009年至2015年間[9,23],國際患者決策輔助標準聯合會研發了國際患者決策輔助標準測量工具并進行更新、優化,最終形成了國際患者決策輔助標準測量工具IPDASi(v4.0)。該工具包含3類標準水平,即合格標準、認證標準和質量標準,標準水平依次升高。這也意味著決策輔助開發至少要滿足合格標準,力爭達到質量標準,讓高質量的決策輔助更好地服務于患者和醫師,幫助其共同做出最好的決策[24]。 我國學者牟瑋等[25]已將 IPDASi(v4.0)版引進我國并進行評估,但在國內尚未經過充分實踐檢驗,仍需進一步探索和驗證。
2.2 國內決策輔助應用現狀相比于國外的發展,我國保護性醫療制度及家長式的決策模式在一定程度上
限制了決策輔助的應用。直到近些年,醫學人士逐漸開始重視共享決策概念。目前,國內相關研究仍處在理論借鑒并嘗試在不同疾病人群中應用決策輔助進行適用性探索的階段。臨床實踐探索主要集中在腫瘤科、骨科、心血管病科、婦產科和普外科等。李玉等[14]基于共享決策模式,構建了早期原發性肝癌患者治療決策輔助工具包及決策輔助手冊,幫助早期原發性肝癌患者及家屬參與到治療決策中。范慧芳等[26]探討了決策輔助對口腔頜面部手術患者治療決策實際參與程度及滿意度的影響。其結果顯示,決策輔助有效提高了患者決策的實際參與程度及滿意度,進而提高了患者的治療信心和治療效果。劉洪娟等[27]對決策輔助在關節置換患者中的應用效果進行了探討,證明雖然決策過程實施不易,但決策輔助能改善關節置換患者的焦慮和關節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其生活質量。王露等[28]則闡述了決策輔助在直腸癌患者中應用的必要性,認為決策輔助可有效增加直腸癌患者手術方式決策方面的知識,降低其決策沖突,提高直腸癌患者的決策準備度。未來有待對共享決策的適應人群進行更全面的調查研究,對決策輔助在各種疾病臨床決策中的實際應用以及模型、流程的推廣進行探索。
3 決策輔助臨床應用的影響因素
3.1 醫護人員因素醫護人員對于共享決策的參與和支持是決策輔助在臨床推廣應用的前提[20]。Visser等基于知識、態度和實踐三要素對決策輔助在臨床應用的局限性進行系統綜述。結果顯示:首先,醫師對于決策輔助普遍了解不夠,缺乏實施決策輔助的知識和能力[29],不了解患者對于疾病決策的真實需求。其次,部分醫師認為自己是患者決策信息的主要來源,擔心決策輔助的應用會帶來對以往醫患溝通模式的質疑,進而破壞已建立好的醫療工作流程[30]。另外,醫師工作繁忙,實施決策輔助可能會額外增加工作量,時間及人力資源不足也是限制醫師使用決策輔助的潛在因素。因此,對醫護人員進行教育和培訓至關重要,培訓可使醫護人員轉變態度,清楚地認識到決策輔助在共享決策中的重要作用,并掌握實踐共享決策所需的能力和必要的溝通技能[31]。醫師和患者在共同決策的過程中,應對雙方的溝通情況(患者是否正確理解了醫師和決策輔助提供的信息,醫師又是否準確理解了患者提供的信息和疑問等)進行有效評估[32]。如果對決策過程未進行有效評估,患者和醫師都可能對決策的結果產生懷疑,進而影響決策輔助的推廣應用[33]。有效評估工具的開發和應用可以促進決策輔助的應用和發展[34]。目前,共享決策相關的評估工具可評估整個決策過程[35]。護士作為醫師的親密合作伙伴,同時也是患者治療護理措施的實施者和健康宣教者,與患者溝通的機會更多,應該能夠更好地理解患者決策意愿和治療選擇傾向,并對患者的決策過程進行有效評估。
3.2 患者因素決策輔助的目標是促進患者積極參與并形成高質量的決策。Longtin等[36]的研究總結了影響患者使用決策輔助的7個因素,分別為:患者維持現狀的愿望、文化程度、對患者進行教育的時間、疾病類型、個人信仰、患者參與培訓不足以及獲得醫療和保健資源的差異。此外,據報道,并不是所有的患者都愿意參與治療決策[37],尤其是癌癥患者在早期階段不愿意參與治療決策[38],可能與疾病風險感知不敏感有關。Joseph-Williams等[39]則認為更大的問題不是患者不想參與決策過程、不愿意使用決策輔助,而是他們不能參與。因患者參與的程度取決于患者的健康素養、年齡、經濟狀況、文化程度以及疾病情況等[40]。健康素養低、年齡大、經濟狀況較差、文化程度低或者身體狀況差的患者,容易出現被動決策。因此,加強患者的決策能力很重要。同時,未來決策輔助的開發要充分考慮患者需求,包括輔助決策流程的易用性、決策內容的通俗易懂等;盡可能照顧患者感受,主要針對敏感信息、相應治療結局的文字表達方式及患者的個體情況等方面,以促進不同情況、不同文化水平的患者都能借助決策輔助參與到疾病決策中來。
3.3 決策輔助因素決策輔助想要融入臨床實踐,其實現形式必定要簡單且易于操作。復雜的決策流程會影響患者的使用體驗,進而阻礙其在臨床的應用[41]。當下,網絡技術高速發展,智能手機全民普及,決策輔助的實現形式也正逐漸由傳統的紙質材料向基于移動醫療的智能化程序過渡,著力實現輔助決策流程互聯的網絡化、操作的簡單化及普適性是目前開發決策輔助需要重點關注的方面。另外,一個高質量的決策輔助,其內容的全面性、循證性及時效性也必須得到保證[42]。這就對醫護人員的參與度和專業知識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時,決策輔助本身也存在一定的缺陷,當前的決策輔助還不能與患者具體的醫學檢測結果結合,目前決策過程的評估工具都是基于患者主觀傾向選擇。因此,如果能將基于患者醫學檢測結果的醫師建議與輔助決策系統相關內容有效結合,則會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43]。
3.4 文化、經濟因素受不同國家文化背景的影響和經濟因素的制約,決策輔助在不同國家可能面臨不同問題。決策輔助要在臨床順利實施首先應與國家衛生保健系統的文化、法律相適應,還需專項資金支持。目前,共享決策在歐美等國家已普遍得到發展,決策輔助幾乎涉及所有臨床學科,同時也逐步建立起保障共享決策及決策輔助在臨床實施的配套法律和法規[2]。在國內,對于患者決策輔助的研究和應用仍處于單病種應用的摸索階段,缺乏符合我國醫療背景的臨床決策流程和決策輔助模型等方面的研究和應用[44]。在我國,除了缺少政策支持,同時受傳統文化及 “家庭本位觀點”的影響,部分家屬會選擇向患者隱瞞診斷和病情,患者決策常常受到家屬的影響,患者的被動參與也使得決策輔助在臨床的推廣受限。
4 展望
4.1 患者知情權和自主權的挑戰患者的知情權和自主權一直是醫學倫理領域持續探索的問題,也是阻礙患者參與治療決策的主要因素。我國患者入院時《授權委托書》的簽署,體現了家屬代替患者行使決策權力的思想根深蒂固。在這種文化背景下,簡單地推行“個人自主決策”或者“家屬代理決策”都難以實現[24]。建議應根據我國的文化背景和實際醫療情況逐步推進。首先,應在醫療決策過程中宣傳知情同意、共享決策理念,逐步實現對患者病情的告知;其次,需拓寬共享決策思路,在共享決策過程中,尋求患者、家屬、醫師三者間的共享決策機制,建立患者、家屬和醫師共同參與的醫療決策模式,逐步過渡。只有當患者、醫師和家屬均認識到患者的知情權和自主權是患者的基本權利,意識到患者參與治療決策是患者的正當權利,決策輔助才會更好地在中國推廣。
4.2 醫患共同參與決策的挑戰醫療決策的四種類型中,只有醫患共享決策模式是需要雙方參與、雙向信息溝通的[45]。因此,建立良好的醫患溝通對于共享決策至關重要。醫護人員在與患者溝通時,要善于運用談話技巧,與患者建立信任關系。信任是共享決策實現的基礎[46],醫護人員的鼓勵、支持和充足的疾病信息給予是決策輔助在臨床推廣應用的重要促進因素。在信任的基礎上,醫護人員要正視決策輔助在幫助臨床決策中發揮的積極作用,正面引導患者積極參與決策,更好地理解患者的問題,清楚地識別患者的偏好。同時,在決策過程中,護士要對患者的決策情況進行有效評估,對發現的問題和困難給予及時解決,最終實現決策輔助價值,達到醫患共享決策的目標。
4.3 移動醫療+決策輔助的挑戰21世紀,科學技術不斷發展,尤其是“互聯網+”時代及5G時代的到來,使得移動互聯網已經滲透到社會的各行各業和人們的日常生活中[47]。互聯網擁有世界上最全的信息資源,基于互聯網的移動醫療被認為是醫療行業最有潛力、新興的醫療保健技術[48]。近些年來,移動醫療作為醫師干預補充的一種補充手段逐漸應用到共享決策領域。研究表明,移動醫療的可及性、交互性、便捷性、可視化,及時準確的信息支持可吸引更多的患者參與治療決策[49]。同時,基于移動醫療的決策輔助還提供了患者與醫師實時連接交流、分享決策信息的平臺,有助于提高醫患溝通效率、促進醫患共同參與治療決策。盡管移動醫療在醫患共享決策方面有諸多優點,但仍有一些挑戰需要我們去面對。首先,如何評估基于移動醫療的決策輔助的質量和決策流程的設計,以及界面是否簡單、易于操作,內容是否權威、專業且通俗易懂等,都是我們在開發過程中需要面臨的問題。其次,部分患者對互聯網缺乏信任,擔心網絡安全,擔心個人隱私被泄露。因此,互聯網的安全性必須給予足夠重視[50]。最后,患者千差萬別,對于新技術的接受度和看法也不盡相同,篩選出適合使用移動醫療進行決策輔助的患者也是我們面臨的一項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