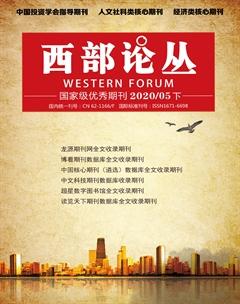啟蒙理性視角下的反猶主義
李靜
摘 要:反猶主義大爆發雖然是在二戰期間,但是其由來歷史久遠,是一個現代與過去并存的特殊問題。反猶主義的產生有其政治歷史傳統,鮑威爾、馬克思、阿倫特等人都給出了不同的回答,從啟蒙理性角度探討反猶主義是霍克海默與阿多諾的做法,其認為反猶主義產生的根源在于啟蒙理性。反猶主義雖然已經銷聲匿跡,但是在當代,還依然存留著反猶主義式的人權問題,現當代我們依然需要時刻保持警惕。
關鍵詞:反猶主義;啟蒙理性;極權主義
反猶主義(antisemitism)一直作為彌漫在德國甚至是歐洲的一種情愫,在二戰前的德國達到了頂峰。有些學者認為德國的納粹運動不應該劃歸為反猶主義的傳統中,因為這一切的開始起源于一個謊言。但又有些學者不這么認同,筆者采取較為折衷的觀點。關于反猶主義,不少學者給出了自己的看法,尤其是西方馬克思主義代表居多,有觀點認為法蘭克福學派中阿多諾和霍克海默做的權威主義人格調查的測試,很大程度是因為在面對所謂文明時代的大屠殺事件時,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已經很難給出較為完善的解釋,所以法蘭克福學派不得不另辟蹊徑,去心理學中尋求答案。在霍克海默與阿多諾合著的《啟蒙辯證法》一書中,特別提到了反猶主義,書中前言就已經闡明了《反猶主義要素》的主題是“已經啟蒙的文明在現實當中又倒退到了野蠻狀態”[1]。這里的野蠻狀態特指了奧斯維辛集中營事件,霍克海默與阿多諾都對此進行了嚴厲的批判,他們認為反猶主義的出現來源于啟蒙理性,形成了與馬克思不同的批判方式。
一、反猶主義的傳統
一談到反猶主義,人們馬上就會想到德國納粹的大屠殺,德國這種爆發式的民粹主義確實令世界膽寒。但事實上,反猶主義不僅在德國,甚至在整個歐洲都是一種常態,探究反猶主義的產生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一)反猶主義與極權主義
阿倫特在其《極權主義的起源》中認為極權主義政治并不是單純的某種主義,還需要使用意識形態宣傳以及政治控制等手段,將現實的基礎徹底消滅,唯有極權是亙古不變的。納粹偽造“錫安長老議定書”作為制造內亂的幌子,這種以秘密會社為政治目標的方式,是帝國主義特有的方式,即各種所謂的“泛運動”。一直處于邊緣的猶太人問題就是在這樣的借口下成為了納粹運動興起和建立第三帝國組織機構的觸發因素,一時間,猶太人問題成為了世界問題的核心。
在反猶主義問題激化上,阿倫特認為猶太人不掌握剝削和壓迫的特權卻掌握最多的財富的時候,反猶主義就達到了頂峰。這也是大多數納粹人所認為的。因為人們總希望權力與財富能夠實現對等,無功不受祿。猶太人沒有做出任何歷史性的功績,即便猶太人是最近而且僅能在金融流通領域進行活動,但對于烏合之眾來說,這就是不公平。另一個原因便是“永恒的反猶主義”(eternal antisemitism),可怕之處在于猶太人自身也接受這一觀念,“實際發生的情形是,大部分猶太人同時受到來自外部物質消滅和來自內部精神解體的威脅。在此情形下,關注自己生存的猶太人會以一種奇怪的、絕望的錯誤解釋,附會一種安慰式的觀念,認為反猶主義畢竟可能成為一種使猶太人保持結合的手段,因此,永恒的反猶主義的假設更能暗含對猶太人生存的永恒保證。”[2]猶太人需要不斷與統治者進行和解,甚至是妥協才可以獲得自己的生存地位。正是因為不斷與統治者進行妥協和解,以至于猶太人最終成為了普通人民中的眼中釘。
(二)反猶主義與經濟
馬克思曾經寫過一篇被學界認為是討伐猶太民族的檄文,即便是身為猶太人,馬克思也不停止對自己種族的批判,因而招致了同時代其他猶太族群的強烈不滿。他在1843年發表的《論猶太人問題》中認為鮑威爾僅僅考察了安息日中的猶太人,只看到了宗教對猶太民族的控制,沒有從更廣泛的角度去考察,猶太人的問題是關乎全人類的問題。猶太人的真正本質就是商業的猶太人本質,也即是猶太人主觀主義的自私自利的狹隘本質。要想真正解決猶太人的問題,應該從天上回到世俗世界,馬克思將猶太人的問題歸結為經濟問題,而不是鮑威爾所說的宗教問題,并提出解決猶太人問題的根本方法在于通過“革命的”“實踐批判的”活動,推翻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消滅資本,消滅私有制,才能徹底將人們從金錢的控制中解放出來,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馬克思并非是要打壓猶太人,否定猶太人,而是要為猶太人尋求一條解放之路。從對社會現實的分析上升至政治經濟制度的變革,這是馬克思的一貫做法。
恩格斯在其《反猶主義》一文中對猶太人加以批判,他認為猶太人是中世紀遺留下來的微弱的反對聲音,對準的是代表著資本家和雇傭勞動者的現代社會。德國產生納粹的原因之一在于魏瑪共和國的軟弱無力,布勞恩政府的倒臺意味著普魯士時代的結束,希特勒的登臺意味著與以往法治浪漫的普魯士相決裂。盡管有人認為,是因為國內經濟蕭條,失業率暴增,通貨膨脹,民眾急需要一個強有力的領導帶領德意志民族重新走向輝煌,所以加快了希特勒的上臺。從經濟角度來講,占據有大部分財富缺又沒有實權的外來猶太人便成了替罪羊,猶太人的“罪”演變成了“惡”。
(三)反猶主義與宗教
猶太民族作為世界上現存的最早的古老民族之一,始終以群居的形式存在于世界各地,由于歷史的因素以及宗教差異的影響,猶太民族在政治上宗教上一直處于邊緣狀態。第一,猶太人在15世紀-16世紀末一直處于事務斷裂狀態。十字軍東征后,猶太教與基督教的矛盾就開始出現了,雖然猶太人在信奉天主教的波蘭度過了短暫的美好時光,但是卻一直被限制在經濟領域,甚至自己的安全都無法得到保障。這也是造成猶太人自我封閉的一個主要原因,雅考伯·凱茨認為,在這一封閉的時期,猶太人開始思考種族差異問題。也即是說,反猶主義的產生首要來源是猶太人的自我解釋。其次,猶太教的歷史書寫中對基督教強烈的理論偏見,并自認為自己是高于其他一切的宗教的上帝特選民,在宗教中互相敵視的傳統也為反猶主義的產生埋下了隱患。
可以說西歐各路宗教的興盛與崛起,是導致反猶主義的原因之一,宗教文化的不同開始讓這古老的民族流離失所,猶太人曾試圖建立自己的國度,但都以失敗而告終。
二、啟蒙理性下的反猶主義
在霍克海默與阿多諾眼中,“文藝復興以來被資產階級自由意識形態捧上天的啟蒙理性(這也是整個資本主義工業文明的深層邏輯支撐點),在推進物質生產力極大發展的過程中逐步地顯現自身具有的兩重性質,即:解放與奴役。”[3]在霍克海默與阿多諾這里,啟蒙具有完全相對立的兩種性質。誕生于現代的文明卻與遠古神話及其相似。他們認為“啟蒙倒退成神話,其原因不能到本身已經成為目的的民族主義神話、異教主義神話以及其他現代神話中去尋找,而只能到畏懼真理的啟蒙自身中去尋找。”[4]
(一)啟蒙的邊界
“反猶主義作為一種全民運動,所追求的正是它的鼓吹者一貫反對的社會民主黨的內容,即要求平等。”[5]正如阿倫特所言之“平庸的惡”,民眾享受這種可以讓他人一無所有的快樂,但是大眾并不知曉這些金錢都流入了上流社會的口袋中,他們僅僅是被一種狂熱的民粹主義鼓動著,并幻想著自己在追求“正義的平等”,但實際上這幫烏合之眾卻發展成了“平等的非正義”。在霍克海默視角下,用“發展生產來掩飾統治支配”是造成資產階級反猶主義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在國民經濟大蕭條的德國,長期被困在經濟流通領域的猶太商人就成了希特勒陰謀詭計的替罪羊,這樣猶太人在經濟上成為了所有不公正的替罪羊。這一替罪羊僅僅是因為充當了統治者和普羅大眾的中間人,成為了“進步的殖民者”。雖然猶太人勤勞聰明的本質讓人羨慕,但是其“固執的自我否定”,在《舊約全書》教義熏陶下,猶太人具有的軟弱無能的特性,而正是這一特性毀掉了整個族群。法西斯主義的極權就表現于此,猶太人這種受壓迫的自然對統治的反叛直接為統治服務。“一旦經濟權力的操縱者戰勝了培植法西斯主義行政長官的恐懼,猶太人就會挺身而出,打破民族共同體的和諧一致。如果統治者憑著與自然的不斷異化重新使他們返回純粹自然的話,他們就會遭到統治者的徹底拋棄。”[6]
虛假投射(Projecktion)作為反猶主義的基礎,是真正模仿行為的反映。感官投射是人類自我持存的一種機制,是人自覺的活動。虛假投射與投射的區別之處在于少了反思這一環節。所投射出來的僅僅是虛假的自我,并且一遍又一遍的不斷重復,近乎偏執狂的狀態,這樣他的自我就成為了一種抽象的自我,已經失去了自然實在的屬性。這種虛假投射被統治者加以利用,成為了將暴政的合理化的最佳工具。在這個現實世界,制度合理化擁護著統治者,強硬的制度不允許任何反叛。霍克海默還認為德國教育本身已經是疾病纏身了,教育以提高個人商品價值為最終目的,文化變成了一種商品在流轉,每個人都被教育成一個法西斯主義者,一個憎恨猶太人的偏執狂。霍克海默與阿多諾做的關于權威主義人格的組群實驗已經充分反映了這一點,德國戰敗則以歷史現實并沒有讓德國法西斯主義者們從自己的強權夢中清醒過來。
啟蒙是自己為自己設限,霍克海默認為,要想破解啟蒙自身的界限,必須通過打破虛妄的啟蒙辯證法,否定的真理不斷揭露欺騙,而我們缺乏了這一否定的反思能力僅僅是因為被遮蔽了心靈而已。具有反思精神,回歸客觀理性是解決方法之一。
(二)同一性邏輯下的反猶主義
阿多諾與霍克海默一樣認為反猶主義的根源在于啟蒙理性,但在阿多諾看來,啟蒙合理化的一個關鍵之處是同一性邏輯。同一性邏輯,一般認為是主客體之間達到和諧一致的一個哲學假設,在邏輯學上看來,同一律就是一概念與事物自身相等同。在阿多諾這里,同一也即是統一。這意味要消除一切特殊的因素才能達到統一的效果。
“被啟蒙摧毀的神話,確實啟蒙自身的產物”“神話變成了啟蒙,自然則變成了純粹的客觀性”,啟蒙就是神話,神話就是啟蒙,二者具有了同一性。不同的事物被同化了,結果便是“萬物不能與自身認同”。阿多諾認為,現代社會是受同一性支配下的社會,任何與同一性相悖的非同一性表現都被視為非法,無論是宗教信仰還是風俗習慣,都逃不出同一性的宰制。合理性的進程就宰制理性對異質摧毀的過程,普遍性和總體性的事業意味著差異性的猶太人的存在恰恰成為宰制理性同化的首要目標。卑微的猶太人在這個不能容忍非同一性的社會中正好作為了破壞同一性邏輯的存在。阿多諾認為,法西斯進行大屠殺正是借助于猶太人這種異于德意志民族的存在。猶太人這種特殊的存在,于法西斯而言,正好滿足了“模仿的厭憎”中所及其厭惡的特殊性。
在同一性宰制下的社會,特殊或者說非同一性便是一種令人討厭的異在。普通大眾在帶有著蠱惑性的宣傳下“團結”在了一起,為著一個烏托邦式的國家而高歌。“由于個體越是系統化,他們的社會總體的功能就越益降低,人也將越來越變得單純無知,作為具有創造力和絕對統治力的個人,也將越加由于其主觀精神的提高而得到安慰。”[7]在這里,人類與動物的區別之處在于,人類把這種潛在的監禁當作自由,當作一種可供炫耀的資本,如同在享受控制的娛樂活動時大喊“我是自由的”。
三、反猶主義的和解之道
霍克海默與阿多諾并沒有給出像馬克思那樣宏大的社會變革方案,但是他們從不同角度進行修修補補,以期能夠避免此類事件的再度發生。
阿多諾有一句在二戰中廣泛流傳的名言:“奧斯維辛之后寫詩是野蠻的。”詩歌的浪漫與奧斯維辛的野蠻形成了強烈對比,以此警醒人們要不斷進行反思批判。阿多諾痛惜經歷過奧斯維辛之后的德國社會民眾的麻木不仁,提出了其對教育存在意義的肯定,“教育的第一任務是阻止奧斯維辛的重演。這一任務優先于其它任務,這一點我認為既無必要也不應該加以論證。我不理解的是,至今人們還是很少關注這個任務,似乎證明這一任務會帶來某種面對曾經發生的暴行似的。人們對這項任務以及它提出了什么問題知之甚少,這說明這件暴行并未震懾人心,其標志就是,就人們的意識狀況或無意識狀況來說,再度重來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每一次關于教育理想的討論都毫無意義,并且對奧斯維辛不能重來這一點漠不關心。那種野蠻是一切教育都反對的。”阿多諾在進行權威主義人格調查時就已經發現教育在德意志人民心中起了強大的作用。電影《浪潮》講述了高中教師賴納·文格爾通過課堂實驗的形式帶領學生體驗法西斯獨裁制度的故事,這是根據1967年4月,美國加利福尼亞克柏萊中學發生的一起真實事件改編而來。法西斯沒有成為過去,它就存在于我們之中,任何一種具有蠱惑性、煽動性的言論或者行為都可能再度帶來法西斯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