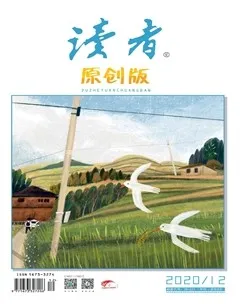醬豆
南在南方
有一陣子,啥東西好吃,我喜歡說“吃到牙縫里,剔出來都是香的”。聞者常常笑說:“惡心!”這話是應伯爵說的—西門慶給了兩條糟鰣魚,他說:“你們那里曉得,江南此魚,一年只過一遭兒。吃到牙縫里,剔出來都是香的……”
前一時,一位離家多年的朋友說,吃了一點兒老家的醬豆,打嗝都是香的!不禁大樂—從牙縫剔出來香至少還“有”,打出嗝香就有點兒“無中生有”了。
醬豆很常見,只是各地的制作手法不同,比如有的里頭加麥麩,有的加果蔬,有的加調料,相同的是都得將豆泡漲,都得蒸煮,都得發酵。
冒辟疆寫董小宛做醬豆,“豆黃以九曬九洗為度,果瓣皆剝去衣膜。種種細料,瓜杏姜桂,以及釀豉之汁”。端的精致。一般人家做醬豆沒那個閑工夫,只以干凈為度。
黃豆篩了簸了,放在盆里泡著。黃豆吃水有一個過程,豆皮開始得皺一下,過不了多久就展開了,直泡得顆顆飽滿嫩黃,再淘洗一回,控干。這邊燒水煮豆子,慢慢煮,直煮得豆子吃著有點兒面,這才算好。好手藝的人會讓豆子把最后那些汁兒給收了,手藝生疏的,汁兒多一點兒也不要緊,盛出來喝。古人說“菽水承歡”,是說家里窮,端一碗煮豆子的湯給雙親都是心意。
煮好的豆子得攤在竹匾里晾涼,再用布蒙著,保溫也保濕,也有用竹葉或者黃蒿來蓋著的,等它發酵。它會發熱,細聽的話,好像總有微微的嘆息聲,不用管它,熱好了就涼下來。三五天后看一下,豆子起絲了,粘在一起了。
這時就可以拌調料了。陜南老家就放三種調料:鹽、辣椒面兒、花椒面兒。一股腦兒撒在豆子上頭,拌均勻,裝進壇子,讓它進味。
瞅個好天氣,將豆子攤在篾席上曬,曬得紅里透亮,再次入壇,灑些白酒,封得嚴嚴的,過一陣開壇,醬香味就跑出來了。
《齊東野語》里有一則:“昔傳江西一士,求見楊誠齋(楊萬里),頗以該洽自負。越數日,誠齋簡之云:‘聞公自江西來,配鹽幽菽欲求少許。士人茫然莫曉,亟往謝曰:‘某讀書不多,實不知為何物?誠齋徐檢《禮部韻略》‘豉字示之,注云:‘配鹽幽菽也。然其義亦未可深曉。”
有個自負的讀書人想見詩人楊萬里,楊萬里寫信說,聽說你從江西來,給我帶點兒“配鹽幽菽”。結果這個讀書人不曉得是啥,空手來了,楊萬里便翻書叫他看,就是豆豉嘛。
這個故事似是說謙虛謹慎的好處,而自負托大則要防備挨“悶棍”。用“配鹽幽菽”這四字來解釋醬豆,實在簡美。

醬豆常常只是配菜,比如墊在臘肉下邊兒—醬豆蒸肉,幾成鄉愁的代名詞。它們相互吸收,肉有醬豆味兒,浸在油脂里的醬豆也有了肉味兒。只是,不宜多吃,到底還是咸。抓一小把醬豆炒莜麥菜,卻是恰好。
還有一種做法,醬好豆子,不放調料,裝在壇子里,倒入涼白開,封好。將壇子放在外頭曬,下雨也不收,偶爾打開攪動。日曬夜露,三個月后,就成了豆醬油,撈去豆瓣,瓶瓶罐罐都能裝,只是要封好。要是想讓醬油多點兒鮮味,也有土法:新筍切碎,凈鍋,倒水來煮,慢慢煮,控出筍汁,放涼,添在醬油里就分外鮮了。
醬豆大多是咸的,也有淡的。還有一種西瓜醬豆,有個朋友說簡直香得要死,要是能吃一小塊兒西瓜醬豆里沒融化的西瓜,那簡直是挨幾個嘴巴都不肯丟啊。我至今還沒吃過,想象不出那個味兒。
還有個朋友在日本見過納豆,說是臭不可聞。許多從中國傳過去的東西,日本人都弄得精致極了,不知為何納豆那么臭,濕乎乎的,還長著長毛,人家卻吃得那么香。
于是翻書,知堂先生在《一歲貨聲之余》里說:“我只記得章太炎先生居東京的時候,每早聽外邊賣鮮豆豉的呼聲,對弟子們說:‘這是賣什么的?natto,natto,叫的那么凄涼?……章先生的批評實在不錯,那賣‘納豆的在清早冷風中在小巷里叫喚,等候吃早飯的人出來買她一兩把,而一把草苞的納豆也就只值一個半銅元罷了,所以這確是很寒苦的生意,而且做這生意的多是女人,往往背上背著一個小兒,假如真是言為心聲,那么其愁苦之音也正是無怪的了。”
知堂先生文章里說,納豆,是咸豆豉。那大約是曬干了的吧,不然“買她一 二把”,不好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