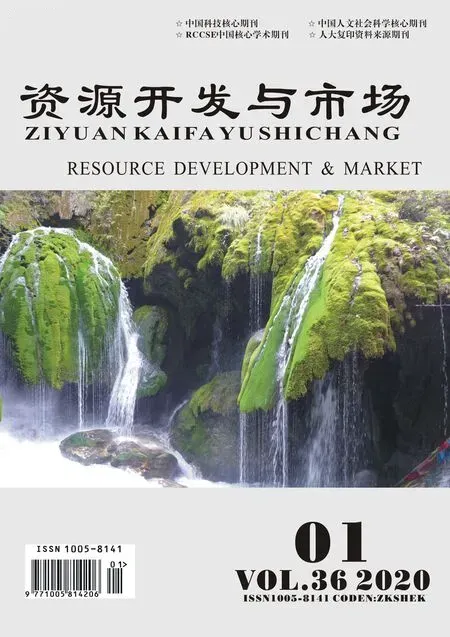基于基準地價的農村土地增值收益調節金核算
——以重慶市大足區為例
任玉龍,牛德利,鄭財貴
(1.重慶市規劃和自然資源調查監測院,重慶 401120;2.自然資源部土地利用重點實驗室重慶研究中心,重慶 401120; 3.重慶市土地政策實證研究基地,重慶 401120)
2019年,我國將建立公平合理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列入農村土地制度三項改革試點的重點任務,規定政府要綜合考慮形成土地增值收益的因素,按合理比例收取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土地增值收益調節金(簡稱“調節金”)[1]。調節金成為構建兼顧國家、集體、個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機制和實現與征地收益大體平衡的核心手段,但目前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市場正處于起步階段,市場機制尚未完全形成,尤其對調節金測算中的土地成本核算缺乏統一、簡便、科學的標準。基準地價作為政府法定公示地價,實施30年來具有公信力強、關注度高、體系完善、管理規范的特點,本文嘗試以基準地價代替土地成本,為調節金測算提供可靠的依據。
1 調節金與基準地價掛鉤
1.1 調節金與國有土地增值稅差異
調節金是在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和再轉讓環節對土地增值收益收取的資金,由集體經濟組織在入市環節、土地使用權轉讓方在轉讓環節向國家繳納,目的是兼顧國家收益,合理調節集體與個人的收益,確保入市收益與征地收益平衡[2,3]。調節金雖然未法定,但改革試點階段仍具有稅收特征,與國有土地增值稅相似,兩者對比見表1。

表1 調節金與土地增值稅對比
從表1可見,調節金與國有土地增值稅既有共性又有不同。從城鄉統一建設用地市場下構建統一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機制的角度看[4],兩者在征收目的、征收環節、征收稅率、稅收用途上存在差異。根本原因是:相較于具有完善稅費體系的國有建設用地市場,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市場正處于起步階段,僅有調節金和契稅,稅費體系不完善,市場機制并不成熟。因此,調節金的征收標準和稅額應符合試點地區的實際,同時也為建立集體與國有建設用地統一的稅收制度奠定基礎。
1.2 重慶市大足區城鄉基準地價現狀
基準地價伴隨著國有土地有償使用制度的施行和城鄉建設用地市場的構建而逐步建立和完善起來[5]。從區域中觀尺度反映市場地價,不同發展階段其定位也不同,尤其是隨著政府公示地價體系由基準地價單核管理向基準地價、標定地價雙核管理的逐步轉變[6,7],基準地價的功能內涵和管理定位進一步變化。從重慶市大足區的實踐看,基準地價與土地成本、市場地價密切相關。如2016年重慶市大足區更新國有建設用地基準地價,按照“體現土地和地價管理政策”[8,9]的定價原則,基準地價平均占市場地價的2/3(50%—80%)。2017年大足區以國有土地級別和基準地價為基礎,制定了全區城鄉統一的土地級別和基準地價[10],形成了覆蓋全域范圍的城鄉基準地價體系,為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提供了基本價格參考。截至2019年3月,大足區累計入市土地54宗,面積98.58hm2,成交總價5.04億元。本次選擇已經完成全部收益分配的7宗地為例進行實證和對比分析,見表2。

表2 大足區入市地塊實際交易及增值收益情況(萬元/hm2)
注:1.由于前后適用標準的變化,1、2宗地的調節金按照交易總價的15%收取,其他宗地按照增值額的20%—50%收取;2.入市主體涉及的鎮(街)與村(社區)名均采用名稱首字母代替。
1.3 調節金與基準地價掛鉤
實際交易情況需要經過一系列修正才具有代表性。通過梳理入市主體和行政主管部門提交的土地成本、出讓底價的測算方案,按照宗地評估案例修正的原理和方法[9],對7宗地的交易情況、成本構成、征收標準等進行客觀修正,得到修正后的收益情況,見表3。

表3 大足區入市地塊修正后的增值收益情況(萬元/hm2)
注:1、2宗地的調節金由原來按照交易總價的15%收取,修正為按照增值額的20%—50%收取,征收標準保持一致。
從表3可見,調節金與修正前后相比,除前兩宗地因征收標準變化導致顯著下降外,其他五宗地基本不變。再以基準地價代替土地成本進行扣除,即與基準地價掛鉤得到增值收益情況,見表4。

表4 大足區入市地塊扣除基準地價后的增值收益情況(萬元/hm2)
由表4可見,以基準地價代替土地成本后,增值額和調節金均顯著上漲,原因在于基準地價與土地實際成本之間存在一定差異。為了實現兩者的順利掛鉤,一方面可依據基準地價與土地成本的關系,調整現行基準地價水平,使其與土地成本相當;另一方面可依據前后調節金的比值關系,對現有調節金標準進行下調,確定新的調節金標準,見表5。

表5 大足區土地增值收益與基準地價掛后的調節金
由表5的測算發現,表中“②”和“③”的調節金在不同的入市途徑中存在一定的比例關系。即表中“③/②”的比值在4宗就地入市途徑中分別為2.03、1.91、2.00、2.36,在3宗集中區入市時分別為2.92、2.48、2.47,掛鉤后的調節金應在原有20%—50%的基礎上參照該比值適當下調,即得到掛鉤后的調節金征收標準。掛鉤后的調節金征收標準明顯與宗地的土地用途、土地級別等無關,這與國有土地增值稅相契合,為簡化調節金制度設計,形成城鄉統一的增值稅費體系奠定了基礎。
2 入市制度與征地制度收益的平衡
調節金除了為建立兼顧國家、集體、個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機制奠定基礎這一核心目的外,同時又具有確保入市收益與征地收益大體平衡的衍生作用。為了不與征地制度產生沖突,這一衍生作用在入市改革中必須兼顧。本文雖然通過調整現行調節金標準,初步實現了調節金與基準地價的掛鉤,但仍需驗證入市收益與征收收益是否平衡。
2.1 土地征收收益
大足區平均征地成本為292萬元/hm2,雖然目前對征地補償的性質尚無定論,但的確改變了土地的所有權歸屬,仍可認為是對土地所有權的補償。從各試點地區的實踐看,不斷提高征地補償標準是普遍做法。征地按照原用途進行一次性補償,不存在長期收益,補償費是對集體土地上所承載的農民生活成本、勞動成本和未來預期收益的補償,是成本補償型收益,名義上不存在被征地集體與個人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情況。大足區征地補償主要包括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助費、地上建構筑物和青苗補償費、征地農民社保、拆遷補償費和其他費用等。根據大足區近五年土地征收臺賬統計結果,不計算稅收和開發成本,平均成本為292萬元/hm2,其中城鎮規劃區范圍外的農村地區平均成本約為174萬元/hm2。
2.2 征收與入市收益對比
入市成本與征收成本大體平衡,入市收益略高于征收收益。本文中述及的7宗地平均入市成本為282萬元/hm2,平均征地成本為296萬元/hm2(就地入市為174萬元/hm2;集中區入市為174萬元/hm2與地票成本價285萬元/hm2之和,即459萬元/hm2),入市成本與征地成本比值為95%,大體平衡。土地入市兼具成本補償型收益和土地增值型收益,7宗地集體與個人獲得總收益(成本補償+扣除調節金后的增值收益額)為平均322萬元/hm2,與征地成本收益比值為109%,說明按照現行調節金標準,集體與個人的入市收益略高于征地收益,見表6。

表6 大足區土地入市與征收的成本及收益對比(萬元/hm2)
基準地價低于入市成本。依據“入市收益與征地收益平衡”的結論,與基準地價掛鉤要對現行20%—50%的調節金標準進行下調,下調后將大幅增加農村集體與個人的入市收益,改變入市收益原本略高于征收收益的現狀,導致入市和征地收益失衡,因此可考慮提高基準地價水平。經測算,7宗地的平均基準地價為194萬元/hm2,占入市成本282萬元/hm2的70%,占入市交易價的60%,表明現行基準地價距離入市土地“客觀成本”有一定的差距。
通過對比農村集體與個人在入市和征地中的成本與收益,入市成本略低于征地成本,入市總收益略高于征地收益,但大體平衡。若要絕對平衡,一是需要通過集體建設用地市場進一步發育和完善,充分釋放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使用權的市場價值,剖析并總結更多交易案例;二是可在現階段通過小幅提高調節金標準,提高國家收益,降低集體與個人收益,實現與征收收益的絕對平衡;三是對現行基準地價進行調整,使其更加接近并代替入市土地客觀成本。但從大足區基準地價管理經驗看,在當前基準地價已占市場地價2/3的情況下,大幅上調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同步調整調節金標準與基準地價水平更加可行。
3 結論
主要結論為:①以基準地價替代土地成本測算調節金可行,但需同步調整現行調節金標準和基準地價水平。成本得到足額補償是經濟活動得以持續的前提,但對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的土地成本進行核算是較困難的。由于宗地之間差異較大,缺乏統一的標準,以重慶市大足區城鄉基準地價作為土地客觀成本進行扣除,同時調整調節金標準和現行基準地價水平,科學計算入市土地增值額和調節金,可解決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成本核算的難題,確保入市改革順利推進。②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使用權的市場定價機制尚未形成。雖然本文通過7宗案例對新的調節金標準進行了初步估算,但仍需通過大量的市場交易案例做進一步修正,以充分反映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的市場價值,為城鄉基準地價的調整和調節金標準的細化奠定基礎。從大足區當前入市交易情況和市場接納度上看,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市場價格逐年升高,市場價值潛力較大,但市場定價機制尚不穩定。③完善公示地價體系,基準地價與標定地價各司其職。目前,政府法定公示地價仍以基準地價為主,雖然從中觀層面確定了市場價格,但與市場價的差距較大,而與成本價接近。以反映微觀層面的宗地市場地價為定位的標定地價體系尚未建立,導致基準地價的管理定位游移不定,無法全方位滿足政府對地價的管理需要。因此,應盡快完善標定地價體系,確保不同公示地價在市場和管理中的功能與定位,為公示地價服務稅費征收奠定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