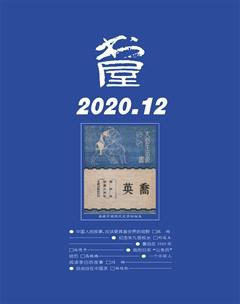中國人的故事 , 應該更具備世界的視野
葉周曾用筆名葉舟,原籍上海,北美洛杉磯華文作家協會會長、資深電視制作人。1989年赴美留學,獲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大眾傳媒系碩士,隨后在美國等地任電視導演和制作人,2004年赴澳門任澳亞衛星電視臺總編輯、總制作人。出版長篇小說《美國愛情》(江蘇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選入南開大學美國華文文學選讀《華人的美國夢》,散文集《文脈傳承的踐行者》(上海三聯書店2011年版)入藏美國斯坦福大學、哈佛大學東亞圖書館,長篇小說《丁香公寓》(上海文藝出版社2014年版)入藏中國現代文學館,作者還出版了散文集《地老天荒》、《巴黎盛宴/城市歷史中的愛情》等。
張娟:葉周老師,您的創作具有強烈的歷史意識和文化情懷,特別是很多小說和散文都回顧了五四時期父輩奮斗的歷史,在歷史的鏡像中結合現實思考進行寫作。能不能談談對您影響比較大的五四時期的文學作品?
葉周:魯迅先生的《狂人日記》是五四時期的著名雜志《新青年》發表的第一篇白話文小說,這篇小說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當時來說,這篇小說具有白話文小說創作的開創性,在小說的語言風格上,擺脫了文言文的束縛,幾乎沒有不文不白的弊病,十分難能可貴。更重要的是,魯迅先生以對于社會的深刻批判精神,假借一個狂人之口,講述了他自己對于那個吃人的社會的犀利批判。魯迅先生的這篇小說發表時就產生了非常正面的社會影響,不僅從內容上,而且從語言風格和敘述風格上都是獨樹一幟的。這正是作為海外作家的我所傾慕的,畢竟我們看到的世界處于多元文化交匯之地,而處于這一區域的文化和人物理應有不同凡響的故事,如果我們自己不具備觀察世界的獨特角度和目光,就會對生活中的許多東西視而不見,輕率地放過了。我們在國內和海外經歷了那么多不同的生活,最根本的是要訓練自己具備當年魯迅的目光,敢于突破陳規,具備獨樹一幟的辨識和評判世界的方法和目光。
張娟:眾所周知,自清朝末年開始,中國的第一次移民潮和留學潮就出現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的先驅們大都具有留學海外的經歷,在留學時期他們的文學思想和主張已經初步形成,其文學創作活動也隨之展開。五四時期的寫作也是一種世界性的寫作,很多寫作是在日本、東歐、德國等世界文學的背景下進行的。您作為一名海外華文作家,能夠談一下跨文化的交流對您創作的影響嗎?
葉周:至今我已在美國居住二十九年,由于職業的關系,接觸了不少移民的故事,感悟最深的是,一個移民在實現夢想的過程中,如何擺脫現存的社會偏見,克服自身的狹隘和居功自傲的情緒,積極參與社會,發揚自己民族文化的優勢,和本土文化交流、融合。
在進入電視行業的初期,我曾拍攝過兩部紀錄片:一部是《平權法案備忘錄》,美國的“排華法案”在1943年被廢除了,以后的移民不會再受到該法案的直接困擾。但無形的歧視和不平等對待仍然彌漫在日常生活中。在拍攝該片時,我采訪了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校長田長霖,他談起在大學求學時,給導師做助教,導師習慣稱他Chinaman,起初他不知道這是一個羞辱中國人的稱呼,就愉快地答應。后來和他相熟的工程師們提醒他,這是白人對華人帶蔑視意味的一個稱呼,尤其不能讓他在學生面前這樣叫,田長霖這才恍然大悟。他即刻去找導師交涉,他說:以后請你不要用Chinaman稱呼我。教授問:那么我怎么稱呼你呢?田長霖說,你可以叫我長霖。教授不悅道:你們中國人的名字這么復雜,我怎么記得住。田長霖堅持道:你可以不叫我的名字,但請不要再叫我Chinaman。由于他的堅持,從此以后教授只好不再用這個侮辱性的稱呼,但他也堅持他的原則,不用中文名字稱呼田長霖。
田長霖的經歷是歧視殘余的證明,作為移民經常會遇到這樣的境遇,用什么因應之道去對待?消極的自我封閉,退縮在狹隘的華人社區,遠離社會并不能使困境有所改善。以正常的交流方式直率表達自己的感受,讓對方知道,使對方改變才是積極的因應之道。田長霖是這樣做的,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作為一個移民進入一個完全陌生的社會環境敞開心胸,不計前嫌,寬容曾經有的誤解,平等交流是十分重要的,讓陌生的人了解我們,讓漠視我們的人接受我們。
文化有其傳承力和影響力,我們雖然客居異鄉,但這個異鄉是一個文化融合的國度,這是我們的幸運。發揚自己文化的優勢,與西方文化互補、交融,這才是人類文化的最高境界。這也是我們這代移民的責任,我是為此感到慶幸的。我能有機會在不同的國度中穿梭行走,在不同的文化族群中扎根下來,身體力行地從事跨文化的交流,這些無疑都增強了我創作上的獨特體驗。剛才說到的田長霖校長和音樂家譚盾,他們的生命體驗也是如此。
在國外工作多年,時常與不同族裔的同事們談起各自民族的文化。十分有趣的是,聊起這個話題,每個人都會津津樂道。即便自己民族的歷史曾有坎坷和波折,可是說起民族的文化,都會充滿了自豪。其實在他們眼里的我也是這樣,中國的每一點發展和進步都會使身居海外的游子充滿興奮之情。
張娟:每個作家的寫作都與自己的童年息息相關,比如五四先驅魯迅的寫作和其幼年成長經歷就有很密切的關系,越地文化、家道中落、紹興民俗等都在他的創作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您的成長經歷和您的創作也有密切的關系,能否具體談一談?
葉周:我是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末期出生的一代,這個年齡層的人,經歷了共和國歷史上波瀾壯闊的不同時期,對于不同歷史時期產生的任何結果,所經歷的人們都不得不親身承受。我所記述的或許都是個人記憶中的一些小事。幾年前,我的第二部長篇小說《丁香公寓》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那部小說更接近我的成長經歷,因為我在小說中充滿情感地陳述的幾個生活在公寓中的孩子,從少年到青年的成長過程,其實就是我自己走過的生命歷程。
我曾經在一篇文章中寫過,有一次回國期間,走過巴金先生故居,正好對外開放。我推開故居的門,踏上二十二級階梯來到二樓。我特別強調那里有二十二級臺階,因為我曾經隨母親拜訪巴金先生時,在那間書房兼臥室里坐過。站在屋子里我不由得問自己:其實在我成長的年代里,親眼所見文壇前輩們經受著不同的磨難,但苦難為什么沒有阻止我愛上文學,卻依然步上了筆耕的道路?我思索著從二樓走回一樓一間狹小的太陽房中,巴金先生曾在屋中的一張小書桌上創作了傳世之作《隨想錄》。我忽然明白,正是前輩們遭遇磨難時,展示的默默承受和人格尊嚴留給我極其深刻的印象。當社會氛圍中阿諛奉承和攻訐陷害彌漫時,他們的沉默和自尊在我年輕的心靈中投上一道永遠無法磨滅的光亮,為人有尊嚴,為文才有品位。這束光在我心中點燃的火苗至今燃燒著,我的文學夢想從此開始。
張娟:五四時期的作家很多都具有跨界的工作和學習經歷,比如胡適在哲學、文學、史學等領域均有貢獻。魯迅學的是醫學,接受過解剖學的專業訓練,他又是一名美術愛好者,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期他將歐洲的版畫藝術引入中國,發起了“木刻運動”,他的作品中也多配有黑白的版畫。聞一多既是一個畫家,同時又是詩人、學者。您作為一個海外華文作家,也是同時做著多樣工作,您覺得這種跨界的藝術精神是怎樣影響您的創作的?
葉周:其實,文學寫作始終是我的業余愛好。我大學畢業后,進入電影界,做編輯,做電影策劃。到了國外學習電視,碩士畢業后,又投身電視行業二十多年,從電視攝像、剪輯、導播一直做到制作人和總編輯,也客串過主持人。我很幸運,在這個行業中,幾乎大部分的職位我都做過。電視這個行業有一種令人著迷的吸引力,因為每天接觸的都是不同的人不同的事,我們看到的世界較常人更為豐富。所以,在電視這個行業中,如果你做一個有心人,你就會有很大收獲。
張娟:五四時期風云激蕩,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興起的社會改造潮流對中國社會改造產生了深刻影響,不僅激發了中國先進分子積極改造中國乃至世界的信心和責任,也助益了文學的發展。當下的世界局勢已產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國在“大國崛起”的時代,您覺得這個時代對您的創作有什么影響?您是如何在這個時代寫作自己的“中國故事”的?
葉周:在出版了長篇小說《美國愛情》和《丁香公寓》后,我有意識地將小說的創作轉向中篇小說。從事一部長篇的創作十分不易,通常是醞釀成熟后開始寫作,然后寫寫停停,這樣漫長的創作周期適合于一些時間性不是太強的題材,但是卻極大地限制了我對于當下一些熱點問題的參與。為此我更多地進行散文的創作,彌補這方面的缺陷。而我是一個電視制作人,日常接觸的都是最熾熱的社會事件和議題,我沒有理由不發揮職業的優勢助力自己的小說創作。
近兩年以來,我連續發表了五個中篇小說,一言以概之,與我的職業生涯較緊密。近期的《布達佩斯奇遇》講述了一個華裔女記者和她女兒在東歐旅游時遇到了中東難民潮的故事。在我的理解中,中國的故事并不僅僅局限于中國的疆域內。中國的故事,應該是一個緊緊維系著中國人命運的故事。在國外住久了我們常說,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找得到中國人;只要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中餐館,出了國的人比國內的人更愛國。中國人素來是喜歡游走的民族。我去了布達佩斯,才了解到那個平原上的先人來自蒙古草原的游牧民族,所以在世界各地走得多了,我都會較為深入地去想一些問題。其實,中國人的故事應該更具備世界的視野,如果不是這樣,我們這些華文作家就枉為自己,浪費了自己海外生活的空間和視野。我所追求的中國人的故事,必然能夠體現各種文化跨越與交流的狀況,更主要的要體現這種文化交流的痛苦與快感。
張娟:從辛亥革命到五四運動前后,是中國社會急劇變化的時代。蔡元培在執掌北大后,提出“兼容并包”的方針,蔡元培、李大釗、魯迅、錢玄同等互相鼓勵,學術觀點百花齊放,形成了一個有益創作的“朋友圈”。您在寫作的過程中有沒有遇到這樣的支持和鼓勵,有沒有朋友或老師給您寫作的精神動力?
葉周:錢玄同造訪周氏兄弟時,魯迅在民國政府的教育部掛著閑職,終日生活于苦悶與彷徨之中,靠抄寫殘碑拓片消磨時光。在這低迷時期,前去訪問的錢玄同發現魯迅案頭堆滿了古碑抄本,便善意地責怪他是在浪費自己的生命。魯迅環顧悶熱的陋室:“中國原本是一個沒有門窗的鐵屋子。假如這座鐵屋子萬難破毀,里面又躺著許多熟睡的人們,這些人最終都要被悶死——在不知不覺中,由昏睡轉入死亡,誰也感覺不到痛苦和要死的悲哀。現在你大聲喊叫起來,驚醒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讓他們盡管醒來卻依舊無可逃脫,讓這些人知道痛苦和將死的悲哀,而你又無力拯救他們,這究竟是仁慈,還是殘忍?”但是魯迅終究還是被喚醒了。
而我似乎是從少年時就喜歡寫作,當然那時寫的東西很幼稚。幸運的是“文革”后,又和父親的作家朋友們建立了緊密的聯系,作家如伶、柯靈、艾明之等都批改過一些我幼稚的稿子,并很認真地給我指導,文學雜志的編輯也給我的投稿提過意見。盡管自己青年時的寫作是坎坷的,但后來進入電影行業做了編輯記者,卻展現了自己評論方面的一些敏感度,于是,就從電影電視的理論評論開始嶄露頭角。出了國生活稍安定后,生活有了積淀,重新開始寫作。當時,我寫了一系列與文壇前輩們交往的散文,也有回憶父親往事的文章。
張娟:您認為海外華文文學和五四傳統有沒有聯系?您的創作中有沒有五四啟蒙的精神追求?
葉周:這個問題的回答也是因人而異。因為,海外華文文學的作家隊伍也是各色紛呈,并不是一個整齊規范的團體。從我個人的角度來看,如果說五四啟蒙精神對我的影響,似乎遠了一點。而更近的更直接地裹挾著我精神成長的,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化反思。也正是從那一個偉大的思潮中,我投身其中,成就了自我成長。而在那個過程中,我接觸到的許多前輩作家,他們都是走在思想反思的前列。他們晚年的著作不僅構筑了當時的思想高峰,并且影響了我等許多后生者的成長。而他們成長的年代正是五四精神廣泛傳揚的年代,盡管經過近代歲月洗禮,他們從自身潛質中重新喚醒的五四精神的余韻,邁步走在思想反思大潮的前沿。他們的這些思想和言論,對我的寫作有根深蒂固的影響,我深刻地理解了一點,做人必須有尊嚴,文字才會有價值。
張娟:我認為您的創作受到五四一代前輩影響非常大,您能不能談一談這一代前輩的文學事業對您創作的內在影響?
葉周:我對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文化啟蒙和文化反思潮流記憶猶新。我記得十分清楚,那時尤其是我父輩的這一代作家,他們經歷了“文革”苦難,回到正常的工作崗位上。那時我熟悉的前輩作家巴金、周揚、夏衍、陳荒煤、王元化等都在自己的寫作中對中國歷史上遭遇的人為災難進行了深刻的反思,他們身體力行自己寫文章,創辦先鋒雜志,并且當中年和年輕一代作家在創作上遭遇無端指責和武斷批判時,也是他們挺身而出,擔當了無懼無畏的思想探索的衛護者,他們的文字和精神無疑深刻影響了我的思想和寫作。當年我所熟悉和接觸的這些前輩作家,都是五四時期后成長起來的,他們的血液中浸泡著濃烈的五四時期的精神。
張娟:您這一代作家和大陸作家都是接受過五四思潮和新時期思潮影響的,但后來就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您認為海外華人作家和大陸作家的區別又是什么?
葉周:海外華文文學創作,從客觀上分析既有局限,也有自由。所謂局限是與兩地主流文化的間離,用中文寫作,對于英文的主流文壇幾乎沒有什么影響。同樣,其對于中國的主流文壇影響力也是微弱的。二十世紀九十年代那些描寫海外華人生活的作品,曾經在特定的時期造成轟動,是遇上了方興未艾的出國潮,這種現象在今后恐怕再難遇到。移民文學作品要再創輝煌,相對于作品在題材上的優勢,作品的主題和對人性的開掘深度都變得更為重要。但在不利中的有利條件是,海外華文作家所進行的跨越文化的創作,在觀照中、西文化時具備了多角度的立足點,這又和西方主流作家,或是中國本土作家有所不同,這種優勢無法取代。
近年來海外華文文學發展顯示了一個新的趨勢和特點。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奇跡般騰飛,遍布于世界各地的華文作家十分重視與中國本土的交流,他們十分頻繁地穿梭于中國和世界各地之間,他們的作品中反映的生活也越來越離不開自己的出生地中國。所以,現在活躍在華文文壇上的中堅力量,他們作品描繪的歷史和現實,已經不僅僅局限于移居地的移民生活,他們筆下所體現的是一個廣大世界的融合,是東方與西方世界沖突中的生存和發展。他們的視野覆蓋中國的近現代歷史,覆蓋移居地的文化和移民生活,他們作品中提供的思索和藝術形象,體現了一種宏闊的具備世界格局視野的文化的反思,這種反思不僅涵蓋海外生活,同樣涵蓋中國的近現代和現實生活,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