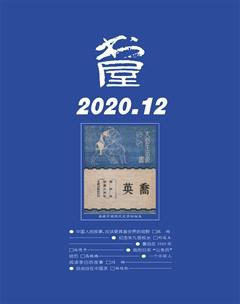馮友蘭與海派文化
劉士林
在《三松堂全集》第四卷,馮友蘭先生曾用“城鄉關系”來比喻文明發展的不同階段及其內在差異。1998—1999年,在寫作《闡釋與批判——當代文化消費中的異化與危機》時,我把馮友蘭先生的這個重要思想梳理、歸納為如下幾個方面:
(一)鄉下是城里的殖民地。
(二)中國自周秦以來,對于四周別的民族,向來是處于城里人的地位。即使有幾次鄉下人沖進城里來,占據了衙門抓住了政權,但是這些鄉下人,終究是鄉下人。他們不能把城里人降為鄉下人,他們至多能把他們自己提升為城里人,這也就是所謂的夷夏之辨。
(三)在現代世界中,英、美及西歐等處是城里,這些地方的人是城里人,所以許多人去逛紐約、巴黎、倫敦,就像劉姥姥進了大觀園,覺得沒有一件事不新奇,沒有一件事物不合適。工業革命造成了這一結果。它使東方靠西方,就像鄉下靠城里一樣,鄉下本來靠城里,不過工業革命之后尤其如此。工業革命使西方成了城里,使東方成了鄉下。
(四)城里徹底破壞了鄉下的生活方式。尤其是經歷了工業革命之后,農民有麥,但他還要上城里買面粉;農民有棉花,但他還要上城里買布。在精神上也如此,所謂中國人往西洋留學者,實即是鄉下人進城學乖而已;所謂中國人往西洋游歷者,實即是鄉下人往城里看熱鬧而已。
(五)有沒有挺身反抗的呢?當然有,比如印度的圣雄甘地,他叫印度人都不用英國布,都用舊式機子,自己織布。又如中國人的抵制日貨,但最后都失敗了。所以,這并不是解決問題的出路。其他如專門提倡“東方精神文明”,以及各種國粹運動,也都未能把野蠻的西方物質文明拒于國門之外。這是因為,文化都是以所謂的城市為中心。
(六)最后,怎么辦?鄉下人如果想不吃虧,唯一的法子,即是把自己變成城里人。至于怎么辦?在當時,馮友蘭極為推崇的有正在工業化的蘇聯,以及清末從事洋務運動的中國人。
記得當年第一次看到這些文字時就很驚奇,一個中國哲學史家,一個曾以“闡舊邦以輔新命,極高明而道中庸”之言名震當時、澤被后學的老夫子,本來應該和一般舊文化人一樣,對燈紅酒綠的現代化城市沒有好感,甚至對之實施“道德批判”,期冀回歸田園和鄉村生活,但馮友蘭完全不同,他在那個年代對工業文明、現代社會和城市就有了這樣深刻的認識和透徹的覺解,真是非常的了不起。但當時只顧為寫作尋找素材,對馮先生的身世和經歷并不是很關心,所以,對這些思想到底從何而來也就沒有去深究。這其中也有個人的原因,就是對待歷史人物和是非,我向來既不喜歡那些指手畫腳的人,也不喜歡那些越抹越黑的人,結果就是對他們寫的東西統統都不看。今天看來,這當然不是一個好的習慣。
己亥歲末,在太湖邊上過庚子春節。房間里藏書不多,但有一套新版《三松堂全集》,把蔡仲德先生的《馮友蘭先生年譜初編》(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二版,以下簡稱《年譜》)拿出來,不巧又翻到另外一段文字。1988年6月24日,臺灣《中國時報》莫昭平采訪馮友蘭先生,兩人談到他和梁漱溟的差別,馮友蘭先生說:“梁是中國現代哲學史重要人物,他也要發揚儒學,但文化觀點與我有分歧,他主張村治,我主張工業化。”時隔五十年,馮友蘭先生對城市和鄉村的思想和態度可以說一以貫之。近現代以來,上海一直是中國最開放、得世界風氣之先的城市,而馮友蘭先生又被看作是緊跟時代步伐的中國哲學史家,因此可知,他對工業文明、現代城市的態度,與他青年時期的上海經歷應該是密切相關的。
據《年譜》記載,1912年,馮先生十七歲時,來到上海的中國公學。當時的情況大致是,辛亥革命以后,革命黨人的領袖人物之一黃興做了上海公學校長,他向各省發電報,請各省選派優秀青年。當時的河南省積極響應,通過考試選拔了二十名,每個學生每年有官費二百兩銀子的資助。馮先生自幼聰慧異常,一考試就被錄取了。當時的校舍在吳淞炮臺灣,是一座非常漂亮的洋樓。關于這段生活,馮先生曾寫道:“到了民國二年春天,終于開學了……閑了到江邊走走,倒也覺得有點像世外桃源。我只是喜歡到河南路棋盤街那一帶,那里書店很多,我喜歡買書,那二百兩銀子花不完就買書,也買了一些大部頭的書,如廿四史之類。”“無論如何,我總算免于學習做傳統的八股文,開始讀一些從西洋的報刊上翻譯過來的文章,學了一點當時所謂新學或西學。”最重要的是,來上海不久,由于對邏輯學的興趣,馮先生萌生了學哲學的志向,上海是為他日后成為中國二十世紀偉大的哲學家的邏輯起點。七年以后,馮友蘭先生出國留學,在回顧在北大的三年學習經歷時寫道:“這三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在第一階段,我開始知道,在八股文、試帖詩和策論之外,還有真正的學問,這就像是進入了一個新的天地。在第二階段,我開始知道,于那個新天地之外還有一個更新的天地……”從第一個階段的具體內容看,這個階段是和他在上海的中學經歷一脈相承的。所以說,作為當年新學和西方文化大本營的上海及其海派文化,對當年那個離家求學的年輕人最終成長為一位具有世界影響的哲學巨匠,一定提供了最適宜的土壤和最適宜的氣候。
1915年,二十歲的馮友蘭從上海公學畢業,并從上海考入了北京大學。這次報考和入學有一個耐人尋味、值得咀嚼的小插曲,對此他曾回憶說:“當時的北京大學,有文、理、法、工四科,報考文科的預科畢業生很少,因為文科畢業在政治上沒有什么出路,只可當個‘教書匠,于是當局就為文科大開方便之門,規定報考文科不要預科畢業文憑,只要有同等學力就行。我有大學預科畢業文憑,在當時說,也是一種資格。我在上海北京大學招考辦事處報名的時候,說的是要報考文科,那位辦事處的人大為驚異,他說:‘你既然有文憑,為什么不報考法科呢?法科畢業后出路好。我堅持要報考文科,那位先生說:‘好吧,我給你出個主意,你還是先報考法科,等到入學的時候,如果你還是要上文科,可以申請改科,由法科改文科,那是沒有不準的。如果你現在就報文科,將來你再想改到法科,那就非常困難了,你會后悔莫及的。我聽了他的話就寫上報考法科,等到9月間入學的時候,我還是申請改科文,果然一申請就準。”
要在過去,也許都會覺得這是“一件小事”,不少人都會有類似的經歷。但這兩年來,隨著上海提出打響文化品牌并把海派文化列為三大文化資源之一,這個細節也就洗去歷史塵埃,具有了全新的意義和意味。我想,招生處負責人一定是江南人或上海人,他們的特點是既洞悉世運時事,又非常精明和精于算計,但同時還應該說他還具有上海人最值得稱道的性格特點,就是對優秀的人,特別是優秀的年輕人格外有耐心和友善,因此他才會喋喋不休地陳述各種利害關系,替這個在他看來不諳世事的年輕人處處精打細算,力勸我們未來的哲學家選擇更有實用價值的法科,而不是去學在他看來沒什么實用價值的文科。但他可能萬萬想不到,從中原文化、傳統儒家文化里面走出來的馮友蘭先生,只是敷衍了一下他的好心和熱心,因為文科在這個年輕人心目中的地位,遠遠高于一般上海人最看重的那些形而下的工具性的學問和職業。這既可以看出海派文化和中原文化的重要區別和對立,也可以看作是源自西方的工具理性和源自傳統的實踐理性的一次別有意味的對話。
當然,從哲學家的一生和思想看,這并不說明海派文化對馮友蘭先生沒有影響,相反,我們還可以說,這段經歷的影響是十分深刻和相當全面的。從本文開始引用的他對城鄉關系的深刻見解和態度,和他從小耳濡目染的中原文化在本質上就是針鋒相對的。馮友蘭先生的這些觀點,不僅可以說與海派文化一個多世紀前對城鎮化的見解和判斷不分伯仲,與當時中原和內陸那些在理論上、在實踐中一直批判和抵觸城市的學者完全不同,甚至還可以說,它們就是放在今天,也比很多人的見識高出很多。毋庸諱言,這既可看作是海派文化對青年馮友蘭的重要啟蒙和沾溉,也是他與海派文化有著深刻的靈魂的默契的主要證據和因果。一個多世紀過去了,我們依然應該說,這是馮友蘭先生的幸運,也是海派文化的榮幸。
最后要補充的一點是,在七十年以后的1985年,馮友蘭先生與上海還有一次重要的交集。這年的9月初,上海市委宣傳部思想研究室朱紅、魏承思采訪馮友蘭先生,請他談對上海文化建設的意見。9月19號,在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理論研究室編《思想研究內參》第三十一期,就刊出了“上海城市文化發展戰略研討”之二十二《馮友蘭教授建議: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后來,這篇文章又收入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研究室主編《上海文化發展戰略研究》,并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時我突然想到,今天上海提出建設人文之城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大都市,這里面說不定還有馮友蘭先生當年的思想貢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