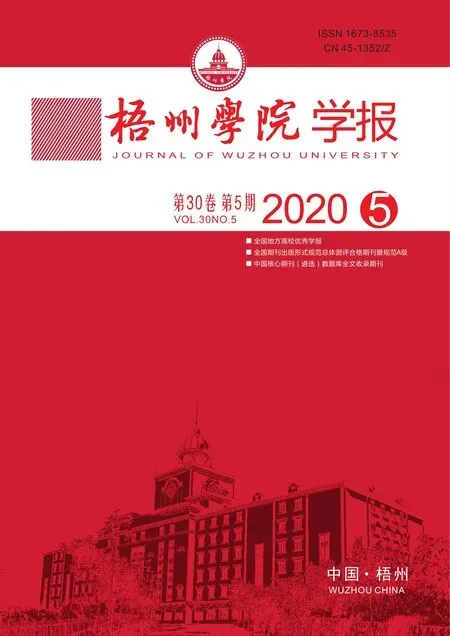公司治理對上市商業銀行風險的影響研究
胡曲應,雷 媛
(1.中南民族大學,湖北 武漢 430074;2.湖北省煙草公司黃岡市公司,湖北 黃岡 438000)
上市商業銀行在金融市場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保證銀行的健康運營,是保證整個金融體系安全的前提。但是,銀行的往來業務往往存在風險,如果銀行風險水平失衡,不僅會嚴重影響商業銀行自身的正常運作,還會危及整個金融體系的安全。
1997年和2008年的兩次大規模金融危機揭示了銀行業承擔過度風險的危險,引起了更多學者的關注。相關國際組織、政府和學者普遍認為,金融危機的原因主要包括外部驅動因素和內部驅動因素。其中,內部動機假設進一步分為產品風險假設和制度動機假設。產品風險假設是指金融產品過度創新引起的金融危機;制度動機假設是金融機構由于自身的管理問題引起風險水平的提高。本研究認為產品風險假設更關注外觀,而制度動機假設則關注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由于商業銀行缺乏有效的公司治理,間接導致了整體金融體系的失衡。所以確保公司治理機制的有效性,有利于保證商業銀行的平穩運營,促進金融體系和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
目前,上市商業銀行迫切需要解決自身風險問題,以確保其順利運作。因此,從公司治理角度出發,研究上市商業銀行的風險水平控制,對完善上市商業銀行內部治理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一、文獻綜述與研究假設
目前,公司治理的定義是指公司形成股東大會、董事會等各責任主體,保證各責任主體獨立運作及相互監督,構建有效的決策機制,以保證企業的健康發展。
有部分學者曾質疑傳統的公司治理理論是否能夠應用于上市商業銀行這一特殊的主體。盡管存在很多爭議,但仍有大量證據支持所有權結構和傳統的公司治理機制,例如執行激勵和董事會制度仍然在銀行公司治理中發揮重要作用。當前研究主要從所有權結構、董事會和執行激勵方面來探討公司治理與銀行風險控制的關系。
(一)上市銀行股東治理視角
從上市銀行股東治理視角,觀察銀行風險的變化。此項研究在國外起步較早,早在1997年Merton就提出了著名的“道德風險假說”,即商業銀行中股東是其風險水平的主要控制人,股東有機會參與到風險決策,以最大化地實現自身權益[1]。但是,Magalhaes et al認為“道德風險假說”不一定成立,股權的分散或集中時,會對銀行的風險水平產生不一樣的影響[2]。國內學者李維安發現,雖然大股東可以監督和激勵銀行經理[3],這對銀行業績有利,但往往存在機會主義行為,增加了銀行風險。吳從根發現,銀行在股權集中度相一致的情況下,企業性質的不同也會造成不同的影響[4]。
據此可發現,“道德風險假設”受到大多數學者的認可。但是,也有部分學者得出不同的研究結論:當股權相對分散時,商業銀行更容易控制,防止股東決策時為了個人利益作出逆向選擇;當股權比較集中時,持股比例較大的股東將放棄有可能導致過度風險的決策,從而降低銀行的風險水平。因此提出假設1。
假設1:上市商業銀行的股權集中度與風險水平處于倒“U”型關系。
上市商業銀行的股東如果是政府背景,在公司治理上將會更多地關注社會利益,它更有可能放松預算限制并最大化地實現社會福利,因此風險很高。基于此,提出假設2。
假設2:如果第一大股東是政府或國有法人,則銀行承擔的風險更大。
(二)上市銀行董事會治理視角
目前,從上市商業銀行董事會治理的角度來看,在董事會規模方面,Changanti、Eisenberg等的實證研究表明,董事會規模越大,難以形成有效的決策機制,這將增加銀行風險[5]。但是,也有大批學者并不認同這一觀點,Simpson和Gleason認為,董事會的規模較大,可以充分采納各位董事的建議,保證決策結果的科學性;與此同時,小規模的董事會更容易受到控制,不利于科學有效的決策[6]。
國內在這個方面也做了大量的研究。劉銀國等研究表明,隨著上市銀行董事會的不斷完善,董事會規模的擴大和獨立董事比例的增加對減少銀行業務風險有顯著影響[7]。然而,一些學者發現,董事會規模對商業銀行風險水平的影響并不顯著[8]。郝臣和崔光耀等利用中國公司治理指數(CCGINK)建立了一個小組模型,發現獨立董事和高管持股比例與銀行風險水平呈負相關,而其余指標與風險承擔沒有顯著關系[9]。
董事會規模過大,容易導致無效的決策和控制機制,并會導致部分股東追逐私人利益。而小規模的董事會有利于更好地監督董事,并增進董事會成員之間的交流,但不能保證決策的科學性和合理性。在此基礎上,提出假設3。
假設3:擴大董事會規模有利于降低上市商業銀行的風險水平。
就董事會的獨立性而言,由于獨立董事的獨立性較強,能夠在決策時發表決策有效有利的建議,從而確保產生利于企業運營的決策。在此基礎上,提出假設4。
假設4:保持董事會的獨立性有利于降低上市商業銀行的風險水平。
(三)上市銀行高管薪酬激勵視角
高管薪酬激勵是公司治理中的重要內容,Schreiber的研究發現,高級管理人員擁有固定的薪酬,那么他們在管理決策時會減少其承擔風險的機會。然而,一些學者進行了深入研究,發現高管薪酬水平與銀行風險呈負相關,但當高管獲得某些股票期權或額外獎金時,會增加銀行的風險[10]。
國內學者從高管薪酬的角度來研究銀行風險,得出與國外學者相類似的結論。曹艷華和牛筱穎發現,高管薪酬水平與銀行的風險水平呈負相關[11]。魏華的實證研究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12]。
較高且固定高管薪酬激勵政策會使管理層減少激進冒險行為,但也會降低其工作的積極性。目前,大多數公司會采用基本工資加獎金或者股權激勵來控制管理層,使得高管人員將自身利益與公司利益相結合來管理公司。由于中國商業銀行高管的持股比例的數據可用性較差,本研究未分析管理層持股對銀行風險水平的影響。因此,主要研究高管薪酬水平與銀行風險水平之間的關系。故提出假設5。
假設5:積極的高管薪酬激勵有助于降低銀行風險水平。
國內外學者從公司治理的角度對商業銀行風險影響的研究有著豐富的成果。但是,可能由于年份數據不同的原因,研究結論尚不一致,這些有待進一步探討。本研究共提出了5種假設,手工收集樣本銀行的數據并借助實證研究方法來論證上述假設。
二、數據變量與模型構建
(一)數據樣本
選擇2017年上市的14家商業銀行作為樣本銀行。2007—2017年的數據來自國泰研究數據庫和世行年度報告。使用的計量工具為SPSS23.0。
(二)變量定義和模型設計
1.變量設計
考慮到樣本數據的有效性和可用性,利用不良貸款率和撥備覆蓋率來衡量中國商業銀行的風險水平。原因在于:第一,不良貸款率和撥備覆蓋率是銀監會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指標,比較符合我國金融行業的發展現狀;第二,破產風險法和市場法是針對要研究的樣本,數量有一定的要求。因此,首先將不良貸款率作為解釋變量,然后根據公司治理的相關理論,選擇5個指標作為解釋變量。選擇的控制變量涵蓋了宏觀及微觀層面,宏觀層面變量(EV)包括GDP增長率(GDP)和通貨膨脹率(CPI)。微觀層面變量(BV)包括:總資產回報率(ROA)和銀行總資產(LnQA)的對數。各個變量所代表的含義如表1所示。

表1 研究變量及釋義
2.模型設定
首先描述性統計分析變量指標的統計特征,并依據相關系數,排除多重共線性問題,然后采用多元回歸分析進行實證研究各治理變量對于銀行風險的影響。為驗證上述假設,根據變量設計,構建以下的回歸模型,具體見公式1:
NPL=α0+α1CR12+α2NIS+α3BODS+α4IDP+α5TS+α6GDP+α7CPI+α8LnQA+α9ROA+ε
(1)
三、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分析
樣本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見表2。

表2 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
由表2可知,不良貸款率的均值為1.218%,2007年的均值為3.15%。樣本期間的最小值為0.36%,最大值為5.64%,表明銀行一直在控制不良貸款率的區間。董事會的規模通常約為11人,變化較小。獨立董事在股份制銀行的占比普遍高于獨立董事在國有銀行的占比。此外,研究期間,銀行的高管薪酬水平處于上升趨勢。
(二)變量間相關性檢驗
運用Pearson相關系數分析變量間線性相關性的強弱。模型涉及變量的檢驗結果見表3。

表3 我國上市商業銀行相關指標的相關系數
由表3可知,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的平方與不良貸款率呈正相關,表明過度集中或分散股權將增加銀行的風險水平;如果第一大股東是政府或國有法人,則與銀行的風險呈正相關,表明如果第一大股東是政府或國有法人,銀行的風險更大。董事會規模和獨立董事比例與銀行風險呈負相關。這表明董事會的擴大和維持獨立性有利于降低銀行風險;高管的薪酬水平與銀行風險水平呈負相關,相關系數是-0.069,即公司治理中采取積極的高管激勵政策,更有利于防范銀行風險。同時當年的經濟增長率、銀行規模和銀行資產收益率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銀行風險。以下回歸分析用于提供進一步的研究和解釋。
(三)多元線性回歸分析
回歸分析以不良貸款率為被解釋變量,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的平方、第一大股東性質、董事會規模、董事會獨立性、高管薪酬水平為解釋變量,經濟增長率、通貨膨脹率、總資產規模、總資產收益率為控制變量,運用統計軟件SPSS23.0,對模型進行回歸分析,結果見表4。

表4 模型回歸結果
1.模型代表性分析
由表4可知,回歸方程的調整R2為0.296。說明對于不良貸款率的變化而言,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可以解釋其29.6%的部分;回歸方程的DW值為2.014,接近于2,顯示此模型有較強獨立性的殘差,沒有顯著的序列相關性;F統計量的值為14.504,P值為0(<0.001),說明資產的總回報率為99%。選定的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具有顯著的效果,回歸方程具有統計學意義。
2.回歸結果與假設驗證
由表4還可以發現:(1)α1為0.034,P值為0.075。即在0.05的水平上,假設H1被驗證,即上市商業銀行的股權集中度和風險水平處于倒“U”型關系。(2)α2為-0.041,P值為0.620,假設H2已經過驗證,也就是說,如果第一大股東是政府背景,那么銀行的風險就更大。但是P值為0.620(>0.05),差異并不顯著,可能是由于樣本數據的篩選問題,后期需要加大樣本量繼續試驗。(3)α3為-0.195,P值為0.001,在0.01的水平上顯著,假設H3已經過驗證,也就是說,當適當擴展董事會規模時,防止銀行風險是有益的。(4)α4為-0.103,P值為0.010,在0.05水平上顯著,假設H4被驗證,即董事會獨立性與銀行風險水平呈負相關。(5)α5為-0.061,P值為0.003,在0.01的水平上顯著,假設H5被驗證,即高管薪酬水平與銀行風險水平呈負相關。說明適當的激勵措施可以鼓勵高管更多地關注銀行業務,并幫助減少代理問題和銀行風險。
(四)穩健性檢驗
穩健性檢驗通過改變解釋變量的方法,將不良貸款率與撥備覆蓋率取代。在正常情況下,不良貸款率和撥備覆蓋率是銀監會在實踐中獨立形成的審慎監管工具,具有很強的實際應用價值。原始模型執行回歸以測試穩健性。回歸結果表明,最大股東持股比例的平方與覆蓋率呈負相關,相關系數為-0.249 7;當第一大股東是政府背景時,撥備覆蓋率就會下降;董事會規模與銀行風險水平呈正相關,顯著水平為5%;董事會獨立董事的規模與撥備覆蓋率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呈正相關;高管薪酬水平與撥備覆蓋率呈顯著正相關,顯著性水平為5%。在對股權集中度、董事會規模、獨立董事所占比例、高管薪酬水平與撥備覆蓋率進一步回歸后,可以維持上述結論。
作為衡量銀行風險的指標,不良貸款率和撥備覆蓋率是相反的指標。當不良貸款率很高時,銀行的風險將更大。而撥備覆蓋率恰恰相反。當撥備覆蓋率增加時,將降低銀行的風險水平。總之,回歸結果與主要回歸結果基本一致。
四、結論與啟示
本研究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所有權的集中度與銀行風險呈倒“U”形相關;第二,如果第一大股東是政府或國有法人,銀行的風險水平可能會提高;第三,適當擴大董事會規模有助于防范銀行風險;第四,董事會的獨立性與銀行風險水平呈負相關;第五,高管人員薪酬水平與銀行風險呈負相關,說明適當的激勵手段能促使高管人員更加注重銀行的經營。
根據研究結論將從股權結構、董事會和高管薪酬水平3個方面提出有關建議,以期達到完善公司治理結構,進而有效控制銀行風險的目的。
首先,我國商業銀行最大的特點就是股權集中度較高,在這種情況下,容易出現大股東為了自身權益而侵犯其他小股東的利益;不科學的決策結果也很容易導致銀行承擔過多的風險。因此,從公司治理的角度看,銀行應該控制所有者的持股比例,引入大量的機構投資者。推進產權制度改革,降低“一大股”帶來的金融風險。同時,對于非國有股東,要制定好其準入標準,并且追索其最終控制人,避免其關聯方持股,導致持股比例過大的問題。
其次,要實現科學合理的決策,商業銀行應提高選舉標準,充分發揮獨立董事的作用。研究發現,政府背景的董事以實現社會福利最大化為目的,可能會增大銀行的風險水平,應該適當減弱其地位和作用。同時,獨立董事的獨立性和專業性得到嚴格保障,每家銀行的董事會投票選出適合其銀行的董事。此外,還要保證獨立董事發揮作用,應賦予其相應權利,并讓獨立董事全面了解銀行的運營狀況,使其提出科學公正的決策意見。
最后,提高銀行高管人員激勵比重。大多數商業銀行會保證高管持股,但出股比例較低。可以考慮通過股份支付等方式來加大高管的持股比例,有利于削弱委托代理問題,提高管理層的工作積極性。當然,在增加高管持股比例時,也要保證高管的回報與銀行的長期業績相一致,才能真正發揮出高管持股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