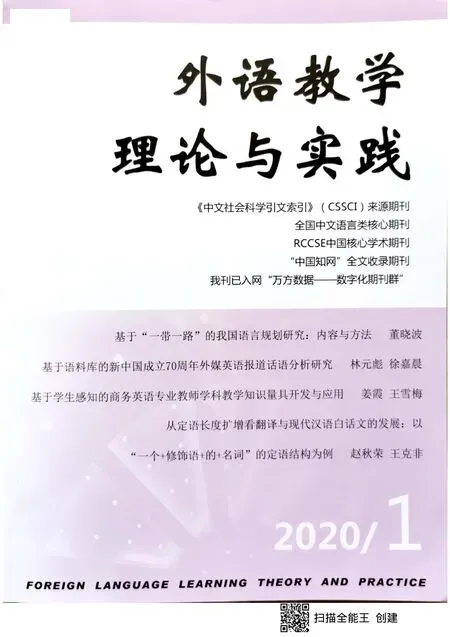中國古代散文在法國的譯介
華東師范大學 唐 鐸
提 要: 中國古代散文歷史悠久、源遠流長,與其悠久的歷史相比,中國古代散文譯入法國的時間要晚得多,直到20世紀方才引起法國漢學家的注意。本文將考察20世紀以來法國出版的中國古代散文譯本,全面梳理法國漢學家對中國古代散文的翻譯成果,深入分析不同時期中國古代散文在法國譯介的重點與特點,以彌補我國目前對中國古代散文在法國譯介狀況認識的不足。
倘若從1926年法國翻譯出版的第一部散文集《中國古文選》算起,中國古代散文在法國的翻譯歷程迄今已走過近百年的歷史。然而,我國對中國古代散文在法國的譯介與學術研究狀況尚未開始予以重視,這與中國古代詩歌在法國已取得豐富、深入的研究成果相比,可謂是天壤之別。其中緣由何在,值得一探究竟。
本文重點考察20世紀以來法國的中國古代散文譯本,全面梳理法國漢學家對中國古代散文的譯介成果與特點,以彌補我國目前對中國古代散文在法國翻譯與研究情況了解甚少的遺憾,填補我國古代文學法譯研究中散文板塊缺失的一環。
一、 馬古烈與法國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古代散文選
馬古烈(Georges Margouliès, 1902—1972)生于圣彼得堡,俄羅斯裔法國漢學家,師從漢學家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巴黎大學文學博士,畢業后任巴黎東方語言學院(l’éco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中國文學教授。馬古烈精通多國語言,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古代文學,在中國古代散文方面著述頗豐。他的《中國文學史: 散文卷》(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prose, 1949)是歐洲第一部中國散文史,也是法國目前出版的唯一一部中國古代散文史;此外,他還著有《〈文選〉中的賦》(Le Fou dans le Wen-Siuan, 1925)、《中國藝術散文的演變》(Evolution de la prose artistique chinoise, 1929)、《中國文學史: 詩歌卷》(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poésie, 1951)等著作。
在翻譯方面,馬古烈于1926年出版的《中國古文選》是法國20世紀上半葉僅有的一部中國古代散文選集。譯文以朝代為綱,從《春秋公羊傳》開始直至明代張溥的《五人墓碑記》為止,共編譯散文119篇,基本涵蓋了中國古代各時期代表性散文家的著名篇目,如《過秦論》《出師表》《蘭亭集序》《桃花源記》《五柳先生傳》《滕王閣序》《阿房宮賦》《師說》《祭鱷魚文》《岳陽樓記》《朋黨論》等。在選文標準上,馬古烈主要依據《古文觀止》《古文析義》《古文評注》三部中國古文傳統中的經典文選,文體劃分則遵循于民國十二年(1923)上海廣益書局刊行的《評點箋注古文辭類纂》,并對入選文章的圈點、評語、簡注多有沿用。在散文翻譯上,馬古烈主要借鑒前人的翻譯經驗,并在此基礎上根據中國經典文選的選文添加新篇章的譯文。他在《中國古文選》序言中說道:
本書中的古文均出自最為著名的古文選集中: 《古文觀止》《古文析義》與《古文評注》,必要時會進行比對后翻譯。書中一部分已由P.Zottoli譯為拉丁文,在《中國文化教程》(Cursus litteraturae sinicae)卷四中出版;還有一部分已由Giles譯為英文,放在《古文選珍》(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一書中。此外,Grube翻譯過大約十篇,大部分收錄于他的《中國文學史》(Geschichte der Chinesichen literatur)一書中。以上三部作品基本是關注古文這一文體的主要歐洲著作。此外,在目錄中我們對譯文做了一些必要說明。(George Margouliès, 1926: c)
在《中國古文選》目錄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馬古烈所譯119篇中國古代散文里有43篇法語譯文參考的是《中國文化教程》中的拉丁譯文、11篇參考了《古文選珍》中的英語譯文、2篇參考了《中國文學史》中的德語譯文、41篇則是共同參考了以上三部譯本,馬古烈本人從漢語原文譯為法語的僅有22篇。
馬古烈序言中那句看似平淡的“以上三部作品基本是關注古文這一文體的主要歐洲著作”,實則極具分量。《中國文化教程》的作者Angelo Zottoli(1826—1902)漢名為晁德蒞,意大利耶穌會士。晁德蒞1846年來華,在上海徐家匯傳教,并創徐匯公學,次年徐匯公學正式建校,并任教十余年。他鉆研漢語,熟讀儒家經典,并用拉丁文編譯有《中國文學讀本》,著有《中國文化教程》。晁德蒞在《中國文化教程》序言中開門見山地說道:“寫作本教程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讓我們近來剛上岸的傳教士們無需花費大量精力,短時間內在了解中國方面有長足的進步,然后他們就有能力在我們學校中從事中國研究,進而嘗試用中文寫作。因此,我寫作的目的是嚴肅傳達中文的最精奧內核,而非給最有教養的歐洲讀者們展示中國事物中的奇珍異寶。”(司佳,2016)《古文選珍》的作者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漢名翟理斯,是英國駐華外交官、漢學家,在劍橋大學中文系任教達35年之久,一生翻譯了孔子、老子、莊子等許多中國古代思想家的著作。《古文選珍》1883年由翟麗斯自費印刷出版,他在該書中“翻譯了不同時期中國著名散文作家的‘優雅的’散文‘片斷’,所有翻譯均為首次翻譯”(Giles, 1922: ii)。1884年4月,遠東報紙《先鋒》(Pioneer)發表書評稱:“英語讀者苦苦搜尋,但都無法找到一些關于中國總體文學的文字,哪怕一丁點介紹性的文字也好。理雅各博士所做的巨大努力確實使獵奇者可以輕易地得到儒家經典;但是,中國大量的文學作品現在仍是一片有待開發的處女地。新近出版的《古文選珍》正好彌補了這一缺憾”(翟思理,2016)。《中國文學史》是德國早期著名漢學家顧路(Wilhelm Grube, 1855—1908)的著作。書中論述了從先秦諸子到唐詩以及后世的戲曲小說,是德國第一部全面論述中國古代文學史的大部頭著作(約470頁)。在該書的前言中,顧路柏稱:“鑒于讀者對中國學的興趣明顯增大,書市上關于中國的書籍顯著增多,而關于中國文學和思想的作品卻很少,作為中國精神生活的一個重要方面的文學至今沒有得到足夠的研究,乃決定寫一部通俗性的中國文學史。”(Grube, 1999: 9)
通過對上述三部關于中國古文的歐洲著作的研讀,可以發現馬古烈翻譯選擇的特點與傾向。晁德蒞長期在中國傳教,不但辦學培養神職后備人員及其在華人才,為來華傳教士和在華儲備傳教人員提供教育與培訓,還精通古文,編寫漢語教材供來華傳教士使用;英國的翟理斯多年在劍橋大學任教,是研究先秦經典的專家,且在語言教材、翻譯、工具書、雜論四類著書方面均有建樹;德國的顧路柏創建東亞文化博物館,推廣女真文化,任教于柏林大學,在文化、民俗方面著述頗豐。三位中兩位是在漢學界工作多年的漢學教授,一位是在傳教前沿的傳教負責人。就三部古文著作本身的價值而言,《中國文化教程》成為19世紀歐洲頗具影響力的中文-拉丁文對照教材,《古文珍選》填補了中國總體文學概覽上的空白,《中國文學史》則順應德國的漢學熱潮,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呈現給更多的讀者。三部著作在對中國古代散文理解的深度和廣度上均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性進展,是中國古代散文歐洲學術性譯本的開先河之作,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也代表了當時歐洲對中國古代散文翻譯的最高水平。選擇這三部譯著作為主要參考譯本的馬古烈,其學術眼光更是獨到,因為這三部已有譯著不僅對《中國古文選》的選文具有直接的參照意義,而且通過已有英、拉、德語譯文與注釋的互相對照給予馬古烈法語翻譯直接、具體的幫助與參考。
此外,馬古烈參考《古文觀止》《古文析義》《古文評注》的選文標準,并以漢學家的眼光有意識地增加唐、宋古代散文的翻譯篇目,選譯了27篇散文作為補充,使其翻譯選編的《中國古文選》能夠比較全面地反映中國古代散文的基本面貌和特點。從以上選文與翻譯策略中,可以發現馬古烈翻譯思路的四個特點: 其一,《中國古文選》法譯本并非承襲歐洲古文譯本的已有內容,相反,馬古烈遵循的是中國古代文學傳統學術路徑,選擇翻譯的是古文歷經千年的歷程后沿襲而來的精華;其二,在中國古文傳統的基礎上翻譯散文的具體方法參考歐洲極具分量的拉丁語、英語、德語三部譯本,由此一方面提高了翻譯中國古代散文的效率,另一方面為譯文與注釋的理解提供了雙重參照與保障;其三,馬古烈在中國古文傳統規范的基礎上“有意識”地添加了27篇中國古代散文,并根據古漢語原文直接譯為法語,充分體現了馬古烈的學術眼光與學術抱負,亦說明他的中國古代散文法譯本并非“拿來主義”的產物,其中凝結了馬古烈作為譯者與漢學家的雙重思考;其四,正是由于譯者在選文標準、譯文參考、譯文增添三方面做出的不懈努力,作為中國古代散文首個法譯本的《中國古文選》一經問世即躋身歐洲古代散文權威譯本之列,成為法國中國古代散文研究不可多得的重要譯本,在此后長達一個多世紀的時間里再無其他法譯本在體量上可與之爭鋒。
馬古烈的《中國古文選》是法國有史以來出版的第一部,也是20世紀上半葉法國唯一一部中國古代散文選集,正是得益于這位“最早系統研究中國古代散文的法國漢學家”(顧彬,2008: 2),中國這一古老的文體才第一次系統、詳盡地呈現于法國讀者面前。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該書的序言是由馬古烈本人撰寫,他在其中詳細介紹了中國古文的形成、流變、文體特征以及歷朝歷代的古文特點,該序言篇幅長達116頁,其內容含量足以獨立成書,是中國古代散文在法國研究的重要成果。《中國古文選》雖已出版近百年,但它依然是法國迄今為止出版的選文數量最多、涵蓋時代最長、涉及散文家最多的中國古代散文選集,這部選集也成為之后法國學者研究中國古代散文時被引用最多的文獻,馬古烈因此成為法國人對中國古代散文研究影響最深遠的權威漢學家。
二、 赫美麗與法國20世紀下半葉的中國古代山水游記
20世紀下半葉中國古代散文在法國的譯本明顯增多,參與翻譯的譯者也有所增加,這50年間共出版六部譯作,分別為: 赫美麗(Martine Vallette-Hémery)的《袁宏道: 云與石(散文)》(Yuan Hongdao: Nuages et Pierres, proses, 1982)與《風景: 中國風景散文》(Les Formes du Vent: paysages chinois en prose, 1987)、譚霞客(Jacques Dars, 1941—2010)的《徐霞客游記》(Randonnées aux Sites Sublimes, 1993)、米歇爾·庫特勒(Michel Kuttler)的《哀江南賦》(Lamentations pour le sud du fleuve, 1995)、皮埃爾·布里艾爾(Pierre Brière)的《歐陽修: 辯誣堂及其他》(Ouyang Xiu, La Salle du Discernement du Vrai et du Faux et autres textes, 1997)以及班文干(Jacques Pimpaneau, 1934—)的《中國古典散文選》(Morceaux choisis de la prose classique chinoise, 1998)。此外,侯思孟(Donald Holzman, 1926—)的著作《嵇康的生平與思想》(La Vie et la Pensée de Hi K’ang, 1957)中有一章專門是對嵇康散文的翻譯。從以上譯作中不難看出,中國古代山水游記成為這一時期法國譯者翻譯的重點,而赫美麗則是其中最為重要的代表之一。
赫美麗1979年在巴黎狄德羅大學-巴黎七大獲得博士學位,她的研究對象是“公安派”代表人物袁宏道,其博士論文題目為《袁宏道(1568—1610): 文學理論與實踐》(Yuan Hong dao (1568—1610): théorie et pratique littéraires)。此后,赫美麗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散文與中國現代詩歌的翻譯工作,是法國20世紀下半葉最重要的中國古代散文譯者。在她的推動下,中國古代山水、園林、風物游覽的游記類散文成為中國古代散文法譯中最為重要的主題。赫美麗在1982年與1987年分別出版了《袁宏道: 云與石(散文)》與《風景: 中國風景散文》兩部散文集。《袁宏道: 云與石(散文)》分為四章:“三座城市: 蘇州、杭州、紹興”、“北京”、“廬山”、“西部與中部山脈”,譯有包括《虎丘》《滿井游記》《靈巖》《陽山》《晚游六橋待月記》《雨后游六橋記》《孤山小記》《宋帝六陵》《天目》《宿落石臺山房》等在內的山水游記50余篇。赫美麗認為,袁宏道是明代反對官方文學與教條主義的代表性人物,其山水游記打破陳規,對山水風景的熱愛源于禪宗思想,其作品為這一文學體裁注入了新的活力。如果說和山水游記的結緣與赫美麗在博士期間對袁宏道的研究息息相關,那么《風景: 中國風景散文》則是她在山水游記領域的又一力作。赫美麗翻譯了從魏晉至明清共26位散文家的49篇風景散文,包括《始得西山宴游記》《小石城山記》《岳陽樓記》《前赤壁賦》《后赤壁賦》《記承天寺夜游》《爽籟亭記》《湖心亭看雪》等名篇。赫美麗除對柳宗元、蘇軾、袁中道、王思任、張岱、袁枚等人的山水游記進行重點翻譯外,其余均為一人一至兩篇,其目的在于突出重點的同時,使法國讀者對不同時期的中國古代山水散文有一定的了解。《風景: 中國風景散文》中所譯篇目均由赫美麗本人從不同的文選中挑選而來,有游記也有散文詩,體裁多樣。赫美麗認為“這些散文除了形式美之外,也非常精彩地表現出作者與自然相接觸時體驗到的驚險與快樂。”(Vallette-Hémery, 1987: 13)赫美麗之所以選擇山水游記作為翻譯對象,與她看重山水游記與大自然的關聯及其所蘊含的文學性與美學性密切相關。
與馬古烈編譯上起先秦、下至明代的通史性中國古代散文選相比,赫美麗將翻譯的眼光投向了古文中的一類——山水游記,不論是承接其博士論文成果的《袁宏道: 云與石(散文)》,還是著重“風景”二字的《風景: 中國風景散文》,亦或是新世紀以園林為切入點的《自然天堂: 中國園林散文》,均為展現中國古代別致、秀美的山水風景,以及古代文人游山玩水的閑情逸致與生活風尚。赫美麗在首部山水游記譯本中即已表明自己的態度:“明代因其輝煌的小說而著稱,雖然這在當時難登大雅之堂。我們將在本書中發現另一番面貌,會驚訝于它不因循守舊的文字。這些散文,或者說是散文詩,一次次地展現出沉思的愉悅以及作者對這一傳統文體的革新,同時表現出寫作的樂趣。”(Vallette-Hémery, 1982: 封底)“我們強調游記這一體裁,我們可將之稱為‘山水’,類似于一種充滿詩意與畫面感的完美文體;或稱為‘游記’,以便使人聯想到以前浪漫主義。大自然一直在中國古代宗教中扮演著主要的角色,且大自然從一開始便在中國詩歌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從公元四世紀起,大自然激發了人們的美學感受,這便是游記的開端,它從最初的簡單描寫發展為一種全新的文學體裁,這種體裁與田園詩歌不同,它表達了大自然與人類相遇時建立的詩化聯結。”(Vallette-Hémery, 1982: 10)在《風景: 中國風景散文》中,赫美麗進一步點明選擇山水游記作為翻譯對象的原因:“‘風景’是一類藝術性散文……這類散文經歷了相似的演變過程,從嚴格的韻律節奏發展到一種更為豐富、自由的結構。它們反映了中國文學傳統中兩股相反的趨勢: 儒家的道德以及源于道家、佛家的個人主義……正如山水畫是對所有元素的總括,文學中的山水風景是從自然風景出發,經由人的視角,在共有形象總和中經過重組后產生的風景。”(Vallette-Hémery, 1987: 13-14)
細究以上表述,可發現赫美麗選擇中國古代山水游記作為翻譯對象是充分考慮讀者接受與市場需求后的結果。首先,法國讀者已接觸過中國古代文學中的詩歌與小說,但尚未接觸過散文,因此可對國別文學中的未知文體進行開發;其次,山水風景散文描繪了中國古代的山川精致,自然的互通性一方面易于法國讀者理解,另一方面其神秘東方主義色彩也易于吸引法國讀者的眼光;最后,中國古代的山水風景散文并非單純的風光描寫,其骨架由儒家、道家、佛家的思想張力構建而成,是中國古典思想在山水風景中的凝結,因而有了思想的深度和魅力,這與法國讀者長期以來為儒、釋、道思想吸引的傳統結合起來,更添譯本的魅力與接受度。正是這三重“知”與“未知”間的張力,成為吸引法國讀者的不二法門,也是中國古代山水游記成為二十世紀下半葉中國古代散文法譯主流的原因所在。
除以上兩部山水游記外,《徐霞客游記》(Randonnées aux sites sublimes)是20世紀下半葉中國古代山水游記法譯中的另一個重要譯本。《徐霞客游記》由譚霞客翻譯,于1993年由伽利瑪出版社出版,收入“認識東方”叢書(No.80)。譚霞客是著名漢學家、遠東地區研究專家,也是法國最杰出的翻譯家之一,曾任法國國家科學研究院(CNRS)研究主任。他在翻譯中追求譯本與原作的語言風格相一致,對語言有極為細密、敏感的體察。譚霞客翻譯的一百二十回本《水滸傳》贏得了法語世界一片“絕妙”的贊嘆,他也因深得著名文學評論家、比較文學家艾田蒲的賞識,成為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主持、艾田蒲主編的“認識東方”叢書里“中國系列”的主編(Kaser, 2011: 14)。譚霞客在《徐霞客游記》中選擇了17篇游記構成法譯本的主要內容,這17篇均是徐霞客在1633年之前寫成,收入《名山游記》文集中,描寫其在天臺山、雁蕩山、黃山、武夷山、廬山等名山大川的所見所聞。文本選擇的背后隱含譯者的眼光,譚霞客在譯本序言中寫道:“《名山游記》中的每一篇雖沿用日記的形式,卻仍然構成一個完整而獨立的整體: 這使得十七篇與《徐霞客游記》中的其他篇章有了本質的不同。”(Dars, 1993: xxiv)“《名山游記》的十七篇僅約五萬字,僅占《徐霞客游記》全書不到10%(全書共60萬字)。這十七篇構成本書翻譯的主體,它們描寫的是中國的壯麗風景,是中國風景中最為卓越、崇高的名勝之地——山。它們提供的地理學、山理學、地質學、洞穴學、人種學、社會學等具有極高價值的科學信息,是當今學者的重要文獻資料。相反,第二部分的文章則沒有太高的文學價值,因而我認為,再次當略過不提……”(Dars, 1993: xxiv)序言所說“第二部分”是指徐霞客于崇禎九年(1636年)至崇禎十二年(1639年)的游歷,他在四年間游覽了浙江、江蘇、湖廣、云貴等江南大山巨川,寫下了九卷游記。為何選擇《名山游記》作為《徐霞客游記》法譯本的翻譯對象,即在于這一部分有第二部分難以相媲美的“文學價值”。譚霞客認為,《徐霞客游記》中詩化的語言與表達也使其位列中國古代散文中的杰作之中,其中徐霞客游覽名山大川的旅行游記可謂是其游記的精華部分。徐霞客看待世界的眼光以及詩化語言表達的樂趣,使他的游記常常存在微妙的區別與變化,同時也給人一種與中國山水畫相似的觀感。與此同時,這位一生幾乎從未停止過旅行的中國史上最偉大的旅行家,極為詳盡、忠實地記錄了途經的地理環境與所見所聞,使《徐霞客游記》在文學貢獻之外成為地理學家和考古學家不可多得的研究材料。因此,對法國讀者而言,《徐霞客游記》既可以作為中國文人寫的旅游指南,又可以作為少有的風景詩集,此外還可作為一份極富個人色彩的文獻資料,其書中展現的冒險與朝圣之旅實際是一次真正的心靈追尋之旅。
相比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古代散文法譯的一枝獨秀,二十世紀下半葉的散文譯本不論在內容或數量上都出現了質的飛躍。這一時期不但有《中國古典散文選》《歐陽修: 辯誣堂及其他》等古代散文集出版,還有《袁宏道: 云與石(散文)》《風景: 中國風景散文》《徐霞客游記》等山水游記問世。山水游記能成為中國古代散文法譯的重點主題得益于譯者赫美麗和譚霞客的不懈努力。赫美麗認為山水游記是展現中國獨特自然風光的重要載體,譚霞客認為山水游記既是風景詩集又是旅行指南,還是文史資料,他們看重山水游記與大自然的關聯,認為山水游記充分體現了中國古代散文中的文學性與美學性,“山水散文中交織著儒家的道德觀以及道家與佛家的人生觀,中國的文人在其中為我們展開了一幅充滿情感與美的地理畫卷。”(Vallette-Hémery, 1987: 14)。
三、 費揚與法國新世紀的蘇軾散文選
到了21世紀,中國古代散文在法國的翻譯一方面延續了歷代散文選與山水游記的翻譯傳統,同時全面開啟了蘇軾散文的譯介工作,成為新世紀以來中國古代散文法譯的新熱點。
一方面,這一時期赫美麗仍是山水游記最重要的譯者,翻譯出版了《自然天堂: 中國園林散文》(Les Paradis naturels: jardins chinois en prose, 2001)和《荊園小語》(Propos anodins du Jardin d’épines, 2008)。在她看來,《自然天堂: 中國園林散文》中所選的38個篇目均為描寫中國古代庭園的佳作,不論是修園、入園、賞園,還是對花鳥魚竹等景物的描寫,都能讓讀者跟著作者的筆鋒,徜徉在中國園林之中,這是散文形象的最大魅力。她認為借助這部文選,人們“可以走進中國古代文人的園林。文中記敘了他們的起居及在園林中的游覽體驗。而中國古代文人對園林的修葺則體現出他們生活的藝術及對山水景觀的見解。園林對中國古代而言,是一個可以躲避時間與俗事紛擾,遠離現實世界的天堂。”(Vallette-Hémery, 2001: 封底)《荊園小語》譯本中收錄了申涵光的《荊園小語》和其他文人的清言雜談。赫美麗認為這些作品蘊含著悠久的文化傳統,既是倫理道德的表達,又是美學情感的抒發,充滿了智者對人生的細心體會,所點撥之處都是容易被人忽略卻又是不可忽視的細節。她認為書中語錄文辭細膩,發人深思,是人生處世的哲學與方法的經典匯集,文字多為生活記事與情緒雜記,均是獨抒己見,雖然詞句言簡意賅,卻往往能一語道破世間玄機。
另一方面,進入21世紀后法國中國古代散文翻譯與研究的一個突出的特點是對蘇軾的重點關注。目前已翻譯出版的七部散文集中有三部是蘇軾的作品,包括費揚(Stéphane Feuillas, 1963—)的《東坡賦》(Un Ermite reclus dans l’alcool, et autres rhapsodies de Su Dongpo, 2003)、《東坡記》(Les Commemorations de Su Shi, 2010)以及班文干的《蘇東坡: 關于自我》(Su Dongpo: Sur moi-même, 2003)。蘇軾的詩文一向受法國讀者和學者的喜愛,盡管20世紀出版的詩集中也常包括《赤壁賦》等名篇的譯文,但21世紀后法國對蘇軾的翻譯明顯增多,表現為不再局限于個別單篇的翻譯,出版了其作品的單行譯本,并出現了專門從事蘇軾翻譯的專家。
費揚是巴黎狄德羅大學-巴黎七大的(Université Denis Diderot-Paris 7)教授,其博士論文題目是《回歸天道: 張載〈正蒙〉中的自然與道德》(Rejoindre le Ciel: nature et morale dans leZhengmengde Zhang Zai),目前出版了《東坡賦》《東坡記》及《陸賈新語》(Les Nouveaux Propos de Lu Jia)(2012)等法譯漢學著作,并翻譯Remi Mathieu主編《中國歷代詩選》(Anthologie de la poesie chinoise, 2015)的宋代部分,主要從事宋代文學與哲學、宋代士人群體、《易經》注疏、中國思想史等方面的研究,是法國公認的蘇軾研究專家。《東坡賦》是費揚翻譯的一部重要著作,包括《前赤壁賦》《后赤壁賦》《洞庭春色賦》《黠鼠賦》等26篇,是蘇軾全部賦作首次以單行本方式在法國出版。此后,他又翻譯了《東坡記》,該書被收入“漢文法譯書庫”(La Bibliothèque chinoise),為漢法對照本,書中翻譯了以“記”為文體的散文共61篇,包括《喜雨亭記》《凌虛臺記》《鳳鳴驛記》《中和勝相院記》《四菩薩閣記》《放鶴亭記》《靈壁張氏園亭記》《眾妙堂記》《雪堂記》等名篇。該書譯文曉暢優美,注釋詳實豐富,除長篇序言外,費揚在每篇“記”前附有簡短介紹,是一部“難得的高質量譯本”(Feuillas, 2010: v)。
費揚在十年間兩度翻譯蘇軾的作品與其從事的宋代哲學研究、宋代士人研究是分不開的。費揚于2013年發起了一個宋代研究小組,“真正從事研究,需要深入閱讀文本,需要大量時間。如果要做真正有趣的、新鮮的研究,我們需要回歸學者(scholar),而不只是當研究者(researcher)。我們的小組成員從歷史、文學、哲學,甚至科學的角度研究重要的宋代士人,如王安石、黃庭堅、楊萬里等。我們大量閱讀他們的主要作品,他們有些人固然主要是詩人,但有時其身份更重要是官員,他們寫回憶錄、經濟報告、史書等等,我們比較這些作品,看當時士人的真實狀態,這是我們現在關于宋代文學研究的主要工作。”(李泊汀,2017)
費揚認為蘇軾是宋代士大夫的典型,有著自成一體的哲學思想,他身上的普世價值時至今日仍有其重要意義。因此,蘇軾研究不僅有意義,而且具有多種研究的可能性,翻譯蘇軾的作品成為開展學術研究的第一步。他曾說,“蘇軾是宋代最偉大的學者之一,他可以說是宋代士大夫的典型,如果要研究宋代士人,似乎蘇軾的身上已經囊括了所有可以研究的面向。對于我來說,比較特別的一點是,蘇軾不僅僅是儒家、道家或佛家的信徒,他從三家之中都汲取了營養,并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哲學思想。”(李泊汀,2017)由此可見,費揚翻譯的最終目的是指向宋代士大夫研究,因而在翻譯文本的選擇上也是向學術研究靠攏,為學術研究服務。因此,“在蘇軾全部文學創作中哲學性最強”(李泊汀,2017)的《東坡記》和“數量不多”,但“從他年輕時候到生命末期的作品都有”、“能夠勾勒出東坡傳記”的《東坡賦》(李泊汀,2017)自然成為蘇軾翻譯的首選。以譯本服務于研究的中國古代散文法譯新趨勢初露端倪。
此外,漢學家班文干于2003年出版的《蘇東坡: 關于自我》(Su Dongpo: Sur moi-même)是一部蘇軾的詩文選集。班文干(又名班巴諾)是法國當代著名漢學家,畢業后一直任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教授直至退休。他是一位興趣廣泛、著述頗豐的學者,翻譯出版了許多關于中國口頭文學、中國民間戲曲、中國神話的著作,班文干不但致力于中國古代文學的翻譯,從事中國歷史與宗教的研究,他還于1971年在巴黎創辦Kwok On博物館,用以舉辦各類亞洲民間傳統藝術展。《蘇東坡: 關于自我》一書只是班文干眾多中國古代文學譯著中的一部,該書從“關于自我,散文”、“關于自我,詩歌”、“關于藝術”、“關于人物”、“關于政治觀點”五個方面對蘇軾的思想進行介紹。其中“關于自我,散文”一章中包括《凌虛臺記》《喜雨亭記》《超然臺記》《放鶴亭記》《答秦太虛書》《答李端叔書(節選)》《書〈東皋子〉傳后》《前赤壁賦》《后赤壁賦》《記承天寺夜游》《記游松風亭》《游白水書付過》《書上元夜游》等散文名篇。班文干作為一位興趣廣泛的學術“雜家”(王舒柳、周興,2014),蘇軾的翻譯并非其譯介工作的重點,但他認為蘇軾作為一位集詩人、散文家、畫家、書法家、音律大家為一身的傳奇人物,是宋代文人中的典范。班文干以一貫的高質量翻譯,為法國讀者奉獻了一部優秀的蘇軾作品選集。
除這部譯作外,班文干于2004年出版了比《中國古典散文選》更為厚重的譯作《中國古典文學選》(Anthologie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Classique, 2004)。該書共分為六章,分別是“古代文學”、“漢代文學”、“魏晉南北朝文學,三至六世紀”、“唐宋文學,七至十二世紀”、“元代文學,十三至十四世紀”、“明清文學,十四至十九世紀”。班文干對自先秦至清末的各種代表性文學體裁中的名作佳篇進行了翻譯,全書近千頁,這是法國漢學家第一次將諸子之說、詩、文、賦、民歌、文論等體裁匯集于一書之中,該書涉及中國古代文學種類之豐富、內容之精深都是前所未有。
新世紀以來,中國古代散文在法國的翻譯穩中求進。一方面,山水游記的翻譯傳統在赫美麗的主導下得到延續,赫美麗的《自然天堂: 中國園林散文》《荊園小語》相繼出版,班文干的《中國古典文學選》不但延續了歷代散文選的傳統,而且在編纂方式上推陳出新,首次將各類文體集成一冊;另一方面,以費揚、班文干為代表的法國漢學家分主題、分文體地對蘇軾的散文進行譯介,將散文翻譯作為學術研究的前提與準備,使中國古代散文法譯的學術化轉向初露鋒芒,也促使蘇軾成為唐宋八大家中在法國流傳度最廣的大家,使蘇軾散文譯介成為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古代散文法譯的新熱點,也標志著法國的中國古代散文翻譯開始由散文選到作家專題翻譯、由面到點不斷向縱深發展的轉變。
四、 余論
中國古代散文歷史悠久、源遠流長,在三千多年的歷史中,它在時代的發展與文化的演進中,產生了大量的散文作家與作品,取得了無比豐碩的成果。可以說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就數量而言,古代散文為最大宗(郭預衡,2002: 1) 。但是與中國古代散文悠久的歷史相比,中國古代散文在法國譯介的歷史則短得多,直到20世紀方才進入法國譯者的視野。20世紀上半葉,法國漢學家馬古烈一枝獨秀,譯作《中國古文選》一方面參照《古文析義》《古文觀止》《古文評注》三部文選,遵循中國古代文學傳統的選文路徑,另一方面參考歐洲極具分量的三部拉丁語、英語、德語譯本,在深入理解的基礎上取長補短,集各文選之所長,使這部中國古代散文法譯的開先河之作一經問世即位列歐洲中國古代散文權威譯本之中。20世紀下半葉,山水游記成為中國古代散文法譯的重要主題,赫美麗、譚霞客等譯者以讀者口味與期待為出發點,選擇山水游記作為譯介的中心,使法國讀者不出國門既能領略中國各地的山水風光,又能如置身中國古代社會,了解古代中國的風土人情、民風民俗,還能借山水游記欣賞中國古代文學的藝術與美學成就。新世紀以來,蘇軾的散文作品成為新的譯介亮點,這與費揚、班文干等漢學家的關注宋代士大夫的研究課題密不可分,散文翻譯成為散文研究的前提,散文研究又成為散文翻譯的動力,二者相輔相成、互為因果,共同推動中國古代散文法譯向學術化、經典化轉向。
中國古代散文在法國百年的譯介歷程中,譯者對中國古代散文文本的選擇在不同歷史語境下發生了明顯的變化與轉向,這與文學系統中各因素間的相互作用是密不可分的。正如翻譯理論家安德烈·勒弗菲爾(André Lefevere)所說,“文學是一個‘人造’的系統,它不僅包括文本,也包括閱讀、寫作、改寫文本的人類代言者”(Lefevere, 1992: 12)。如果僅僅將龐雜的文學譯介現象看作許多孤立的“物質實體”,就永遠無法達到解釋翻譯與接受機制的目的,只有將復雜譯介現象所涉及的所有因素簡約為幾組系統,致力于分析系統內的“相互關系”,而非僅僅“物質實體”,才能最終“描述和解釋不同意義的聚合體是怎樣運行的”,從而發現各類譯介現象的功能性特征以及背后存在的運作機制(André Lefevere, 1992: 12)。
中國古代散文的法文譯介史是特定時間和特定地區的文學運作,換言之,是一連串特定時間和特定地區文學運作的歷時性集合。馬古烈的《中國古文選》出版于1922年,彼時他還是位青年學者,彼時的法國漢學尚處于學院派漢學初步確立的時期,而在遙遠的東方,中國正在經歷著巨大的政治、社會、文化變革,“反傳統、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學革命運動正在中國如火如荼地展開,未來古文是否還能延續其輝煌尚不得而知。在這一歷史語境下,馬古烈以追本溯源的嚴謹態度,選擇翻譯的是一部全面、系統、有歷史傳承、囊括中國古代散文數千年精華的歷代散文選集,這一選擇飽含譯者的期待。作為出色的學院派漢學家,他極為關切中國古代散文的未來命運,他曾在書中說道:“如今的古文顯示出衰弱的跡象,因為古文所有的力量和秘密都藏于對詞句的運用中,藏在它提供的富含意義的藝術中。但這種衰落將是暫時的……一旦現在的中國擺脫它正在經歷的政治、經濟危機,一旦生活恢復正常,我們非常確定,古文將以其歷經變幻后的面貌重現光彩。”(Margouliès, 1926: 2)然而,歷史并未如馬古烈所料,白話文逐漸取代古文的地位,中國古代散文到了20世紀下半葉已不再是文人使用的“活的”語言,它本身成為歷史的一部分。隨著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中國經濟不斷繁榮,世界影響力持續擴大,法國讀者再次對新中國投來好奇的目光,中國現當代文學法譯成為主流,中國古代散文借其“東風”,也在這一時期涌現出一批散文譯本。在這一背景下,讀者的喜好成為選擇文本與出版發行的主要動因,篇幅短、展現古代地理與人文風貌、蘊含古人處世哲學的山水游記順勢而發,成為中國古代散文法譯的主流,這一階段的翻譯選擇是以翻譯接受為導向的。而到了21世紀,中國古代散文的熱度逐漸散去,其接受對象從法國普通讀者逐漸轉變為專業讀者,中國古代散文法譯本的數量逐漸減少,但篇幅和質量卻逐步上升,其中原由在于專業讀者對中國古代散文譯本的需求與期待。所謂專業讀者,是指對中國古代散文進行學術性解讀的漢學研究領域及其他學術研究領域的教師、學生和研究人員等,他們在學習與研究的過程中,發現其研究對象的法譯本多處于零散、片段甚至空白的狀況,而他們又需要較為完整、權威的譯本作為研究材料。在這一背景下,出自漢學家之手的注釋詳實、譯文準確的散文法譯本應運而生,而中國古代散文法譯的目的也從迎合普通讀者需求轉變為迎合專業讀者的需求,中國古代散文法譯的趨勢轉向學術化和經典化。
中國古代散文研究專家費揚曾呼吁:“對于法國漢學家,或西方漢學家,我想說: 盡量多做翻譯。現在,中國,或東方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我們面對世界時,需要新的思考方式,這就需要新的工具,而中國文化正可以扮演這樣的角色。我們必須要多做翻譯,這樣才可以讓非漢學家的讀者有可能接觸到中國文本。這不僅是我的目標,也是我對于整個學界的期待。”(李泊汀,2017)誠然,中國古代散文在法國的翻譯與接受雖已走過百年,卻尚處于初始階段,但中國古代散文法譯的百年歷程不應湮沒于歷史的塵埃之中,未來在中法兩國學者的共同努力下,隨著中國文化國際傳播與研究的不斷深入,期待中國古代散文在法國的譯介能迎來更大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