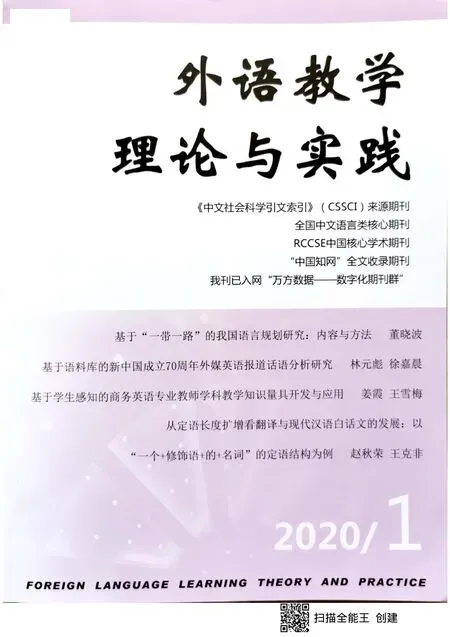規(guī)范與深入: 文學導論課教學的要素
華東師范大學 金衡山
一、 問題所在
在英語學科的課程設置中文學課占有重要位置,是主干課程,這本是英語專業(yè)的共識。在付克所著《中國外語教育史》中,對1949年前的外文系的課程設置有這樣的表述,“課程設置及教學內容多與歐美一些大學類同,一般是重文學,輕語言,而在文學中尤重英國文學,特別是古典文學”(付克,1986: 127)。盡管從語句的表述來看,作者似對文學為重的課程設置有一些微詞,但文學課作為主干課程這個事實還是非常清楚的。在最近出版的《西南聯(lián)大英文課》(2017)一書里,可以看出文學內容占有一定比例,有些課文雖然不是純粹意義上的文學,但內涵豐富、描述精致、邏輯思辨強烈,也可以看作是與文學相關的文本(1)著名翻譯家許淵沖先生在其回憶錄《夢與真—許淵沖自述》一書中提及在高中階段英語課上曾背誦三十篇短文,其中有莎士比亞《凱撒大將》中的演說詞。此外,也讀了一些小說,如莫泊桑的《項鏈》,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見許淵沖: 《夢與真-許淵沖自述》,鄭州: 河南文藝出版社,2017年,第74頁、75頁以及80頁)可見其時,高中英語已含有不少文學篇章。許先生后來畢業(yè)于西南聯(lián)大外文系。。解放后五十年代初,大學中外文系英文課程進行了改革與變動,但在不少綜合性大學中依然保留了諸多文學課程。以南京大學外文系為例,第二學年設中國文學、文藝學,第三學年設文藝學、文學選讀,第四學年設英國文學史、文學選讀(付克,1986: 130)。可見,文學課程依舊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學習年限也比較長。在上世紀改革開放后的八十年代,大部分學校的英語學科基本上還是延續(xù)了文學課為主的傳統(tǒng),筆者于1981年入讀北京師范大學外語系,記憶中二年級后除了精泛讀、聽力和口語外,主要以文學課為主,包括英國文學、美國文學、短篇選讀、歐洲文學經典選讀等,而且都是一年的課程。
曾幾何時,中國大學中英語學科的文學課程遭遇各種各樣的困難和挑戰(zhàn),文學課程的萎縮成了普遍現(xiàn)象,有學者為此描述了如下情景:“從主干課、必修課的地位淪落到輔修課、選修課的地位,從一二十人小班的、討論式地上課到一二百人大課堂的講座式地上課,從兩個學年的課程‘濃縮’到一個學年,甚至一個學期”(李公昭,2002: 11)。或許,這并不是所有學校中發(fā)生的情況,但文學課程的式微基本上已成事實。這與上世紀九十年代后期面對經濟大潮和社會對英語學科實用人才的需求有關,復合型人才的培養(yǎng)對英語學科提出了新的挑戰(zhàn),同時也對文學課程的設置帶來了沖擊。在何其莘等所撰寫的有關自改革開放以來三十年國內高校英語專業(yè)教學評估的文章中,一方面肯定了過去幾十年取得的成就,另一方面也指出貫徹實行復合型人才規(guī)劃的《高等學校英語專業(yè)教學大綱》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如一些學校沒有開全規(guī)定的知識必修課,“英美文學”被特別提到(何其莘等,2008: 430)。復合型人才培養(yǎng)是近二三十年中國高校英語學科發(fā)展的轉折點,但同時也帶來了很多爭議和問題(見金衡山,2019)。其中之一便是對英語學科本身地位的討論,英語能力加其他學科方向的復合型培養(yǎng)模式撼動了本屬于人文學科的英語專業(yè)的地位,而造成這種現(xiàn)象的一個重要原因則是文學課程地位的下降。在實用能力的培養(yǎng)面前,“無用”的文學自然成為了邊緣化的對象,甚至在有些地方產生了生存危機(見崔少元,2000: 52)。但另一方面,在復合型人才培養(yǎng)發(fā)展過程中,也有很多反思和深入思考英語學科本質的意見產生。其中,很多是圍繞文學課程設置和教學進行。一些著名學者如張中載、虞建華、殷企平等撰文討論英語學科中存在的功用主義及其危害,討論的核心在于如何判斷文學的“用”與“無用”,學者們指出文學之“用”不能簡單用“功用之用”來衡量(張中載,2003: 454),學習文學的目的是“學以致知”,而不是單純的“學以致用”(虞建華,2002: 8;2010: 15;2013: 207),學習文學幫助認識人生、豐富經驗,開啟心智(虞建華,2002: 8),在這個意義上,“文學何嘗無用?”(殷企平,2002: 9)的提出實是很有針對性。
有關文學課程在英語學科的作用和地位的討論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一直延續(xù)到新世紀的當下。應該說,在這個過程中,對文學課程作用的共識正在形成。最新出爐的《外國語言文學類教學質量國家標準》對文學課程的教學有了明確的規(guī)定。有學者認為,“相較于2000年高等學校外語專業(yè)教學指導委員會關于英語專業(yè)復合型人才培養(yǎng)的主張,《國標》在回歸英語專業(yè)人文學科屬性上已有很大的進步”(查明建,2017: 24)。不能說新世紀初的《大綱》沒有對文學等人文素質教育和知識性課程設置的要求,但因為強調復合型人才的培養(yǎng),在實際過程中,對前者的教學實際上發(fā)生了很多偏差。相對而言,現(xiàn)在的《國標》是重新回歸英語學科的本質,其中自然有對文學課程的具體要求。
另一方面,在有關文學課程的作用和目的的討論中,也有不少意見針對文學課的教學方法和教學改革。在新世紀初程愛民等做的英語學科文學課程教學的調查報告中,就教學內容、方法與手段這一項而言,他們發(fā)現(xiàn)60%以上的學校遵循的是傳統(tǒng)的教學方法,即時代背景、作家生平介紹、作品思想內容介紹以及藝術特點介紹的“四段論”教學套路(程愛民等,2002: 16)。與此同時,王守仁提出是時候終結“文學史”加“選讀”的教學模式了(王守仁,2002)。以上兩種批評與不少論者對現(xiàn)有文學課程教學方式的意見類似,如認為很多教師的教學還處在中心思想、段落大意,泛泛分析的老套路中(許慶紅、戚濤,2012: 63),也有論者指出教學單一,只放在知識傳授上的問題(范誼、芮渝萍,2005: 152),更有批評者描繪了這種教學方式產生的一個結果:“學生記筆記,對筆記,考試背筆記,考完全忘記”(王春暉,2011: 120)。這種評述可能存在夸張的內容,但其中傳遞出的把文學課上成條條框框、劃塊劃區(qū)以記憶為考核標準的問題確實存在,而且非常普遍。除了教學方式問題以外,有關教材的問題,也有不少論者提出了看法。如內容厚古薄今,尤其是缺少二十世紀文學理論的介紹和運用(崔少元,2000: 53),編寫簡單,“缺少對文學理論,文學術語和文學的基本構成成分,即文學語法的介紹”(范誼、芮渝萍,2005: 155)。這個問題尤其值得注意,因為它涉及到如何理解文學,如何進入文學文本這個大問題。文學教學,即便是本科層次的文學課程的教學,其實離不開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和思考。
二、 文本形式與進入文本的途徑
上述討論一方面是要再次明確文學課程在英文學科的地位,另一方面則是要引向一個話題,即文學課程到底應該如何上?英語學科的文學課程一般會有文學史、文學選讀以及其他的專題課程。因此,不一樣的課程,面對不一樣的學生以及必修和選修的區(qū)別,這些都可以導致不一樣的上課模式,沒有必要統(tǒng)一。但另一方面,所有這些課程在本質上都是文學課程,所以可以從一個基本的方面考慮如何面對文學、面對文學文本的問題。換言之,即便是上成精讀或泛讀課,但也面對同樣的問題,即如何體現(xiàn)文學文本的特征。這里,限于篇幅和文章本身的要求,無法對這個問題進行展開論述。只是需要提及一個問題,即文學課程應該體現(xiàn)閱讀文學的一些基本規(guī)律和特征,換言之,需要從文學文本的一些基本形式入手找到進入文本的途徑。在這方面,一些為我們所熟悉的關鍵詞可以發(fā)揮其作用,如主題、人物塑造、敘述角度、象征等,但只是知道這些詞還不夠,還須知曉這些詞本身有哪些含義,是怎么來的;另一方面,更須有意識地把對這些關鍵詞的認識置入對文學文本的閱讀過程中去。就這一層次意思而言,這其實已經涉及到了如何理解文學文本的形式問題了。在這里,我們或許可以借用形式主義的主要批評手段,也即英美新批評的方式做一闡釋。新批評的主要闡釋者之一威姆薩特和比茲利在其著名的《意圖謬誤》一文中針對如何進入文學文本提出兩種途徑,前一種的關鍵詞如下: sincerity(真誠),fidelity(誠實),spontaneity(自發(fā)),authenticity (真實),genuineness(真正),originality(獨創(chuàng));后一種關鍵詞如下: integrity(完整),relevance(關聯(lián)),unity (統(tǒng)一),function(功用),maturity(成熟度),subtlety(微妙性),adequacy(飽滿度)(Wimsatt & Beardsley, 1971: 1018)。按照這兩位批評家的看法,后一種應該替代前一種,以體現(xiàn)對于文本的關注,而這正是新批評的形式主義的要旨所在。后一種關鍵詞關注文本的完整性、篇章的關聯(lián)度、語詞的功用和表現(xiàn)的微妙性,并由此可以看出文本的統(tǒng)一性和(表現(xiàn)的)飽滿度,這些正是文學文本應該有的一些基本特征,從這些方面入手,可以有助于進入文本的語言和語篇層面,包括語言的表現(xiàn)、語篇的結構、達到目的的方式等。前一種關鍵詞指向的是作家的創(chuàng)作過程和結果,包括是否忠實于生活、是否發(fā)自內心、是否具有獨創(chuàng)性、感情是否真誠等。按照新批評的看法,這些東西很難把握,不靠譜,所以須用后者的形式途徑加以替代。這是二十世紀文學批評史的一個重大轉折,就批評方式而言,新批評開創(chuàng)了一個新的時代,影響深遠。但現(xiàn)在來看,新批評也不是沒有問題,一味關注形式其實是排除了文學的社會和現(xiàn)實意義。所以,從這個角度而言,我們大可不必唯其馬首是瞻。之所以在這里提到這兩位學者述及的兩種切入文本的模式,是因為一則就進入文本而言,可以找到一些依據(jù),即上述一些關鍵詞所指引的方向,而不是泛泛而言;在關注語言及語篇層面上,尤其能夠給予一些指導方向,而這對基礎文學教學應很有幫助。二則,兩位學者提及的第一種關鍵詞其實也提供了另一種形式(一種相對而言,比較傳統(tǒng),為我們所熟悉)的切入文本的方式。如果把這兩種方式結合在一起,那么進入文本的途徑就大致可以確定。這是可以很好地為文學課程教學所用的進入文本的途徑。
其實,就進入文學文本而言,我們也可以從另一種二十世紀的批評方式,即讀者批評學派得到諸多啟示。德國學者、讀者批評的主要倡導者之一伊塞爾在其名著《閱讀行為》中提出了著名的“隱含讀者”的概念,意指一個可以達及文本內容和結構的讀者的存在;簡而言之,“隱含讀者”指的是進入文本后的一個結果。“隱含讀者”其實并不存在,存在的是進入文本的一個可能的途徑。在伊塞爾看來,這個途徑包括兩個方面: 其一是“文本結構”(textual structure) (Iser, 1976: 35),其二是“結構化的行為”(structured act)(Iser, 1976: 36)。前者說的是文本本身具有的結構特征包括敘述者、人物、情節(jié)等,但是這些因素需要讀者有意地去發(fā)現(xiàn),而這種發(fā)現(xiàn)是在閱讀過程中展現(xiàn)出來的,這也就是“結構化的行為”的意思。換言之,讀者需要有意關注文本的這些形式內容,并內化在閱讀過程中。從二十世紀影響深遠的結構主義批評的角度來看,這就意味著“把文本讀成文學”(to read a text as literature)(Culler, 1975: 149),此話中“文本”是指文字組成的材料,而“文學”一詞則指讀出文學意味的那個“文本”,其實指的是文學的形式,也就是可以體現(xiàn)文學文本特征的一些基本要素,用結構主義評述者、美國學者卡勒的話說,“依賴于一種特殊形式閱讀的文學其實是一種更加堅實、更加誠實的(閱讀的開始)”(Culler, 1975: 150)。自然,所謂“讀出來”就是指通過尋找文本形式的一整套方式讀出文本的意味。而從讀者批評的角度而言,當文本的結構要素與讀者的結構化的發(fā)現(xiàn)趨于一致時,“隱含讀者”就誕生了。伊塞爾的提法有其理想化的地方,也即過于形式化的問題。但與此同時,他的讀者批評方法也給我們提供了進入文本的一個路徑,與上述新批評的方法有異曲同工之妙,也即從形式的要素入手,塑形閱讀的過程,找到進入文本的一個有效途徑。
三、 文學導論課的實踐及其啟示
關注文學文本的形式以及通過尋找形式進入文本,這可以對文學課程的教學產生啟迪意義,而就類似文學導論課這樣的文學入門基本課程則更具有緊密的相關性,尤其是對教材的選擇和教學方式的實行提出了與進入文本要素相關的具體要求。下面,以我們最近幾年開設的《文學閱讀與批評和寫作》(Reading and Writing about Literature)作為一個例子,對這個問題展開討論。
首先,是關于這門課開設的背景。從2012年起,筆者所在的華東師范大學英語系開始英語專業(yè)綜合改革,改革內容之一是設置文學閱讀系列課程(見金衡山,2016),把一二年級的所有泛讀課改成文學閱讀課,以英語長篇小說閱讀為主,一個學期的閱讀量在三至四部小說,按照語言難易程度,依序進行。在閱讀的同時配以一定量的文學評論寫作。經過兩年的文學閱讀訓練后,在三年級的第一個學期開設《文學閱讀與批評和寫作》。這個改革先在一個實驗班進行,經過兩屆學生的實驗后,推廣到兩個班的師范生,之后再在所有學生中間全面鋪開。
這門課的開設初衷是在學生經過兩年的文學閱讀后,對文學閱讀進行總結,在感性與理性上進行進一步提升。從文學文本特征,也即“文學性”(2)“文學性”概念由著名語言學家雅各布森提出:“文學之學科的目標不是文學而是文學性——即讓一個特定的作品成為文學作品的東西”(見朱剛編: 《二十世紀西方文藝批評理論》,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2頁)。這個概念屬于俄國形式主義的范疇,力圖把文學研究上升為一種“科學”,故而有其弊端,文學性內容表述并不清楚。但概念的提出對后來的文學研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的角度要求學生掌握一定程度的文學閱讀的規(guī)律與基本要求,對文本的形式尤其能夠具有一定的敏感性;與此同時,加強對文學文本的闡釋能力,這主要表現(xiàn)在文學評論與寫作上面。因此,這門課也可以看作是文學導論課,但就我們的具體背景而言,這個“導論”是建立在學生已經有一定的文學閱讀的基礎和評論寫作的經驗之上。從這幾個方面出發(fā),這門課確定了以下課程目標(也是課程大綱中的內容描述):
文學閱讀一方面基于心靈感應,另一方面依賴一套閱讀程式,后者在學校教育中作用尤甚,體現(xiàn)在語句與詞藻、結構與情節(jié)、意境與象征、敘事與視角、題材與主題等各個方面。這些既是作品的內容和形式,也構成了閱讀的路徑,為對作品的解讀指示了一種方向,目的是更好、更有效地理解和把握作品。同理,對于文學作品的評論寫作也是如此,一方面離不開最基本的閱讀感觸,另一方面須關注構成作品文學性的基本因素,兩者的有機結合形成對作品的有意味的探究。閱讀與評論寫作也因此構成了文學教育的不可分割的整體過程。
大綱描述從文學閱讀和評論寫作的基本要素的角度出發(fā),提出這門課的基本要求和希望達到的目的。要達到這個目的,首先是需要一本與之相關的教材。筆者為此選擇了北京大學出版社引進出版的美國教材: 《文學解讀和論文寫作: 指南與范例(第七版)》(Writing Essays about Literature: A Guide and Style Sheet)。如教材題目所指,此書既包括文學閱讀解讀指南,也包括評論寫作指導,從這兩個方面而言,此教材可以基本滿足這門課的目的要求。這是一本比較典型的美國大學應用型教材,從文學作品解讀(interpretation)的角度出發(fā),首先講述什么是“解讀”以及回答“什么是文學”這個基本問題,從概念上給予讀者一個理解文學的框架。之后,再從文學作品類型——小說、詩歌、戲劇——出發(fā),分別加以具體說明解讀的過程,包含情節(jié)、人物塑造、情景設置、主題和體裁、詩歌句型、意象與象征、格律、戲劇沖突等各個方面,這體現(xiàn)了教材對文學文本形式的重視并以此作為進入文本的路徑。此外,教材還專辟一章,介紹文學批評理論,從作品、作者、讀者與現(xiàn)實四個角度介紹與之相關的文學理論,很多是二十世紀影響甚大的文學批評流派,包括新批評、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原型批評、歷史和社會批評、新歷史主義、讀者批評、馬克思主義批評、心理批評和女性主義和性別批評等。這些批評流派本身內容龐雜,一個章節(jié)不可能面面俱到,當然,作為一本面向本科生的教材也用不著朝向這個目的。但另一方面,這個章節(jié)敘述清晰,闡釋到位,點到為止,是一篇很好的二十世紀文學流派介紹文字,對初次接觸者幫助尤其明顯。上述內容是這本教材的第一部分。教材的第二部分是有關文學批評寫作方面,介紹寫作的一些過程,如題目選擇、草稿修改以及研究方式,尤其是注釋格式,這一部分非常詳細地介紹了MLA格式的各種表現(xiàn)形式。其中有一章專門以學生寫的評論習作為范例進行點評,指出問題以及修改的路徑,對初學者可以起到引導作用。
面對如此內容豐富的教材,一方面提供了很多有用的素材,另一方面也會產生很多問題,如果只是照搬教材教學的話。問題之一,教材本身包含了一定數(shù)量的閱讀內容,尤其是詩歌和戲劇方面,但就整體而言,以這門課的要求來衡量,閱讀內容遠遠不夠。這里涉及到一個很大的問題,即所謂文學導論,一方面是要提醒學生注意抓住文本的形式,找到進入文本的路徑,另一方面是要牢記一個簡單的道理,學習進入文本的一些基本形式規(guī)律,只是一種手段,不是最終目的。最終目的是要提高文本解讀和分析的能力以及體現(xiàn)這種能力的表現(xiàn),也就是評論寫作。從這個角度而言,教材提供了諸多文學文本分析的“條條框框”,在很大程度上,對于文學文本分析規(guī)范訓練和能力培養(yǎng)非常有幫助,但這種幫助不能只建立在“條條框框”的記憶和背誦上,而是放在實際應用上。由此來看,就需要有足夠的文本材料來實現(xiàn)這種應用。換言之,“導論”一方面要體現(xiàn)“導”的地方,另一方面要以充分的閱讀量為基礎讓“導”有所作為。從根本上而言,文學解讀能力是和閱讀的多少分不開的。而就這門課程設置的背景來說,此前學生已經具備了一定數(shù)量的閱讀經驗,進入這門課程時應該繼續(xù)保持一定的閱讀數(shù)量,同時再在應用文本形式規(guī)律的基礎上進行提高分析能力的訓練。這是問題之二。所以,這本教材只是這門課的一種材料,除此之外,我們還選擇了一些小說、詩歌和戲劇文本,包括美國作家莫里森的長篇小說《最藍的眼睛》(The Bluest Eye)以及四篇短篇小說: 喬伊斯的《阿爾比》(Araby)、莫泊桑的《項鏈》(Necklace)、海明威的《大象似的山》(Hills Like White Elephant)、福克納的《送給艾米麗的玫瑰》(A Rose for Emily)以及王爾德的戲劇《不可兒戲》(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教材中已經包括美國作家蘇姍·格萊斯佩爾(Susan Glaspell)的獨幕劇《瑣事》(Trifles),詩歌方面則是增加了一本郭沫若1981年出版的《英詩譯稿》(英漢對照),其中包括五十首英美及愛爾蘭詩人的名作(其中的大部分詩歌以學生自己閱讀為主)。選擇這些材料的原則有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作品有一定的知名度,可以被稱為經典;其二,代表各種風格,故事敘述的形式有明顯的特征,以利于分析敏感度的培養(yǎng);其三,作品語言難易程度符合學生的水平;其四,作品的字數(shù)在一定限度之內,能夠讓學生在規(guī)定的時間內讀完。應該說,上述選擇的作品還都能體現(xiàn)這些原則,如莫里森的處女作《最藍的眼睛》寫作風格獨特,語言平易但不乏深度與激情,敘事角度富有變化,人物形象突出,作品現(xiàn)實意義深刻。其他作品也在不同程度上體現(xiàn)了這些特征。
在具體教學過程中,同樣也有一些原則需要遵循。首先,如上所述,從形式入手進入文本是體悟文本的一個有力渠道,教材在這方面提供了具體和細致的引導內容。但是在具體教學中,因為時間的限制,也更是因為不要把活生生的文學閱讀變成規(guī)則陳述,所以特別需要把形式規(guī)則放到具體的文本閱讀過程中去闡釋和實踐。這是這門課的最重要的上課原則。而要做到這一點,教師需要吃透教材中相關內容,在要求學生通讀教材相關部分的同時,也給出自己的理解,用簡明扼要的語言闡釋一些基本術語和概念,同時做出一些富有哲理的總結。例如,在講述小說中的敘述的意義時,給學生提供了這么一段中英文總結話語:“In the narration a world is created, and in the way of the narration lies the way of how the world is created. Yet, the meaning is never to be displayed without the simultaneous effort to relate it to the themes of the work(在敘述中一個世界誕生了,而要知道誕生的過程和情景,則不能不關注敘述的角度,但是另一方面,關注敘述不能離開主題等其他方面,否則文本的意義照樣不會顯現(xiàn))”。敘述其實是一個世界誕生和展示的過程,關注敘述是手段,目的是要通過這個關注直達主題。這也就是要告訴學生文學文本分析過程中手段與目的關系,同時也說明敘述的本質含義。之所以也用中文解釋,不是為了翻譯,而是更好地說明。在講述文本中的象征的含義時,同樣也提供了一段出自自己理解的文字:“象征是一個意象,一種物體,一個具體的行動,一段場景……,象征可以意指,可以指向,可以表示,可以轉告,可以蘊涵,可以意味,可以……;象征構筑于文本之中,與人物、情節(jié)、場景、行動、對話……絲絲相扣;象征緣于作者的意圖,但依賴于讀者的破解;象征有獨立存在的理由,因此讀者的破解與作者的意圖并不需要一致,事實上,作者的意圖并不需要成為讀者破解象征的依據(jù)。象征原本就是一個世界”。這一方面補充了教材中的內容,另一方面也向學生展示了教師的看法。文學話題本就有各種討論的可能性,教師應該在這個方面做出榜樣,而不只是傳輸書本內容。
如上所述,文學課程的一個傳統(tǒng)問題是講課方式的“四段論”。其中的關鍵,一方面是教師的滿堂灌,另一方面是脫離文本的解釋,或者是浮于文本之上,也就是缺少與文本實際內容緊密相關的解釋。所謂“進入文本”,一方面是要按照文學文本的形式路數(shù),如上所述,進入文本,另一方面,教師的講解也要發(fā)揮引導的作用,幫助學生感受文本“字里行間”(read between line)的意味。比如,在《最藍的眼睛》中,莫里森使用的敘述角度非常值得探究,其中既有作為人物之一的一個孩子的敘述,也有全知全能的敘述,還有人物獨白式的講述,莫里森的藝術特點在于在這幾種敘述之中有機地轉換,而意義也就在轉換過程中展示出來。但作為作家和敘述者的化身,莫里森并不會把這個意義直接用文字表述出來,需要讀者自己讀出來。教師就要起到這個“(隱含)讀者”的作用,用啟發(fā)的方式,提醒學生注意,并一同進入,發(fā)現(xiàn)這種文本形式方面的意義以及與主題的關系。這是循著形式的路子進入文本的一種方式。除此之外,如果還能同時對文本進行一番“細讀”則更能深化“進入”的過程。比如,在小說第一部分,作者對主人公佩科拉有這么一番描述: 小女孩去一家店里買糖果,店主是一個白人,根本不待見這個相貌難看的黑人小女孩。佩科拉感受到了深深的種族歧視,心情自然受到影響。莫里森并沒有直接描述其心情的變化,而是通過買糖前后,小女孩對路邊的蒲公英的態(tài)度的變化,由喜愛而討厭,反映出她內心的苦楚。上課時,教師把這個例子作為“細讀”的一個展示,以說明人物塑造的方式之一。小說中,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課上不可能、更沒有時間一一加以說明。但是,可以集中講解幾個例子,更重要的是,要引導學生從這些例子中看到“形式”的痕跡,也就是文學性的表現(xiàn),這是問題的關鍵。“形式”提供進入文本的渠道,但“形式”本身并不能完全表現(xiàn)文本的全部內容,畢竟講述的故事每個都不同,每一個都與具體的社會歷史背景相關。所以,提醒學生注意作品的背景也是文本闡釋的一個重要方面。只是背景的解釋與講解也要緊密聯(lián)系文本內容,從具體的敘述情景出發(fā),引出具體的歷史背景,而不是泛泛而談的背景知識。就這部小說而言,美國黑人的苦難歷史自然是背景之一,需要了解。但這些知識其實可以讓學生先前自己做一些研究,很容易找到相關的材料,教師也可以把相關材料事先發(fā)給學生,用不著在課上作為重點介紹。重要的是從文本的細節(jié)出發(fā),引導到對背景的理解,以及對這種理解的重要性的闡釋。例如,在小說中,敘述者提及佩科拉的母親波琳一家原住在南方阿拉巴馬州,后到了中部肯塔基州,再后來波琳與新婚丈夫喬利一同又到了更加北邊的俄亥俄州。這其實就是一個理解小說的重要背景點,背后涉及的是上世紀初發(fā)生在美國的黑人從南方移向北方的“大遷移”,對美國社會產生了重大影響,也是理解黑人歷史的一個重要方面。小說對這個過程只是簡單提及,但深入探索這個過程,可以幫助理解黑人即便到了機會更多的北方,依然逃脫不了種族歧視的影響,“美國夢”與其而言,只是一個噩夢。從一個細節(jié)入手,進而進入大的背景,之后再回到文本本身,這種由“點”到“面”再回到“點”的過程也是從文本出發(fā)到跳出文本再回到文本的過程(見金衡山,2016;17),由此可以從細微之處看出文本可以指向的歷史和現(xiàn)實意義。這本身也是從“形式”(情節(jié))入手拓展到文本意義的一個途徑。
這門課在考察和考試方式上也進行了大幅度改革。取消了期末和期中考試,代之以平時需要完成的論文,以各篇論文的平均分作為期末成績的最主要部分。一個學期內,要寫一篇長篇小說閱讀過程讀書報告,長篇小說評論一篇,短篇小說評論一篇,詩歌評論一篇,戲劇評論一篇,總共5篇。每篇在1500字左右(第一篇可以簡短一點)。我們使用的教材的核心內容是教授如何進行文學文本的闡釋,而闡釋過程自然包括闡釋者的表達過程。正如為此教材寫“導讀”的文學研究學者丁宏為所言,“闡釋我們的思想收獲,可能就是在闡釋外在的文本,也是另一篇文字的形成過程,成為我們理解力的物證。因此,離開表達談闡釋,意義不大。自己的話都說不清楚,文本的內涵何在?”(丁宏為,2006: ii)確實如此!反過來看,因為有了闡釋的過程,對文本的理解就能更加深入。簡而言之,文學課程不能離開闡釋活動,也就是評論寫作過程。那些通過背誦、記憶、復述,完成做題和考試的過程,當然也是衡量對文學和文本知識考察的一種方式,但就個體闡釋而言,沒有更好地完成這個過程,也就算不上是真正的文學學習過程。這也是上述提及的一些學者對文學課程教學中存在問題的批評之一。作為一門內涵豐富的“文學導論”課,評論寫作更應是題中之義。
這門課把“形式”作為進入文本的導航儀,同樣,在指導學生評論寫作方面,從“形式”入手也是重中之重。教材提供的范例已經在這方面樹立了榜樣,教師在上課伊始,就從這些范例開始講授如何從“形式”分析出發(fā),做好文學評論。換言之,一個基本的要求是,所有的學生都要從文本的形式和內容出發(fā)去談自己的閱讀感受,在分析過程中運用學到的一些基本術語和概念,繼而上升到理性總結,而不是泛泛而談,只說一些沒有細節(jié)分析支撐的“讀后感”,后者在不少學生的評論中表現(xiàn)明顯,這與以往他們已經養(yǎng)成的夸夸其談的習慣有關,也與時時被要求說出如何受到作品的“教育”的感受有關。因此,這門課的評論寫作的一個目的之一是培養(yǎng)學生有方式地進行文學評論的能力,在規(guī)范的基礎上,再說出自己的獨特理解。這兩者的結合是一篇好的評論的要素。當然,這只是樹立一個大的方向,并不是要求完全按照套路去做評論,而是強調評論過程中要抓住文本的文學特征,進而進行有效的、有一定深度的分析。事實表明,從第一篇到后面幾篇,大部分學生的評論寫作出現(xiàn)了一個變化的過程,從簡單的情節(jié)串講到某些細節(jié)分析再到通過分析凸顯作品主題,同時,在這個過程中,具有獨特理解但又有理有據(jù)有邏輯的分析也時時出現(xiàn),這說明了一個進步的過程,非常可喜可賀。此外,在這個過程中,也會鼓勵學生模仿范例,進行一定程度的研究,查詢資料,文中引述,文后列出參考書目。有不少學生在寫作中逐漸學會了做研究,這也是一項很有成就的收獲。以最新上過此課的一個年級的學生作業(yè)為例,有一同學評論《最藍的眼睛》,題目為Motherhood Without Mothering Love(從題目上就可窺一斑其用心所在),文章引述了五部(篇)英文著作,有力論證其觀點。就一個三年級本科生而言,能夠有意去找尋他人研究成果,用到自己的論述中去,還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也是這個同學在關于《送給艾米麗的玫瑰》一文中(題目: Order Makes a Difference: Narratology and Time Concept),從福克納的敘述技巧入手,分析小說中的時間展示及其與主題的關系,而這正是這篇名作的顯著敘述特征所在。另一學生則在評論這篇作品時(題目: What Makes a Devil out of a Fair Lady?),能夠從小說描述的關于艾米麗拒絕下葬其父親這個細節(jié)出發(fā),很是細致地分析這個人物有可能存在的戀父情節(jié),并延伸到美國南方沒落貴族女性的矛盾心理和在社會上的尷尬地位,從一個側面揭示了福克納筆下人物的怪誕但讓人同情的形象。文章立意特別,甚至有點大膽,但論述中用了很多具體細節(jié)加以佐證,也頗有說服力。還有一個學生在討論《阿爾比》這篇小說時(題目: A Failed Pilgrimage to Araby: Irish Paralysis and Joycean Epiphany),聚焦小說中的各種象征手法,從情感、精神、宗教、經濟等幾個層面,有層次地分析喬伊斯在小說中使用的“頓悟(epiphany)”手法的引申含義;文章從一個簡單的短篇中讀出諸多深層意味,有些闡釋或許可以被認為是有過度闡釋的嫌疑,但其每個論點都有文本細節(jié)的支持,這說明了“細讀”的努力,換言之,已經進入到了文本之中了。相對而言,很多單獨的詩歌篇幅更短,如何讓學生進行評論并寫成一篇文章,這看起來會成為一個問題。不過,事實表明,只要充分關注文本的細節(jié)、關注詩歌的表達形式,也可以發(fā)現(xiàn)有很多內容可以闡釋。如上述提及的第一位學生在其寫的關于美國詩人羅賓遜(Edwin Arlington Robinson)的名詩《理查德·考利》(Richard Cory)的評論里,關注了詩歌使用的敘述角度,由此論述敘述者的聲音與主題表現(xiàn)的關系;文章分析作品的詩節(jié)和用詞,層層深入,頗有道理,成文兩千字。也有別的學生,從課上提及的詩人的一首詩聯(lián)系到其他詩,一同加以分析,如英國詩人華茲華斯的系列詩歌《露西五首》,在課上只提及其中的一首,有同學自己去閱讀和研究剩下的幾首,寫成頗有分量的評論;另有同學從課上提及的威廉·布萊克的一首簡單的詩歌出發(fā),聯(lián)系其作品中其他相關主題的詩歌一同評論。這說明于這些學生而言,對詩歌閱讀著實發(fā)生了興趣,激發(fā)了其研究的動力,這種自發(fā)的學習精神應是比寫出一篇評論更值得肯定。
四、 結語: 課堂教學的深入
過去三四十年來,中國的英語學科一直在發(fā)展與發(fā)現(xiàn)問題、提出新的理念與改動和糾正行動方向的過程中行進。在經歷了從重文到實用再到復合性方向的過程后,當下關于英語學科的人文屬性的認識成為了熱議話題。從邏輯上而言,作為人文學科重點的文學課程的重要性自然也會恢復其應有的地位。由于歷史的緣故,這可能需要一些時日。目前可以做的是,一方面加強已有的文學課程的設置和在閱讀課程中提高文學內容教學的水平,另一方面則是需要深入討論文學教學的方式,檢討以往的失敗經驗,總結可以傳承的優(yōu)秀傳統(tǒng)。其中,重要的一點是認識進入文學文本的路徑,在教學中充分發(fā)揮作用,使得文學的意味能夠在此過程中得以盡可能地展示。由此,文學的情感與意義的探究,感觸的激發(fā)與理性的闡釋,兩者可以比翼齊飛,這應該是讓文學課重新煥發(fā)文學氤氳的道路。以上有關探究與摸索的介紹,或許可以起到借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