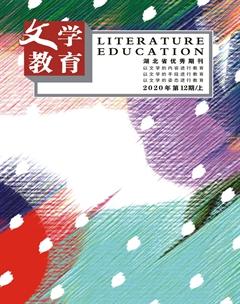白居易佛教思想與其詩歌中“心”的發(fā)展
宋擎擎
內(nèi)容摘要:本文分析在中唐特殊政治環(huán)境下,白居易等士大夫們接受洪州禪的原因、以及洪州禪對他們?nèi)松^的影響。白居易詩歌中頻繁出現(xiàn)的“心”,是一個(gè)漸次深入的連續(xù)哲學(xué)思考,反映出他逐漸接近洪州宗思想,并以洪州禪法為處世哲學(xué)的過程。
關(guān)鍵詞:白居易 洪州禪法 安心 忘心 無心 閑心
在中唐文壇,白居易是受到洪州宗禪法影響較為深刻的人之一。他的佛教思想雖然被學(xué)術(shù)界公認(rèn)為禪凈雙修,然而細(xì)析之下,白居易的思想更能體現(xiàn)出洪州禪宗后期“平常心是道”和“非心非佛”的宗旨,其不同時(shí)段的詩歌中也明確反映出這一特點(diǎn)。
一.安史之亂后中唐社會(huì)狀況與士大夫思想變化
“安史之亂”后,中唐朝廷的政治環(huán)境惡化,盛唐蓬勃昂揚(yáng)的氣象呈現(xiàn)衰頹之勢:一方面藩鎮(zhèn)割據(jù)削弱了中央集權(quán),另一方面朝廷內(nèi)部宦官專權(quán)、結(jié)黨營私。文人士大夫個(gè)人命運(yùn)出現(xiàn)巨大變化。中唐統(tǒng)治者進(jìn)行了“永貞革新”,文人階層推行了“儒學(xué)復(fù)興”、“古文運(yùn)動(dòng)”、“新樂府運(yùn)動(dòng)”等一系列思想整頓和文學(xué)革新運(yùn)動(dòng)。文士大夫們面對時(shí)代的陰霾凋敝,積極參與時(shí)政,裨補(bǔ)時(shí)弊。短暫中興局面鼓蕩起中唐士人的用世之心,但王權(quán)反覆無常、宦官專擅、朝官黨爭,使眾多中唐英才在朝政斗爭漩渦中飽受打擊與挫折。劉長卿、劉禹錫、柳宗元等都因?yàn)樯婕俺獾劫H謫。白居易等的中唐文士面臨著兩個(gè)無法調(diào)和的矛盾:一方面是儒家知識(shí)分子對國家興亡的責(zé)任感,對成就功業(yè)、立德立行的深刻渴望;另一方卻是叵測無常的朝政,以及隨時(shí)可能來臨的災(zāi)難和貶謫。白居易在《江州司馬廳記》中說:“為國謀,則尸素之尤蠹者;為身謀,則祿仕之優(yōu)穩(wěn)者”,[1]反映出知識(shí)分子們內(nèi)心價(jià)值取向的矛盾。
二.白居易等中唐士人接受洪州禪法的因由
在沉重的現(xiàn)實(shí)面前,大部分的知識(shí)分子選擇了保全自身。士大夫們雖然卸下了責(zé)任的重壓,遠(yuǎn)離政治漩渦,但治國平天下的圣人之志卻讓他們內(nèi)心難以解脫。流行于世的洪州宗思想成為這些文人大夫的解脫之路。
洪州宗禪法強(qiáng)調(diào)“平常心是道”、“非心非佛”、“無心是道”,修習(xí)洪州禪法的禪僧們狂放無拘、自然適意。洪州禪在否定規(guī)則與教義的同時(shí),直接突出了個(gè)人存在的意義。在洪州禪師的思想中,人的內(nèi)心沒有干凈、污染和是非、對錯(cuò)的區(qū)別,修禪者在日常生活的行住坐臥中感受個(gè)體本有的心性,任何一條道路、方法都可以達(dá)到佛的境界。洪州宗的禪法否決了是非對錯(cuò)的原則,也否定了文士大夫內(nèi)心中無法釋懷的道德責(zé)任。洪州宗的“無心便是道”,把士人們不可承受之重消融在終極的“道”所涵蓋的佛法之中。
在這樣的背景下,白居易選擇了洪州禪法。《醉吟先生傳》他說自己:“性嗜酒,耽琴,淫詩。凡酒徒、琴侶、詩客多與之游。游之外,棲心釋氏,通學(xué)小、中、大乘法。”[2]白居易試圖以佛道的思想,實(shí)現(xiàn)“兼濟(jì)”、“獨(dú)善”二者相容的人生理想。很多士大夫紛紛效仿白居易的行為,選擇了禪門隱逸。白居易元《答戶部崔侍郎書》中寫到:“頃與閣下在禁中日,每視草之暇,匡床接枕,言不及他,常以南宗心要互相誘導(dǎo)”。[3]在《贈(zèng)杓直》一詩中,白居易說到:“近歲將心地,回向南宗禪,外順世間法,內(nèi)脫區(qū)中緣”。[4]這兩首詩中所說的南宗心要,指的就是由六祖慧能延傳到中唐時(shí)期的洪州宗禪法。白居易在研習(xí)禪法之中,找到解決內(nèi)心矛盾的途徑。
三.白居易詩歌中“心”的概念的發(fā)展與洪州禪法的關(guān)系
在白氏詩歌和文章中,“心”字出現(xiàn)頻率非常高,大約一千七百多次。這些詩篇中,與禪宗明確相關(guān)的有“安心”、“忘心”、“無心”、“閑心”等。仔細(xì)考辨可以發(fā)現(xiàn):從“安心”到“忘心”到“無心”最后到“閑心”,這是一個(gè)逐漸深入的哲學(xué)思考過程,反映了白居易對禪法的逐漸深入的理解。
“安心”是白居易詩歌中反復(fù)出現(xiàn)的重點(diǎn)。宋代的吳開在其《優(yōu)古堂詩話》敏銳的捕捉到了白居易詩歌中這個(gè)重要的思想概念。進(jìn)一步解白氏詩歌中的“安心”,將有下面的發(fā)現(xiàn)。
身心安處為吾土,豈限長安與洛陽。[5]
我生本無鄉(xiāng),心安是歸處。[6]
心泰身寧是歸處,故鄉(xiāng)何獨(dú)在長安。[7]
始悟獨(dú)往人,心安時(shí)亦過。[8]
這四首詩歌的核心思想是:心安之處是家鄉(xiāng)和歸宿。作者在“水竹花前”、“琴詩酒里”怡情適意,希望得到心中的寧靜快樂忘記家鄉(xiāng)。然細(xì)讀詩歌會(huì)發(fā)現(xiàn)詩人的內(nèi)心深處并非已經(jīng)安于所在之地。《吾土》中白居易寫道:“琴詩酒里到家鄉(xiāng)”,“到”字泄露了對家鄉(xiāng)的渴望。《初出城留別》作者寫道:“勿言城東陌,便是江南路。揚(yáng)鞭簇車馬,揮手辭親故”,表面上故作瀟灑地離別故鄉(xiāng),然而“勿言”、“辭親”兩個(gè)詞卻表現(xiàn)出作者對家鄉(xiāng)的留戀。在《重題》詩中白居易表面上訴說自己身在異鄉(xiāng),并不覺得異鄉(xiāng)的寒冷,但是深夜無眠聽鐘聲、看香爐峰寒雪——如果不是因?yàn)樗监l(xiāng)難眠,那是因?yàn)槭裁瓷钜共荒苋胨兀客ㄟ^細(xì)讀,可以發(fā)現(xiàn)白居易一直在強(qiáng)調(diào)“心安是歸處”,但是其內(nèi)心的深處并沒有真正快樂。他未找到真正的“安心”法門。
至此,很容易想到禪宗史上慧可與達(dá)摩的“安心”的公案,即南宗禪法的關(guān)鍵:個(gè)體修行應(yīng)該確定自己心中的真性(佛性),人人可能超越自己,達(dá)到無自無他、無有分別的涅槃境界。白居易以上的詩歌并未提到“安心”典故,但是他在詩歌中對“安心”、渴望,就如同像達(dá)摩問道的慧可一樣。
“安心是吾鄉(xiāng)”最終不可能解決白居易面臨的現(xiàn)實(shí)問題,因此他提出了“忘心”:忘卻自心的執(zhí)著,才能得到內(nèi)心自由,達(dá)到禪的境界。白居易在他很多詩歌中都對“忘心”有所抒發(fā):
不學(xué)坐忘心,寂寞安可過。[9]
默然相顧哂,心適而忘心。[10]
榮枯事過都成夢,憂喜心忘便是禪。[11]
我心忘世久,世亦不我干。[12]
以上四首詩明確地提出了“忘心”的概念:身外榮枯之事不足為道,只有忘記自心的存在,才能得到禪法的精髓。從詩歌中可以很明顯地看出白居易佛教思想的發(fā)展:他此期已經(jīng)開始接受洪州禪法,“非心非佛”的思想對白居易產(chǎn)生了影響:用外物安撫自心是徒勞的;只有自由適意地感悟本心、不受自心的拘束,才能真正得到心靈的解脫,即其詩歌《閑吟》中所寫“自從苦學(xué)空門法,銷盡平生種種心。”[13]在此之后,白居易提出了“無心”、“無念”。這是詩人真正得到內(nèi)心自由的境界:
報(bào)君一語君應(yīng)笑,兼亦無心羨保厘。[14]
泰山不要欺毫末,顏?zhàn)訜o心羨老彭。[15]
唯吟一句偈,無念是無生。[16]
小潭澄見底,閑客坐開襟。試問不流水,何如無念心。[17]
以上的詩句當(dāng)描述了一種無思、無念的境界:不絕對否定個(gè)體自心的存在,但是重點(diǎn)在于保持內(nèi)心的自由,除去執(zhí)著和迷妄,使自心不被萬物所役。以上的詩句中,沒有對自心的執(zhí)著和追問。詩人炮筍烹魚、擁袍醉眠,隨心適意面對生活,不再受到內(nèi)心羈絆,實(shí)現(xiàn)了“無心”、“無念”的境界:開襟閑坐、不問流水、無思無念。
從“安心”到“忘心”到“無心”,白石氏詩歌中洪州宗禪法理路越來越明晰:完全否定對心、對佛的執(zhí)著,進(jìn)一步發(fā)揮了修行主體意識(shí)的自由能動(dòng),使修行者在平常現(xiàn)實(shí)生活中超越現(xiàn)實(shí)。明確了解脫自心的唯一途徑是“無心”、“無念”之后,白居易提出了自己實(shí)現(xiàn)“無心”、“無念”的具體方法:在現(xiàn)實(shí)的世俗生活中以一顆“閑心”,應(yīng)對世間的紛紛紜紜,做到萬事不留心,閑心不感物:
閑心對定水,清凈兩無塵。[18]
詩成暗著閑心記,山好遙偷病眼看。[19]
身閑無所為,心閑無所思。[20]
身覺浮云無所著,心同止水有何情。[21]
詩中一個(gè)“閑”字,容納了豐富的含義:身處俗世之間,但不為所限,隨意無為,隨順而行。這不僅是對現(xiàn)實(shí)的超越,更是超越現(xiàn)實(shí)之后的回歸。白居易把心靈的解脫放入現(xiàn)實(shí)世界,與外物同流合化,但不受其羈絆。“閑心”標(biāo)志著白居易在思想上達(dá)到了:人本是人,不必刻意去做人;世本是世,無須精心處世。白居易詩歌中潛藏“心”的發(fā)展理路,直指洪州禪宗“平常心是道”、“非心非佛”的宗旨。
參考文獻(xiàn)
[1](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箋注:《白居易集箋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2]佛陀耶舍譯.《大正藏》.[M]上海.上海佛學(xué)書局,1998年版
[3]藍(lán)吉富主編:《禪宗全書》[M]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版
注 釋
[1](唐)白居易著,朱金城箋注:《白居易集箋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卷四十三,五冊,2732頁。
[2]《醉吟先生傳》,見《白居易集箋校》卷七十,第六冊,3812頁。
[3]《白居易集箋校》,卷四十五,第五冊,2806頁。
[4]《白居易集箋校》,卷六,第一冊,352頁。
[5]《吾土》見《白居易集箋校》卷二十八,第四冊,1967頁。
[6]《初出城留別》見《白居易集箋校》卷八,414頁。
[7]《重題》見《白居易集箋校》卷十六,第二冊,1029頁。
[8]《效陶潛體詩十六首》見《白居易集箋校》卷五,第一冊,303頁。
[9]《冬夜》見《白居易集箋校》卷六,第一冊,336頁。
[10]《舟中李山人訪宿》見《白居易集箋校》卷八,第一冊,392頁。
[11]《寄李相公崔侍郎錢舍人》見《白居易集箋校》卷十六,第二冊,1011頁。
[12]《閉關(guān)》見《白居易集箋校》卷七,第一冊,392頁。
[13]《閑吟》,見《白居易集箋校》卷十六,第二冊,1053頁。
[14]《分司諸寮友》,見《白居易集箋校》卷七十一,第六冊,3721頁。
[15]《讀李杜詩集因題卷后》,見《白居易集箋校》卷十五,第二冊,971頁。
[16]《晚起》,見《白居易集箋校》卷二十八,第四冊,第1941頁。
[17]《對小潭寄遠(yuǎn)上人》見《白居易集箋校》卷二十八,第四冊,1944頁。
[18]《題玉泉寺》見《白居易集箋校》卷六,第一冊,第355頁。
[19]《曲江亭晚望》見《白居易集箋校》,第三冊,1227頁。
[20]《中隱》見《白居易集箋校》卷二十二,第三冊,1493頁。
[21]《答元八郎中楊十二博士》見《白居易集箋校》卷十七,第二冊,1107頁。
(作者單位:北京郵電大學(xué)人文學(xué)院國際漢語培訓(xùn)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