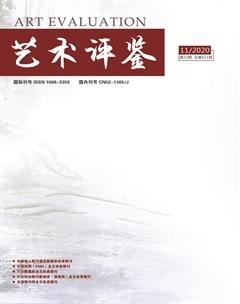古代題材類中國古典舞創作初探
賈楠
摘要:中國古典舞作為一門學科,創建于20世紀50年代,北京舞蹈學院將其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建設,旨在培養屬于自己的民族舞蹈人才。在全國解放后,響應黨“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號召進而開啟了中國古典舞教學體系建設。在如今全球多元文化與社會經濟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新的學科不斷紛涌而至,它們的出現與科技進步、社會發展、世界經濟緊密相連,新事物的產生更是對中國古典舞發展提出了具有時代特性的新要求。本文立足孫穎藝術觀的基礎上,試從“題材設定——以‘胡旋舞為例;意境構思——何為‘胡旋舞;形象設計——‘胡旋舞之魂;編舞環節——‘胡旋舞語言規劃”四個角度分析,探索中國古典舞創作。
關鍵詞:古代題材 ?中國古典舞 ?創作 ?胡旋舞 ?孫穎藝術觀
中圖分類號:J70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3359(2020)22-0052-03
眾所周知,中國古典舞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創建于20世紀50年代的北京舞蹈學院。教學體系是其學科建構的最初設定,旨為培養屬于自己的民族舞蹈人才。在全國解放后,響應黨“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號召進而開啟了中國古典舞發展的歷程。60多年風雨,飽受坎坷卻也碩果累累,到今天仍不斷地在探索中砥礪前行。如今在社會經濟發展緊密相連的時代背景下、全球多元文化的不斷沖擊下,中國古典舞如何更好發展,書寫大國形象與民族風范,已不單是要繼承還是要發展這樣簡單的選擇題了。新形勢下,傳統與現代相生相合的時代特性的需求愈發地鮮明,只有在不斷的實踐過程中,才能逐漸發現新的可能。藝術創作是自由的、具有無限可能與生機的,中國古典舞創作亦如此,而自由的背后是需要令人深思的。
在孫穎藝術觀中,歷史唯物主義和辨證唯物主義的理念、態度與方法貫穿其理論與實踐始終。本文以先生藝術觀為指導思想,秉承其創作觀點,通過“題材設定——以“胡旋舞”為例;意境構思——何為“胡旋舞”;形象設計——“胡旋舞”之魂;編舞環節——“胡旋舞”語言規劃等四個環節依次闡述。
一、題材設定——以“胡旋舞”為例
中國古典舞,是民族舞蹈中集民族性與典范性于一體的藝術表現形式,這里的民族性更多是指以國家形象為呈現原則的存在。那么,首先我們先要清楚的認知到舞蹈在社會結構中的一個位置。我們都知道,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是社會結構的兩個組成部分。經濟基礎由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組成;上層建筑則含有觀念性上層建筑與實體性上層建筑兩種,舞蹈隸屬藝術范疇,屬于觀念性上層建筑。而在觀念性上層建筑中存在相對的高低之義,如法律、法規略低于宗教、藝術、文學等。作為藝術的一個分支,受其經濟基礎的影響可以說很小、甚至可以說沒有。由此,從社會、國家發展的語境角度來看,舞蹈藝術的發展是隨時代變換的,而非穩固不變;它是一種受到意識形態影響的價值判斷,也是會不斷變化的,并不是穩固不變的東西。因此,對于舞蹈本體的追問也要在不斷的探索過程中。中國古典舞要堅持本民族的階級立場,要有屬于自己的信念體系,其意義和觀念的一般性生產過程也是要在特定的范疇內。換言之,也就是說中國古典舞的民族性體現的問題,體現在哪?若我們認同舞蹈是一種肢體語言的相對定義,那么中國古典舞的民族性應從肢體形態上就賦予其價值內涵,在此基礎上才有一切可能。帶著這樣的思考看向中國古代傳統文化,于民族文化母體內找到其價值(民族形態)的存在——漢畫像磚石、敦煌石窟群、唐代壁畫、明清戲曲等等。同時,我們可以發現中國古典舞蹈創作的立足點以及與其相適的審美風尚的統一。
中國古典舞,是具有強烈的歷史意識和民族意識的。在所創作的作品中,更是要散發一種氣韻、風骨,一種文化的精神,于無形中傳承民族精神,體現舞蹈作為文化分支的歷史性與社會性。
因此,以“胡旋舞”為首的古代舞蹈題材類的創作,從時代所遺留的“遺品”中,能窺探到歷史賦予當下的人文內涵。這不僅體現在“形”上,更需要從多方面、多角度去把握其背后的“象”,于漫漫歷史長河之中去了解、認識,在有所依據的文化思考中賦予新活力。
二、意境構思——何為“胡旋舞”
創作是有感而發的,是因觸動內心情感而生發出的一種欲望——創作沖動。當單純的情感因素上升到一個具體的內涵意義上來時,此時你想表達的內容是帶有自己對動情事物的一個態度或者說取向的,這是一個創作思維的開始。那么,“胡旋舞”的創作之感在哪?是什么?提到這個問題,便不得不回溯歷史去了解它,于是在這里就會出現一個重要的問題,即尊重客觀和無視客觀。它決定著意境與形象后期創作的方向,會牽引出藝術的真實性問題等。但若理解為尊重客觀歷史只是注重去了解認識“胡旋舞”,又將了解客觀事實簡易化了。
在學術界,由于與“胡旋舞”直接相關的文獻資料可考的有限性,導致目前對于“胡旋舞”的認識仍模糊不清。多數人是知道“胡旋舞”,但了解很有限。可以肯定的是,“胡旋舞”不是自古流傳至今的舞蹈,并且據相關權威學者考證得出,胡旋舞最早出現時并沒有名字,只是以形為名;100年后因其舞的基本特證:旋轉,才明確稱為胡旋舞之名,并且指出旋轉并非站立中的左旋右轉一種。空間方位不同的轉,中國人統稱為“旋”,如,空翻、前滾翻等。深入了解“胡旋舞”背后的歷史文化、審美特征、時代風尚后,客觀辯證地認識“胡旋舞”的歷史發展流程,才能明確這一題材后期創作的思路與方向。在其發展流程中找尋與其相依的規律和各種文化因素,辯證思考和分析“胡旋舞”在歷史長河中的“所以然”,這顯然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并非一蹴而就。
三、形象設計——“胡旋舞”之魂
創作是自由的,中國古典舞創作亦然。如人們常說,真正的自由并非隨心所欲,而是源于一個人自律的結果。古典舞創作在發揮其區別于其它藝術種類、區別于芭蕾舞、現代舞與民間舞之所長時,選擇回溯歷史,以古代題材為創作基礎,作品形象已經有了大致的方向。那么形象的“捕捉”就成為創作的核心工程。這形象若不是起于對人、事、物的直接感悟,那么便無法更深層的去把握這一形象。然而在上述我們對于胡旋舞的認識了解中會發現,詩、史、圖(敦煌石窟群中也存有“胡旋舞”的身影)資料記載中雖有與之相關的信息,卻都無法明確到底何為胡旋舞?胡旋舞的動作如何區分?更不用說理解胡旋舞的含義了,這使得在創作過程中對“胡旋舞”的把握充滿了無限幻想而又難以捉摸。創作要獨家產生,沒有真情實感的創作會落入虛假的套用之中。對創作者而言,形象思維的活躍,是在思維上出現的活性形象,也就是所謂的對其形象的具體勾勒,也就是形象的動勢舞姿和氣韻。在其產生之前,不能帶有先入為主的思想理念,不能為了構思形象而構思形象,或是借以其他物種的現成形象為借鑒進行構思。前者會缺少形象的真實性,而后者或許會借鑒成別人的模樣,早已不見了自己的樣子。
因此,對于“胡旋舞”的形象設定可采用斷代的思維方式,在明確定位唐代這一歷史時期基礎上,盡可能地去挖掘、體現大唐王朝的時代特色。除去形象的外觀,亦不能忽略對文化心態、文化氣韻、性格、情懷的考慮,否則會出現形神不符的尷尬現象。要知道形象的含義不僅是外觀形態,更是其內在蘊含的時代氣息。通過對歷史和文化的解讀,為外觀形象輸入“精氣神”,才算完成對于形象的設計。也就是說,我們需要有一個古典舞基本的歷史形態作為可參考的涵蓋古典意趣的語言風范和形象基礎,因此需要有一個綜合性的形式體系和審美體系作為提供舞種特征的前提。
編導在“胡旋舞”的創作題材中想要表現人,那必然要將其形象置于時代背景、社會環境、文化品位中去找尋其人的典型性,將這個人視為一個社會去思考、研究。此時形象的意義在于體現創作者所發現、認定的審美價值。而若想取一歷史事件、歷史故事編輯舞蹈,則是以表現事情的“情”多為主要方式,而這則需要借助故事的“知名度”,抒發情感。而抒發情感需要通過形象美感體現,形象美又涉及形象的真實性問題等,如此便不是以形象思維去把握作品的審美價值。我們還可以選擇由虛入實的去把握形象、取象塑形。在中國古代,古人對“象”的認識不僅只是人、事、物的外觀,而是包括了人、事、物的內涵和人對客觀世界的感悟、認識。因而在“胡旋舞”中你觀到了什么“象”,你所觀到的這個“象”是否會否定掉“胡旋舞”這個千古流傳的價值和意義。有形無象是動機先行的結果。形不似而神似或形不似而意似,是處人、事外表現自然物和自然現象的舞蹈,這是無法達到形似的。形與象要完美統一和諧,才能達到作為古典舞作品應具備的基本水準。因而對于“胡旋舞”發展的脈絡認識與把握,是創作前期重要的一步。
四、編舞環節——“胡旋舞”語言規劃
筆者認為編舞部分其實是最簡單的環節,動作很容易練,而為什么這樣做,這樣做想表達什么;動作語言是否能體現出韻味,體現什么樣的韻味?這才是創作的關鍵。因此,編導掌握多種“語言”是必備的基本素養。沒有古典舞語言的學習,不積累語言,不經古典舞的習染熏陶,便缺少創作的關鍵一環。其次就是“創造語言”,創造不是憑空重新創造,而是在學習古典舞素材后,從文化的空間去探索認識古典舞的發生以及發展演變流程。通過接觸足以影響舞蹈形態、風格、氣韻的各個因素,從根上了解形的本質,然后綜合創造出適合“胡旋舞”的典型動作。
“胡旋舞”以旋轉為特征,是眾所周知。而旋轉背后的“象”是渾厚、強大、包容的文化氣象所造就的,縱觀唐代書法、石雕刻、金玉文化與唐詩壁畫等藝術便能發現。在創作中僅一個“旋轉”的肢體運動,是無法支撐起一個完整的藝術作品的,藝術作品創作注重作品內在、背后的那個“象”,而決非是臨摹其外在的形態。或者說,“轉”不只肢體旋轉一種可能,舞蹈藝術作品的表達除動作形態外,還有舞臺調度、表演形式、服裝道具等因素。語言必然是作品風格的基礎,但調度、情節、形式等也同樣重要,因為它是一門綜合性的表演藝術。
因此通過對現有的中國民族民間舞蹈的大量學習,對現有中國古典舞訓練體系的把握,結合圖像造型形態的特征,對比文獻資料、史詩記載描述等文化信息所透漏的風格美感,綜合多個角度,選擇最具有審美共性存在的肢體形態,加以整合、調整,這樣的形態至少需要四到五個——“詞”;再將“詞”進行流動連接形成五到十組的動作衍生——“句”;隨著過度到句的形式不斷嘗試,不斷回顧上述多種藝術種類等文化因素中體現出的審美共性,篩選保留出符合其要求的“詞”與“句”,逐漸成“章”——舞段。而至此并未結束,在其上述實驗過程中每一步都會遇到“跑偏”的現象,因此在實踐的過程中要不斷反復、謹記先前對于時代背景“胡旋舞”信息的把握,通過上述文化因素對舞蹈形態進行制約和影響,兩者交叉進行,最終再以同時代的相鄰藝術進行驗證,是否符合其表現出的藝術韻味,情調及文化內涵和形式特色是否統一和諧。
總之,在“胡旋舞”題材的中國古典舞創作過程中,意境、題材、形象、編舞是舞蹈藝術作品創作的基本要素,不分先后、不論高低,四者不是孰是孰非的關系,而是相生相合的統一體,即中國古典舞。這一過程簡單而又艱苦,不僅需要編導具有較強的舞蹈實踐功底、藝術創作敏感度、厚而廣博的文化修養支撐,還要對舞蹈創作有著深刻的思考并能予以付出實踐。本文上述四點歸納是立足孫穎先生藝術觀的基礎上對古代題材類——“胡旋舞”展開的一些創作思考,其后也會在此基礎上展開實踐,不斷在過程中思考、學習、總結,再思考,反哺理論的不足之處,提升實踐技能水平,為中國古典舞發展增添新的血液。
參考文獻:
[1]孫穎.中國古典舞評說集[M].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6.
[2]孫穎.三論中國古典舞[C].北京舞蹈學院內部教材,2002.
[3]郜大琨.從繼承性與流動性談古典舞的發展——與孫穎同志商榷[J].舞蹈,1986(08):14.
[4]葉寧,李正一,資華筠等.中國古典舞學術論壇專家發言選登[J].北京舞蹈學院學報,2004(04).
[5]費孝通.費孝通論文化自覺[M].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6]王毓紅,馮少波.胡旋之義世莫知: 胡旋舞在中國1500年被誤解的歷史命運解析[J].西夏研究,2015(02).
[7]朱曉峰.基于歷史文獻的胡旋舞考證[J].敦煌學輯刊,201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