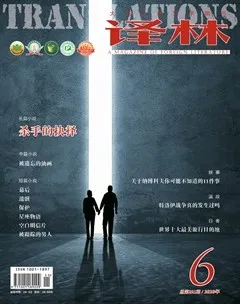陽光下的嚴霜和暴風雪:文學中的俄羅斯冬天
俄羅斯冬天給人的印象仿佛永遠是寒冷和嚴酷,但在作家的筆下,它又常常是美麗和浪漫的。
事實上,每個季節都是創作的源泉,只是在俄羅斯,冬天更能激發作家的靈感:萬籟俱寂的山林中的一聲鳥鳴,陽光下皚皚白雪的耀眼光芒,三駕馬車疾馳而過時叮叮作響的清脆鈴聲,滑冰者在冰面上翩翩起舞的優雅身姿,腳步踏在臺階上發出的嘎吱聲。這些都是我們在俄羅斯經典文學作品中熟悉的場景。
俄羅斯人的性格特征體現在對冬天的熱愛中:夢想,體貼,超然,存在于某種“超越”,存在于某種童話般的半睡半醒中。同時,俄羅斯人又與暴風雪和嚴寒等惡劣自然環境做著不懈的斗爭,改變了自身的民族素養,使其更加強大和完整。
當然,因為時值圣誕節,所以冬天也是神奇故事上演的時候。
可是,弗拉基米爾剛剛出了村口來到田野上,起風了,暴風雪鋪天蓋地而來,他啥也看不見了。一分鐘工夫,道路就蓋滿了雪。四周景物全都消失在昏黃的一團混沌之中,但見一片片雪花狂舞,天地渾然莫辨。弗拉基米爾發覺陷在田里,于是想再趕到路上去,但卻白費勁。那匹馬瞎忙一氣,時而跑上雪堆,時而陷進溝壑,雪橇時時翻倒。弗拉基米爾費盡心力,但求不要迷失大方向。他覺得已經過了半個多鐘頭了,而他還沒有到達冉得林諾村的叢林。又過了十來分鐘,叢林還是看不見。弗拉基米爾駛過一片溝渠縱橫的田野。暴風雪還沒停,天色不開。馬兒也疲倦了,身上汗流如注,雖然它不時陷進齊腰深的雪里。
——亞歷山大·普希金:《暴風雪》(1830),劉文飛譯

圣誕節前的最后一天過去了。一個晴朗的冬夜降臨了。繁星映著眼睛。一輪明月流光溢彩地冉冉升起,照徹人家和世間善良的人們,好讓大家興高采烈地挨家挨戶去唱圣誕節祝禱歌和贊頌上帝。從清早起,天氣就越來越冷了;然而,四周悄然無聲,人們腳上的靴子踩在冰凍的雪地上嘎吱作響,半俄里開外都聽得分明。這時還沒有三五成群的年輕人出現在村舍的窗戶跟前;只有一輪明月在俯看著家家農舍,仿佛在等待那些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姑娘們快到嘎吱作響的雪地上來。這時,一家房舍的煙囪里升起了一團團炊煙,像烏云似的布滿天空,一個妖精跨著掃帚,隨著煙霧一道騰空而起。
——尼古拉·果戈理:《圣誕節前夜》(1832),滿濤譯

天氣真好,晴朗,一絲風也沒有,干冷干冷的。那是沒有月亮的夜晚,可是整個村子——白房頂啦,煙囪里冒出來的一縷縷的煙啦,披著濃霜一身銀白的樹木啦,雪堆啦,全看得見。天空撒滿了快活地眨著眼睛的星星,天河顯得很清楚,仿佛為了過節,有人拿雪把它擦亮了似的……
——安東·契訶夫:《凡卡》(1886),馮加譯

過去了六個月,又到了四野白茫茫的冷寂的冬天。萬里無云,積雪被腳踩得嘎吱響,枝頭掛起粉紅的霜花,蒼穹忽地變得那么蒼白,裊裊炊煙升到半空聚而不散,猛一開門便從門洞里涌出一團白霧,行人的臉兒因襲人的寒氣成了紅通通的了,凍得發抖的馬兒不由揚起蹄子急遽地奔跑。正月的白晝將盡,夜晚的冷氣使得凝然不動的空氣更增加了幾分嚴寒,血紅的晚霞眨眼便消失了。
——伊凡·屠格涅夫:《父與子》(1862),石枕川譯

她打開門。暴風雪向她迎面撲來,同她爭奪著車門。她覺得很有趣。她來開門,走了出去。風仿佛就在等著她,快樂地呼嘯著,想把她擒住帶走,但她抓住冰冷的門柱,按住衣服,走到站臺上,離開那節車廂。風在踏級上很猛烈,但在站臺上被車廂擋住,變得輕微些了。她舒暢地深深吸著雪花飛舞的凜冽的空氣,站在車廂旁邊,環顧著站臺和燈光輝煌的車站。
暴風雪從車站角落里,經過一排柱子,在火車車輪之間沖擊著,咆哮著。車廂、柱子、人,凡是看得見的東西全都半邊蓋滿了雪,而且越蓋越厚。暴風雪平靜了片刻,接著又更加猛烈地刮來,簡直使人無法抵擋。
——列夫·托爾斯泰:《安娜·卡列尼娜》(1877),草嬰譯

尼基塔踏著白雪咯吱作響的一級級臺階,從臺階上往下飛跑。臺階下面放著一輛新簇簇的松木滑雪車,帶著一卷已經搓好的韌皮繩子。尼基塔上上下下前前后后細細打量著——它做得結結實實,他試了一試——它滑得輕輕快快。他把滑雪車背到背上,抓起一把小鏟子,心想也許用得著它,便順著繞花園的路,向河堤上跑去。那里矗立著一棵棵樹干粗大、樹冠很寬、高得幾乎挨著藍天的柳樹,全身披著皚皚的一層厚厚冰霜,每一根枝條就像是用雪做成的一樣。
尼基塔轉向右邊,朝河邊走去,盡量踩著別人的腳印,走在大路中間,碰到還沒有人走過的潔白無瑕的雪地……
恰格拉河壁陡壁陡的兩岸,在這些天里,已經被風吹集了一個個毛茸茸的巨大雪堆。有些地方,雪堆以假亂真地變成了高聳河上的河岬。只要一站到這樣的河岬上——它就立即嘁咔一聲裂開,往下崩落,整個雪山就在雪塵飛揚而成的一片云霧里轟然倒塌下去。
——阿·托爾斯泰:《尼基塔的童年》(1920),曾思藝譯

直到現在,她第二次來到戶外,才仔細朝四外看了看。現在是冬天。這里是城市。已經到了晚上。
天氣冷得要命,路面覆蓋著一層厚厚的黑色的冰,仿佛碎啤酒瓶的瓶底。天冷得連呼吸都很困難。彌漫著灰霜的空氣,就像拉拉圍著的那條結了冰的毛圍巾那樣扎人,往嘴里鉆,用濃密的鬃毛刺人的臉。拉拉走在空蕩蕩的街上,心劇烈地跳動。沿路的茶室和酒館從門里往外冒著蒸氣。從霧里不斷顯出過路人的凍得像香腸一樣通紅的面孔,還有身上掛著冰凌的馬匹和毛茸茸的狗的嘴臉。房屋的窗子被厚厚的雪蒙住,仿佛刷了一道白灰;從不透明的窗玻璃后面閃現出圣誕樹色彩繽紛的反光和歡樂的人的影子,就像從屋里映到幻燈前白幕布上、給街上人看的不清晰的圖像。
——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日瓦戈醫生》(1957),藍英年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