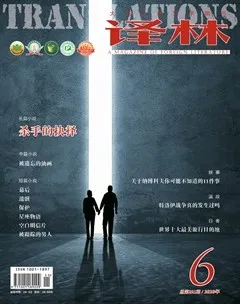星座物語

那是9月的一個夜晚,紅彤彤的落日像一頂便帽,大海猶如披上了閃閃發光的斗篷。我倚在碼頭的欄桿上,釣魚人喜歡在此垂釣,不過此時他們早就收拾好東西離開了。有幾個和我一樣生性浪漫的家伙被這幅美麗的景象打動,旁若無人地站在那里沉思。
我并未注意到旁邊的女孩,直到她開口說話。她的聲音不大,一聽便覺得魅力非凡。她好像套了一件披風。
“我看見一顆星星了。”她說。
“是木星。”我答道。
“確定嗎?”
“當然。”
“不會是金星嗎?金星也很亮。”
“不會在這個月。金星正處在與太陽上合的位置,所以這個月我們根本看不到金星。”
“你懂得真多啊。”她說。
“懂一點,有些興趣。”這是實話。我可不是什么天文專家。
“這兒是站立觀賞的絕佳位置,”她說,“我還是第一次來這里。”
直到現在我一直都沒有好好看她。我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天空上。我轉過身子,只見她長著一張漂亮的瘦臉蛋,籠罩在奇異的紅色霞光之中,加上又黑又直的披肩長發,都可以為意大利繪畫大師莫迪里阿尼當模特了。“我之前沒在這兒見過你。是有人推薦你來這兒的嗎?”
她睜大眼睛,“你是怎么知道的?”
“猜的。”
“我可不這么想。你肯定有敏銳的洞察力。我經常在當地報紙《阿格斯》上讀我的星座物語。本周報紙上說,周五晚上適合去一個能給你不同空間感的地方。我想不出有哪個地方比這兒更合適了。”
“我也是。”我禮貌地回答。私下里,我對那些星座迷們可沒有什么好感。
好像察覺出了我的懷疑,她說:“要知道,那可是門科學。”
“這個說法很有意思。”
“星座可不撒謊。如果不準,那也是人為錯誤。誰都可以自稱占星家,但一些人是騙子,最優秀的占星家可是非常準確。我都驗證過好幾次了。”
那樣的話不容置疑——尤其是從你剛剛認識的一個美女嘴里說出來時。“對。如果有個好結果,管它呢!你來到這兒,也看了這么美的日落。”
后來,幾個小時之后,我對她仍然念念不忘,這時才意識到我當時該說的話:星座物語有沒有告訴你接下來該做什么?這可是請她出來吃飯的絕佳借口。唉,我總是事后諸葛亮。
她已經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而我甚至都沒問她叫什么名字。
真蠢。
接下來的幾天,碼頭上的一幕在我腦海里一遍遍重演。是她先開口說的話,下一步本該由我掌握主動。現在為時已晚,除非我再次與她偶遇。我又回到碼頭,連續看了三次日落。好吧,說實話,大多數時間我只是扭頭觀望。她沒有來。
我無法專心工作。我是《阿格斯》的一名助理編輯——對,就是她提到的那家報紙。那一周我的編輯工作干得糟透了,以至于主編皮爾先生把我叫過去,一個自然段內指出了三個拼寫錯誤。“你是怎么回事,羅伯?好好干,否則這個工作你也干不成。”
盡管如此,我還是對那個穿披風的女孩念念不忘。我無法解釋她給我帶來的影響。我聽說過一見鐘情,但這更像意亂情迷。我今年32歲了,不應該和個毛頭小伙子一樣迷戀上誰。
經過一周的內心煎熬,我才醒悟過來,明白自己占據天時地利,能再安排一次見面。我對她的唯一了解是她讀《阿格斯》的星座物語,并據此行動。那是我的報紙。
星座物語欄目出自一個自由撰稿人,是坦布里奇韋爾斯一位可愛的老太太。她的文章是她從扎著舊絲帶的老打字機上敲出來的,總是每周一寄來。在我看來,那都是些毫無意義的空話,但作為一個作者,她極為專業。單詞計數總是準確無誤,沒有一個單詞拼寫錯誤。每周我把稿件錄到電腦上時,幾乎不用費腦子。
這一周我要履行一下我的工作職責——做些文字編輯工作。
首先,我讀了上一周的星座物語,尋找那個神秘女郎提到的話語。其中有一條目幾乎一字不差。周五去一個不同的地方。空間感會讓你感受到自由。她是水瓶座的。生日在1月末到2月上半月之間。終于我又多了些對她的了解。
我拿起那張剛從坦布里奇韋爾斯寄來的薄薄紙片,上面寫著本周的胡言亂語。對水瓶座的人來說,本周是單調乏味的一周。適合整理櫥柜,繼續干沒干完的雜活。我能寫得更好,我想。
“周六,”我寫道,“對單身的水瓶座來說,最適合來一場浪漫的約會。不要在家吃晚餐,到外面吃一頓,或許你會受到更多邀請。”
我的文字中有一個單詞意義特殊,意思只有當地人明白。就在濱海大道的一個角落,有一家名叫“約會”(rendezvous)的法國餐廳。我相信,我的日落女郎能接收到這個信號。
報紙發行后的那天,我收到“占卜師”——那位來自坦布里奇韋爾斯的占星專家喜歡讀者這樣稱呼她——怒氣沖沖寫來的一封信,并不十分吃驚。信是寫給主編的。幸運的是,皮爾先生的秘書琳達——她人好,總是特別小心謹慎——打開了信,趁老板沒看見,將它放進了我的信盒。占卜師在信中質問,難道報社不知道,她寫的每一條星座物語都是對各大行星的排列和相互影響進行了好幾個小時研究的結果嗎?17年來,從未有人竄改過她的文字。對她上周文章所做的改動是極其可惡的陰謀破壞行徑,是肆意破壞成千上萬的忠實讀者對她的信任,十分令人震驚。她要求對此事進行徹底調查,查出相關責任人,并“嚴肅處理”。如若一周之內收不到保證,她將與報紙所有者,蒙太古·威靈戴爾爵士,也是她的私交,談一談,她相信對方會“大光其火”。
說得也太離譜了,我想。但是,我對這份工作還是很重視的,于是以皮爾先生的語氣寫了一封蹩腳的回信,信中說事情真是令人難以置信,他表示極為震驚,并對此事進行了徹底追查,結果發現肇事者是一個參加見習就業項目的男學生。這個倒霉的學生在電腦上誤刪了一部分文字,驚慌之余就臨時拼湊了幾句,不等被人發現,報紙便交付印刷。又添上一句:“不必說,該生在《阿格斯》不會有見習的機會了。”然后我加上了一些奴顏婢膝、搖尾乞憐的話,最后偽造了皮爾先生的簽名。
寫完這封富有靈感的信件后,我只希望,冒了如此大的風險,希望能達到想要的效果。
你必須要自信,不是嗎?我在約會餐廳訂了一個周六晚上的兩人席位,這家法式餐廳很是體面,價格合理,酒單也不錯。
餐廳晚上7點營業,我是第一個客人。經理查了一下預訂記錄,我站在離他很近的地方,看到上面的名字還真不少。
“我想你們周六都很忙吧。”我說。
“并不像今天這樣忙,先生。真是有點奇怪。當然了,我們很受歡迎,但是這周六的晚餐兩天前就預訂滿了,就好像又要過情人節。”
我希望如此。
就在這時,其他客人陸陸續續來到,有男有女,大都是獨自一人,神情緊張。我知道為什么。他們的眼睛朝左右掃來掃去,在看其他桌旁都有誰。看到這個,我感到很有趣。我敢打賭,這些人都是同一個星座的。
永遠不要低估媒體的力量。
接下來的20分鐘,餐廳里的人越來越多。一兩對坐在相鄰座位上的人開始交談。悄無聲息地,我成了一個了不起的媒人。
不幸的是,沒有一個女人長得和我最希望見到的相似。我坐在那里小口喝著一杯夏布利酒,之前早就告訴了服務生,我要等同伴來了再點餐。
又過了20分鐘,我又點了一杯酒。服務生給了我一個眼神,意思是說我該面對現實了——我被人放了鴿子。
周圍一些客人早就開始吃起了主菜。餐廳那頭一個漂亮的紅發女子獨自坐在桌旁,朝我赧然一笑,然后扭過臉看向別處。她真迷人啊。也許我該及時止損,到她那邊去,我心想。
這時我的心跳加速。那個在門口把披風遞給服務生的女子,正是我苦苦尋覓的佳人。她身穿一件藍色天鵝絨裙子,胸前閃閃發光,看上去真是美極了。
我不禁飄飄然起來,在其他人采取行動之前,起身以優雅的姿態沖向門口。
“又是你?”我說,“幾天前我們在碼頭見過面。還記得嗎?”
“哎呀,記得!真巧呀。”因為認出了我,她的藍眼睛閃著光——抑或是因為開心,她的星座終于發揮了魔力?
r8lt0rg4FK6ik+iVCWm1kw==我說我一個人,建議她跟我一起用餐,她說她很樂意。太棒了。
餐桌上我們先初步認識了一下對方。她叫海倫娜,是農產品供應商普拉克斯頓公司的一名化學研究員,三年前因為工作從東英格蘭的諾福克郡搬來此地。
“海倫娜——名字真好聽。”我說。
“其實我希望還不如直接叫海倫。這樣我就不用一個勁兒提醒別人,我的名字最后還有一個字母‘a’了。”
我告訴她我一直在這兒生活,“事實上,我是一個媒體人。”
“真刺激。是辦雜志的嗎?”
“報紙。”
“哪一家?”
“你都看哪家星期日報啊?”
“《獨立報》。”
“那么,你很可能也讀了一些我寫的東西。我是特約撰稿人。”不是事實真相,但我可不想提到《阿格斯》,以免她起疑心。
“能告訴我你的名字嗎?”她問。
“你是說我的文章署名?不足掛齒,”我謙虛地回答,“是羅伯——羅伯·牛頓。”
“聽起來挺耳熟。”
“有一個電影明星就叫這名。他自稱羅伯特。已經去世了。”
“這個我知道!扮演《霧都孤兒》里比爾·塞克斯的那個。”
“對,還有《珍寶島》里的朗·約翰·西爾弗。他可是演惡棍的專業戶。”
“希望你不是什么惡棍。”
“也不是什么電影明星。”實際上,我對自己的長相挺驕傲。
“今晚是什么讓你來這里的?你常來這兒?”
這個問題聽上去很天真,但我不能疏忽大意。我知道她對關于星座的胡說八道很是當真。
“不,”我回答道,竭盡全力擺出一副超凡脫俗的神情,“事情很是奇怪。似乎有股神秘的力量,幾乎是內心的一個聲音,催著我來預訂。我很高興聽從了那聲音。我們在碼頭交談之后,我就真的很想再見你一面。”
對此她并未做評論。但是她的眼睛告訴我,我說了正確的話。
服務生走了過來,我因為自己的小計謀得逞而沾沾自喜,不等看菜單就先點了香檳。海倫娜說了句最后賬單平分,但我擺出一副紳士派頭,對她表示感謝,并叫她不必多慮。畢竟,我自己說過的話得身體力行:或許你會受到更多邀請。香檳只是一個開始。
“你呢?”點餐之后我問她,“是什么讓你今晚來這里?”
“是星星。”她也能看起來超凡脫俗。
“你真相信它們的影響?”
她眼里閃著光,堅定地說:“我很確定。”但是并未直接提到《阿格斯》上的星座物語。
吃完晚餐后,我們沿海灘散步,去看星星。那是夏末一個不可思議的夜晚,繁星宛若鉆石鑲嵌在黑絲絨般的夜空中。海倫娜指著構成她的星座——水瓶座的一組10顆星星。私下里說,我根本看不出任何星座的形狀,但我假裝看得很清楚。
“讓我猜一猜,”她說,“你也是水瓶座的?”
我搖搖頭,“摩羯座——就是山羊。”
聽我這么一說,她咯咯笑起來。
“我知道,”我說,“山羊(在英語中,山羊還含有老色鬼之意。——譯注)名聲不好。但我很老實本分,真的。”
“遺憾啊。”說著,她一只手從后面摟住我的脖子,吻了我。就這樣,沒用我采取任何行動。
我必須得忠于星星,不是嗎?我把她帶回公寓,又請她做了許多。她是個激情四射的情人,而我也真有點像只山羊了。
接下來的一周我們每晚都外出,去酒吧、溜旱冰、看電影、看戲劇。最后我們總是回到我的住處。本來這應該很完美,如果我富可敵國的話。水瓶座的人應該與水關系密切,但海倫娜喜歡香檳。她的品位很昂貴,而且從第一晚之后,她就再也沒有提過AA制。顯然,她希望別人一直請她——無限期地請下去。
那個星期五情況急轉直下。
那天我們去了倫敦,因為海倫娜想到常春藤餐廳就餐,之后再去看皇家芭蕾舞團的演出。我本不應該答應她的。我的銀行賬戶早已透支,現在一切費用都靠信用卡,我努力不去想下個月對賬單上的數額會有多少。即便如此,知道這些消費數額后我還是嚇了一跳。她甚至連自己的火車票錢也不想出。
“又過了一天。”在回去的火車上,她嘆了口氣說。沒有談論芭蕾舞。
“喜歡嗎?”
“那么明天我們該去哪兒呢?”
我盡力用平靜的語氣說:“我們換換樣,晚上在家待著,怎么樣?”
“星期六晚上?我們可不能待在家里。”
“為什么不呢?我家的冰箱里有比薩,還有好幾瓶啤酒。”
“希望你是在開玩笑。”
“咱們可以租張碟片看。”
“得了吧,羅伯。”
“我別無選擇,”我坦白道,“過了今晚我就一窮二白了。”聽了這話,她應該知道這是在暗示她,該由她請客了。
“你的意思是你沒錢請我出去玩了?”
“這一周的花銷可不小,海倫娜。”
“你覺得我不值?你是想說這個嗎?”
“我不是這么想的。我覺得你棒極了。但是我不能再這樣消費下去了,我沒錢了。”
“你是特約撰稿人,是你告訴我的,全國性報紙上發一篇文章能掙一大筆稿費。”
到了這個地步,我該告訴她我只是《阿格斯》的一個小助理編輯。但是我很蠢,沒有說。我試圖蒙混過關,“是,但是想賺一大筆稿費你得寫出好文章啊。那意味著好幾個月的前期調研、出差和采訪。現金流是個老問題了。”
“去你的,”她說,“你真是典型的摩羯座,看重金錢,心思細密得和會計一樣。我敢說你有個記賬本,每筆花費都記在上面。”
“這不公平,海倫娜。”
她不說話了,默默地盯著車窗外。過了一會兒,她說:“你一直在騙我,對嗎?我真的以為我們兩個注定一輩子要在一起。我全身心地付出,毫無保留。你要知道,我可不是隨隨便便的女孩。你把在我身上花的每一分錢都記下來,現在讓我感到自己很廉價。這讓發生在我們之間的一切美好回憶都成了泡影。”
“你都在胡說些什么啊。”
“蠢豬!”
我們到站后,她徑直走到出租車停靠站,鉆進一輛正在等候的出租車。我再也沒有見過她。我步行回家,比起生她的氣,我更氣我自己。之前我的一切小聰明都白費力氣。一直以來我相信都是我在掌控局面,卻沒料到其實是被別人占了便宜。被剃了毛的山羊可夠丟人現眼的。
至少我不用給她付出租車車費了。
我開始跟丹妮絲約會,把海倫娜的事情拋到腦后。還記得在約會餐廳那個朝我微笑的紅發女孩嗎?她就是丹妮絲。一天下午排隊等公交車時我們兩個對視了一眼,都頓了頓,試圖想在哪里見過對方。然后我打著響指說:“餐廳。”
我們從一開始就情投意合。我對她言無不盡,把我在《阿格斯》上改寫星座物語的故事都告訴了她,她覺得很好笑。丹妮絲很愛笑,這可真好。她坦承經常看自己的星座物語,那個周六晚上她到餐廳去——“只是好玩”——希望能在那里遇上情投意合的人。跟海倫娜如此坦白是不可能的,她總是嚴肅認真。我對丹妮絲講了關于海倫娜的一切,她對此一點兒也不在乎。她說每個期望男人為一切買單的女人都是不切實際的。對我來說,這也是對海倫娜極好的總結。
“難道她沒有工作嗎?”丹妮絲問。
“不是。據我所知,她是個科研人員,在普拉克斯頓公司開發農產品,收入還不錯。”
“一個科研人員還信什么星座,真讓人難以置信。”
“相信我,她對這個可當真了。她說占星術也是一門科學。”
丹妮絲咯咯笑了。之后很長一段時間,我們都不再談起海倫娜。我們有更好的事情要做。
上班時,我一直對郵戳上顯示來自坦布里奇韋爾斯的信保持高度警覺,萬一占卜師決定給皮爾先生寫回信呢,但是除了她寫的每周專欄,并沒有別的——當然,對于她的文章,我還是一字不落地排好版,連逗號都不用修改。看來我之前的拍馬屁和道歉起作用了。我繼續干著枯燥乏味的文字編輯工作,盼望周五盡快到來,那天晚上我跟丹妮絲有約會。所以,當收到一個由《阿格斯》報社轉交,寄給占卜師、放在馬尼拉紙信封里的包裹時,我和往常一樣,把想知道星座物語或者未來建議的人寄給她的所有物品一起,重新寫上坦布里奇韋爾斯的地址,扔進了郵袋。
我們那次約會,丹妮絲告訴我她跟海倫娜發生了不愉快,“那是上周一吃午飯的時間,在國王街上那家三明治店里。我每天都去那兒。我當時正在排隊,有人碰了一下我的胳膊,說:‘你是羅伯·牛頓的新女友,是嗎?’——聽上去這是什么丟人現眼的事。我聳聳肩不看她,接著她告訴我她是誰,開始對我說起你來——嗯,那些話我不想再重復。我一點也不想理她,但她根本停不下來,在我買完長棍面包和飲料離開之后還那樣。她真是豁出去了。最后我告訴她不管她想對我說什么,我都已經知道了。我還說至于你怎么對待我,我沒什么可抱怨的。”
“多謝!”
“啊,但是我卻讓事情變得更糟糕了。說起你對待我,就好像觸動了開關。她想知道我是什么星座的。我沒說我是水瓶座,但她說我肯定是,開始告訴我她在《阿格斯》上讀到的星座物語。我說:‘聽著,海倫娜,在你說下去之前,有件事你應該知道。羅伯就在《阿格斯》報社上班。那篇星座物語是他自己寫的,因為他那時喜歡你,知道你足夠愚蠢,迷信占星術。’那句話真就讓她住嘴了。”
“我能相信。”
“好吧,她也該知道了,對吧?她的性格有問題,羅伯。”
“她是怎么說的?”
“她臉色變得慘白,什么也沒說,直接走了。我做錯什么了嗎?”
“沒有,是我的錯。我當時就應該告訴她真相。她現在知道了也好。反正她對我的評價也不能更差了。”
周六早上我被手機鈴聲吵醒。躺在我身邊的丹妮絲也因為被打斷了好夢而不滿地哼哼。“抱歉,”我越過她去夠手機,“不知道該死的是誰,這個時間來電話。”
是我的老板,皮爾先生。“有你忙的了,羅伯。”他說,“你聽新聞了嗎?”
我說:“我剛剛起床。”
“發生了一起郵件炸彈襲擊事件。坦布里奇韋爾斯的一個女人死了。”
“坦布里奇韋爾斯又不是本地新聞。”我說,仍然沒完全清醒。
“沒錯,但對《阿格斯》來說是個好題材。死去的女人就是占卜師,我們星座物語的作者。趕快去那兒,羅伯。查一查是誰對我們的老好人心懷不滿,動了殺機。”
其實根本不必去坦布里奇韋爾斯,我現在就可以告訴他。
上周一早上警察逮捕了我,指控我犯了謀殺罪。我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訴了他們,但是他們根本不信。他們說我有明顯的殺死老太太的動機。在她的信件中間,他們找到了一封寫給皮爾先生的信,抱怨有人竄改她的專欄文章,并要求將相關責任人“嚴肅處理”。他們跟琳達,皮爾先生的秘書談話,她確認說當時把這封信轉給了我。在占卜師的家里,他們還發現我偽造皮爾先生簽名的回信。他們說我拼命想保住飯碗,寄出了這封信,肯定也寄出了那個郵件炸彈。最糟糕的是,包裹上還發現了一枚指紋。是我的。
我告訴他們寄給占卜師的包裹送到《阿格斯》報社時我為什么那么處理。我說現在我相信炸彈是海倫娜寄給我的,她誤以為我就是星座物語專欄的作者。我說我跟她有過短暫交往,她的腦子有點問題。我還告訴他們她是個科研人員,能搞到農用肥料,這個能用來制作爆炸物。她完全有能力自制一個郵件炸彈。
讓我驚恐的是,他們拒絕相信我。他們去找海倫娜談過,當然了,她說對郵件炸彈一無所知。她說她不再跟我出去約會,是因為我是個有病的騙子,整日幻想能成為倫敦頂級的特約撰稿人。你知道嗎,他們竟然相信她的話!他們一再告訴我,我才是腦子有問題的那個人,他們要羈押我去做一次心理測試。我對星座物語專欄的竄改,正說明我是個控制狂。很明顯,這個事關權力。我從使喚別人去干無意義的事上獲得刺激的快感——還包括給老太太寄郵件炸彈。
難道沒有人相信我是清白的嗎?我發誓我剛寫的一切都是真的。
(任愛紅:山東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郵編:250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