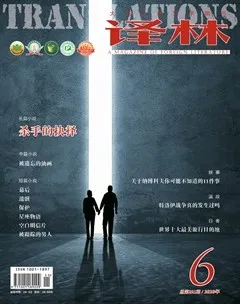遺 骸
我坐在農場房子的門廊上,無所事事。像往常一樣,晚餐過后,如果天氣尚好,我有時會坐在這里休息。就在此時,查利·林德曼突然造訪,向我透露了一個消息。
時值夏末,晚間仍有暑氣,蟋蟀和樹蛙的叫聲不絕于耳,空氣中彌漫著金銀花的香味。一切都是那么安寧,一切又是那么寂寥。22年前,瑪麗·安妮因癌癥去世。17年前,我們唯一的孩子海軍下士小克萊頓·德萊瓦斯在伊拉克陣亡。此后,我一直獨居生活,不愛與人交往,基本上都待在家里。可是人老了總難免寂寞,特別是在這樣的傍晚,真是百無聊賴。
所以看見查利那輛破舊的福特車轟隆隆駛入院子,我倒也不排斥,只是有點意外。今天這么晚了,他怎么還來找我呢?他大概是我唯一的朋友,跟他結識也僅僅因為他以前在這里送郵件。現在他已經退休了,可我還在農場干活,很少有閑下來的時候。我們每月聚一兩次,大多在周日下午。聚在一起也無非是喝點啤酒,玩玩克里比奇紙牌而已。
他一個急轉彎,把車停在院子里,急匆匆地奔向我。他矮小精瘦,體形和體重估計只有我的一半,激動起來,滿臉通紅,左蹦右跳,活像一只矮腳公雞。查利這個人,天生就喜歡小道消息。但凡聽到什么風聲,或者探得一些眾人不知道的事,他肯定會找個人添油加醋地抖摟出來。
“克萊,給你爆個料,”他說,“是個猛料,你肯定很想知道。”
“當然是重磅消息,否則你也不會這么大老遠跑到我這兒來。”
“邊喝邊說吧,給我來一杯唄。”
我去廚房開了一瓶百威啤酒,回來后遞給他。他拿起酒瓶,一頓痛飲,接著用手背在嘴上一抹,擦去胡子上的泡沫。此時暮色漸濃,他的眼神顯得格外狡黠閃亮。
“那個消失很久的女孩終于有下落了,”他說,“至少他們能肯定就是她。沒錯,不可能是別人。”
“什么女孩?我沒聽說有誰失蹤了啊。”
“不是失蹤,而是遇害,跟大家推測的一樣。”
“等等,查利。你說的究竟是誰?”
“漢森姑娘,全名琳內·漢森。可能她當時就已經死了,而不是失蹤。克萊,你還記得嗎,那個時候這件事還引發了不小的騷動。”
我想了幾秒鐘,說道:“想起來了,那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
“差不多20年了。想不到她竟然被人找到了,真是夠巧的。”
“在哪里找到的?”
“離這里幾英里的鮑爾德山,在山的一側被人發現的。有人殺了她,把尸體藏在一個小山洞里,洞口用大石塊和灌木掩蓋起來。幾位地質學家在野外考察,偶然發現了山洞,進去一看,發現了她。不過,躺在那里的只是一具遺骸。”
“遺骸。”我重復了一遍。
“還有一些破爛的帆布塊,她應該是被帆布包裹著抬進山洞的,”查利說,“憑這一點,他們斷定她被帶進洞之前已經死了,是被人謀殺的。還有一點,從骨架上看,她的腦袋向下垂,舌骨受損,第一頸椎斷裂。一個人被掐死之后脖子會斷,骨架看起來就是那個樣子。”
“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侄子告訴我的,這應該就是事情的真相。”
他侄子叫托尼·彼得斯,是卡勒姆縣的警員。“他們怎么能確定那就是琳內·漢森呢?”
“呃,他們還不能完全確定。遺骸已經送到州首府做法醫鑒定和牙齒檢測。肯定是她,準沒錯,不可能是別人。”
“我看未必。”
“或許,法醫能發現一些線索來確定兇手,但是希望不大。我的意思是,找到兇手的希望渺茫,畢竟這么多年過去了,有嫌疑的人太多了。”查利將一側突起的髖關節靠在門廊的欄桿上,又喝了一大口啤酒潤潤喉嚨,“大美人,真是個大美人,還有一頭金發。黃金一般的秀發,當時報紙就是這么形容她的吧?”
“想不起來了。”
“沒錯,就是黃金一般的秀發,還有天使一樣的臉龐,可美貌之下卻潛藏著一個惡魔,盡管她還只是個孩子。真是十足的野貓做派。她可以跟任何人行茍且之事,不管老少,然后拿錢走人。為了達到目的,任何違法犯罪的事她都做得出來。她曾因兩項盜竊罪受到指控,其中一項還讓她丟了雜貨店的工作。千真萬確,她就是個女魔頭。殺她的那個人算是為民除害了。”
“沒有誰是應該被殺害的,查利。”
“嗯,或許是吧,”他表示贊同,“反正她失蹤以后,霍斯金斯警長審問了十來個跟她有染的人,到頭來沒有發現任何線索。可能還有些人警長沒有查到,或者兇手現在已經死了也不足為奇。”
“查利,這真的重要嗎?”
“什么真的重要?”
“殺人兇手和殺人動機。畢竟都過去這么多年了。”
“當然重要。你也知道,我們這里平時也不會有什么新鮮事。所以,在山洞里發現她的遺骸估計就是自從……讓我想想,自從她失蹤以來,真面目公之于眾后最重大的消息。你該不會一點興趣都沒有吧?”
“好吧,我還真沒什么興趣。”
他搖搖頭,似乎覺得我很沒勁,對我的反應也大為失望。隨后他舉起酒瓶,一飲而盡,順手把瓶子放在欄桿上,說他得回城里了。而我也不想多留他。
查利離開時已是暮色逼人,而我仍坐在那里,看著天空慢慢暗下來,逐漸由深紫變得漆黑,往事一幕幕在腦海中浮現。此時,蟋蟀和樹蛙的低鳴好像離我很遠,金銀花的香味也惹人生厭。遠處的鮑爾德山現出黑色的輪廓,在滿天繁星的映襯下依稀可見。
曾經,也是這樣一個夜晚,一切都發生在我眼前。只是那天的夜更深,月圓未滿,高懸蒼穹。此刻只要閉上雙眼,我就又看見她直挺挺地躺在綠草如茵的河岸上,皎潔的月光下,冰冷蒼白的臉上污跡斑斑,喉嚨印著深深的指痕,腦袋扭向胸口,腦后是散落一地的金色長發。
那么年輕,那么美麗,又是那么丑惡。一片死寂。
片刻之后,我站起身,回到屋里,把晚上吃的東西全部吐進了馬桶。我漱了漱口,把手和臉洗干凈,又走到外面。不過我沒有坐下,而是離開門廊,經過車庫,走出院子,然后沿著苜蓿地走在泥土路上。我不由自主地往前走,欲罷不能,仿佛背后有雙無形的大手在驅使我前行。雖然這種狀態以前也曾有過,還不止一次,但已經很久沒有發生了。
我來到路口,泥土路在此與一條從縣道分出來的鄉道交會,我穿過路口,爬上道路后面的小山丘。站在山頂遠眺,可以看見400米開外一條寬闊蜿蜒的河流和對岸成排的柳樹。一鉤彎月正慢慢升起,河面上泛起點點微光。月色朦朧之中,河岸上琳內·漢森遇害的位置難以辨認,只有一片陰影,晦暗不清。
我走到半山腰那塊長椅狀的巨石旁,坐在冰冷的石面上,控制自己不朝下面的陰影處看。然而,記憶中的畫面紛紛涌現,這次我把眼睛睜得很大。一幕幕往事躍然眼前,像無聲電影的片段一樣輪流播放。
我看見自己戴著手套,把她抱起來,用一塊舊防水帆布包住,拎起來,放進皮卡車尾箱。我看見自己開車從鄉道駛入縣道,再經縣道飛馳在鮑爾德山一側彎彎曲曲的舊防火帶上。我看見自己拿著手電筒在黑暗中尋覓兒時發現的山洞,找到之后迅速把她放進漆黑狹小的洞內,然后在洞口堆起大石塊。我看見自己又握著方向盤,在漫長的回家之路上驅車前行……
我不知道自己在石頭上坐了多久,應該有一會兒了,因為月亮比之前升得更高了。一只貓頭鷹撲棱一聲飛起來,嘎嘎鳴叫著,我這才回過神來。夜晚依然很熱,而我卻感到陣陣涼意,不由得一陣戰栗。我快步返回家中。
我從不酗酒,可我走進廚房,從櫥柜里取出那瓶占邊威士忌,又拿出一個半透明玻璃杯,倒了半杯酒,連喝三口。喝完酒我不再顫抖,但依然沒有覺得暖和。我想洗個熱水澡,只要受得了,水越熱越好。然而,我卻不得不走向前廳的壁爐架。我不由自主朝前走,就像無法控制自己走向河岸一樣。
壁爐架上有張鑲在相框里的照片,立在瑪麗·安妮的婚紗照旁。我拿起相框,捧在手心。這是小克萊頓的高中畢業照。他高大威武,跟我一樣。照片里的他英俊瀟灑,笑容滿面,正值最美好的年華。
突然,他的容貌漸漸模糊起來,幻化出另外一副模樣。上揚的嘴角開始向下撇,神色驚恐,滿頭大汗,面目扭曲。那天晚上,他就是這樣驚慌失措地跑回家,沖我大喊,連聲音都在顫抖。我又聽到他在呼喊,支支吾吾,上氣不接下氣。這么多年過去了,他的話依然在我耳邊回響,清清楚楚。
“爸爸,天哪,爸爸,我剛才勾搭上那個女孩,把她帶到河邊……我們發生關系之后,她說她只有17歲,如果我不給錢,她就叫警察把我抓起來……我動手打她,她又踢又抓,我就……我就急壞了,一把掐住她的喉嚨……我不想弄死她,可不知道怎么搞的,我抓住她的腦袋,啪的一聲,她就不動了……她死了,爸爸,我殺了她,我把她的脖子擰斷了……天哪,你快救救我,我不知道該怎么辦了。”
在那種情況下,只有一個辦法,這是唯一的出路。我一不做二不休,做了我能做的一切。他是我的兒子,是我在世上唯一的親人。
只是我終究還是沒能留住他。
六周后,他突然離我而去,一句話都沒留下。他加入了海軍陸戰隊。差不多一年后,傷亡通告處來人告知他在戰場上營救受傷戰友時,遭遇敵人炮火襲擊,不幸犧牲。
悲痛之余,我真想開車到縣里,向警長交代事情的始末。如果琳內·漢森有親戚住在這里,我多半會去自首,但她在這里沒有親戚,只有一個叔叔住在偏僻的東部,而且不想跟她有任何瓜葛。所以,我當時沒有自首,而且任何時候都不會這么做。倒不是因為害怕我會怎么樣,而是因為小克萊頓為國捐軀,是個大英雄,無論如何我都不能讓他的名譽和形象受損。
他參軍是愛國精神使然?還是因為羞愧?抑或是良心不安?他在戰場上英勇無畏是想將功贖罪?我不知道,我大概永遠也不會知道了。
但我知道的是,他終究會受到懲罰。
我也一樣。
過去18年,琳內·漢森并非獨自躺在山洞里。那晚過后,我人性中的某些東西就留在了她身旁。而終有一天,我的遺骸也將長守洞中。
(王聞:三峽大學外國語學院,郵編:443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