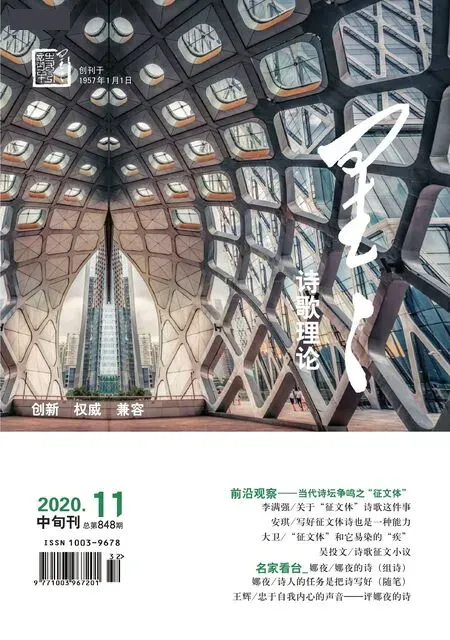“征文體”和它易染的“疾”
準備動筆寫此文之前,也就是10月8日晚,2020諾貝爾文學獎公布!來自美國的詩人露易斯·格麗克獲獎,獲獎理由是“因為她那無可辯駁的詩意般的聲音,用樸素的美使個人的存在變得普遍”。
我感興趣的,兩點:一是繼前幾年剛獲獎的美國歌手鮑勃·迪倫,瑞典詩人特朗斯特羅姆之后,諾貝爾獎又頒給詩人,可見詩歌在評委中的分量.事實上,諾獎首次文學獎也是頒給了詩人,那個叫普呂多姆的,為所有詩人贏得頭彩。
因為職業的原因,我對諾獎的詩歌獎最關注,仿佛這個獎,才是最高的含金量。
其二,我關心的是,此屆獲獎的美國詩人露易斯·格麗克,是否像我們的國內詩歌大賽一樣,主動參賽,搞個投評委所好的“征文體”并眼巴巴地等待獲獎。事實上,露易斯·格麗克不僅沒有主動參賽,連投稿的沖動也沒有。她的諾獎賠率是很高的,像那一年的小說獎頒給石黑一雄一樣,露易斯·格麗克可謂爆了個冷門。
這些年,諾獎有幾個著名的參賽選手,幾乎每一屆都興高采烈地陪跑,像大家熟知的村上春樹、阿多尼斯、米蘭·昆德拉。
主動參賽未必不可取,但主動參賽而獲獎的似乎少之又少,沒有金鋼鉆,別攬瓷器活。
由此,我聯想到國內的“征文體”詩歌。
如果我說獲諾獎的詩人,沒有一個“征文體”,怕是沒有人反對的,別說諾獎了,就是國內的“魯獎”,也沒有征文體。當然,這不是說,“征文體”不好,而是想說,“征文體”有先天缺陷,讓其止步于各種真正的藝術作品前。
濟慈說,如果一首詩不能像樹長出葉子一樣自然,還是不寫為妙。詩,強調的是自然,行于所當行,止于不得不止。詩人是上帝的秘書,他所要做的就是把上帝寫好的神性詩篇拿到人間,“征文體”也有優秀作品,這是不能否認的,有些人,甚至專寫“征文體”,手到擒來,四兩撥千金。說實話,我作評委的一些大賽,雖然隱名編號,但,依然能猜出是某某之文筆,八九不離十,有的甚至讓我拍疼了大腿:好,真好,雖然是征文,有嚴格的要求,與各種束縛,但,戴著鐐銬跳舞,確實了得。在幾次大腿快拍腫之后,我似乎想到了另一個問題:如果不是征文體,這些詩會不會寫得更好呢?
我不是一個高尚的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寫征文詩,難免功利之心。雖說任何人,任何事,都難免功利,所謂“無利不起早”是也,我不擔心功利,我擔心的是,長此下去,寫作成了一個套路,仿佛一棵自由生長的樹,被做成了盆景,好看是好看,但總覺得少了些什么,有一丟丟的別扭。
“征文體”讓人詬病的,就是“寫作套路”——套路出來的東西,又一個說法叫流水線,如果這個成立,并形成一種風氣,以后機器人小冰,成為“征文體”的獲得者與代言人,也并非沒有可能。
沒有一條河流,是按照征文的樣子流淌的——如果河流是一首詩;也沒有一個太陽,是按照征文的樣子升起的,如果太陽是一個標題;更沒有一個作者,是按照征文的樣子走進唐詩宋詞的。
“征文體”詩歌,非藝高人膽大者不可為,但,常在河邊走,沒有不濕鞋的,一個人一旦在某種體裁里嘗到了甜頭并樂此不疲,那么,征文體就需提防變成“分行的鴉片”了。除此之外,有些征文體詩歌還涉及“高大上”“形而上”,甚至政治上的禁忌,如果處理不好,那么,接下來我要明確反對這樣的“征文體”:
為政治而政治,為物質而物質,為強說愁而上高樓——退一萬步講,哪怕我不反對征文體,但我反對征文體最易染的疾:“無病呻吟,急功近利,為詩而詩。”
化用魯迅先生名言來說,世界上本沒有“征文體”,投的人多了便有了言不由衷的詩。